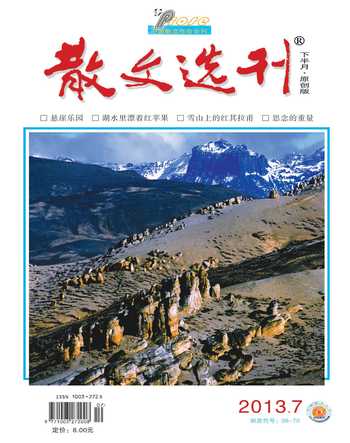悬崖乐园
王族
一个人和羊
神说,在新疆一定要爱羊。其实,这是我替神说的,我觉得神应该对新疆的羊说这样一句话。在新疆,羊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动物,这似乎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许只有神知道答案。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接触和听说的有关羊的故事已数不胜数,但印象最深的还是吐尔逊的那只羊。1993年8月,我认识了在喀什卖羊肉的吐尔逊,他养了两千多只羊,当我问他一头羊值多少钱时,他略带自豪地说,二百。我一算,很是吃惊,他拥有40多万元呀。在1993年,这不是一个小数字。
我问他这么多羊怎么来的。他嗨嗨一笑说:“大羊嘛下小羊,小羊长大了嘛再下小羊,小羊再长大嘛再下小羊,就是这个样子,快得很!”呵,如此发财之道,足让那些想发财却摸不着门道的人悲哀!我不敢小看他,但他似乎对我不感兴趣,扔下欲言又止的我,对他的羊唱着歌走了。我不知道这个相貌邋遢的牧人在内心想些什么,他与我告别后,与羊混在一起,变得也像一只羊,让人难以分辨。
一年多以后,朋友约好了吐尔逊,叫我去他家做客。刚一进门,吐尔逊说,他为我们准备了大块手抓羊肉。在新疆吃大块手抓羊肉总是让人兴奋,所以我们立刻激动起来,急忙在四周寻找煮肉的大锅,但是什么也没有。“大块羊肉在哪儿,开始煮了吗?”有人已迫不及待。
“在那个地方——”吐尔逊用手向院子里指了一下,我们向院子里望去,一棵树上拴着一头羊,浑身肥嘟嘟的,让人觉得是一只不错的羊。刚才进门时,我注意到了这只羊,它可怜巴巴的样子,并没引起我对它的关注。我知道,在维吾尔族老乡家做客,更吸引人的是他们别具民族特色的食品和独特的待客方式,还有热情而又美丽的少女。至于一只羊是如何被宰杀的,做客者几乎无人问津。看来,今天这只羊将结束它可怜的生命,它睁着一双纯洁的眼睛,打量着我们这些来登门做客的人。我在心里说,羊啊,你不知道,我们可是来消灭你的,上天注定你长得越好,便越会被人吃掉,多少年了,人吃羊历来都心安理得,而要是让羊吃人,那就乱套了,是万万使不得的,这是造物主早已给我们界定的生命关系,谁也不能改变。
大家一致提出要亲手宰羊。吐尔逊笑了笑:“那就看你们的。”
三个小伙子挽起袖子,高举着刀步伐坚定地向羊走过去。羊扬头咩咩了两声,洪亮而坦然,像是对他们三人不屑一顾。他们没有答理羊的叫声,同时向羊扑去。但是,杀羊的情景完全不是他们三人想的那样简单,羊与他们展开了较量,说是较量,过多暴露杀性的完全是他们,羊被一条粗硬的大绳绑着,没有多少施展本领的余地,它只是灵巧地躲避着他们。他们于是杀性大发,食欲加上吐尔逊的热情,已让他们无法收手。但是,他们一个个全扑空了,有一个人居然一下子栽倒在地。另外的几个人,在扑向羊时有一种怯畏,怕它那对尖利的角刺进自己的身子。几个回合下来,他们徒劳地退开了。
吐尔逊笑了笑,“大块羊肉嘛,不容易吃!”他走到羊跟前,伸出手抚摸羊的头,并开始在喉咙里发出一种奇异的声音。羊很乖顺地向吐尔逊靠了过来,并闭上了眼睛。吐尔逊轻吟曼唱的曲调,完全是一种古老而悠远的旋律,让人感觉到歌声中有掠过高原的白云,草原上悠闲吃草的群羊,或者是从深山汩汩流出的雪水,美丽的少女们正在掬水洗着头发……羊有了一种沉醉的样子。吐尔逊继续发出对羊颇具吸引力的声音,羊缓缓卧倒,将喉咙的部位呈现给吐尔逊。吐尔逊的刀轻轻地刺了进去,羊没有挣扎,连颤动也没有,如注的血喷了出来,洒在吐尔逊的脚下。
我们惊呆了!顷刻间,一头充满灵性的羊,和维吾尔族汉子吐尔逊彻底将我们震撼了。眼前完全是幻象一样的世界:神秘、宁静、从容、而又安详……
坐在吐尔逊的土房子里吃抓肉的时候,我想起那天是1994年2月10日,透过小窗户,我看见帕米尔的雪峰正在闪闪发光。
小巷
我不知道这个叫奥斯喀依的小巷在喀什有多重的分量。当我从尘土飞扬的一座新型建筑中钻出,爬上一个被挖掘机切出的断崖,一个全新的世界立刻就展现在了我面前。
古老的房子和笔直的巷子在那一刻好像都变得沉重,只有安静和从容,像暗暗游动的气息,从小巷深处弥漫过来。行之不远,哗哗的流水声传了过来。走近一看,这水倒是奇特,从一户人家的墙壁上流出。水一经从出口流出,便冲荡起一根水线,落在一米开外的地方。所以那堵墙虽然经年累月向外流水,居然无一处被浸蚀。
这就怪了,为何要把水从半墙上引出来呢?细问之下才知道,因为在此处要盖房子,水管子无法处理,索性从墙中接出。以前并没有墙上出水的事情,待接好了水管子,拧开水龙头,一声脆响,一股细流从中涌出。人们捧水一尝,居然甜爽润口,是为好水。从此,该巷中的人便用起了这水。
一个小伙子手提几把青菜来洗,见我看他时神情专注,便朝小巷里一指,说“亚克西吗?(朋友好吗?)”我忙还上两句亚克西,便跟着他走进了巷子。这种热情的引领让我于内心已十分激动,七拐八拐,我已失去方向。而这时小伙子轻轻说了一句话,到了。进了院子,有三个男人正在剁牛肉。经过这一番礼节,气氛马上就融洽起来。老太太搬来凳子,一连声用维吾尔语说着坐下坐下。
一头牛已经被他们剁去一半。剁肉的男人可以说是维吾尔族美男。他不光长相俊朗,而且剁肉的动作也细腻干练,每举起斧子,总是把嘴抿一下,才用力砍下去,粉红的牛肉块方方正正地被分离出来,在旁边码成了一座小山。
旁边的两个小伙子一直眯着眼睛在看着他的动作。他剁到肋骨时,就问:“皮夹克八吗?(刀子有没有?)”小伙子回答着“八(有)”,便把一把“英吉沙”小刀递给了他。
旁边是一口大铁锅,另一个小伙子已经把火生着。锅里的水慢慢冒起水泡,过不了一会儿,牛肉就要下锅了。烧锅的木柴是粗硬的胡杨树根,小伙子用另一种刀把它们劈开,扔到炉前。那把刀很利索,他每砍下去,木柴必脆响着裂开。
看着他们忙碌,我不便打扰,遂决定离去。走出那个院门时,发现门板上刻有两朵石榴花。阳光从它们上面反射出强烈的光芒,我一愣,似乎隐隐感到它们正在绽放。
我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方向,只好顺着小巷随意往深处走去。
远远地,就听见一群孩子在欢叫。走近一看,他们有的在玩扑克,有的在踢足球。孩子们的天性更加衬托出小巷的博大与幽深。我向他们致以礼节,他们便围了过来。由于语言不通,他们便像大人似的一一给我提问题。可以看得出,他们想知道我要去哪里,要不要他们带路,需不需要他们帮忙。我连说带比画,他们终于明白,我只是想和他们玩一玩。我掏出纸和笔,一一记下了他们的名字,他们是阿热木,阿依巴哈古丽,买力甫,阿依古丽,阿不都艾比,阿都力江,司马义。用汉语顺着维语的调子往下念,他们便一一都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阿热木为我表演起了足球。小巷很窄,他只能飞快地用脚接着球,不让它落下,如果脚不够用,就用起了头。我问他这些是不是从电视里学来的,他自豪地点了点头。一说起电视,9岁的阿依巴哈古丽用生硬的汉语说:“电视,你看过吗?好看得很。模特在里面呢!”说完,她就在巷子中间走起了模特步。小伙伴在旁哈哈大笑。
阿依古丽只有六七岁的样子。我第一次见到维吾尔女孩有她这样美丽的眼睛。她在看着什么时,大而黑的眸子像敞开的窗户,让人觉得她一眨一眨之间,能把整个世界装进去。也许她天生害羞,只要我一看她,转身就跑。我把相机对准她,她吓得“啊加(哎呀)”一声,就哭了起来。我忙让阿依巴哈古丽去哄她,她才不哭了,但从此便远远地躲着我,再也不到我跟前来。
9岁的买力甫则大方多了。她有一双黑黑的眼睛,扑闪之间,童心暴露无遗。她见我腰上别着手机,便要求打个电话。我帮她把号拨通,她高兴地跳着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一个小男孩飞跑而来,一问才知是买力甫的弟弟依力夏提,上汉语小学,是买力甫让他来给我当翻译。
有了依力夏提,我就方便多了。他虽然只有9岁,但却把伙伴们一一安排好与我说话的次序。买力甫用维吾尔语对我说了一句,经依力夏提翻译,我才知道她说的是:路有出口,你的双脚一定能到达。但我面对着买力甫那双黑黑的眸子,赶紧掏出本子记下了他说的这两句话。我觉得这是两句诗。
11岁的阿都力江说他会照相,我把相机递给他,于是就有了我和买力甫,阿依巴哈古丽的一张合影。照片洗出来,我们三人都高兴地笑着。
要离开他们了,买力甫一把拉住我的手,让依力夏提告诉我什么,而且似乎显得很着急。等依力夏提一开口,我才知道她要告诉我:巷子里铺长条砖的路是死的,六角砖铺的路是活的,尽管往前走。我握了握她的小手,心里充满了感激。想不到在喀什的小巷里,一对不到10岁的姐弟就这样教会了我怎样走路。后来我才知道,全喀什的巷子都是以这样的准则在缓慢延伸。
我立竿见影运用了买力甫姐弟俩传授给我的知识,沿着六角砖铺成的小巷放大了胆子往深处走去。光线越来越暗,小巷变得更为古老和幽深。抬起头,已望不见大街上的那些高楼。
一切都静下来了。
我曾多少次渴望到达这种时刻,现在,终于身临其境了。
我试探着敲开一户人家。身材苗条的少女为我开了门,就躲到一边去了。葡萄架下坐着一位70开外的老人,手里拿着一本有红色封面的《古兰经》。我双手抚胸,向他行一个全礼。他起身给我让了座。
葡萄架给宽大的院落罩上了浓浓的荫凉,有阳光从葡萄架的空隙中洒下,在地上变成耀眼的小圆圈。院子里除了老人让给我的这把椅子,再无他物,出奇的干净。我有些过意不去,要把椅子让给老人。他推让着的同时,朝屋内喊了一声,刚才开门的少女便又端出一把木椅。
我想和老人谈谈小巷,然而语言不通再次难住了我。我刚准备要走,老人一声“萨拉姆空(祝福你)”,使他的神情更为庄重。送我到门口,他又说了一句“萨拉姆空”,并向我点了点头。
出了门,七拐八拐,我却迷了路。脚下铺的全是长条砖,走不远就是死胡同。没办法,我只好又返回到老人家里,吃力地给他比画一番,他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他放下《古兰经》,向后院唤了几声,一只大白狗欢快地叫着,跑了过来。他带着那只大白狗走到门口,在它脑袋上拍了几下,它便摇着尾巴向小巷深处走去。我已明白过来,便紧跟在它的身后。走不多远,我眼前果然出现了六角砖。它们是那么细密地铺开了小巷,一直向远处延伸而去。
那只狗叫了一声,转身返回。它经过我身边时,我差点忍不住掉了泪。
邦克
一阵马蹄声从远处响起,少顷,就有两辆马车从小巷驶过。马车上装着高高的棉花包,驾车者端坐其上,吆喝声粗粗的,那马跑得飞快。
整个古城寂静无声。我是第一次凝视夜色中的喀什,突然觉得,它的古朴和凝重与夜色是如此的相融,好像它们原本就是一体,白天被暂时分开了,到了这会儿,便迫不及待地拥抱在了一起。
远处有一个更大的黑影,那是帕米尔,在它的背后,是更大的乔格里峰。这样看来,喀什噶尔这座古城就有着一个不易察觉的,巨大的依靠。事实上,当我这几年沉迷地奔波于帕米尔和喀什之间时,曾不止一次地暗暗惊异,何以在帕米尔高原和赤野的塔克拉玛干之间,会出现一个明珠般的喀什噶尔呢?“喀什噶尔”是指“月亮,玉石,城堡”,从这个名字上看,基本上可以肯定喀什噶尔是历史摆弄出的奇迹。现在还可以从很多地方找到证词,老城东端有一个突兀的山崖,人们称其为“悬崖乐园”,上面密密匝匝地叠落着一大群黄泥小屋。据说这是喀什噶尔最古老的建筑了,但维吾尔人仍将它保留成一条街道,尽管它高高低低,时有登高跌下之虞,但人们却爱恋着它,时间愈久,愈是把它看得珍贵。
还有克孜勒河,平日几乎见不到有水。我在疏勒县生活了五年,几乎习惯了它的干涸和苍老。然而有一年雪山上的积雪融化时,整个河道突然溢满了水。从表面上看,它携带着泥沙,一片浊黄,然而那个灼热夏日却被它散浸漫溢的寒凉改变了,在河边站了很久,浑身清凉,不愿离去。所有的这些,几乎都暗含了一种黑夜的品质,从蕴涵到显现,几乎都不能让人明谙,而一旦成形,就带着铁血柔骨般的气势伫立在你面前。
也许感到与喀什的夜贴得很近了,居然整夜没有睡意。
五点多,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呼喊叫。紧接着,艾提尕方向就响起了邦克声。这些邦克声好像是某个篇章的过门,随后又有许多咚咚的邦克也响了起来。显然,邦克是激越的,不多一会儿,咚咚声就升入夜空。
有虔诚的信徒们起得早,已经在向真主祈祷。这应该是穆斯林一日五次“讨白(忏悔)”中的晨礼。
我凝神倾听,人们正在庄严而严肃地用阿拉伯语重复着在念“作证词”:
“艾施亥杜安”
“俩宜俩亥印烂拉乎……”
一天开始了。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穆斯林要做五次拜礼:晨礼“发吉尔”;中午礼“祖合尔”;傍晚礼“阿苏尔”;日落礼“买格利布”和夜间礼“尔沙宜”。
我突然也有了朝拜的心思,动身走向大街。邦克一声紧似一声,疑惑间一愣,感觉它仍在远处,只是不停地响动着,吸引着我加快了速度。
夜依然很黑。新疆与内地时差两个小时,所以,此刻还是凌晨。人们大多都已起来,路灯下可见小花帽到处晃动,帽檐的绿色花纹像树叶,正在晨风中呼吸着空气,在圣洁中明亮起来。
我拐进一个小巷,从这里可直通艾提尕。走过一户人家大门时,邦克忽然停了。四周立刻寂静下来,像一段音乐到达高潮戛然而止,而余音久长。
我以为这就是喀什噶尔邦克的全部了,不料,当我走出小巷,面对艾提尕时,邦克又一次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飞升了。
“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再次站在喀什广场毛主席塑像前,望着他笔直挥出,指引着前方的那只手,感觉似乎有一股气从他手指飞离而去。
这就是大气。
迷人的夕阳把最后一抹光彩洒在了毛主席塑像脸上,使他看上去更具神光。几只鸽子扑棱着落在他的肩头,转动着脑袋在看着喀什。广场上的人不知不觉已经多了起来,主席像下面就是已经被加宽的马路,人流车海川流不息,像一条热闹的河流。
主席在那么高的地方在凝视什么呢?怀念毛泽东时代,就可以想象到,当时从他心里滚动过,继而又弥漫了整个神州的,是多么激烈的心之澎湃啊?我曾爬上地处喀什西面的乌帕尔山,站在大学者玉素甫的墓旁向毛主席手指的方向观看,出现在我面前的是喀什大片田地簇拥的绿洲,大漠毅然决然与田地断开,向更远处恣肆出一派野性。沙丘一层层形成,向天边铺去,如同翻卷的浪波。“海纳百川”,毛主席的心念和赤野的塔克拉玛干相比,哪个更远,哪个更高呢?
答案自然在人们心间。
雕像是1969年的产物,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最火的日子。那只在半空中向前指引的手,自然也是当时最响亮的一句口号——“毛主席挥手我前进”。这也是当年最强烈的一句口号,正是这“一挥手”,多少人的革命激情被点燃。如今30年岁月已逝,它历经风风雨雨,居然岿然不动。在新疆,这是唯一幸存的一尊毛泽东雕像。白须飘动的维吾尔长者赶着毛驴车从雕像下走过,久久凝视着毛主席像,眸子里面充满敬仰之情。
毛主席是深入人心的神。最有意思的传说是“九大”期间,一位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后致使下肢瘫痪的将军,作为候补委员坐着轮椅来参加会议,经过主席台时,毛主席亲切地叫了一声他的名字,将军噌的一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激动万分地给毛主席行了一个军礼,声泪俱下地呜咽着:“毛主席还记得我!”说完后奇迹般地大踏步朝自己的座位走去,瘫痪从此不治而愈。人们心里有毛主席,自然时时刻刻受到他的影响。
毛主席雕像的那只手指引的不远处就是帕哈太克里乡。解放不久,当八月的果园飘出醉人的芬芳时,维吾尔族人想起了毛主席,就给他写了一封信。毛主席给他们回了信。这在当时可是了不得的一件事,几十年过去了,这个乡的人都似乎显得比别人要优越。毛主席的那封信如今仍端端正正地挂在乡政府。
在兵团农七师驻哈巴河县的185团,路前进至今见人就说他见过毛主席。路前进年轻的时候,正值中苏关系紧张,双方天天处在要开火的紧张气氛中。那时候兵团的农工都把家什变卖,把当时最值钱的缝纫机绑在自行走后,准备一旦风吹草动骑上就跑。一次苏联边防站打信号弹,一位农工在自行车前面驮着孩子,后面驮着妻子,匆匆向县城跑。正跑着,孩子从车上掉下。妻子大喊捡孩子。他说,来不及了,要是一停,苏联人打过来,咱们就都活不成了。只要你在,有鸡就有蛋,咱们再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路前进忽一日向大家宣布,毛主席准备从中央带人到新疆来给咱们帮忙呢?这话一传十,十传百,人们竟都相信了,过了一段安宁日子。后来中苏在塔城铁列克提发生战争,那几天之中,人们复又惶恐不安起来。路前进这时又说话了,昨天晚上毛主席带人已经把苏联人打跑了,我亲眼看见的。果然到了那天中午,有消息说苏联人已经撤了。人们一下子觉得路前进能看见毛主席,真是了不得,就连张福明家刚过门的小媳妇也对着他灿灿烂烂地笑。我1999年见到路前进时,他仍是那么认真地说,谁要是没见过毛主席,谁撒谎谁是毛驴子。闲聊中我出去解手,返回时路前进居然睡着了。从窗户中透进来的阳光,洒在他脸上,使饱经沧桑的他显得无比安详。如今毛主席他老人家已从神坛上走下,回到了凡间。
夕阳把最后一抹余光反射到雕像上,那只伸向前方的右臂,变得更像一支利剑。雕像就在这时好像又上升了一个高度。这时候,想站在主席脚下照一张相,无论如何上下取舍不全,它太高大了,照相机镜头中要么只有雕像,要么只有你自己。
带着遗憾走下台阶,忽然被“嘚嘚嘚”的蹄声惊扰,猛醒间,维吾尔长者驾着毛驴车已从这里跑出很远。
家畜的战斗
依明江提出要带我去看斗鸡和斗羊。空气里有一股燥热,体内更加难受,想想去消磨一下也好。
坐上喀什刚时兴的“摩的”,一路凉风扑面,“突突突”地就到了乡村。下了车走过一片沙地,迎面是一片墨绿的白杨林。就在看见这片白杨林的同时,我听见了一群维吾尔男人的吆喝声。依明江像个要冲锋陷阵的士兵一样,把横在路上的树梢扒拉开,走了没几步,一个宽大的斗鸡场便出现在面前。人们大多都将鸡抱在怀里,三五成群地扎在一起,在谈论着什么,场地上有几只闲散的鸡,正低着头在地上觅食。
喀什一带是斗鸡出名的地方。据说这里有一种鸡叫大骨鸡,是新疆的地方优良家禽品种,它头似蛇头,鸡冠极小,嘴如鹰喙,骨骼粗壮,胸部宽厚有力,身高可达六七十公分。
很快,我就在人群里发现了好几只大骨鸡。它们温柔地躺在主人的怀抱里,像待机一搏的勇士。在不远处的看台上,放了十几个笼子,每个里面都关着一只鸡。依明江告诉我,这是庄家的鸡,要是有人开价与庄家赌,一般才用它们。我细看那些笼中鸡,果然比大骨鸡要威武许多。它们身上多带有伤痕,这是“专业”的表现。想必庄家靠它们吃饭,平日定然要让它们努力去拼斗。
一个维吾尔小伙子在一旁摆了一个西瓜摊,他见我在耐心等待,就递了一个过来。我和依明江用拳头把瓜砸开,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过了一会儿,人们大概讲好了什么,有一老一少两个男子各捧出自己的鸡,放入场中。我注意到那位长者身材魁伟,一双浓眉有两三寸长,罩在眼帘上,很是英武。他也许为自己的浓眉自豪,不时地用手去摸一下。我掏出相机抓拍了他一个特写。
那两只鸡走到场中心,忽然盯着对方不动了。两位主人吆喝一声,同时用力把双手一拍,两只鸡像是听到了号令,忽然向对方扑去。也许是它们都用力太猛,爪子在地上抠起了尘灰。
接下来的战斗想必每个人都能想象得到。它们时而用翅膀猛打对方,时而腾空猛啄,这两只鸡有一个共同点,几乎在扑向对方还没有落地时,就开始了“空战”。当其中的一只狠狠叼住另一只的羽毛死死不放时,还能够发出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有胜利者的喜悦。
怎么说呢?战争毕竟是残酷的。不一会儿,它们就浑身鲜血淋淋,羽毛落于一地。虽然这两只鸡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但场上的杀气,不亚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而操纵这一切的,是在一旁为了消散心情的人。人就是这样可怕,总是会在弱于人类的物体中制造闹剧。假如有一天有另外一种强大的东西操纵人类像斗鸡一样生死拼杀时,人类将会是多么的悲哀。
斗鸡没有和局,两个多小时后,长者的鸡被少年的鸡斗败。最后决于胜负的一刻颇为惊险,长者的鸡被少年的鸡连续两下啄瞎双目,并一爪狠狠把它击倒在地。而倒地的那只鸡还是奋力一搏,把对方腹部的一块肉撕了下来。
两声惨叫一并响起。
长者气得不行,那双长眉上下跳动着,懊丧与愤怒溢于言表。他转身而去,身后,那只鸡已倒地身亡。
第二场是斗狗。
这场战斗比刚才激烈多了。两位主人牵着狗尚未入场,它们就对叫起来,等到主人一放手,它们便迅猛扑向对方。
我觉得斗狗是残酷的,从一开始,两只狗就咬着对方没放,想想它们在用力撕扯对方身上的肉时,自己身上肯定正一阵阵地疼痛。
这是一黑一白两只狗。慢慢地,白狗占了上风。尽管它身上在流着血,但它嘴上却沾满了血,这是胜利的表现,因为它嘴上的血是撕对方时对方流出的。
我想任何一种动物的杀性其实都比人还要大,只要你稍微训练一下它,它准能领会你的意图,为你去拼死拼活。而这些动物中,尤其以与人距离最近,基本上熟知人类的家禽家畜表现得更为突出。所以,经常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便是斗鸡和斗狗之类的大拼杀。
狗本来是看家的,这会儿却有了神圣的使命,用自己的性命去实现一次战斗,满足一下主人的意愿……
渐渐地,黑狗支持不住了。它不光没有了进攻的力量,就连招架也显得力不从心。但我却感到奇怪,黑狗到了这种地步,居然没有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从一上场,它就没叫,倒是那只白狗一直呐喊个不停。慢慢地,我发现黑狗不但不叫,而且也没表现出痛苦的神情。它只是那样挨着白狗的撕咬,好像只要一走进这个场子,就必须得这样。
终于,黑狗趴在地上起不来了。
白狗一方的人发出欢呼声,一场战斗结束了。
而就在这时,奇异的情景出现了,白狗慢慢走到了黑狗身边,俯下身子,用嘴去 舔它脸上的血。同时也用两只前爪努力推它。黑狗慢慢地抬起了头,与白狗对视着。
人们停止了欢呼,愣愣地望着眼前的这一幕。
白狗终于把黑狗推起,它们摇摇晃晃地向场外走去。
带路的草
出喀什不远,是去克州的路,一个长者骑着毛驴又向我走来。像所有维吾尔长者一样,他身上最醒目的仍然是白衣白帽,脚蹬长靴,身板有硬朗之感。小毛驴很是高兴,扬着头,撒开四蹄快速向前跑着。小路上铺了沥青,它的蹄子踩在上面发出清脆的声响。
长者在驴背上往前移动了一点,便腾出了放布袋的地方。布袋中所装东西并不多,但已足够长者食用。维吾尔人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每个生活用品都给他们带来享受着快乐的感觉。我曾见过一家维吾尔人为儿子举行割礼,前来恭贺的人神情庄重地进入屋内。那一天其实和任何一个日子一样毫无特殊之处,但人们都已经从繁忙的农活中抽身而出,在那里欢聚。一个小小的院落顿时变成了一个热闹的地方,生活的芬芳弥漫开来,给每一个人带来安歇下来的舒适之感。有两个艺人在院子的一角弹起了都它尔,琴声清脆,传递出对生活的赞美。走近他们一看,才发现他们的手指却都残疾,但美妙的琴声就是从他们残缺的手指下产生的。欢乐变成了一种平静的持续。多少年过去了,那个小院的情景依然时时在心头闪现。
长者到了我跟前,看见我望着他出神,便一抬腿从驴上跳下,向我打了一声招呼。我双手抚胸,向他行过大礼。细看老人,我忽然发现他眸子里的智慧之光颇浓,举手投足之间也隐隐有超脱之气。与他闲聊,不料他讲了一个毛驴骗狼的故事,我立刻为之一震。有一天他在沙漠中迷了路,因为没有明确的路线,他和毛驴只好乱闯,偶尔被沙丘阻挡,偶尔又陷入泥淖。后来,他根据几座山峰的位置终于确定了方向,但毛驴却惶恐地在原地打转,死活不往前走。他这才发现有一只狼远远跟在毛驴后面,因为毛驴被凸凹不平的沙漠弄得很烦,上蹿下跳不好好往前走,狼便与毛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不急于扑过来咬它。他心中吃惊,遇上狼就是麻烦,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麻烦呢?他想起毛驴喜欢吃嫩草,便从驴背上下来,从地上捡了一根树枝,揪几把嫩草,然后又骑上去把草伸到驴嘴前,驴因为想吃草,便将嘴往前拱,而由于他在驴背上一直把草伸在距它的嘴一尺的地方,所以,驴因为吃不上草便总是一步一步向前。这样,不用再赶驴,它在食欲的驱使下不知不觉向前走去。遇到需要拐弯的地方,他就把草往旁边一伸,毛驴自然而然拐过去了。就那样,他走出沙漠上了马路。 路上有来来往往的车辆, 那只狼悄悄转身,去了沙漠深处。
这是一个活生生的阿凡提啊!这样的智慧对于我来说显得弥足珍贵,但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就像把一个东西装在了口袋里,需要时很随意地掏出来使用一下而已。老人说完这些哈哈一笑,不再多说一句。
老人与我告别,腿一抬,便跨上驴背向前走去。
一人一驴,被路带向远处去了。
鸽子
傍晚,喀什小巷会被突然响起的一种声音打破寂静,正在吃晚饭的人们抬起头,就看见天空中有一些黑点正由远及近,向村子里飞来。
是鸽子!它们在外不管飞得多远,都要在傍晚时分回家。它们快要飞到小巷跟前时先向主人发出鸣叫,让主人知道自己回来了。飞到主人的房顶时,它们不再发出声音,用一个俯冲的姿势快速进入巢中。
其实鸽子不应该去当信使,当它把艰巨的任务完成后,它虽然被赞誉为忠诚、勇敢、能够吃苦耐劳,有坚韧意志的战士,甚至后来又被誉为和平使者,但它温柔可爱,清洁高雅的一面却因此被遮蔽了,它们的快乐从此便只能在某个屋檐下的角落或飞翔中的一次停留中,人们对它们漠不关心,认为它们始终应该穿越硝烟战火才对,它应该在伟大使命的高度永不下降,至于它的内心到底有多少欢乐和痛苦,似乎从来都不应该与它外在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鸽子从远处飞回来了,我们应该爱安静的鸽子。艾力曾告诉我一件事,他养的鸽子不知被一只什么鸟勾引,飞走后再也没有回来。我去看他房顶上的鸽笼,隐隐约约看见了鸽子栖息的痕迹……我突然觉得,对于一只鸟儿来说,正是因为有了一个家,它才要去飞翔。因为飞翔是沿着大地实现无边的梦想。
维吾尔族人喜欢养鸽子,小巷内的屋顶几乎处外可见横七竖八的鸽子架。鸽子回家的时候是极其庄重的,它飞到主人屋顶上空后,缓缓地盘旋几圈,然后才落到屋顶上或鸽笼中。有时候,鸽子的主人是一位老人,他会走上房顶伸出手臂将它们缓缓接住,眯着双眼望着它。一只鸽子飞了很远,经历了很多磨难,最终仍回到喂养它,爱它的老人身边;它带回的,不光有征服了远天之后的成功,还有从未改变过的对家园的眷恋。老人也许一直在等着它归来,当它终于缓缓落在自己的掌心,他才释然了,他脸上舒坦的神情,像一个变得清晰了的梦。在这一时刻,有游子的眷恋,有家人的守望,温暖和幸福就这样被呈现了出来。
这就是家。不往外飞的日子,鸽子会在主人家的屋子上空飞翔。春天已经到来多日,它们上下翻飞,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它们飞着飞着,突然迎着太阳翻转过身子。在那一刻,它们的身子都被照得金黄,而且因为倾斜,发出了亮光。很快,就有另外的一些鸽子飞了过来,它们也许都发现了别的鸽子身上的金黄色亮光,居然都选准一只去追逐,不一会儿,鸽子们便聚成了一片,像天空正在飘洒着金币一样,鸽子们闪闪发光。它们一会儿降落,一会儿飞升,使那些光亮变得闪烁不定。
幸福的鸽子啊,正在享受着太阳赐予它们的欢乐和光荣。但它们只是偶尔飞过这里,不知道它们飞到太阳背后时,还有怎样的幸福?
进入一家人的院子,在院子的一角,有一个通向房顶的台阶。维吾尔的庭院生活有一部分在房顶上,房子因而也就多了一种功能。有的维吾尔人把房子建成了过街楼,底下走人,上面居住。房子在路上面,人在路上面生存,这也算维吾尔人独有的一种情调吧。他们把柴火、粮食、鸽子笼等都安顿在房顶上,远远地看上去,房顶像一个仓库。有的人在房顶上又立起了木杆,有黑色和灰色的鸽子落在木杆上,长时间一动不动,像守卫着小屋的哨兵。
而一旦进入院子,才能发现通向房顶的台阶显得极其醒目。环顾四周,空空如也,该上房的东西都已经被搬到了房上面,人生活在高处,而高处却又像这个小院一样,显得极其平静。我目睹过一位老太太攀登台阶去喂鸽子的情景。她漫不经心地往上爬着,习以为常的从容使她的表情显得颇为安详和沉迷。爬到中间,她一扭头发现我在注视她,便突然加快了速度,以致脚步也显得有些慌乱。到了房顶后,她便认认真真地喂起鸽子来,好久都没有下来。我不得不离去,人都有一种心理,即自己被别人注视的时候难免慌乱;我无意间打乱了她的生活,在心里觉得过意不去。我相信,她喂完那些鸽子后会望一望天空,在心里说,感谢胡大啊,你把这么多这么好的鸽子送给了我们。然后,她就像感激胡大似的,一个又一个地抚摸着鸽子,她脸上的神情很沉迷,似乎这个世界仅属于她一个人拥有。
我在院中的台阶前徘徊,既想离去又有些不舍。生活情趣和民族特色已经体现得这么明显,你只要站在这里用双眼静静地观察,一些细微的东西便慢慢地向你浸漫开光芒。在这块土地上,有时候做一个观望者其实也是很幸福的。
再次走到院中台阶前,看到的便是另一幕。早晨的阳光从屋顶的一角斜射下来,把台阶照射得无比明亮,屋顶的鸽子受到了这束光的影响,“咕咕咕”地欢叫起来,为这束光在这一刻间发出的光亮而欢欣。两个四五岁的孩子听到了鸽子的叫声,他们觅着叫声望过去,也看到了照亮台阶的阳光。起初,他们只是愣愣地看着,不自觉地停止了游戏,过了一会儿,他们变得兴奋起来,抬起头看了看房顶后便向上爬去。阳光一下子把他们裹在了一抹明亮之中。此时这两个孩子向上爬着的姿势,多么像人类进化的情景——人类,不就是一步步艰难地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吗?梦想、希望和生活,一旦对人起到了影响的作用后,它们就是高悬于头顶的光明,人不顾一切要走向光明。人类在努力前行的时候,才有了思想、感情和语言。而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的人的反应,则显得更为具体和真实。
多少年的岁月里,人类其实一直都是孩子。
责任编辑:黄艳秋
题图摄影:子 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