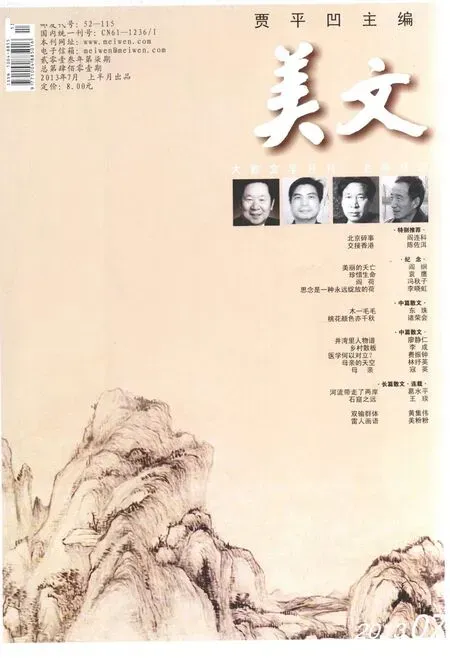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
葛水平

我喜欢民间的铁铺首,轻叩门环的响在夜静的时候是压得住黑暗的,可以使走向村子的东西远远停住,也可以让它们悄无声息地融进墙影尘土里不再出现。
盘腿坐在床上,回想我睡土炕的乡亲,一辈一辈的生命从土炕上站起来出门,又从土炕上躺下,最后移挪进土里,他们何曾睡过一张雕花木床?我突然觉得泥土是吃人的,吃人的泥土没有良心,那么没明没黑地伺候你,给你一生的劳动,到最后富裕不来一张床。
风把手艺刮进了天堂
谁把打铁声摁在了文明喧嚣深处?
此时的雨覆盖了这个山村的各个部位,那个叫铁匠铺的地方,蛛网上粘着许多小虫子,我能想象出当年铺子里的热闹,所有的人都是顶着雨声到来的。
铁匠铺永远都是一个动词,动在雨声的浸淫之下。
它的持续时间是那么久。
红钢从烈火中钳制到铁砧上,锤起锤落,叮当磅礴,小锤点击,大锤紧跟。铁匠对于铁是一场浩劫般的惊扰。
铁匠铺的热闹为什么总是在雨天里?当然,更多的热闹是在冬天。真正的冬天开始了,北风呜呜吹过,一路卷起干枯的树叶和草根。农人看在眼里的活计都拾掇完了,那么收拾好残缺的农具,沿着蜿蜒曲折的路走进铁匠铺。一个长长的冬季,锄头、镢头、铁锹、镰刀,日出或日落的声音,对于敏锐听觉的农人,大锤小锤的声音都是奢望,都是天籁,都是比时间要重要得多的来年春暖河开。
猎人走进了铁匠铺,他是来漏铁砂的。我曾看到过一只狼的腹部,一杆猎枪冲着它直射过去,视野里没有遮挡,那只狼打了个滚抽搐着,它被猎人提回到村庄,它的胸腔开满了紫色的小花。那只狼的死亡对我是一种神秘的极致,它活着时曾绕道来到村庄,它学着小孩的哭声,声东击西叼走了一头母猪。
轧钢淬火,好铁匠的声名是一把镢头能刨几亩地。钢水好能出活。农人说:好地费农具,好汉费老婆。
铁匠的另一生活是给马蹄钉蹄铁,冬用的蹄铁要打出三个防滑蹄爪,夏季蹄铁是平薄的。牵马人站在铁匠铺门前,铁匠揽住马腿,削平蹄底的老皮。铁匠和马腿,在我看来应是臻于禅境的,无悲无喜,无怨无怒,对造化万物心存感念,并与万物同一同在。只见那铁匠把一排铁钉含在口中,肩膀顶紧马后胸抱紧弯曲朝上的马腿,把蹄铁合紧马蹄,钉子穿入蹄铁的孔眼,那一片唾沫湿,随蹄铁直接钉入马蹄深处。铁匠此时有可能抬头看一下远处,廓外斜依的青山,风姿万千的杨柳,时光无时不在,无处不存,目无所视,手有所触,寸寸光阴,都只在盈手之间。那双手,就那么优雅而琐碎地生动着。
铁匠是农耕文明的先驱。也是土地本身的选择。
那是一个打铁的镇子,每年的农历九月十三,一年一度的庙会开始,铁匠们聚集在集市上,搭起炉灶,燃起炭火,拉起风箱,将烧红的铁块放在砧子上,抡起铁锤,甩开臂膀,丁丁当当,各自施展本身的绝艺,吸引四外八省的商人前来交易。空气里弥漫着烧红的铁锈味,这气味又随着热风,浸入一切开放的空间。热浪一阵紧似一阵,像潮汐,奔来涌去。镇子上因为交易铁货,所有的木门,木窗户都钉了密麻麻的铁钉。嘎吱作响的铁门用劲推开时,门头上挂着南瓜大一个铁铃铛,如现代人的门铃。人勤的时候,铁铃铛像一树花,开得肆无忌惮,随风微颤,这家的热闹仿佛要挥霍尽铁匠最后的元气。

铁门上的“铺首”给岁月古拙沧桑之感,门环轻叩,从门楼上倒挂下来的雨滴,一只素手,到底是撩人的,悬如雨,和铁的内部有着脉络牵系。人生故事都是轻叩中寻来。是的,那铺首,过去,无论是帝王将相的皇宫、宅邸,还是平民百姓的小家小院,一般都要有一座院门,两扇街门中央门缝两侧、在一人来高的地方都装有一个类似门把手的物件,可以是门环,也可以是菱形的门坠,而衔着门环或吊着门坠,固定镶扣在大门上的底座称为铺首,又叫门铺。铺首、门环都是大门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件。
龙生九子不成龙,各有所好。铺首由龙子演变而来。世上本无龙,龙的神话由人创作。编造龙神话的枝枝蔓蔓,于是有“鲤鱼跳”,有“生九子”。关于铺首,兽首衔环,作为龙的九子之一,其“形似螺蛳,性好闭,故立于门上”,由商、周人模仿螺蛳,到“形似螺蛳”的椒图,形式未变,变化的只是源出。螺为水族类,归于龙的家族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事。椒图,包含在形式里的内容,即所谓“性好闭”以螺之闭,来强调门之闭。“守御”慎闭塞,闭藏周密,铺首以一种精神,在朱漆的黑漆的门扇上展示了几千年,它透露着属于中华门文化精髓的东西,由铁匠铺锻打出形。
铺首造型之精美,以庙宇皇宫大门所饰用者为华贵。华贵的铺首呈和圆形,兽首下面,分上下两层,上层形若衔环,饰以飞龙戏珠图案,叫做“仰月千年铞”,只具装饰功能,而无门环功用。这一层之下,有飞龙饰纹衬托“仰月千年铞”铺首在朱漆宫门上,同金色门钉相互映衬,显示出皇家建筑的帝王气派。铺首别名金铺、金兽。汉代司马相如《长门赋》:“挤玉户以撼金铺兮,声噌呐以面似钏音。”描写叩响门环的情形,玉户金铺的视觉效果,和金属碰撞的听觉效果。皇家流落到民间的东西少,尤其是金子做的,如果不是含了足量的铜,那响声能出得来出不来还是两说。我喜欢民间的铁铺首,轻叩门环的响在夜静的时候是压得住黑暗的,可以使走向村子的东西远远停住,也可以让它们悄无声息地融进墙影尘土里不再出现。
谁呀?
我呀。听不出来?
声音是话语的影子,走近时隔着门缝就能辨出是谁家来人。
与兽面铺首相类,是门钹。门钹状似钹,周边通常取圆形、六边形、八角形,中部隆起如球面,上带钮头圈子。变通民宅门上的这种门钹,样式乘法,却不乏装饰美,有的还带着吉祥符号,如外滑圈以如意纹,或镂出蝙蝠的图形。在民间,更多的是铁匠铺里的手艺,也只有铺首可以抬高铁匠的文化素养。
我们的党旗图案有镰刀锤头,这同民间工艺关联,作为一个物件,它完成了符号代表阶级的过程。我还记得收割谷子,有一个谜语说:河南上来个逗打逗(意思两个谷穗弯腰逗趣),脊背朝前肚朝后。谜底是谷子。春天的谷子到秋天黄灿灿的,在北方的泥地上,谷子、玉米、大豆、高粱、麦子,全都要镰刀来收割。我还记得五月端阳我娘领我去一个叫雨井山的高处用镰刀割艾,端阳节家家门前的铺首上插艾,闭五毒。艾药香的端阳节,在我精神的午后让我欢愉、心安、美好。若干年前铁匠送我一只他锻打的锤子,锤形像一只豆包,我喜欢它敦厚温良的样子。不知为什么,我一直不喜欢钢钉,手工的铁钉不守规矩,可它们适合挂厨房的用具,时间越久它们越是黑得像天空下的夜色。坐在院子里的阳光下用手中的铁锤砸核桃,像人脑一样的核桃仁引来很多活跃的蜜蜂,它们依附在核桃仁上面,阳光照着它们,我不像一个经历风浪的人,我看着它们笑,在它们面前我如此卑微。
我在夜空下看到过最壮丽的铁花,化开的铁水由匠人拍打进夜空,那是堪与秋日丰收无垠的繁华相媲美的一种壮观,一种极为廓大的气象,看的人和被看的人嘴都咧开很大,铁花承载了某种希冀,映着他们的笑脸,光彩夺目。
我喜欢铁匠,喜欢铁匠铺子里的雨声。大锤小锤的击打声,仿佛天地间万物生出无数的口子,它们从隐处进入显处,我看到铁匠手中的铁精巧灵活,它们构成了人生凡世,让我看到了人间奇迹。铁匠,铁匠铺子,我一想到它,我手心就有了热气。
也许,我把铁匠铺子想得过于富有了,只想用文字的方式去理解他们,但是,毕竟是一个远去了的把文明活在骨子里的年代。如今的村子里再没有铁匠铺子里打铁的声音,没有了铁匠铺子,似乎整个村子里都没有了声音。铁铺首都锈烂了,铁钉子换成了膨胀螺栓,五毛一斤的旧门板买了用去烧木炭。我们丧失了许多,恰恰可能是有关生命最高秘密的隐喻和福音。我不能知,在衰败中,唯一不想放弃的是想入非非。
要命的欢喜
当我有限的记忆因岁月漫漶得模糊不清,而又迫切想回忆当时情景的时候,我什么都不顾忌了,只会躺在床上,平息自己的红尘欲望,去想。帘下的风抚过来,窗外有什么已经不重要了,我很惬意,一半的想回到了过去,一半的想徒具了其形。我不太窈窕的姿态,谁又能够说我不好!我不能说床就是纯粹的私人化空间,我只能说我爱床就像爱天空一样情深。
去年冬天,我在山西沁河岸边寻得一张清中期富家小姐的闺床。精致的木格雕花完好无损,红色的大漆旧了,旧得纯粹就成了一种时尚。床体采用贴金箔、嵌螺钿等工艺技法,共雕有十个戏剧故事情节,有《三娘教子》《龙凤再生缘》《唐伯虎点秋香》《琵琶记》等。每个作品形态生动,惟妙惟肖。描金人物故事更显出古床的华丽美艳。只是床板有些不太稳重,疏忽之间来一声响,那一声响倒叫我想起曾经的男欢女爱。床的三面有花格窗户,也都是描了金的。花格下画了人物故事,细细的婆娑的画面,我一直没有考证出她们都是哪出古典戏剧里的女子?那腰身,那兰花翘指,凤眼细眯着,往悠悠的时间深里去想,那真叫个袅娜。二百多年的历史,假如二十年一代人,十代人过去了,与空气摩擦着溅出了多少火花。盘腿坐在床上,回想我睡土炕的乡亲,一辈一辈的生命从土炕上站起来出门,又从土炕上躺下,最后移挪进土里,他们何曾睡过一张雕花木床?我突然觉得泥土是吃人的,吃人的泥土没有良心,那么没明没黑地伺候你,给你一生的劳动,到最后富裕不来一张床。在我熟悉的回忆里支撑我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该是床上事,就像时间里敞开的一间间店面,算盘珠子噼里啪啦,都算计走了,你活下去的心事,你活下去的目的,你活下去的争斗,一张床,会有多少故事发生呢?我坐在床上,再一次看那些时光下的雕刻,那满月的脸儿,俏丽的眉眼呼之欲出,什么样美丽能经得起岁月这般残酷的打磨,难道只能是一双匠人的手才够得上美丽、绵长?
坐在床上的人,心思不动,便无悲无喜。
可坐在床上的人往往会生出许多人间幻景。
沁河岸边出过许多有能耐的人,比如阳城县皇城相府的陈廷敬。陈廷敬原名陈敬,顺治十五年(1658)考中戊戌科进士。因同榜有同名者,因此朝廷给他加上了个“廷”字,改名为廷敬。此人生平好学,诗、文、乐皆佳,与清初散文家汪琬、著名诗人王士祯皆有往来,“皆能得其深处,而面目各不相假”。康熙对陈廷敬有“房姚比雅韵,李杜并诗豪”的评价。过去对官宦人家的称呼是有讲究的,一直到了民国,称呼都很规范。做了大官的人家叫“府邸”,经商人家的叫“公馆”,有钱有势的人家叫“宅院”,有文化有脸面的人家称呼“寓所”,只有老百姓才叫“家”,喊老婆叫“家属”。“皇城相府”,原本也不叫这重口味的名字,虽然乾隆皇帝亲书过“德积一门九进士,恩荣三世六翰林”的楹联,可是康熙为陈廷敬题匾“午亭山村”四个字告诉我们它原本是叫这个谦称的。“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康熙的这两句词和午亭山庄与陈廷敬很吻合,很有点故乡的脐带陪伴一生的感觉。做了“皇城相府”,不能说不好,与平民来说只能说是不家常。相府正门,有高大巍峨的城堡式门楼,上方书有“中道庄”三个大字。中道庄,为皇城相府的旧称,内城为陈廷敬伯父陈昌言于明崇祯六年(1633)所建,名为“斗筑可居”。外城为清康熙四十二(1703)年陈廷敬所建,名为“中道庄”。这样的名字实在没有让人心情不好的理由。
我这张床传说就是从“相府”流落出来的。床是一个最宜于梦想的地方,传说给它抹上了一层浪漫色彩,并点点滴滴完成了我对它的基本怀想。它是一张大家闺秀的婚床,也是睡床,20世纪40年代流落到了民间,70年代它一直在大队的库房里放着,当没有大队库房的时候它流落到了一户人家的柴房,90年代末当柴禾卖了。它的运气来了,木头的运气就是被一个木匠看到。木匠是木头的伯乐。木匠打着手电筒照着,灰不塌塌的床上堆着谷壳,老鼠跳上跳下,快乐地闻着秋天田野上粮食的气味。木匠喊了一声:“去,都走开!”老鼠散了,木匠看到眉目传情的美。木匠把手艺信奉为神,木匠坐在谷壳上,许多心事来了。木匠开始抽他的旱烟,安抚他的心事。木匠和主家说,我给你做活我不要工钱,走时你送给我它。主家说:“快拿走,你就不怕床上出妖精!”说罢此话嘴扯得和脸盆似的大笑。木匠买了它就睡在它上面。2000年有人开始收购古床,它的身价一下就提升了。此时的木匠老了,儿子打着光棍,没有人喜欢雕花手艺,时间对于所有都是一样的,让你生存,让你决定,又让你无法决定。卖吧,卖了是钱,不卖是命。古玩贩子买走的第二天木匠去要,其实也不是去要,就是去看看。那张床已经不在了。木匠的心一下跌落到了肚脐眼下,他不能骂,也不说人家的不是,他已经预先知道床会消失,可谁也没有想到他重重地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讲这个传言故事的人告诉我,那个木匠失去了床就疯了,就因为床上那几个妇女木头人人,那张床上睡过妖精。
我说,你不怕那妖精让我也疯掉?
古玩贩子看着我笑了:“因为你也是妖精。”
传言是一个罪恶的群体,人们拥有统一的语言,统一的情感,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方向,那个方向必须有所牺牲,没有一个人相信木匠的疯是因为再也看不见床上的手艺。得到可以让人亢奋不已,失去也可以让人亢奋不已。我得到它时已经经历了几手。买了它回来,我仔细擦干净,上了一遍桐油,暗红的光泽下散发出来的芬芳让我如此欢喜。
就那份意境,无端地从花格伸进来一盏台灯,台灯蛋黄的光照在一册喜欢的书上,静夜的好时光下便觉得幸福莫过于此了。古人说:“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我试着就想找这种感觉。人活一辈子就为了找一种感觉,感觉找到的时候,就发现幸福了。
今年春天的四月,我去看桃花,沁河岸边的一座古庙里,所有的一切衰败得厉害,桃花是唯一的鲜活。我走近一棵桃树时,发现它的树干动了一下,吓我一跳,仔细看看却发现是一个头发蓬乱的人,一层灰土一层黑皮,一只手耷拉在离地三尺高的地方,像一枝折断了的桃枝。他居然躺在桃树上睡觉,树下有半个黑馍,黑馍上爬了许多蚂蚁。蜜蜂嗡嗡嗡地绕着桃花,绕着他飞,围绕着把他和桃花区别开,蜜蜂知道他身体上没有花粉可采。一个人,树也可以做床。
最早的人是不是也睡在树上?《广博物志》里有记载,传说最早的床是神农氏发明,谁发明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人在夜晚离开了土地。
我们的先祖最早是从哪里走来的,树还是海洋?可以肯定,在农业与文明还没有发展起来之前,树可以遮风避雨,可以钻木取火,人身体的中段部位的私处是用树皮和树叶来遮挡的,一棵树可以是我们的一切,生命的居所,想象的还原,人是多么离不开树木!当树成为木头的时候,木头在人心目中无限放大,天地人寰,木匠来了。对美好事物的巨大热爱,对生活需求的幸福满足,木匠成为一个日常奢侈的欲望。
中国最早的床的实物是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彩漆木床。该床长218厘米,宽139厘米,六足,足高19厘米,床面为活抽屉板,四面装配围栏,前后各留一缺口以便上下。我觉得当时的床是放在房子的正中间,不然不会有前后缺口。屋子能有多大?一张装得下夜晚梦境的床占据了屋子中央,木匠让我们后来的出生固定在大地一个位置上。想想,真是透着一股古老传统的时间和诡异之谜。说一个地方人杰地灵,也与床有关系。说是东汉时期的徐稺(公元97年—168年),字孺子,豫章南昌(今南昌市高新区北沥徐村)人。一贯崇尚“恭俭义让,淡泊明志”,不愿为官而乐于助人,被人们尊称为“南州高士”和“布衣学者”。十五岁拜当时著名学者唐檀为师。唐檀去世以后,徐孺子便在槠山过起长期的隐居生活,一面种地,一面设帐授徒。东汉名臣陈蕃到豫章做太守,立志做一番大事,一到当地就急着找名流徐孺子请教天下大事,随从劝谏应该先到衙门去,结果被他臭骂一顿。当时徐已年过半百,陈蕃派人将他从槠山请来时,专门为他准备了一张可活动的床,徐来时放下,走后挂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说“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把徐孺子作为灵秀之地生长出的杰出人才。杰出人才多少年后依然杰出在文字里,这世界能有几人?人活着的意义就在于能在世上留下一段佳话。很多时候很多人没了,一辈子活得似乎很凌乱的样子,爱恨荣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势头到最后和佳话始终是不沾边儿。
沁河两岸一路走过来,我留意那些窗户下放着的床,大都已经现代化了,阳城一带有一种床叫簸箕床,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后很流行,也还有点意思,很像是榻和罗汉床演变过来。清代的床在沁河两岸大体保留了明代的风格和特点,一般用硬杂木,好的用核桃木,没有南方的精雕细刻。在沁河岸边的豆庄我见过一张老床,三块独板连绵不断结合而成的屏风,床头床尾画“功名富贵”。古人的功名富贵怎么来画?就画牡丹就画公鸡。公鸡有五德:头顶红冠,被古人认为是“文德”;姿态凶猛,是“武德”;公鸡好斗,见比自己勇猛的就会应战,被认为是“勇德”;觅见食物就招呼同伴,是“仁德”;按时报晓是“信德”。唐朝诗人李贺有“雄鸡一唱天下白”的诗句,鸡鸣预示着日头要升起来了。“公”与“功”同音,“鸣”与“名”同音。牡丹则寓意富贵。功名富贵是高官厚禄,是丰衣足食,是无忧无虑,是吉祥美好。床身和抛物线的华丽束腰一体,透雕狮子和阳雕草龙纹、云纹一气呵成;靠背中间阳文雕刻了“福寿三多”瓜果。“三多”来源于《庄子·天地》中的“华封三祝”。佛手的“佛”与“福”声音相近;传说中的桃子吃了可以长生不老,是长寿的象征;石榴多籽,寓意多子孙。圆雕和透雕结合的榻脚踏着底端是神兽。该榻通体黑漆为底,以极细的工笔和富有层次感的写意手法,在屏板内侧描金绘满蝙蝠。这让我想起来乾隆下江南时的一张老床,乾隆在那张老床上书写了七言古诗:“轩辕液金作神物,德合乾坤明日月。阴阳精气此蕴郁,万八千春岂湮没。丁甲护持魑魅祓,中圆光外绿云蔚。如星重轮丽天阙,四灵五岳交唯榻。汉唐俗制气早夺,其祥应不让屈轶……”并附二印,其一为“德充符”,另一为“会心不远”。乾隆皇帝的七言诗和二印很有些意蕴,乾隆不是一个没有节制地生活的皇帝,不像汉刘骜因了贪恋床上功夫到了最后连走路都有点迟钝,一个竭尽自己欲望活着的人,床笫之欢让他合上眼时不是醒,是绝命而去。
床上的人性是解放的,与床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层次性得以逐步展开,和自然山水有一样的疗疾功能,弥散和蕴含着使人身心舒畅的“释放”,也可驱郁化闷,但却不能叫人耳聪目明。“床事”是一个暧昧的词,我的一位学医的朋友说,床事可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抑制状态、改善心肌营养、刺激造血系统功能,可使红细胞和血红蛋白增加,明显的可使人放松。也就是说,能叫你神凝形释,豁然疏朗。
我走进一户人家,正是采摘花椒的季节,院子里铺了一层,屋子里床上铺了一层,花椒的香气无端的叫我想起了“椒房” 。洪昇的《长生殿·定情》:“怕庸姿下体,不堪陪从椒房。受宠承恩,一霎里身判人间天上。”我看见那个在灶台边炸麻花的女人笑了。麻油在锅里慢慢地鼓着油窝,她一边往面盆里撒椒盐一边和我说话,两只手搓着长长的面,拧成麻花,“哧溜”一声下锅了。我看到她的嘴唇四周起了一层干皮,一个缺了水分的女人。她说:“那是一张地主家的床,祖上土改分来的,那画着的金人儿是老戏《西厢记》,来看的人,多没有一个出高价。我睡这床糟蹋了。”我说:“嗨,床就是叫人睡觉,叫人生儿育女。”她大笑了起来,好像有一星唾沫落进了油锅里,响了一下,她手上的一根麻花又下进了锅里。果然是画了《西厢记》,有些衣纹不是太清晰了,我站在床前看,始终看不仔细。一个男孩跑进来喊:“妈,麻花好了没有,戏快要开了。”村子里唱戏才要炸麻花煮油糕,村中央的什么地方传来锣鼓家伙,男孩拿了一根麻花跑了出去,女人喊:“还没有给老爷烧香,你个吃嘴东西!”女人看着我说:“他就是在这个床上生的,坐月子,没少往那画上尿,看不清,尿洗过还是看不清。小孩家屁也不懂。”案板上的麻花已经堆起来,她麻利洗手也赶着出门去看戏。
我走过戏台,看到戏台上有红帐子,一个头顶盖头的女子正在听谯楼上打三更,那个舞台上的男人不去掀她的盖头,一掀了盖头便就是含情脉脉,半推半就。我一时想不起唱的是哪出戏,看到所有的人僵僵的,等洞房花烛夜一波三折风生水起。
《梁书·羊侃传》记载:有个叫张僧胤的宦官去找羊侃,羊侃不理他,说:“我床非阉人所坐!”过去的人是如此决绝,床是人生交际的开始。《世说新语》也有记载:“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齐世祖告诉他:“此事由江敩、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于是纪僧真领旨去了江敩处,他刚“登榻坐定”,江敩就马上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弄得纪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而齐世祖的回答却是:“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表示他也无可奈何。士大夫应该就是当今有文化的人,有文化的人有骨气,也当有一种不一样的世道人心。
这一点农民比“士大夫”胸怀开阔,你只要一进门,家里的女人都会说:“坐,床上坐。”上门不欺客,是打心眼亲热,无一点生分。对于上门的客人,农民的情感来得总是卑微。

假如床上生出的都是不成仙不成佛的孽种,断不掉尘念,超脱不得,在人界冥界天界之间一个连魂扯肉的半界世界徘徊,离开床便开始神经直跳,灵肉俱狂,终将成为一个自私的人,一个欲望唯我世界的人。回到床上,谁都会想到明天是最美的永远,那么连接明天的永远是一张床,床是人的三分之二人生,那么床上床下都请不要叛离自己吧。
据说“床”在汉代是一个名称使用范围更广的词汇,不仅卧具,连坐具也称床。如“移吾床远客!”汉代还有梳洗床、火炉床、居床、册床等。西汉后期出现了“榻”,“榻”的出现和“床”才有了明显的区分。对于床,汉代刘熙在《释名·床篇》中解释道:“人所坐卧曰床。”又说:“长狭而卑者曰榻。”《说文》也说:“床,身之安也。”而榻,则是专供休息与待客所用的坐具。汉代少数民族的“胡床”,是一种高足坐具,其实也是我们所叫的“榻”。隋朝“胡床”又变称“交床”,唐朝又变称“绳床”,宋代又变称“交椅”或“太师椅”。沁河两岸的“交椅”和“太师椅”多,20世纪90年代末期,有收古家具的从古村往出拉椅子,拉到大路口或县城出河北、河南的地界,有人不到两年时间跑坏了两辆四轮车。美好的东西都与知识有关。那么是谁叫生活逼迫得疯了要做出一些无知的事情?“破四旧”让农民与俗世隔绝,当所有的“美”全部以“新”为准时,“新”竟是如此霸道!
我在沁河岸边的上庄见过一张架子床。它的做法是四角安立柱,床顶安盖,俗谓“承尘”,顶盖四围装楣板和倒挂牙子。床面的两侧和后面装有围栏,多用小块木料做榫拼接成多种几何纹样。因为床有顶架,所以叫架子床。上庄的村民告诉我,原来上庄的王家有一张拔步床。他说不来那床的样子,只说是其外形好像把架子床安放在一个木制平台上,平台长出床的前沿二三尺,平台四角立柱镶以木制围栏。还有的在两边安上窗户,使床前形成一个小廊子,廊子两侧放些桌凳小家具,也可放铜脸盆和尿桶。说拔步床放在王姓大户人家的室内,很像一幢独立的小屋子。王家的另一串院子有过一张罗汉床。它的左右和后面装有围栏,但不带床架,围栏多用小木做榫攒接而成。围栏两端做出阶梯形软圆角,有几分大气入了进去。后来叫人当柴火烧了,因为木头硬,竟然燃得不够欢。我见到王家宅院的时候,王家门前已经只剩下了三棵老槐树。原来上庄是有煤矿的,借助煤矿可以带动旅游,小煤矿关了,谁也不拿闲钱出来维护。大热的夏天,我想大喝一声:这么好的东西,谁该来埋单!
有一本书上说,以前土家男女青年结婚,男家要打一架“滴水床”。滴水床并不滴水,只是形状上好像屋檐的滴水一样。素常有一道滴水和两道滴水之分。两道滴水床,又称为“出一步”床,雕龙画凤,十分讲究,堪称土家一绝。一道滴水和二道滴水之间为踏板,宽六市尺零半寸,深四市尺零半寸,左右设床头柜,可当坐凳,主要木雕在二道滴水上,如“八仙过海”“金瓜垂吊”“龙凤呈祥”以及各种花纹的“芽饰”,加上漆工艺术处理,显得斑斓绚丽。按鄂西习俗,床的尺码,均不得用整数,必须加半寸,俗话说,“床不离半,屋不离八”,“半”由“伴”的谐音而来,“八”由“发”而来。古人的可爱处是把一个汉字真当一个字来用,用尽用透用出一种惊魂来。我们现在用汉字就像用一粒空壳子弹,怎么都射不进一个人的心灵。
床事不能情绪化,而要理性化,否则就是对生命的摧残。床上油匠和木匠雕刻和画出的那些人物故事,重要的不是图了个好看,重要的是睡醒之后提醒人活着的意义。有一个说书人,开场前说了一个段子,说一个老头娶了个少妻,终于一病不起。大夫警告他“你骨髓已经没了,只剩下脑髓了。”老头大喜,看着床上的娇妻发自肺腑地问:“大夫,你着实和我说,脑髓还可供我战上几次?”居家过日子,从而得有一种把握,床是天堂也是地狱。
人安居方能乐业。可往往居不易。守护土地的是一座村庄,守护家庭的是一场婚姻。婚姻最主要的用具是床。婚姻不和出现先兆前期反应是分床。“阿妹的肚子像牙床,是个冬暖夏凉的好地方。”近乎于承袭和稳定了生命最初的忠实,白描见心的入骨,床的重要性就看出来了。词语对婚姻的解释是这样的:男人和女人结为夫妻,已结婚的状态。男人为女人而婚,女人为自己而嫁。我以为婚姻最主要的一件大事,就是依赖床合法化的生儿育女。
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去一个工地找我表弟,晚上的建筑工地楼层地上睡满了民工,他们只穿裤衩,躺在凉席上,睡得很放肆,四仰八叉,有的人在旁边摔扑克叫喊声很大居然也没有吵醒。各种牌子的烟雾懒散地飘在建筑工地的上空,灰的幕笼罩了一切,月光懒懒散散相拥,不亲近,也不拒绝,地上的鼾声此起彼伏,如同白天他们的体力活那样沉重。一辈子没有睡过一张好床,睡眠却很踏实。柳青说过:“人是一架耐磨的机器。”就他们那样的集体睡姿我以后再没有见过。童年时夏日的夜里,院子里铺一领苇席,男人女人孩子们都坐在上面,月光明晃晃地当头照下来,就等于给梦找一个憩身之地。我听到了不远处的玉米地里,蛙鸣声弹着青玉米的叶子,明丽的月影朗照一切,白天出山的大人们把山外听来的事努力用农民文学家的口吻复述一遍,谁都怕上茅厕误了精彩的一段。小孩子们不敢大声喊叫,怕一不留神碰落了玉米的香气,青草的香气。月影下老窑花纹繁复的窗栏板,一棵树宽的门扇,紫铜的门环,铁葫芦锁,看着看着睡意来了,不等散场人就睡过去了,被大人喊醒时骨软心糊得恨不得死过去。那样的睡眠我再没有找到过,尽管我处心积虑买了一张清代的雕花床。换一种说法,我在雕花老床上读书却是读得入迷,读得有了要命的欢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