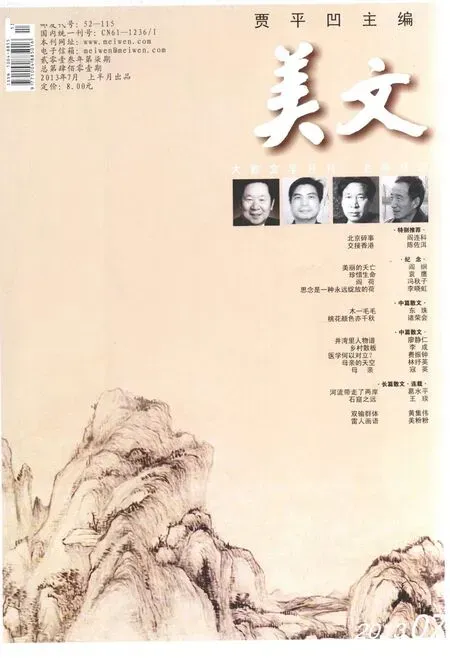公民三题
刘元林

有事别找我
同学打电话来,说是他的一位朋友被警察欺负了,问我能不能找找人。因为忝列警营做宣传报道,同学、朋友遇到一些与警察相关的事,偶尔会找到我。我曾经对朋友说,本人一字警耳,常年看猪跑,基本不吃肉,拉关系、走后门、违法乱纪的事,就免开尊口了。一是我没有那个能力;二是跟我的价值观冲突。侄儿说他的车有好几个违章,要罚上千元,问我能不能找人把它铲了,我说你老老实实去交罚款吧,我违章了也是这样做的。求人莫如求己,以后尽量不违章就是了。但我也向朋友表示过,如果碰到警察胡乱作为,伤害、冤屈了你,你一时又投告无门,可以说给我,警队的情况我比你们熟悉些,可以帮你一起想想办法。
既然这么说了,同学的电话求援,自然没有推辞的道理。原来同学的朋友小张,去南方某省会城市出差,刚入住宾馆房间,便来了两个警察,说是当地派出所的,接到举报,这个房间有人吸毒。小张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只好任警察去查。一查不要紧,果然从床头的抽屉里“搜”出了吸食毒品的疑似针管。小张就这样被带到了派出所。他反复申明自己从不沾毒品,对那个针管并不知情,警察却反问不是你又会是谁呢?虽然既没打也没骂,但架不住接连数小时地审问。小张有公务在身,又担心这事被单位知道,若不能自证清白,连工作都可能保不住了。万般无奈之际,他在讯问笔录上签了自己的名字,并交了一万元罚款后,才脱了身。出差归来,回想自己噩梦般的经历,他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
我对同学说,容我想一想,过会儿再给你回电话。
我首先想到的是同学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我的经验是,有些投诉者,为了争取同情和重视,介绍情况时,往往会夸大其词。但我判断同学所言当基本属实。他的朋友若真吸了毒,一定唯恐天下知之,决无自扰的道理。铁打的宾馆流水的客,警察用一个来路不明的针管就判定一个人吸毒,既没有对当事人进行抽血化验,又没有其他旁证,即便不是蓄意的讹诈,也不符合基本的办案程序。若办了错案,需要还当事人一个清白的。
我拨电话过去,对同学说:让小张写份申诉材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特别是办案警察的姓名和所在单位,明确提出自己的质疑和要求,多打印几份,用特快专递寄给当地公安局督察大队和纪委负责同志。同学说,小张当时吓得不行,根本没有记住当事警察的姓名。我说对警察的长相该有印象吧,他们所在的派出所不会记错吧。同学又问,要不要给你也寄一份。我说先不用,看看当地的反应再说。
过了大概十多天,同学来电话,说那两个警察已经主动跟小张联系,承认他们办了错案,一要登门道歉,送回全部罚款;二要给他支付一笔精神赔偿金。小张也见好就收,说只要把案底销了,把罚款退还,就算了。同学很感激,说:“元林谢谢你啊。”
我说:“何谢之有,我什么也没做呀。”
这事让我感慨了半天。不知从何时起,我们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或者遭遇了不公平对待,已经不习惯走“前门”,即通过合理合法渠道解决,第一反应往往是托关系、找门路。其实这多出于无奈。一些政府机关和部门,官僚主义盛行,门难进,脸难看,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加之监督缺失而形成的权力寻租,没钱不办事,有钱乱办事,群众通过“前门”办事的难度大、代价大,于是便纷纷投奔“后门”。前门不畅,后门和邪门必然洞开。
另一方面,作为当事人也需要反思。大家都感叹政风披靡,法治不行,权力部门当官做老爷,不依法给百姓办事。不妨问一下,这些“老爷”的面孔和作风,是不是跟我们的娇惯和放任有关?官员是由纳税者雇佣和养活的“公仆”,依法为百姓办事,天经地义。不作为或者乱作为,都是不能允许的。仆大欺主,仆固可恶,主亦有责。我们有没有拿出“主人”的姿态,跟他们较真,责问他们为什么不办事、乱办事?就他们的失职或过错,有没有找他们的主管领导和部门反映?没有走的路,就不能断言走不通。上述的小张,他所以首先找同学、朋友,就是先入为主地认为,正常的投诉不会管用。尽管当今中国政治生活中有太多的丑恶、腐败、不合理、不合法,但我还是不主张把世道看得一团漆黑,不主张低估了人间正义和公道的力量。
建设民主法治和政治文明,首先是执政党和政府的事,同时也是每一位公民的事。甚至可以说,公民的力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的力量。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和政府。顺民支持的是专制,暴民支持的是暴政,只有公民才能支持民主法治。当我们习惯于沉默和逆来顺受,权力就会更加放肆和无所顾忌;当我们习惯了“旁门左道”和“曲径通幽”,法治的大道就永远荒草蔓生。
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那么推动社会文明进步,自然人人有份。为了自身的权益,为了子孙的福祉,对于那些不合理的体制和制度,对于随时可能发生的侵犯和伤害,我们除了“跟伢死磕”——依法据理地、非暴力地、持之以恒地力争,还能有更好的选择吗?
且慢骂警察
汪刚强从我拍的几张澳洲警察的照片中读出了“纯净”,也印证了我对他们的总体感受。在与澳洲警察相处的十多天里,他们的热情、敬业、对生命价值的关爱以及由衷的职业自豪感,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说两件我印象深刻的事吧。在墨尔本,一晚我从亚拉河拍照回来,走岔了路。看到路边巡逻的警察。其实我大体知道该怎么回宾馆,只是想试探一下他们,就走上前去,用蹩脚的英语问:“How to Spencer Street?”警察收住脚步,微笑着,边说边比划。我不住地点头,其实一句也没有听懂。一句“thanks”之后,我想,他们对一个东方面孔的“老外”如此,对本国国民还有说的吗?
还有一件事,是维多利亚州警察局向我们介绍的。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维州多次发生警员反应过激开枪致死人命的案件,包括打死一名持刀攻击警察的15岁女精神病患者,社会反响强烈。对此,维州警方认真反思,认为主要原因是警员操之过急,缺乏实战策略。于是,他们在教学中向学员强调决不轻易使用枪支的原则,规定遇到袭警,必然首先有节制地后撤,而不是“迎着尖刀而上”。在维多利亚州警察学院训练馆,我们看到,遇到持刀袭警如何后撤和应对,是警察训练的一个基本科目。
澳洲警察是怎样练成的?我在有关报告里总结了三条:一切从实战出发的教育培训,全面的装备和技术支持,对职业荣誉感的高度重视。其实还有两条我没有写:对上帝的信仰和民主体制。
在一些场合,我们不愿谈或不能谈西方人的信仰,因为我们是无神论者,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虽然我们一面又在高声歌唱“人民的大救星”“继往开来的领路人”等等。不说并不等于不存在,信仰其实是解析西方文明一把重要的钥匙。
维多利亚州警察学院,前身就是一所教堂。维州警察厅负责教育的官员指着这所教堂悬挂着十字架的大厅对我们说:“这里就是我们警察的精神殿堂!”信仰上帝,为他们的爱岗敬业、热爱生命、尊重人权提供了最可靠的精神依据。因为上帝告诉世人:人人受造平等,都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
第二,民主体制,也是造就澳洲警察的重要前提。在民主体制下,警察只是“纳税人的保安”,只对代表全体纳税人意志的法律负责,而不听命于任何党派和个人,这就从根本上避免了沦为“私器”的命运。什么刮宫流产、催粮要款,什么清理摆摊、强制拆迁,中国警察经常从事的这些非警务活动,跟澳洲警察是不沾边的。
如果不能把“警察”放在整个社会坐标系中,是说不清警察的。
跟中国警察打交道多年,深知中国警察队伍问题很多,警匪勾结、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生冷硬横的现象十分普遍,我痛恨这些现象,也时刻警醒自己。但总体而言,我对中国的警察是同情的。没有法治至上的体制,没有依法行政的政府,就没有依法办事的警察。由方方面面制造的矛盾,却总是把警察推到一线,让警察与民众直接对立。中国警察的很多过犯,都是在替政府背书。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警察,也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
我常对朋友讲,不要怕警察。中国警察脾气很大,胆子却很小,因为他们很在乎那身制服。他们一旦侵犯了你的权利,就跟他们干——不是打架,是依法维权。维权的渠道很多,可以打110投诉,可以找警务督察纪检部门,可以找检察院,还有新闻单位,还有网络,一次不管用,就不停地找。为自己争权利,就是为社会争权利。不必逆来顺受作顺民,也不要学北京杨佳以暴制暴作暴民,要学就学湖南孙志刚的父亲——锲而不舍、以法维权做公民。
最不可取的就是“难民心态”,见了警察哆嗦,警察走了开骂,特别是砍一树损百枝地骂,既不解决问题,又会强化警察的“伤兵心态”——老子在前线给你们卖命,你们还这样骂老子——这样只能恶化警民关系。一个人一旦不被尊重,缺乏对自身价值的基本认同,行为会更加不堪,回头受害的又会是谁呢?
每一个人的言行都是有意义的,都是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当我们怨这个、骂那个,能否反躬自问:我为践行民主法治、净化社会空气到底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你敲过邻居家的门吗?
这个问题是博友商铁军不久前在他的博客里提出来的。看过他的博文,我也生发了一些联想。
我的儿子都都进入四岁以后,似乎没有那么闹了,这让我们颇感欣慰。他两三岁上,闹得太凶,以至我一度怀疑他患有“多动症”。那一段时间,他除了睡觉和看动画片,在家里几乎没有消停的时候,爬高上低,翻箱倒柜,二十来平方米的客厅,整个就是他的“游乐场”,玩遥控汽车、滑板车,骑儿童自行车,玩气球、足球甚至还打过儿童保龄球。客厅是木地板的,动静太大的时候,姥爷姥姥和我们都会提醒制止,但有时确实管不胜管。他如此疯玩的后果,一是客厅的茶几、餐桌椅、电视机柜还有墙壁被各种玩具碰撞得斑斑点点、伤痕累累,二是楼下不答应了。
一天晚上,儿子和我正兴致勃勃地推一个气球,为了不让气球着地,他一会儿沙发一会儿地面地上下跳跃。忽然有人敲门。我打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中年男子,满脸烦恼和怨忿,劈头就说:“你家干什么呢,还要不要楼下的人活了?!”
我和儿子正玩在兴头上,这无疑兜头一盆凉水。如果来者态度温和一些,我可能就赔礼了;但他一幅兴师问罪的架势,我心生不快,冷淡地问了一句:“有这么严重吗?”
妻子从厨房出来,很和气地对对方说:“对不起,小家伙比较闹,我们没有管教好。”没想到对方又来了一句:“别让他整天乱跑,咚咚咚的,谁受得了!”
我试图克制自己,但还是没有搂得住。闻听此言,我火了:“他是个孩子,你小时候整天坐着?”
对方更火了:“你们这是扰民,知道吗?再这样,我就打110!”
“爱打不打,随你便!”
妻子用力把我推到屋里,拉上门。她则在门外耐心地劝慰对方。
送走了来客,妻子一进门就批评我不该与对方吵。“知道吗,他是一个中学老师,还有心脏病,晚上得备课、改作业,都都这么闹,确实影响人家了!”
我半天无语,心生愧疚。平心而论,儿子是太闹了,连我这当爹的有时都不胜其烦,何况人家身体不好。我应当理解他刚才的态度,人家一定是“积攒”了多日、实在忍无可忍才找上门来的。儿子小不更事,但这不能成为让他为所欲为的理由,监管不力,噪音扰民,我们做父母的难辞其咎。
我于是开始对儿子严加约束。不久以后就是春节。大年三十下午,我带着儿子,提着一盒礼品,敲开了楼下邻居的门。开门的正是男主人。我说:孩子这一年来没少给你们添麻烦,多担待了,给你们全家拜个年!主人显然大感意外,不住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孩子嘛”,就让我们进屋里坐。
不敢说儿子自此就“鸦雀无声”,我们两家却于是相安无事。每次在电梯和小区遇到,都会热情地打个招呼。
这是我住进新址三年多来唯一一次与邻居打交道。
与我家同层毗连、共用一个走廊的两户人家,都是乍结婚的年轻人,虽然见面也打招呼,但彼此没有走动过。今年春节起过这念头,但两家都锁着门——他们都是北京二代,提前上父母家过年去了。
在邻里关系上,城市和乡村判若霄壤。这是不同的居住方式、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决定的。同样在城市,若同处四合院、大杂院,共用水房和厕所,低头不见抬头见,邻居来往就多些。住进高楼,楼下保安和门禁森然,各家防盗铁门冰然,阻隔了盗贼和不测,也阻滞了交往和温情,家家躲进“鸽笼”成一体,个个无事不登三宝殿。正如一则手机短信上总结的:上网和欧洲人交朋友,却和邻居并不认识。
乡村属小农经济形态,邻居关系既是精神的,也是实用的。没有像城市一样自足的精神生活,人际交往的重要性就凸显了出来,邻居不在一起扎堆儿聊天,打发时间都可能是一件难事。何况在低下的生产力水平下,在可能遭遇不法侵害的情况下,相互扶助、彼此照应又是多么必要。张家中午吃什么饭,李家老母鸡下了几个蛋,邻居们都清楚。这种信息高度透明的邻里关系,让人享受温情的同时,个人的私密空间所剩无几,自由和权利随时会被侵害。
乡村和城市,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温情和自我的缺失,一面是冷漠和精神的独立,各有利弊,实难两全。于是村里人带着盼望往城里挤,城里人载着热情往乡下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