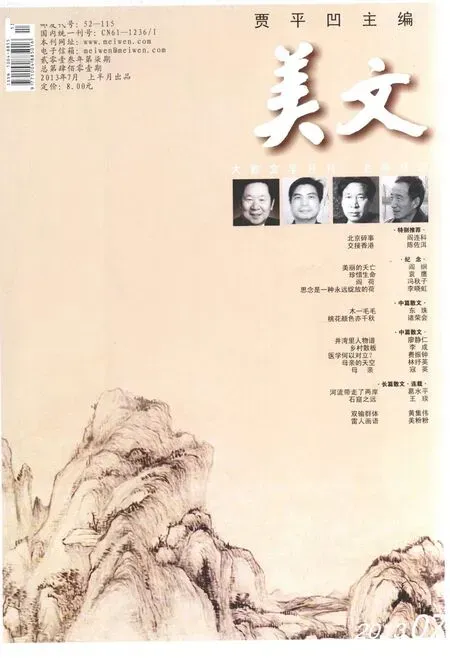信任的道德动机
费振钟

与中国医学不确定性连带的是医学信任问题,不确定性的疑雾笼罩在中国医学上空,对中国医人产生了持久的历史与道德困惑。
如果《扁鹊见蔡桓公》属于一则流传中被改写的医案,那么记录中的扁鹊,就是遭遇不信任而导致医学失败的第一人。当后世民间赋予扁鹊神性特点,与其说是对其医学才能的认同,不如说是转化信任危机的一种叙事策略。在古典医学时期,无法建立标准用来判断医学能力和医疗效果时,神明化甚至神秘化是一种必要而合法的选择。
不过,信任问题,虽产生于医学的不确定性,最后却归结到医学权力。中国医学在前现代从未有过专业考核与评定,因而也未能形成制度性的职业特权。来自扁鹊的教训,说明民间医学远远不足以从制度上建构医学权力。医人的权威性,既非客观地由他的医学才能和专业水平考测,则往往通过另外身份加以申明,这一点到宋代新儒医产生尤其显著。拥有儒学身份的医人,借助儒学知识对于医学权力的掌控,从而获得更大的权威,正是通过儒学知识权力的追认,中国医学在尊崇3世纪医人张仲景为医圣的同时,整体上提升了医学的信任度。主流医学之外,边缘的道医与僧医,在其医学活动中,则通过宗教身份,一如既往地获取民间社会敬重。南宋时期以杭州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僧医团体曾经成为本地区从皇室到平民普遍信赖的医学力量。
但是信任在医学活动中,存现于作为医学主体的医人与作为医学对象的病者及其亲属之间的关系中,信任不是一种单方面的态度,而是一种医学对话呈示出来的语义表现。然而,在中国医学未能有效建立职业特权的历史中,通过医人与他的诊治对象之间的对话形成信任的语言,通常难以进行。医人的普遍感受是,他与病人之间很难“说理”。他们自认为通晓医道,掌握了权威性的知识,可以在医学领地树起一面信任的旗帜,然而那一套关于医学的“准确的理论和高深的语义”,除普通病人难以理解外,又往往受到有儒学知识训练的病者或其家属的责难与挑战,这些有知识的病人与其家属往往用自己的理解干涉医人诊断。以上两种情况,都给了病人自由更换医师的理由,从而使医人与病人之间的对话中断。自认为才学高超的医人往往因此失语,对话变成口干舌焦的自白,以及令人沮丧的自我辩解。某些性情高傲的医人,甚至情急之下不得不在医学对象面前自立保状发下誓词,争取病人回到自己在诊案。
11、12世纪,只有为数很少的医学个人记录。这些零碎的记录,基本上沉浸在当时医药的发现与技术整合的乐观情绪之中。南宋初期,许叔微《普济本事方》里,关于经验药方的使用和疗效观察,似乎使这位著名的“学士”医师,只顾“漫集已试之方及所得心意,录以传远”,而有意忽略了他与病人之间在医疗过程中遇到所有那些麻烦;或者由于突出和强调“普济性”的医学效果,他不自觉地掩盖了医学信任危机。然而,当医案成为17世纪医人的普遍医学叙事时,信任问题便无法回避地暴露了。喻嘉言在他的《寓意草》中,坦承他个人多次面临的窘况,后于喻嘉言百年的另一位著名苏州医师徐大椿,在医治一位女性病人时,也继续报怨过:“盖欲涉世行道,万一不中,则谤声随之。”可知当时医人,对来自病人的不信任有着普遍忧虑。
这年初秋,病人刘泰来因疟病胸腹鼓胀,在其他医师进行治疗的同时,又请喻嘉言参与诊治,这已反映了病人的不信任态度,所以喻嘉言从一开始就在病人的疑虑中进入现场,其后与病人之间在服药上讨价还价,甚至发生喻嘉言与病人家属抢药的冲突,将治疗过程演变成一场戏剧性的医学事件。病人结局,当然是悲剧性的死亡。对于这样一种由不信任导致的后果,喻嘉言感叹说“余但恨不能分身剖心,指引迷津耳。”
检《寓意草》的记录,与上述类似或程度更严重的案例,如徐国祯案、黄长人案、李萍槎案、顾枚先案、顾諟明儿子案、徐岳生案等近二十个。《寓意草》病案总数也就九十多个,疑案占了近二成,尽管作者认为这类医案更适合医学讨论,但推知当时情景,作者无疑深感困扰。其中如顾枚先案,五起五落,治疗时间历经夏秋三个多月,让喻嘉言“焦劳百日,心力俱殚”,仍因未能有效地让病人按照他的医学观点治疗,最后病重不治。喻嘉言为他这类医学活动作传时,由于涉及他作为名医的个人形象所受到的影响,心情相当复杂。在李萍槎案中,他写道:“先生闻名而请,极其敬重,及见议病议方,反多疑意,不才即于方末慨叹数语,飘然而别”,对喻嘉言推崇备至的胡卣臣,深表同情和理解:“此嘉言所以昭述,亦曰不得已欤”,并总结为,医人的不受信任,如同忠臣贤士一样,“献玉而遭刖,投珠而按剑”,是一种道德才学之士的共同宿命。
事实上,喻嘉言和他同时代中国医人,仅靠“以理议病”,而缺乏其他有说服力的医学技术支持,他们通常会将这种不信任的压力转向个人道德上的自我释放,相信有一种道德的动机与力量,能够改变由于不信任造成的医学被动。在始终将医学作为个人“涉世行道”的志业对待的医人看来,他既担负着“济世”重任,那么在不受信任时,一方面可以坚持说服劝导,甚至通过担承风险的方式强制施行他的医学方案,以尽自己的道义责任;另一方面则又可以在由于不信任而导致医疗失败后,将失败的后果归结到“不能大行我志”的普遍人生局限当中,如徐大椿所说:“天下事尽然,岂独医也哉?”由此获得道德上的自我解脱。
显然,当中国医学从特有意识形态出发,处理医学不信任问题时,它所持的有效方法,就是这样一种道德化解方法,或者说是一种政治哲学方法。非此,则无从将医人从不信任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与西方医学致力于现代科学技术,来解决传统医学中的不信任问题相比,正是从这个道德性方案中,我们看到中国医学何以能够构筑它的知识基础,使它成为最稳固的保守主义文化堡垒。这个堡垒形成了对中国医学历史的维护,其代价则阻挡医学技术的解放和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