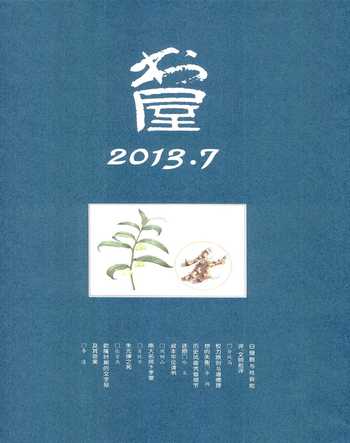杜荀鹤人生的标本意义
陈建华
一
晚唐杜荀鹤写过一首《春宫怨》,名气很大,清代蘅塘退士的《唐诗三百首》作过收录,更使这首诗几近妇孺皆知,全诗如下:
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
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
此诗以“风暖”一联饮誉诗坛,古今论者多推举之。寥寥十字就写尽了春风骀荡、鸟声轻脆、丽日高照、花影层叠的春景,就投入的文字与产生的效果而言,其“性价比”之高确已直追盛唐王、孟诸公,且十字也极好地反衬了宫女的怨情,特别是碎、重二字,极其生动传神,可谓深得风人之旨。
笔者却倾心于颔联两句:“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从诗学角度而言,这两句直白浅露,有悖于诗歌含蓄蕴藉的传统,反近于白居易的浅切通俗,算不得诗中的上品。但这两句好在对个体生存状况的揭示及思想瞬间绽放的光芒,作者在饱受潜规则之苦后终于悟出了传统社会所普遍存在的历史真实:逆淘汰。
表面上看,这两句揭示了后宫中残酷的生存环境,表现了一个宫女欲妆又罢的思想活动:在后宫这种女性竞争极为惨烈的地方,真能得到皇上青睐的并非容貌的漂亮与德行的高洁,相反,勾心斗角、献媚邀宠等有违公平竞争的刻意钻营却成为了最佳通行证——王昭君不见幸于汉元帝便是为人所熟知的反例。但稍具诗学修养的读者会明白,此诗继承了古典诗歌源远流长的香草美人传统,表面写宫女,但实为自况,是不得志的读书人的愤切之语。这种“以色事人”的手法创自屈原,在古典文学中被广泛使用,唐人张籍、朱庆馀、秦韬玉用得炉火纯青。皓首穷经的杜荀鹤经历了一次次失败后,开始反思权力迷局与权力真相:原来社会选拔人才并非以真才实学为唯一标准,自己寒窗苦读、练就一身真本事又有什么意义?
相传杜荀鹤是杜牧的微子,即共小妾有身孕后另嫁他人生下的。和一切才高位卑、志不获展的诗人一样,杜荀鹤在诗坛上享名很早,但文学才华,一如英国作家王尔德所言“所有的艺术都有无用的”,在价值取向单一的传统社会更是如此,诗人并不能成为一个有固定经济来源的光鲜体面的职业,再优秀的诗人如果缺乏权力的赋值,仍将被归并为失意者之列而只能发出“古来才命两相妨”的浩叹。智力超群且成名颇早,让杜荀鹤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可以一展抱负,他的《小松》诗借松写人:“时人不识凌云木,直待凌云如道高。”虽讥刺时人目光短浅,亦自负栋梁之才。和晚唐大多数萎靡颓废的诗人相比,杜荀鹤算得上一位有兼济情怀的儒者。他自称“诗旨未能忘救物”(《自叙》),又称“言论关时务,篇章见国风”(《秋日山中》),其诗篇再现了黄巢起义被镇压以后,藩镇混战年月里,人民痛苦生活的悲惨世界。《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再经胡城县》、《题所居村舍》、《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在当时便脍炙人口流传甚广。他本人也赢得了“壮言大语”能使“贪夫廉,邪臣正”的美誉,人们甚至希望他远绍陈子昂而成为“中兴诗宗”。虽然民间与文坛的舆论对他比较有利,但如果他不仅仅满足于外在的清誉而试图有所作为,他就要经过科举考试成为体制内的一员。尽管宣称“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但只是说说而已,不可当真,他和绝大多数士人一样,本质上是儒家,在拯救与逍遥之间选择的是前者。因此怀有济世胸怀的他一而再地参加科举考试,又一而再地失意于科场。
虽有诗卷却无处投呈,虽有文名却无人延誉,虽有诗名却屡试不第,杜荀鹤的心态便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其早年的诗篇展现出安贫乐道、质朴刚健的气质:“无人开口不言利,只我白头空爱吟”,“昼短夜长须强学,学成贫亦胜他贫”,这样的诗句与其说是作者的故作惊人之语,毋宁说是他精神上的自足和对未来的自信,虽不像盛唐气象那般极端自负,比起大历诗人的格调倒差不到哪里去。但接连的选场失利让他牢骚满腹,他甚至怀疑诗才与禄位二者之间是否彼此不兼容:“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岂能诗苦者,便是命羁人”;有时他又哀怜命运,感叹寒门士子的不幸:“空有篇章传海内,更无亲族在朝中”,“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读着读着似乎可感受到一股虫吟草间、郊寒岛瘦的味道了。
二
可以不厚道地设想一下:如果在仕途上邅迍蹉跎的杜荀鹤回首起曾经写过带有励志味道的《闲居书事》,会作何感想?在这首诗里,诗人曾如此信心满怀:“窗竹影摇书案上,野泉声入砚池中。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明惰寸功。”窗竹影摇,野泉滴砚,书斋生活何等诗意盎然,令人神往!在这里,作者将寒窗苦读作了诗意化和光彩化的处理,求取知识过程的艰辛与漫长被幻化成与自然冥合的精神娱乐,这里只有修竹、野泉,只有乐以忘忧令人神往的乌托邦美景,而与遗忘的反复搏斗、吟安一字的痛苦斟酌、卷帙浩瀚的典籍梳爬等令人望而生畏的修业过程却被有意无意地过滤与删除了。不过,在后两句诗里,作者还是露出了马脚,“少年辛苦终事成,莫向光阴惰寸功”,自然环境的优美只不过淡化了求学的艰辛与痛苦。“辛苦”是确实存在的,只是作者心里隐约包含着一项成本的计算,少年时代的辛苦会换来未来事业的成功,或如俗语所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孔子曾言,“吾十又五而志于学”,孔子志于学的目的今已不可考,但在杜荀鹤那里,其求学目的不可能是为了弘扬文化与学术,在传统读书人看来,文化与学术没有用,满腹经纶如果派不上用场,自己不能为人所用,就太可惜了。存有这份心理预设与心理期待,对于选拔制度上“承恩不在貌”这一实为逆淘汰操作手法的潜规则,他的反应才颇为失望,不那么心平气和。这样,人生便产生了一种根本性张力,这张力主要来自于价值层面,基于崎岖不平的人生经历的主体难免会有上当受骗大梦初醒的感觉,因此产生难以估量的心理落差。
一个读书人意图追求功名富贵本无可厚非,经世致用的思想源于儒家,孔子便是践行这种人生观的代表。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与子贡的对话中,他表达过待价而沽的愿望,他还因为受叛军首领的召唤、希望出山从政而与子路发生过不愉快,甚至还说过“如用我,其为东周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之类的大话。但,孔子的可贵之处在于,虽知富贵为人之所欲,可他不会违背人格与道义去求取,从而真正做到了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他还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固穷”。在他看来,贫困与漂泊实乃正直人士的别名,并不值得担忧与恐惧。
庄子则显示出更洒脱更通达的态度,一句话,叫超脱与去执。当暴发户曹商前来炫富夸耀,庄子只是冷语相嘲,你曹商不过干了些吮痈舐痔之类见不得人的事情而已。而当他的老朋友惠施出于嫉妒欲加害自己,他却主动上门,嘲讽惠施只不过是吃几只死老鼠的猫头鹰,而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的凤凰哪会看得上眼?庄子的眼光不仅停留在在价值层面,他的思考还穿越了存在层面,结论则相当悲观——无论价值层面还是存在层面,从未始有物的高度看都是虚无的,世人所汲汲追求的财富、地位、禄爵实际上了无意义。有了这般深邃思想的观照,庄子完全做到了“知其不可为而安之若命”,“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他总是以睿智的慧眼睥睨那些“智不知论极妙之言而自适一时之利”的人们。
回到杜荀鹤。他的“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的感情色彩可以用“怨而不怒”来定位,他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还算相当克制,尚不悖离温柔敦厚的诗学传统。他虽心存着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是弃妇般的哀怨与惆怅,似乎在呼唤移情别恋的丈夫回心转意,却不曾从根本上去反思造成自身悲剧的夫权社会。须知就连作为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典范的《诗经》,其《小雅·正月之四》也直接对作为人间秩序最终裁决者的“天”的不作为产生过质疑与不满:“民今方殆,视天梦梦。”可杜荀鹤没有,他显得身不由己与无可奈何。
杜荀鹤如果力图对天下苍生有所帮助对现实有所改变,他就不能做一个冷眼旁观的人,而是要力争进入仕途成为统治者的一员。于是道德上的乡愿便产生了。缺乏后台又想有所作为,诗人只好干起“为侵星起谒朱门”之类的事情。顾云在《唐风集序》中说杜荀鹤“左揽工部袂,右拍翰林肩”,虽出语刻薄但也活画出干谒者谄媚的奴态。干谒陈情难免要投其所好,真话实话自然不受欢迎,歌功颂德则可大行其道。有记载表明,四十多岁的杜荀鹤游大梁,献《时世行》十首于朱温,希望他省徭役,薄赋敛,但并不合朱温的心意。他旅寄僧寺之中得到朱温部下的指点,“稍削古风,即可进身”,这便成为他思想转变的关键契机。那个曾经温婉批评过“承恩不在貌”的不合理用人制度的诗人,最终无奈地背叛了自我与操守,在他四十五岁时,他写出《颂德诗》三十章取悦于朱温。朱温大喜,为他送名礼部,杜荀鹤因此得中大顺二年(891)第八名进士。天复三年(903)入梁,他又赋诗颂扬朱温,授翰林学士。
三
朱温如果是明君,杜荀鹤在后世所遭受的道德指责也许不会那么强烈,恰恰他不是个好主儿,生性残暴,时人称乳虎,他杀昭宗,立哀帝,又废哀帝自立。杜荀鹤向他陈情干谒,难道没想过史家会以“附逆”来将自己钉在耻辱柱上?
在试图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外,他内心深处其实还有超越庸常人生的别样价值向度。比如七律《赠彭蠡钓者》:“偏坐渔舟出苇林,苇花零落向秋深。只将波上鸥为侣,不把人间事系心。傍岸歌来风欲起,卷丝眠去月初沈。若教我似君闲放,赢得湖山到老吟。”再如《题德玄上人院》:“刳得心来忙处闲,闲中方寸阔于天。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磐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虽未似师被衲,此理同师悟了然。”在这样的诗篇里展现出深受佛道思想影响的闲适自在意趣,读者何尝见得到那个汲汲求取功名的焦虑不安的诗人?这里没有名缰利锁,只有看透世事的禅趣与淡定,我们实在不相信这些文字出自于矫情。这就展现出了其心理矛盾与人生的两难,正因为矛盾,杜荀鹤的人生轨迹才引人深思,一个以逸士为人生最高目标的诗人为什么走上了有损名节的不归路?翻看历史,其实读书人的分布呈橄榄型:斗士、烈士、壮志少得可怜,高士、逸士、隐士也数得清,绝大多数都和杜荀鹤一样,前后两端都靠不着,摇摇摆摆,首鼠两端。《鉴诫录》称杜荀鹤“壮志清名,中道而废”,语含无限惋惜之意。。
检视《唐风集》,杜荀鹤的形象很明显地自相矛盾、相互牴牾。在《自叙》诗里,杜将自己描述成“熟谙时事乐于贫”的睿智通脱之士,他“怕作乾坤窃禄人”而试图成为“白发吾唐一逸人”。另一方面,其干谒诗高达将近三十首,几乎占其诗集的十分之一。他在与狼共舞中也学会了狼性生存法则。其干谒之作“朱门只见朱门事,犹把孤寒问阿谁”、“多情御史应嗟见,未上青云白发新”、“应怜住山者,头白未登科”等诗句,哀求恳切之情溢于言表,语气神情几尽声泪俱下。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对他这种做派甚为不满:“杜荀鹤老而未第,求知己甚切。《投裴侍郎》云:‘只望至公将卷读,不求朝士致书论。《投李给事》云:‘相知不相荐,何以自谋身。《投所知》云:‘知己虽然切,春官未必私。宁教读书眼,不有看花期。《投崔尚书》云:‘闭户十年专笔砚,仰天无处认梯媒。如此等等,几于哀鸣也……则杜荀鹤之哀鸣,犹为可怜也。”这些诗作几乎完全抹杀了《春宫怨》所绽放的批判机锋与思想光芒。透过《春宫怨》与干谒诗的对比,可以看到一个以两副不同面貌出现的诗人:一个是勘破世态人情、意欲归隐山林的智者,另一个却是在权门之外摇尾乞怜的可卑寒儒。
也许是生前就承受来自士人圈子的舆论压力,杜荀鹤不得不在《江山与从弟话别》一诗中小心翼翼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干人不得已,非我欲为之。”就凭这句话,我不相信《旧五代史》把杜荀鹤说成小人得志,借朱温之势,将自己不喜欢的士人,“屈指怒数,将谋尽杀之”。他固然算不得君子,也不至于如此小肚鸡肠。他确实有隐忧:自己将以何种形象为史册所记载?宋初张齐贤已经开始大肆渲染他与朱温的传奇际遇了,《洛阳缙绅旧闻记》中的《梁太祖优待文士》,以漫画的手法将他见朱温的故事写得活灵活现,辛辣的讽刺加无情的调侃。当代散文家张宗子有一句话:“我宁可喜欢和佩服一个堂堂正正的坏蛋,也看不起一个猥琐的好人。”这话放在朱温与杜荀鹤的身上还真合适。
在写作《江山与从弟话别》时,杜荀鹤或许感受到杜甫“独耻事干谒”所包含的酸甜苦辣。假使我们无意用孔子与庄子的高度对他进行道德审判的话,那么更应思考的是:读书人坚守风骨的代价又是什么?朝廷怎么会变成一座中央监控式全景监狱?它又如何用缜密温柔的权力技术来控制和驯服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