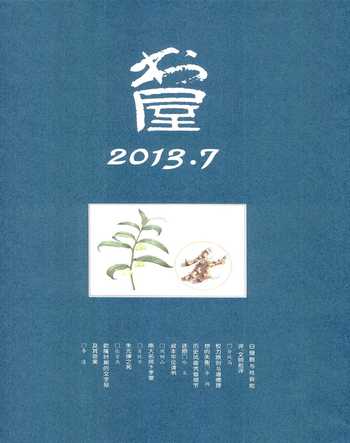白细胞与社会批评、文明批评
余凤高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热风·题记》
1925年4月28日,鲁迅在给景宋即许广平的信中感叹:“中国现今文坛的状况,实在不佳……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我之……起哄,大半也就为得想引出些新的这样的批评者来……继续撕去旧社会的假面。”
任何一个社会,在发展中总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毛病,需要给以清醒地指出,帮助社会克服这些毛病,继续健康地发展,向着更高阶段的文明前进。所以批评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可以说,没有批评,社会就无文明可言。鲁迅便是抱着揭出社会疾苦、引起疗救注意的态度创作小说和杂文,进行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为此,他甚至甘愿像“白血轮”攻击病菌那样,对时弊做不屈的以致忘我的斗争,即使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
鲁迅借用“白血轮”不惜自我牺牲地攻击病菌的特性来比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十分恰当,也十分生动。
“白血轮”,即如今通译的“白细胞”,发现这种细胞攻击病菌的特性,是医学史上一件有趣的事。
伊利亚·伊里奇·梅契尼科夫(1845—1916)生于乌克兰哈尔科夫附近一个小村子的犹太人家庭,父亲伊利亚·伊万诺维奇是警卫队的军官。
梅契尼科夫十七岁进哈尔科夫大学,以两年的时间完成四年的学业,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先是在北海德意志湾的黑尔戈兰研究海洋动物。然后去吉森大学、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科学院深造,获动物学博士学位。他于1867年回到俄国,在新创办的“新俄罗斯帝国大学”,即现今的“敖德萨大学”任讲师。后得到圣彼得堡大学的任命。1870年回敖德萨,得到一个动物学和比较解剖学的挂名教授。
梅契尼科夫对微生物特别是对人体所具有的免疫系统,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1882年,与敖德萨大学当局发生争吵辞职后,他带着在第一个妻子柳德米拉病逝之后于1875年结婚的奥尔迦·别罗科普托娃以及奥尔迦的一大群弟妹,去了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墨西拿。这里,科研条件虽然远不如敖德萨大学,他还是兴趣盎然地在他的起居室里建起他的私人实验室。在这里,他为穿越迷人的海面可以远眺蓝色的卡拉布里亚海岸而感到兴奋不已。
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梅契尼科夫就下决心将来要成为一名研究家。这个决心他始终不会忘记。此刻,尽管他常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但不时还要兴趣盎然地给奥尔加大讲生物学的理论。
梅契尼科夫是闲不住的。后来,他开始研究海星和海绵的消化系统了。很久以前,他已经窥探出这些动物的透明的体内有一些奇怪的细胞,它们是动物身体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又是自由自在的,会通过躯体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它们就是“游走细胞”,以流动的方式行动,像是变形虫一样。梅契尼科夫对自己发现这种细胞的过程做过详细的描述:
我正从促使我从大学辞职的那事件的震动中平静下来,而狂热地沉迷于深究那墨西拿海峡的壮丽的景色。
一天,全家都到马戏场去看几只演技非凡的猴子去了,我独个儿留下来。用显微镜观察一只透明的海星幼体里的游走细胞的活动情况。这时,一个新的想法蓦地闪过我的脑际,它使我觉得,类似的细胞可能会对机体防御入侵者有作用。我对这个玩意儿有异乎寻常的兴趣,感到十分兴奋,以致在房内大踏步地来回走动起来,甚至跑到海滨区清理清理我的思想。
我对自己说,如果我的推测不错,那么有一丝碎片落到一直没有血管和神经系统的海星幼体里,很快就会被游走细胞包围起来,好像一丝碎片刺入人的手指、不久就可以看到四面有脓那样。
我们的寓所旁有一个小花园,以前我们在这里曾用一棵小小的灌木为孩子们制作过“圣诞树”,我从那里摘来几枚玫瑰的刺,立刻把它刺进一只像水一样透明的美丽的海星的体内。
那天晚上我过于兴奋,无法入睡,只是期待我的实验的结果。第二天清早,我弄清楚了,事情完全成功。
后来梅契尼科夫果然看到:“在这小小的透明体里面,有一大群游走细胞聚集在被刺进去的(玫瑰刺的)周围……”
这一发现让梅契尼科夫兴奋无比,觉得自己就是一位病理学家了。他觉得,“用不着再要什么,他就肯定了自己已经有了对疾病的所有免疫的解释。当天下午他急忙出去,向正好也在墨西拿这个意大利港市的欧洲名教授们说明他的卓见。‘这就是动物经受得住微生物攻击的原因,他说,……连最有名的科学界教皇的教授(德国的鲁道夫·菲尔绍)也相信了!”
梅契尼科夫根据希腊文中意思是“吃或吞”的“phagein”这个词,给这种白细胞取名为“吞噬细胞”(phagocytes)。后来,他再次验证了这一吞噬作用:“他研究一只水蚤可能有的某种疾病”:“这种小动物同海星一样,浑身透明,他可以用透镜看到它们体内发生的事情。”
他观察水蚤的无目的的日常生活,而突然之间,他经透镜看到了有一只竟吞下一种恶性酵母的尖利如针的芽孢。这些针进了微细的食管,它们的尖头穿过水蚤的胃壁,滑入这个小动物的体内。然后……梅契尼科夫看见水蚤的游走细胞,就是它的吞噬细胞,流向这些有害的针,团团围住它们,溶解它们,消化它们……
……梅契尼科夫……深信它的理论是绝对而决定性的正确了……就写了一篇学术论文:“水蚤由于它的吞噬细胞而获得免疫,是自然免疫的一例……因为游走细胞倘不在酵母芽孢侵入体内时将其吞下,酵母就发芽……分泌毒素,这不仅迫使吞噬细胞后退,而且完全溶解它们,使它们死亡。”
梅契尼科夫因这一“吞噬作品”的发现,和德国细菌学家保罗·埃尔利希后来对人体自身的免疫作用的研究,两人分享1908年的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
白细胞在动物和人的血循环和组织中数以百万计,它们在机体组织内行使的功能,是吞噬异物和产生抗体,以帮助机体防御感染。当病菌等异物侵入人体时,对于机体由此而发生的变化,白细胞非常敏感:这时,病菌等异物对于血管腔中的白细胞呈现出一种化学吸引性,被称作“白细胞的趋向性”。于是,白细胞便聚集到血管壁上,一个个伸出丝状的突起,并渐渐构成“伪足”,穿过毛细血管壁。慢慢地,这“伪足”逐渐伸长且变得粗大了。大约几分钟后,白细胞便都脱离血管壁,游向感染部位;随后,它们将病菌包围起来,使病灶与周围组织隔开,将病菌或异物摄入自己体内。接着,白细胞的溶酶体系统合成多种水解酶物质,将被吞噬的物质分解,有时也会使组织连同侵入的病原体一起溶解,形成溃疡和脓肿……
在鲁迅之前,我国已有人注意到白细胞吞噬病菌这一生理知识了。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就曾经谈到白细胞吞噬病菌的作用。
鲁迅这样评价他的老师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太炎先生的学术成就十分辉煌。作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他所受的训练主要是传统的朴学,是著名的经学大师,一位成就卓著的中医文献学家。但他对当时欧洲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有深入的研究。
早在1899年,章太炎就在他写的论文《儒术真论》里,附了一篇题为《菌说》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章太炎说自己读了一册由一个叫礼敦根的人讲述的书《人与微生物争战论》,懂得了人的患病,往往都是由于微生物侵入的缘故。他引述德国细菌学家告格,也就是罗伯特·科赫发现“尾点微生物”和“土巴苦里尼”的例子,说明传染病是由相应的致病菌引起的。尾点微生物即科赫所称的“霍乱逗号”,也就是霍乱的致病菌霍乱杆菌;土巴苦里尼是tuberculin一词的音译,意思是“结核杆菌”,为结核病的致病菌。在《菌说》中,章太炎先生这样描述白细胞吞噬致病菌的过程:“动植皆有知,而人之胚珠血轮又有知。其胚珠时出游荡,他发小分支,如掌生指,常出收定质微点,以入胚珠之中,为其食物。如微生动物已种一病,则胚珠必收之。再种之,则有无数白色血轮,行至种病之处,围其微生物,或噬蚀以杀之。是则物能蛊人,而人之胚珠血轮又能蛊物……”
他对白细胞吞噬致病菌的机理,解释得大致正确,且形象生动。
章太炎先生写《儒术真论》和《菌説》是意在以近代的自然科学知识来解释自然现象,力图以唯物主义的原理来批判宗教有神论,批判封建的“儒术”。稍后,胡适在他影响极大的《易卜生主义》一文中也以白细胞对人身体作用的原理,来解释社会中新与旧的斗争。他写道:
……社会更加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年后或者须用泻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变”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人”来施行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包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诸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数量的白血轮时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便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绝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
斯铎曼,即易卜生1881年创作的社会问题剧《人民公敌》中的主人公,他发现浴场的水源被污染了,不顾包括他市长兄弟在内的恶势力的阻挠和暴力打击,绝不低头,坚决跟他们作不屈的斗争。
虽然鲁迅在1933年曾经借用苏俄批评家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列维佐夫对易卜生和英国剧作家萧伯纳所作的比较,说萧伯纳是一个“伟大的感叹号”,而易卜生则是一个“伟大的疑问号”,然后指出易卜生作品的局限性是在于,“虽然也揭发一点隐蔽,但并不加上结论”。但是在“五四”反封建的时期,鲁迅无疑觉得易卜生的态度是当时的时代所需要的,因而特别赏识和称道他。他称赞易卜生是一位“偶像破坏的大人物”,甚至称:“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并赞赏易卜生“大呼猛进,将碍脚的旧轨道不论整条或碎片,一扫而空”。1928年8月,鲁迅在谈到《新青年》的那一期《易卜生号》时还说,主要是“因为Ibsen(易卜生)敢于攻击社会,敢于独战多数”,所以当时大家要选出他,出版这一期专号来介绍是“确当的”。
当年的鲁迅和当年的胡适,对易卜生的看法是如此的一致,两人也同样以白细胞的功能来比喻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作用,可谓是文坛的一段佳话。
易卜生尖锐地揭露了腐朽社会的本质,并给近代戏剧开辟一个新纪元,有如鲁迅写作杂文攻击时弊,并创造出杂文的独特风格。只是到了后期,易卜生作品中的战斗精神有所减弱。而鲁迅,尽管长期病患在身,仍不停止工作,仍像白细胞吞噬病菌那样,不停止与恶势力的斗争。
细胞学和细菌学研究表明,白细胞或者吞噬细胞在吞噬病菌后,便将病菌和其他异物包含在围成一层膜的液泡内,直至它本身一一变质。在这段时间里,病菌中的毒素就不能危害白细胞,也不能为害机体。白细胞变质是由于它在吞噬病菌时遭受病菌毒素侵害而死亡,形成为稠厚、不透明的黄白色的液态物质,即鲁迅所说的“酿成疮疖”,也就是通常所称的“脓”。当想到这脓原来就是在与病菌英勇斗争中牺牲了的白细胞,人们不免怀有一种崇敬之心,因而在阅读十九世纪细菌学时代的一些文献时,不时会看到“Respectable pus”(可敬的脓)这样的词语,来表示对它的崇敬之意。
鲁迅把自己创作杂文比作白血轮——白细胞或吞噬细胞,意义深刻。吞噬细胞和病菌是一对你死我活的矛盾。鲁迅指出,在吞噬细胞的生命仍旧“存留”的时候,“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因为社会的“病菌”——时弊存在,才需要揭露这时弊的杂文;在时弊不再存在之后,也就不再需要有杂文来揭露了。八年之后,鲁迅在谈到讽刺的作用时,又再一次重申他的这一观点:因为“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因此,不需要杂文和讽刺的时代,也只有社会上时弊已经不再存在或者已经被消除的时代,那时,杂文将与时弊一同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