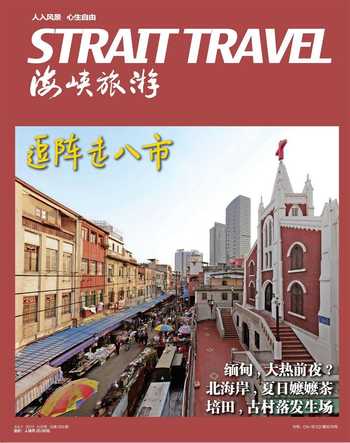培田的启发 我们需要怎样的乡村游?


如何让培田的旅游“精细”、丰富起来,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而且能够有助于村庄的长期发展? ,但这却是很多外来的观摩者都在私下讨论的话题。
培田在外来的知识分子面前,同时具有两重身份:一方面,它是个楷模,拥有让人仰视的文化传统,它的故事被知识分子们用来藉以改变公众关于乡村在城市面前,文化处于落后地位的想象。同时,它也是这些知识分子开展乡村建设的对象,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在村中设立了“培田客家社区大学”,以它为基地,在培田探索晏阳初提出的“平民教育”。
培田并不穷,没有突出的社会问题,甚至还拥有着优越的旅游资源,让人起初想问:“为什么要在这里做乡村建设?”但仔细看去,培田事实上也同样面对着无数中国村庄共同面对着的难题:城乡失衡造成年轻人流出乡村,村庄人口结构老龄化;村中原本的宗族权力瓦解,缺少替代性的机制去有效地组织公共生活;种地的收益差,土地被大面积抛荒,农业传统逐渐丢失;山林植被因缺少有效的管理机制而遭到破坏。
而旅游也还没有给培田带来真正的活力。村中没有从事旅游服务业的人家,就不能从旅游中获得直接收入,而只能间接地分享到政府下拨的并不丰厚的门票收入,用于集体祭祀等公共事务。而那些极少数返乡的年轻人,虽然正在积极尝试,但也缺乏足够好的创业机会和支持机制。培田对他们来说,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归属感的故乡,但还不是一个蕴藏着很多机会的地方。
这些,无疑是乡村建设可以开拓的空间,而旅游在其中无疑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培田当前的旅游体验还十分粗放——游客来此基本上就是看古民居、在农家乐吃饭住宿,尚缺乏了解村庄的传统和习俗的机会,也不会深入村庄周边的山林、河川、古道,这样就难以进入一座古村落的相对完整的生活世界。另一方面,培田除了建筑之外的文化传统,也还没有借助旅游而获得发扬光大的机会。代表培田艺术传统、由本村耆老组成的十番古乐团,因为已经有县城的乐团占据了在村中开展周末表演的舞台而失去演出机会,面临失传。同样在培田找到空间的外来文艺形式是盘鼓表演,培田客家社区大学从河南请来教练培训村民,但这种来自中原、风格雄壮的艺术形式,实在与本地的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格格不入,将这作为旅游表演,也只能让游客感到困惑。
如何让培田的旅游“精细”、丰富起来,创造更多的附加值,而且能够有助于村庄的长期发展?虽然没有正式议程来讨论这个话题,但这却是很多外来的观摩者都在私下讨论的话题。事实上,本次参加培田春耕节的多位台湾嘉宾带来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今年第二届培田春耕节的乡土影像展中放映的台湾纪录片导演柯金源的作品《退潮》,关注的是位于彰化县南部、临近浊水溪入海口的芳苑乡。这里濒临台湾最大的泥质滩涂,居民传统上以滩涂上进行的海水养殖为生。影片前半部用富有美感和力度的画面记录了讨海乡民在滩涂上劳作的场景。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退潮时,蚵农架着牛车在一望无际的滩涂上缓缓驶向大海,简直如同神话中的画面。事实上,这幅画面通过媒体报道和旅游观光,在台湾已经十分有名,成为彰化滩涂和沿岸社区耕海传统的象征,而且贡献于反对国光石化厂落户芳苑乡的运动。2008年,被民进党当局作为重大投资计划的国光石化厂选址在位于南彰化海滩的芳苑乡海滨,意味着这片台湾最大的泥质滩涂生态系统将付诸湮灭,沿岸世代以讨海为生的村庄也将被迫放弃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而依赖于工厂和城市获取营生。影片下半部记录了反国光运动中,大批的游客来到芳苑乡滩涂体验“海牛生态之旅”,滩涂和耕海之美,扩大了反国光的民意基础。在民众的强烈反对下,该计划在2011年4月被撤销。
来自台湾南投鹿谷乡内湖村的张伯志在海峡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作了题为“营造一个以萤火虫为主题的乡村社区”的演讲,介绍了他在“921大地震”之后,在家乡通过培育萤火虫来带动家乡旅游业发展并继而开展环境保护和社区营造的经验。内湖村在“921大地震”中受到重创,灾后重建需要有产业来带动。鹿谷乡海拔落差大,空气湿度高,动植物资源特别丰富,其中尤其是萤火虫,全台湾61种,这里有29种。萤火虫既美丽浪漫,又是优质环境的指标,证明本地环境质量的优越。张伯志看准了萤火虫潜在的观光价值,在村中着力野放复育,同时建立生态园区,开发环境教育课程,将“生态保育、生活历史、生计产业”纳入本社区的“社区总体营造”。社区总体营造的成果与萤火虫一起,吸引了大量游客,为灾后重建开拓了钱流,赢得了外界目光平等,而且满怀欣羡的关注。
这两个故事,都是社区调动出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深挖出本地寻常事物的美感和文化价值,对它们加以包装推广,而成为一种独特的旅游资源。这种旅游资源的特点是具有生态和文化内涵,让游客在体验到它们的时候,就学会去珍视它们,想要保护它们。
对接游客和旅游目的地社区,推广生态和文化旅游,正是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嘉宾高茹萍即将启动的事业。之前身为台湾“社区大学促进会”主任的她,刚刚创办了一家叫做“恩吉欧”的社会企业(指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公益目标的企业),计划通过策划学习型的生态旅游来增进公众的环境和文化保护意识,同时为观光目的地社区创造收入。她的这个创想直接来自于她在之前担任“社区大学促进会”主任期间参与“低碳·旅游·生活——社区大学低碳旅游体验学习”活动所获得的经验——通过在位于二十余个社区的社区大学之间进行“串联”式考察,来相互学习如何将各自的生态和人文旅游资源展示给游客。其中包括原住民文化体验、生态农业观摩、传统饮食文化探索、湿地探访、历史街区寻访、眷村文化巡礼,还有真正带有尖锐议题的地区,比如“核四”(第四核电站)拟建地新北贡寮海滨的参观,每一种都试图充分展现一个自然和人文兼备的、完整的本土生活世界。
春耕节期间,正值湖南古城凤凰因为官家设卡收费,造成全城居民不满。这只是主题公园式的旅游开发思维的一个极端表现——社区变成主题公园,正常的生活屈从于旅游。更常见的表现是:一个社区的自然和人文为了满足游客的喜好,迎合游客的想象而被改造;环境失去其固有的风貌,习俗也开始具有虚假的表演性,面向游客的表演也与社会生活脱节。而游客往往是坐着大巴团进团出、走马观花,对所观光的社区缺乏基本的了解不说,有时甚至还对他们构成骚扰。这些也是台湾旅游业至今仍然存在的问题。高茹萍的生态旅游社会企业就是希望成为游客和旅游目的地社区之间的一个纽带,一方面在旅游内容策划中凸显出地方生态和文化特点,另一方面,对游客开展必要的行前教育,让他们懂得尊重即将造访的社区,并且获得一双能够看懂社区的妙处的“慧眼”,改变游客和目的地社区两端相互隔膜的“团进团出”状态的旅游现状,而使两边交上朋友。游客放缓的脚步和更加仔细的端详、更强烈的好奇心,也意味着他们在社区中更长时间的停留和更多的消费。
高茹萍的计划的可行性,部分缘于遍布台湾的社区大学系统已经在开展“社区总体营建”的过程中保护和开发了当地的生态和人文资源,为开展这种学习型生态旅游项目创造了条件。
由于培田春耕节的一位东道主是培田客家社区大学,“社区大学”在本次春耕节和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上,一直是一个被反复探讨的话题。
美浓爱乡协进会理事钟永丰在自己的演讲《全球化下的台湾三农运动》中,介绍了台湾的社区大学成立的脉络:上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在几十年的追求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目标的“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的年轻人都已经走空,乡村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与此同时,肇端于上世纪70年代末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在后来的校园民歌、新民谣、社区剧场和新电影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文化运动中传递下来的对乡村命运的关注作为一个因素,而80年代以来因为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加,年轻人的返乡运动的到来作为另一个因素,使得政府和民间都认识到:需要建立能够帮助返乡者认知本乡本土,并且获得生存技能的,立足乡村社区的教育。
1994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推行“社区总体营造”政策,以寻求培养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建立社区文化、凝聚社区共识,培养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在这一政策背景下,乡村教育的需求与当时追求全体民众的终身教育的社区大学运动汇流,在2001年,出现了台湾最早的乡村型社区大学(早先的社区大学都位于城市,第一所社区大学于1997年成立于台北市文山区),并且越来越多,逐渐成为了台湾乡村建设(或者叫“乡村社区总体营造”)的主力。到了本世纪的头十年,台湾加入WTO之后,其农业又开始面临挤压和萎缩,农业的消亡不仅意味着农民生计的改变,也意味着农村生活方式的改变,这又为社区大学的社区营建提出了新的任务。
高雄师范大学助理教授洪馨兰在她演讲的开头说道:“台湾的教育用了半世纪教人们怎么离开乡村,却从来没有教人们怎么回家。人们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所以社区大学花了很大的精力,通过在乡村兴学,让这个‘家成为人们可以回去的地方。”社区大学都以本乡人为运营主体,作为一个资源平台来接驳来自城乡各行各业有特长之人作为师资,通过深入观察、研究所立足的乡村,来构建关于本乡本土的一整套知识体系,洪馨兰称之为具有高度的应用性,而非理论性的“农村地方学”。用她所研究的位于高雄市美浓区的旗美社大的经验之谈来说,就是“所有发生在农村的人事物,都是农村型社大要积极面对的议题,都是农村课程。”而所有这些课程,都是为了实现“建立农村意识”的目标——使农村社区能够为了把握自己的命运,而去探索和思考。
台湾的社区大学所追求的,不是外来知识分子对乡村社区开展“手把手”式的“平民教育”(这个概念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农村社会气若游丝的历史语境下产生,所以捆绑了浓重的以晏阳初为楷模的知识分子通过教育来“拯救”农民的意象),而是创造平台、输送资源,让乡村能够自我发现,自我教育,并最终能够用本土的生态和文化资源,通过旅游等媒介,去教育城里人。
所以,对培田深厚的“兴养立教”传统的取用,不应该仅仅是用它来提醒公众:相比往昔,如今中国农村的学校教育已经彻底没落,也不应仅仅是唤起公众对乡村文明的美好想象,它更应该是创造出一个能真正为村庄社区所拥有的,类似台湾的社区大学那样的机制,使他们能够以主人翁的姿态来整理和创造关于家乡的一整套知识,以它为基础,去营造富有魅力的家乡。
如果以福建为视野,去探讨此地乡村旅游的未来,我们会发现:福建不仅是一个乡村地域十分广袤的省份,而且其乡村普遍拥有美丽的景观和良好的生态状况。闽地乡村的文化积淀也十分深厚,而且具有很大的多元性。同时,福建受到宗族文化强烈影响的村庄,普遍具有很强的内部组织协调能力。在这些条件之下,福建乡村十分适合开展以乡村社区营造为基础,以乡村生态和文化传统为吸引力的学习型旅游。这将有助于福建乡村在保持本身的生态和文化的前提下获得发展,使之既不必为了求得经济发展而被城市化和工业化抹杀,也不必为了发展旅游而沦为失去自我的“主题公园”。
1.乡建分子的关注与介入,使得培田成为一个发生场,一个表象就是村里到处是大红色的通知公告,邀请村民参与各种“乡建活动”。2/3/4.旅游还没有给培田带来真正的活力,但是培田人和外来人都有所努力,譬如,十番乐队还在坚持木偶戏表演,当地人尝试做手工纪念品,乡建分子则组织农具展等活动,吸引外来客流。
春耕节草记
培田的春耕节今年是第二届,同时启动的还有首届海峡乡村文明发展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温铁军等知名三农专家,以及来自海峡两岸的30多名学者,齐聚培田,讨论乡村建设、乡村教育、乡村文化艺术以及生态保育、有机种植等乡村经济问题。配套的乡土影像展,则邀约大陆、台湾独立电影人,展映乡土题材影片,介入“乡村建设”。
来自海峡两岸的影片,如毛晨雨的《稻电影》,邓伯超的《余光之下》,鬼叔中的《砻谷记》,以及台湾颜兰权、庄益增的《无米乐》和培田村民吴来星导演的《培田土改记》,试图给予或展示一种乡村“发声渠道”。
1.从北京到培田来支教的女老师和村里的孩子,她在这里教英文。2.来自两岸的学者在观看影像展作品。
导演的培田
邓伯超:纪录片导演,作品有《余光之下》等。在培田过了两个年,跟踪拍摄曹林凤一家半年多,目前正在创作与培田相关的纪录片。
邓伯超是四川人。他和朋友邓世杰,原本想做一个以广东梅县为基点、与客家相关的纪录片。前期调研时,在梅县遇到诸多问题,便继续边走边记录。后在福建永定,遇见一个专门赶庙会的“神人”,那人手上有张地图,标注了各地方各种庙会的日期,其中提到了连城一带的河源十三坊。河源十三坊的共性之一,是入公太习俗,于是,邓伯超到了连城,到了培田。
在培田拍摄的这部片子还在剪接,计划定名为《浪漫的国度》,他说,“是反讽。”
邓伯超对他所拍摄片子的定义是:在客家地区拍摄的与风土人情有关的片子。他很喜欢培田,他住的地方,隔一条河就是山,他说这里有“生猛的生活”。村里人对他的印象是,骑着摩托车,肩上扛着摄像机,在田埂上呼呼狂奔,“好厉害”。
入公太、十番乐队、曹林凤、吴晓霞的母亲……所有培田人事,都是邓伯超的记录要素。曹林凤说,干儿子邓伯超拍纪录片好认真,认真到她养蜂的技术,都被他学走了。
关于乡村,邓伯超有一些自己的论述。他说,农村往往有一种区别于行政村的村族联盟,譬如河源十三坊,乡村的祖宗崇拜和土地信仰,能凝聚力量,把“凝固的东西去掉后,可以看到其中的人性之光”。
清明计划
鬼叔中、孔德林、杨韬:三个福建三明宁化人,一位纪录片导演,一位画家,一位先锋设计师。
《清明計畫·畬忘錄》是鬼叔中、孔德林、杨韬目前正在进行的一件事情。其内容,是关注乡村、传统、民艺。他们这次也到培田,参观、交流,也许,找点灵感。
画家孔德林和设计师杨韬已常住厦门,导演鬼叔中则依旧待在宁化,并用镜头记录了宁化当地众多传统民艺的流程和民风民俗。去年清明节期间,三人在宁化鬼叔中家中想出了“清明計畫”的点子,说是“不想再做局外人”。于是,鬼叔中用纪录片的形式记录工艺、传统的流程,孔德林则更为随意地做一些绘画创作,杨韬则希望,把鬼叔中镜头下的那些好东西,最终通过设计,使之功能发生变化,与现代生活产生关联。
“清明計畫”目前呈现的“作业”是在宁化一个废弃兵工厂开设的实验展。孔德林在墙面上作画,在传统物件上种植青苔,鬼叔中的纪录片在荒凉的兵工厂放映,杨韬的设计,体现在展览的摆设,还有一些物品的设计上。譬如,他将鬼叔中片中所述宁化玉扣纸,作为包装元素,用来包装一些食物,或普洱茶。他甚至创立了自己的品牌“涩品”,在“清明計畫”中,他们发现了当地少有的几株茶树,其茶味很酸,于是,小众的“寒谷酸茶”变成了“涩品”的第一款产品。在杨韬看来,很多传统的老物件、老民艺,“完全可以和当下结合”,一旦结合到位,这些传统民艺的价值,“或许就会苏醒”。
他们也希望,“清明計畫”并不是三个人的,而是每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