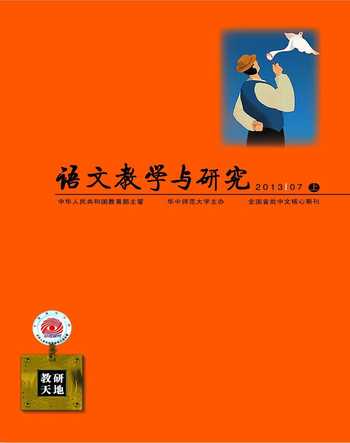一言难尽的现实
苏童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文坛非常活跃的作家,《妻妾成群》《红粉》《米》等小说被改编成影视作品后声名大振,苏童因而成为普通读者心中描写女性的高手。《在中日韩三国作家论坛上的演讲》是苏童2008年5月在韩国首尔作的一场演讲,以非常感性的语言阐发了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在传统的文学反映论看来,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作家通过创作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把握,读者通过阅读作品获取对现实的认识,文学反映论特别注重文学作品的反映现实与认识教育功能,相对忽视了作家的主观创造。而现代派文学观则视“现实”为可以任意缀合缝补的碎片,是非逻辑、非因果的混沌存在,所谓的“现实”只能通过“叙述”、“虚构”来把握,这就从根本上质疑文学反映现实世界的可能性,走向文学反映论相反的极端。苏童以一个作家的创作实践与敏感体悟取两者所长弃其所短,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并道出现实的复杂与一言难尽。
苏童以自己上庐山的经历开篇,援引苏轼《题西林壁》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说明现实的难以描摹:“我们在山中,看不见山的真面目。我们每天都在遭遇日常生活,但我们究竟在哪里遭遇那个现实呢?”接下来苏童为读者呈现3种不同的“文学现实”:
第一种是“基于不同立场的现实”,苏童以法国大革命在雨果和福楼拜笔下不同的表现为例说明同一个时代、同一种题材不同作家会有截然不同的表现,“有人唱赞歌,有人唱挽歌”,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由此我想到有关20世纪中叶历史巨变的不同叙述:对于一些人这是一个高歌“我今真解放”的时代,对于另一些人却是面临痛苦抉择甚至是生离死别的时代。同样是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既可以写成《红旗谱》,又可以写成《白鹿原》。而苏童的《妻妾成群》则无疑颠覆了“五四”以来对于“新女性”和“大家族”的启蒙性想象: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非但没有像《伤逝》中的子君、《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那样走出家庭追求幸福,反而飞蛾扑火加入大家族妻妾争斗的行列。
第二种是“舍近求远的现实”,“大量的作家们一生都在做舍近求远的事情,除了自传必须拿自己开刀,他们一生都忙于南水北调,北水南调,偏偏绕过了自己的生活”,接着以“跳出水池的鱼”作比。也就是说,作家不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经历的事情,作品不一定是作家的自叙传,作家要有向遥远的、未知的远方探险的野心,文学要有一种“鲁莽和冒险的精神”。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写自己未经的、不熟悉的题材更能考验一个作家的想象力。此外,我觉得“追求舍近求远的现实”还表达了作家的一种超脱的情怀,他不计较自己的得失悲欢,不为自己所处的环境所限,能够追求一种遥远的、阔达的境界,所谓俯察万物,仰望星空,都可以统摄笔下,体现出作家的一种高远追求。
第三种是“扭曲变形的现实”,也就是一种打破日常生活秩序与逻辑的“现实”,苏童以卡夫卡《城堡》《变形记》,托马斯·曼《磨山》,卡彭铁尔《种子的旅行》,爱伦·坡《玛丽罗杰的秘密》等作品为例阐述这种“文学现实”。这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变形记》,人变成虫的情节当然是不现实的,但它却最深刻地寄寓了人在哲理意义上的生存状态。作家并不是让读者接受人变成虫的客观事实,而是去领会这种荒诞情节里的更深层次上的现实——人的扭曲、异化,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及其造成的孤独、绝望。类似的还有《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聊斋志异》中的花妖狐媚等都在揭示一种更深刻的现实,或者如苏童所说可以当作“预言”或“寓言”的“最好的现实”。
这篇演讲的正题为“我们在哪里遭遇现实”,更准确地说,它重在辨析“文学现实”与“日常现实”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联系人人熟知,即“文学源于生活”,区别则见仁见智,远非一句“文学高于生活”所能概括尽。苏童在这里举出“基于不同立场的现实”、“舍近求远的现实”、“扭曲变形的现实”来说明文学反映现实的不同情况,让读者对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文学与现实关系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创作实践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文学理论问题,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得清楚,文学理论家可以就此问题发表许多高论、宏论,甚至可以写成专著。但这些理论著作只能供同道研讨切磋,很难为普通读者理解。而苏童的这篇演讲朴实无华,通俗易懂,没有高深的理论和眩人的技巧,而是结合自己的体会与具体作品娓娓而谈,能让读者很好地理解与信服。
张文民,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责任编校:郑利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