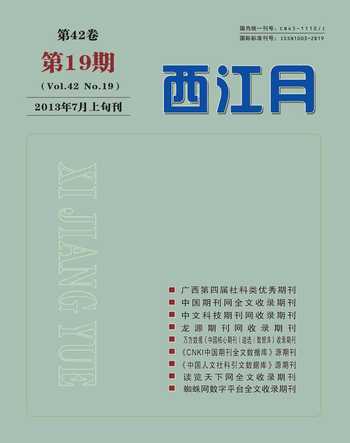析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摘 要】由于全球范围内环境问题的突出,人类环保意识亦日益增强,但保护环境的一些政策、法规和手段难免会削弱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同时,国家对其自然资源的排他管辖权又会制约对环境的保护。因此,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问题急需有效处理。
【关键词】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环保意识
引 言
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已从区域性转变为全球性、从暂时性转变为长远性、从潜在性转变为公开性,以至于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切实解决这一问题。因此,环境保护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而由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它对现代国际法提出了新的挑战;对传统国际法原则尤其是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影响特别突出。
一、环境问题的突出与环保意识的增强
何谓“环境”?根据我国环保法规定:“环境主要是指人类生产与活动所牵涉的所有天然的及人工的因素集合,其中有水分、大气……天然遗迹、乡村城市等”。i而环境问题则产生于“大自然本身的变异和人为因素引发的环境损害及其质变”。[1]一旦生态系统的平衡和承载极限被打破,就会导致其急剧退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代工业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人类对资源无限制地索取都一再挑战生态系统的承载极限,加之环境本身所具有的流动性使得环境问题延伸至世界各地,最终引发了全球环境危机。而且,环境问题还在继续恶化,例如沙化侵蚀着越来越多的沃土,海洋、空气和水体污染正继续剥夺人类的美好生活;此外,温室效应还是导致厄尔尼诺、拉尼娜等灾害性现象频发的主要祸首。
然而,对环境进行保护直到上世纪60年代才兴起。1962年,来自美国的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呼吁人们重新仔细对待环境问题,并对环境危机加以警醒。[2]十年后,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全球环境保护的开端,会议诞生的《人类环境宣言》对“环境保护”进行了定义,同时制定了环保的全球战略。1987年,“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出现在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作品“Our Common Future”中,ii意味着人类环保意识又上升了一个高度。90年代后,环境保护发展为当今世界的三大主题之一,而《21世纪议程》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的通过更具有划时代意义,其中贯穿着“可持续发展”的主要观念。随后,世界各国相继以该文件为蓝本,制定符合各自国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规划。
二、环境保护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影响
(一)可持续发展战略弱化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早在1962年,联大就通过了题为“经济发展和自然保护”的决议,并首次提出了不应浪费自然资源的目标。十年后,《人类环境宣言》则指出:要周详地计划保护地球自然资源的工作,以便为这一代和下一代谋福利。此后,《地球宪章》和《21世纪议程》都敦促国际可持续发展法的深入发展。《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国际可持续发展法将更加关注‘环境与发展的平衡,要求各有关国家采取有效措施评估、检查过去的行为和现存的国际文件及相关制度,同时要未雨绸缪,优先考虑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可能性立法”。[3]鉴于对发展与环保的并重,自然资源永久主权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在环境和发展领域,联大通过了一系列有关自然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决议,例如,1982年产生的《世界自然宪章》不仅要求“不准浪费自然资源”,还对其利用规则进行了细化:“利用生物资源,不可超过其再生力;采取措施防止一切形式的土壤退化,并保持或提升其生产率;对使用后零消耗型资源应将其循环利用;对使用后不可再生的消耗型资源,应综合考虑进行保护性开发。”iii
就全球性国际公约而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台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指出:各国对本国领土范围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明确、保全及传于后代负有主要责任和义务;任何致使其他缔约国领土内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受损的行为都是禁止的。至于区域性国际公约,如《养护自然和自然资源非洲公约》、《西半球自然和野生物保护公约》、《欧共体关于保护自然生境和野生动植物种的指令》等,这些都为该区域的生物资源保护提供了国际法律框架。[4]
总而言之,国际法的发展已证明,各国有义务保护其自然资源和财富,以确保为世界各国人民及下一代的利益而能持续地利用自然资源;各国还有义务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植物、各类濒危物种的生境,从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因此,根据现代国际法,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不再是一国专属的国内管辖权。
(二)保护人类共同利益高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
国际环境法的迅速发展对国际法上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原可以说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随着对自然资源的本身价值及其开发对环境影响的认识,各国开始放弃传统手段而采用一种新的结合生态系统的开发资源方法。这种方法是认识到全球环境问题严峻性和“环境利用空间”有限性后的升华,其结果就是限制各国对自然资源和财富的管辖,并要求其承担一定义务。另一方面,就目前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来看,虽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得到了进一步重申,但有关自然资源和环境保护的义务也备受凸显,例如在《人类环境宣言》和《世界自然宪章》等国际软法中都强调了此点;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的开放签署也必将对自然资源永久主权这一原则产生深远影响。例如,《生物多样性公约》在重申一国国内的生物资源属于该国主权范围的同时也强调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问题。[5]此外,在国际贸易领域,对外贸易管理制度指出:“一国可基于社会公共利益或道德、国家的安全,……保护环境或稀有自然资源而采取相应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出口。”iv可见,一国管理其自然资源对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性。
综上,社会的整体利益、人类的共同利益在国际层面的法律文件中愈发受到关注。鉴于此,各国有义务站在宏观角度上合理行使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主权。
三、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对环境保护的制约
(一)主权国家有权自由处置、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
1960年联大通过了关于自主管理国家自然资源和财富的第1515号决议,并要求各国承认和尊重主权国家这一不可剥夺的权利。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也重申“各国有权自主自由地处理其自然资源”。此外,1952年国际法院以其无管辖权驳回了英伊石油公司通过英国政府对伊朗石油国有化提起的诉讼,1977年利比亚美国石油公司仲裁案中适用了利比亚国内法和一般法律原则,[6]这些都表明国际司法机构已认可“自由处置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对于自由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其被普遍认为是由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引申而来的核心权利之一,联大的第626号、1803号、以及3171号决议都提到了这一权利。不仅如此,一些国际条约、仲裁决议及国际法学家著作都无一例外地承认各国有自由地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权利。例如,1978年《亚马逊流域合作条约》中指出:“缔约国在各自领土范围内享有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固有权利。”另外,1982年科威特石油国有化仲裁案的裁决也显示:“科政府决定终止美国独立石油公司勘探和开发石油与天然气的特许协议的行为是合法的,鉴于其需要全盘接手管理石油资源的所有权并处置之。” [7]
(二)主权国家有权按国家环境政策、为民族发展而利用和管理自然资源
暨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和国家环境保护责任间的平衡便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议话题。(下转第143页)
(上接第141页)不可否认,为其民族发展而制定环境政策的权利,是每个主权国家都享有的。《人类环境宣言》就率先规定:“各国在《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原则的指导下,可按自己的环境政策来开发资源……”随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也作出类似规定:“各国可按其环境方面的政策,并以其维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责任来开发自然资源。”而90年代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则进一步明确了“主权国家有为追求自己的发展政策而开发其资源的权利”。此外,其他一些区域性和多边性国际公约也都提到了此项权利,如1985年《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协定》和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综上可见,各个国家为其民族发展、按其环境政策开发利用和管理处置自然资源的权利,无疑是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
四、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协调
(一)《人类环境宣言》在理论上的协调作用
《人类环境宣言》不仅认可了“各国享有按照自己的环境政策开辟其资源的权利”,同时还指出“各国对它们管辖或控制之内的环境损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上述旨在协调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的创造性规定,可以说对国际环境法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它不仅确认了各国对其自然资源及财富的永久主权权利,而且还要求他们在保护环境这一人类集体利益的基础上,承担起维护生态环境的责任与义务。所以,国际环境法不但要明确各国的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及对这一权利的相互尊重,而且还要协调各国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与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关系。[8]
(二)公众环境意识与生态舆论在实践中的协调作用
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政府对环保的态度,促使各国政府放远眼光、高瞻远瞩,走环保与发展共赢的可持续之路。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崭新的发展观可以说为世界各国的繁荣发展指明了道路。首先,它强调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融合;其次,强调在人们经济活动中应注重环境资源的价值;再次它要求发展过程中不能忽略后代的利益。[9]由此可见,可持续发展观在更高层次上使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得到统一。
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生态舆论也促成了许多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出台。“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生态文化安全”等舆论都促使各国当局更加注重环境保护,继而主动对本国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作出部分限制,并积极参加各类国际环境大会,签订有关环境保护的多边性或区域性条约,加速相关决议、宣言和协定的诞生。其中,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举办,以及《人类环境宣言》和《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的产生,都是鲜明例证。
总之,不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法律文件的相关规定,都体现了国际社会在保护人类环境方面所形成的协调一致,对国家自然资源永久主权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环境保护与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在这些国际法律文件所确立的各项原则、规则和内容的基础上得到了统一。
注释:
i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一章第二条。而《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指出:“环境不仅包括周围的事物,还囊括作用于一个有机组织或一个生态共同体并最终决定其形式和生存的气候、土壤和生物因素等”。参见【美】熊玠:《无政府状态与世界秩序》,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7页。
ii 参见“Our Common Future, From One Earth To One World”,The Global Challenge--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ii 参见1982年10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自然宪章》“功能”部分。
iv 参见《对外贸易法》第16条。
【参考文献】
[1][9]王秀霞.论生态环境的国际法保护[D].中国海洋大学,2008:7,25.
[2]韩健,陈立虎.国际环境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36.
[3][4]杨泽伟.主权论—国际法上的主权问题及其发展趋势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5,108.
[5]王曦.国际环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39.
[6]衣淑玲.论国际投资法中的国家责任问题[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3(8):58.
[7]张广东.国际投资领域中的国有化及其补偿的法律问题[J].河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学报,2007(2):77.
[8]李耀芳.国际环境法缘起[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2:145.
作者简介:丁燕(1989.03—),女,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2011级国际法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公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