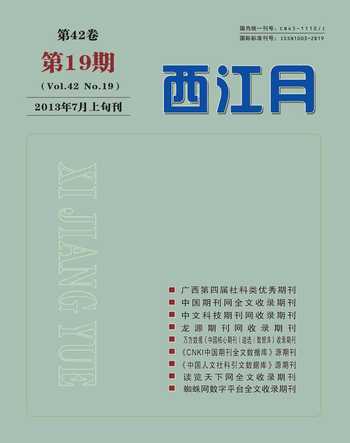从宋代咏梅诗词中探析梅与古代文人的关系
【摘 要】梅是宋代咏物诗词中的重要题材,众多文人都以梅为媒介抒发审美情感、寄托人格理想。宋代文人中,林逋、陆游和姜夔都被认为是爱梅之人,且有不少出色的咏梅作品,本文将以这三位文人的咏梅诗词为例,结合他们各自的身份背景和人生遭遇,分析他们赋予梅这一意象的丰富意蕴,并讨论在创作这些诗歌时,这些诗人、词人在自身这一主体和梅花这一客体之间建立的多样的联系,及其对梅所寄托的情怀,从而试着探析梅与古代文人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宋诗宋词;梅;文人;关系
梅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的审美意象,自六朝以来就有不少咏梅之作,到了宋朝,咏梅文学更是极其繁荣,主要以诗和词这两种文学体裁为主。《全宋诗》收诗约25万4千多首,梅花题材之作(含题梅花绘画作品的诗歌)近5千首,约占1.86%,《全宋词》收词2万多首,其中咏物词近3000首,在咏物词中咏花词2208首,其中咏梅词达1041首,咏梅词占咏物词总量的34.73%,占咏花词总量的47.15%。①另外,有学者作过统计,现存宋代咏梅诗词是宋以前咏梅总数的50倍,在同期诗词存量中所占比重也是宋以前的额12倍。②梅花题材在宋朝诗词创作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梅花字字香前集》中提及咏梅文学的发展情况:“《离骚》遍擷香草,独不及梅。六代及唐,渐有赋咏,而偶然寄意,视之亦与诸花等。自北宋林逋诸人递相吟诵、‘暗香疏影、‘半树横枝之句,作者始别立品题。南宋以来,遂以咏梅为诗家一大公案……”宋代以前,对于梅花的审美大多停留在花色、花香、习性等梅的自身特征,咏梅也多以客观描绘为主,只是“偶然寄意”,而自北宋初期林逋的咏梅诗作后,文人们提升了对于梅的审美认识,将自己的主体意识渗透到对于梅的审美中,赋予梅花以品格意趣,道德情操和气节志向,使它具有更丰富的象征意义。
在两宋诸多的爱梅文人中,林逋,陆游和姜夔名声不菲,他们创作咏梅诗,赋予梅花鲜明而独特的形象,这些形象往往跟文人自己的品性和追求都有密切的联系,梅花这一客体上,实则承载了他们自己的人格或是对于生活、理想的感知和憧憬。这些诗人词人借助梅花的客观之象,融入主观之情,使得他们笔下的梅花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从他们的咏梅诗词中,我们可以捕捉到梅与古代文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一、林逋:梅与隐士
林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隐士,他性格恬淡、不趋名利,一生过的都是隐逸生活,没有妻子儿女,只和梅花、仙鹤作伴,后人称其“梅妻鹤子”。林逋喜爱梅花,共创作八首咏梅诗,被称为“孤山八梅”,另有一首咏梅词《霜天晓角》。赏梅,咏梅是他孤寂的隐逸生活里的雅趣,在他的咏梅诗词中,处处体现着他作为处士的审美取向和心性意趣,所以他笔下梅花的神韵,往往有着鲜明的隐士的人格烙印。
林逋咏梅作品中最负盛名的应是《山园小梅》:“众芳摇落独喧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其中又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一联最脍炙人口,被认为是咏梅文学中的绝唱,司马光《翁公续诗话》载林逋处士“有诗名,人称其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曲尽梅之体态。”③文人写梅花向来都突出它的幽香和冷艳特质,而林逋是第一个着力描写梅枝的,开创了对于梅的审美认识的新视点,而这对梅的品格的阐释也至关重要,程杰先生对此有过分析:“与一般春花时艳优于花色花容不同,梅之‘疏影横斜是一种特殊的视觉形象,它以线条造型为主,又以舒爽(状态)、直劲(力度)为特征,具有独特的审美效果,是一种极有意味的形式。正由于‘疏影横斜的凸显,梅花开始展示出萧疏简淡的幽姿形象,洋溢着疏淡幽雅、清瘦峭劲的意味风神,成了士人娴静雅逸意趣的具体体现。”④此外,林逋还用水和月的柔和、空灵的意象来陪衬梅的“疏影横斜”和“暗香”,又有夜的幽静闲适氛围的烘托,使得整个情境都充满淡雅、静谧和高洁的意味。诗人则言:“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只与梅低吟浅唱,相知相伴,隐居湖山之中,不许世俗之物亵渎。当林逋在赏梅时,眼前的梅已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关照对象,更是其人格理想和精神意趣的寄托,他写梅幽逸之品,是寄托了自己超越俗流的精神追求和闲逸孤傲的人生态度,他歌咏梅花时,总将隐士对于高雅幽独、闲静淡泊的品格的追求通过梅这一意象表现出来,这些品格不是梅形象本身的客观特征,而是林逋这个江南隐士渗透进去的人格情趣。
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里谈到“物我”的关系:“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心外,可对而观赏;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⑤我认为林逋与梅之间的关系也正是这种“相未泯,情已契”的关系,是“梅我相融”的关系。诗中梅的形象是诗人作为隐者的眼中梅,心中梅,它深深融入了诗人自我人格追求的期许和信念。
二、陆游:梅与爱国志士
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对梅花极其钟爱,创作了大量的咏梅诗词,他笔下的梅被赋予了爱国志士忠贞不渝的品格情操,傲雪斗霜的梅俨然成了他的化身。
在他的咏梅词中,《卜算子》最为突出:“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在这首词中,几乎没有对梅的香味体态作任何的描写,而是着重强调梅所处的凄凉、昏暗、风雨交加的环境,梅花的处境实为作者自己的政治遭遇,“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妬”则暗指朝廷中主和派对自己的排挤和打压,最后一句写梅花化尘犹香则是象征自己坚贞不屈的孤高与劲节。整首词看似咏梅,实为借梅写己,所塑造的梅花形象是他自己身世的缩影和高洁品格的化身。在陆游大量的咏梅诗中,也多是借梅言志。如《落梅》:“雪虐风号愈凛然,花中气节最高坚。过时自会飘零去,耻向东君更乞怜。”写出梅花虽然饱受风雪折磨,但仍然誓不低头,在逆境中保持高坚气节,这与陆游的遭遇十分契合,他一生志在恢复中原却壮志难酬,处境险恶却仍然坚持独立的品格。
陆游咏梅,很少细致描写梅的幽香和“疏影横斜”的体态等特征,往往突出强调梅所处的严寒环境以及梅耐寒,傲雪盛开的特质,陆游因自己的身世遭遇在梅的意象上找到了共鸣,所以他咏梅总是极力歌颂梅的不畏严寒,孤傲自洁,坚贞不屈的精神,他写梅总是遗貌取神,实际上,诗词中的梅的客体早已被“我”的主体所取代。程杰先生分析南宋时期文人对梅的品格美的深化时说:“北宋时期对梅花的审美认识虽然受到了主观意趣和人格意志的作用与渗透,但总体上仍然紧扣梅花的自然形象,所谓品格美也侧重在自然形象独具的风姿神韵。而进入南宋,梅花描写越来越受制于主体情趣的作用,服从于意趣表达的需要,梅花形象越来越被视为精神境界的象征,道德品节意义得到了充分的揭示和阐发,梅花的许多方面都被明确地理解为气节德性的体现,整个形象几乎构成一个德行纯全、至高无上的人格境界。”④所以,对比林逋梅“我”两相融的关系,陆游虽看似在写梅,实则在写自我,是借梅写“我”的关系。
三、姜夔:梅与江湖游士
姜夔是南宋时期的词人,他一生浪迹江湖,寄食于人,青年时代曾北游淮楚,南历潇湘,后又客居合肥、湖州和杭州等地,是知名的江湖游士。姜夔为人耿介清高,曾辞谢贵族为他买官爵。姜夔艺术造诣很高,诗词散文和书法音乐无不精通,其中尤以词著称。在他现存的八十多首词中,写梅或者与梅相关的词达到了二十多首,可见他对梅的喜爱。对于姜夔词风的评价,刘熙载在《艺概》中也曾以梅作比:“姜白石幽韵冷香,令人挹之无尽。拟诸形容,在乐则琴,在花则梅也。” ⑥
与林逋和陆游相比,姜夔在咏梅词中并没有在梅和自己之间建立如此明确、紧密的联系,他咏梅往往有所寄托,但蕴藉含蓄,主要有思念远方恋人,或是怀念友人,也有融入江湖飘零之感等等。如《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见梅枝,忽相思。几度小窗幽梦手同携。今夜梦中无觅处,漫徘徊,寒侵被,尚未知。湿红恨墨浅封题。宝筝空,无雁飞。俊游巷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旧约扁舟,心事已成非。歌罢淮南春草赋,又萋萋。漂零客、泪满衣。”词人睹梅思人,上片写结想成梦,下片写醒后离思,时空交错,将离思酸楚写得哀婉动人,表达出对恋人的无限思念。在《清波引》中,姜夔咏梅怀友。“冷云迷浦,倩谁唤玉妃起舞。岁华如许,野梅弄眉妩。屐齿印苍藓,渐为寻花来去。自随秋雁南来,望江国,渺何处。新诗漫与,风景长是暗度。故人知否,抱幽恨难语。何时共渔艇,莫负沧浪烟雨。况有清夜啼猿,怨人良苦。”上片写独自步绕梅园,在冷云迷蒙的湘水之畔见寒梅像玉妃般起舞,忽而转入乡关之思,倾出漂泊之憾。下片则写自己与友人关山远隔,心事难通,彼此寂寞,盼望着与友人早日重逢,充满怀乡思友之情。在这些词作中都可以发现,姜夔往往是由景入情,由梅及人,之后便是展现人物行动,心理和意绪,很难看出梅的意象和词人,以及词人所怀之人,所述之情有什么具体明确的相关,梅与人之间总感觉隔着一层。
《暗香》和《疏影》被认为是姜夔最有名的咏梅词,词境深婉悠长,寄托深远,词旨隐晦。如《疏影》:“苔枝缀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里相逢,篱角黄昏,无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犹记深宫旧事,那人正睡里,飞近蛾绿。莫似春风,不管盈盈,早与安排金屋。还教一片随波去,又却怨、玉龙哀曲。等恁时、重觅幽香,已入小窗横幅。”词中大量用典,似乎句句都与梅花相关,但词人都是运用隐喻和象征的手法含蓄地表达主体情感,在一个个清雅的典故背后词旨被深深隐藏。陈廷焯评价说:“南渡以后,国势日非,白石目及心伤,多于词中寄慨……特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尔。”⑦过多的典故运用,曲折的寓意抒怀,倘若不结合词人的家国身世之悲去体会词中的情感,便很难理解词旨。王国维曾评:“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 ⑧
姜夔借梅怀人,借梅抒怀,但已经不再把自己的主观意趣如此鲜明强烈地加诸于梅,而是更含蓄地隐藏于梅的意象之后。缪钺《论姜夔词》说:“姜白石所以独借梅与荷以发抒而不借旁的花,则是由于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其品最清;梅花凌冰雪而独开,其格最劲,与自己的性情最合。”⑨所以梅之于姜夔,是人格精神的比附,而这种联系更多地是存在于词人的内心,并没有透过词表现出来。所以往往外者看来,姜夔的咏梅词通常是借助梅来起兴,表达自己所思所感,而梅与词人似乎有一层隔膜,虽然咏梅但与梅关系隐晦而疏离,不同于林逋、陆游和梅之间的那么紧密。
宋代咏梅的诗人、词人不在少数,而林逋、陆游和姜夔的咏梅作品独树一帜,他们在自己和梅之间建立的关系也很具代表性,透过他们,也可以概括出我国古代文人与梅之间的关系。隐士林逋咏梅,追求超越世俗、闲静淡泊的幽雅的隐者意趣,在他咏梅作品中,梅与自己互相融合;爱国志士陆游咏梅,歌颂不屈不饶,坚贞不渝的斗争精神和气节意志,而在他的咏梅诗词中,所咏之梅就是自己的化身;江湖游士姜夔咏梅,则主要是以梅起兴,抒发自己的对恋人的思恋,对友人的怀念,或是抒发自己的江湖飘零之感,抒发对国家兴亡的哀思,他写梅重在抒怀,与梅之间的若即若离,既相隔又有融合。在林逋、陆游和姜夔以外,还有很多诗人词人创作了大量的咏梅诗,赋予梅花丰富的意蕴。
可以看出,不同的身份、不同的社会经历和人生遭遇让这些文人们对于梅花有不同的审美需求,带给梅花不同的象征意义和不同的精神立意,而与这些文人千丝万缕的关系也让梅在作为普通花木具有的自然审美之外,更是上升为道德品格和气节意志的象征,寄托着文人们的种种情怀和理想,蕴含了更深刻的文化意义。
注释:
①黄杰.宋词与民俗[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49.
②程杰.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J].阴山学刊,2002(1).
③翁公续诗话[A].历代诗话[C].北京:中华书局,1981:275.
④程杰.从魏晋到两宋:文学对梅花美的抉发与演绎[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23(06).
⑤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8.
⑥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3694.
⑦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28.
⑧王国维.人间词话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71.
⑨缪钺,叶嘉莹.灵溪词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458.
【参考文献】
[1]程杰.梅花意象及其象征意义的发生[J].南京师大学报,1998(4).
[2]胡云翼选注.宋词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刘宝明.宋代咏梅词论说[D].曲阜师范大学,2009.
[4][宋]姜夔著.陈书良笺注.姜白石词笺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宋]陆游.陆游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6][宋]林逋.林和靖诗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作者简介:包琳(1990.11—),女,汉族,浙江台州人,现为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