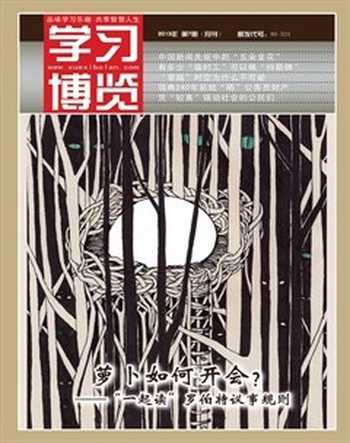卖劳力的男人们,是那么脆弱
张家瑜
这几个月,或天灾,或人祸,此起彼落的新闻,皆令人沮丧。去年的世界末日没有来到,但是今天的末日心情却沉沉地压下,和着春雨湿濡。
香港最近的货柜码头工人罢工,已经一个月了。到底还有多久工人们才能回家?不知。电视上那些什么哥、阿什么名的,因出镜多,样子都看熟了。他们每天坐在帐篷外,有的聊天扯淡,有的吸烟看新闻,百无聊赖地等着奇迹。
码头工人为求加薪,在户外抗议一个月。报纸版面、广播电视的报道,起的作用似仅在民间,但公司没有任何动摇,财团也视若无睹。
劳动基层,尤其是工人,多是外包外判,抗议与讨价还价,往往找不到对象,那对头的人不是一个据实的公司,而是一个包工头、一家外判。他们简直像一个个独行侠。
但他们也是某人的儿子、某个孩子的父亲、某个女人的丈夫,他们的财、技就是他们的劳力,他们没法像金融家、地产商可以像魔术师一变就多出几倍的财富。劳力就那么多,二十四小时就那么多,而薪水就那么万把块,还是家庭支柱呢。所以你看这些什么哥、阿什么名的,他们不光鲜,说着重粗口,狠狠地吸烟,他们被损害的程度和经济增长的程度成正比。
我手上的两本书:由潘毅、卢晖临、张慧临合写的《大工地上中国农工之歌》和贾樟柯的《中国工人访谈录》,或可以代言这时代工人们的困境与命运。他们是建造繁荣的主体,但却成为享受繁荣的他者。工人阶级如今不再是挂着红丝带被歌颂的对象,他们没有尊严,没有保障,没有未来的憧憬,当然更不会有美好的出路。他们的身份,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大工地上》全书用的是田野式的调查,潘毅是香港理工大学的副教授,他同北大的卢晖临、学生张慧临在国内几个地区,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采访和学术调查,写就这本以农民工特别是建筑工人为对象的悲歌。就如潘毅在导论所言:就农民工的范围,建筑工人的农民属性更强,如果有一个无产阶级系谱的话,他们当属系谱的低端。而统计中国的农民工人数,已达两亿多人,其中建筑工人就有四千多万。
他们的劳动力都只是服务其他阶级的梦境成真,他们打造别人的理想,他们建起一个富丽堂皇的“皇宫”,但他们住在铁皮屋。那些由资本家所挑选出的模范劳工,都如一个巨大的吹气公仔站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门口,反嘲着劳工与劳动力的虚无与无助。
贾樟柯的《中国工人访谈录》,则是他在拍摄电影《二十四城记》纪录片时,以在成都的一家国营军工厂的工人为主,把他所做的采访集结成书。那是一座有三万工人、十万家属的飞机工厂。经过六十年,终于抵不住潮流,地产商收购并建了一套套美轮美奂的豪宅,就在工人们生活了几十年、充满回忆的地皮上,铲除并重塑另一个有园林、有绿地的另一个阶级的回忆。
只留下贾导的电影和这本书做个历史的见证。
见证什么呢?这两本书告诉我们,实体的是已筑成的有空调、有舒适空间的建物,实体是所有已落入另一阶级袋中的利润。而虚幻的是劳工们的体力,他们甚至还无法拿到应得的工资,工人皆如鬼魂,黑夜的黯淡属于他们,寒冷、没有光明,白日的明亮温暖一起,他们需隐没消失,阳光一出,他们就注定要散去。
这是两本伤感与挫折之书。如工人的骆驼队依然在沙漠中前进,他们最后被取了生命的一根稻草,随时压上。我看见码头工人们在领取一个便当、一包纸装绿茶红茶,他们一群人坐下来,吃将起来。我想,那在每盏灯下看着自己的老公、父亲、儿子的家庭,都有另一种心情。
原来这些出卖劳力的男人们,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如果世界不站他们这一边……
(摘自《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