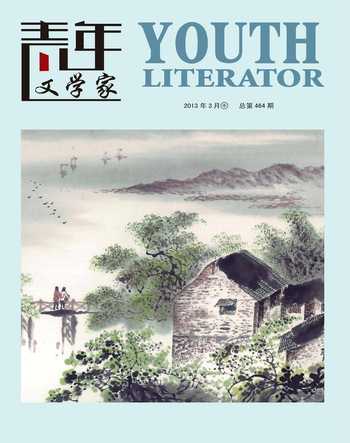骆家辉的“Soft Power”
摘 要:文化外交是近年国际关系研究中极受关注的一个主题,也是传播学跨文化传播领域一个新的热点。但在文化外交的实践领域,中国政府却少有出彩之作。反倒是一个美籍华人的到来,让我们领会到了所谓“Soft Power”的威力。文化外交到底应该怎样做?“国际传播”传播什么才能令人接受和信服?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一个人的言行,就将其所代表的价值观和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当然他也带来争论和异议,但正是这些争议及由此而来的讨论,使得其理念和价值观的传播更为深远。
关键词:Soft Power;文化外交;骆家辉;多样性;普世价值
作者简介:何庆平,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传播学硕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8--02
进入新世纪,提升文化“软实力”逐渐成为国际关系领域的新趋势,文化外交逐渐被各主权国家置于越来越重要的地位。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指的是以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所展开的外交。一种解释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对外文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文化手段来进行的外交活动”。[1]近年来,在政府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关于文化外交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但除了孔子学院开始遍布世界各地外(效果待验证),政府文化外交实践中的亮点乏善可陈。花巨资打造的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似乎外国人并不都买账。国家形象是宣传出来的嚒?文化外交应该传播什么内容?也许我们可以从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表现中获得有益借鉴。
一、官媒PK骆家辉
自从2010年8月背着大包小包,全家五口降落在首都机场以来,骆家辉不断成为新闻话题人物。他的每一次在国人看来与其身份极不相称的行为都引发媒体及网民的关注与讨论,尤其是在微博等新媒体平台上。针对骆家辉的种种表现,光明网、《环球时报》等官媒先后发表批评性评论,指责骆家辉“给中国官员们上课绝不是骆家辉的目的,为美国收揽赢得中国的民心强化中国民众崇洋媚外的奴性…借以分化中国断裂甚至碎裂的意識形态才是这位华裔大使的如意算盘。”[2]“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国舆论中的‘廉洁秀,尽管他最清楚,他并没有中国互联网上宣传的那么‘朴素。”[3]
2012年5月4日,由于在山东临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出逃美国大使馆一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骆家辉及美国大使馆受到北京市委宣传部下辖四家纸媒(《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京华时报》、《新京报》)以评论形式的点名批评。其中以《北京日报》发表的《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言辞最为激烈。“一段时间以来…新任驻华大使骆家辉的种种行为与其自身职责颇为不符,‘小动作不断…从乘飞机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的‘平民生活秀…再到胆大妄为地以非正常方式将陈光诚带入使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主动搅起矛盾漩涡的标准美国政客”。[4]其他三家报纸亦口径一致加以批判,京城媒体如此高度统一的同仇敌忾几乎前所未见,有关部门刻意为之的痕迹十分明显。
二、骆家辉的“Soft power”与文化外交
骆家辉何以令中国网民如此之关注?又何以令一些官媒尤其是党报如此之不满?笔者认为,实质在于他种种行为所体现出的一种“Soft Power”。“Soft Power”这个词由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出。李智教授在其著作《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中将“Soft Power”译为“软权力”,认为“作为吸引力和同化力的软权力靠的是示范(demonstration)和劝服(persuasiveness),诉诸人心,包括人的心理、思想、情感和意志,达到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以意(志)化人”。毫无疑问,骆家辉深谙此道。他作为美国政府的部长级官员,出行不坐头等舱、不住五星级酒店,甚至想拿优惠券买咖啡,让那些习惯了警车开道、前呼后拥、公款吃喝的“人民公仆”们汗颜不已,击中了中国官员群体的软肋,也让国内普通民众对美国政府官员的廉洁奉公有了直观的认识。
骆家辉如此抢镜,肯定有人不高兴,“作秀”的批评甚至阴谋论随之而来。以其外交官的身份,我们难以否认骆家辉张扬美国式的务实民主、珍惜纳税人钱财,可能有“作秀”成分。但即便如此,能做到一以贯之,则说明他的手腕娴熟,擅长以小博大,这就是他的“Soft Power”。在媒介多元化时代,政治传播与“作秀”也属于市场自由竞争,谁的“秀”更有说服力,要各凭本事。《中国青年报》就曾中肯评论,“指责骆家辉的所作所为‘别有用心,大可不必。一个国家的驻外使节,当然会努力展示本国的正面形象。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只要他的做法合乎法律和社会道德,能给我们有益的启示,我们不但没必要排斥,相反还应该借鉴。对骆家辉所展示的朴素品质感到纠结甚至百般指责,是内心极为脆弱的人才会做出的事。”[5]
三、文化外交的内核:多样性与普世价值
李智教授认为,将“Soft Power”译成“软权力”抑或“软实力”,其意义有着本质区别。应当把“行为力”意义上的“Soft Power”译为“软权力”,亦即上文所述骆家辉的行为产生的力量;而把基于“资源力”意义上的“Soft Power”译为“软实力”。软实力的唯一构成要素是文化,文化软实力的实现就是文化的权力化过程。[6]
一国文化只有在国际社会广为传播并得到普遍认同后才能成为一种软权力。[7]而这种所谓的权力化过程就是获得目标对象国民众的理解接受并使其产生情感和价值观上的共鸣,进而对其行为产生影响。很多研究都提出了我国文化外交的可行模式,比如加强对外人际传播的跨国文化交流(如正在推行的孔子学院和“中X文化年”模式),比如强化对外国际大众传播(如我们重金打造的国家形象宣传片)等等。笔者以为,以何种方式去开展文化外交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在于这种文化外交的文化内核是什么?笔者以为,是两个关键词:多样性与普世价值。
当今世界是个多元化的世界,多元化的国家民族,多元化的传统文化,多元化的宗教信仰,多元化的社会制度。与多元化的世界对话,需要多元化的视角。时至今日,一个国家在文化外交中若仍以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和界定别人,其在国际上必然不会有真正的朋友,也很难取得他国的信任,一如我们的邻邦朝鲜。承认并尊重多样性文化,特别重要一点就是破除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尤其是政府主管对外传播的部门必须认清这一点。以意识形态区分敌友的“冷战”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现在的中国有着全世界最多的人口,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在自由开放市场的路上蹒跚迈进(虽然举步维艰),“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早已过去,意识形态宣传早已过时。
关于普世价值,是个议论很久也颇具争议的话题。普世价值以自由民主为核心,涵盖的关键词包括: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等。很多人反对这个词的理由就是这个词源于欧美国家,代表“资本主义价值观”,是西方国家用来渗透、分化、瓦解我们的工具,是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但笔者以为,普世价值之所以普世,就表明它不仅代表欧美国家民众的价值观,它同样适合于中国,适合于所有亚非拉国家,适合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所谓普世,意即作为一个正常的个体(无论其国家、民族、语言等有多么不同)都会接受并认同、践行的价值观,因为它是对人本身的关怀。我们只要思考下民主、法制、自由等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是否重要,就可以明白普世价值对我们的意义。
四、骆家辉的启示
我们的文化外交更多强调的是宣傳,意在传播国家形象的广告片也被命名为“国家形象宣传片”。“宣传”这个在欧美国家颇为禁忌的词,在中国被毫无顾忌地在各个领域广泛使用,包括对外传播的内容。仅此一点,也可能会令外人敬而远之。
再回到骆家辉身上来。网上流传过一张图片,作者将骆家辉的头像PS到一名跪地犯人身上,只见他低垂着头,像文革被批斗对象般跪在地上,脖子上套了大牌子,牌子上“骆家辉”三字被打了大大的“叉”,另有三行字列数他的罪状:“坐经济舱”、“自己背包”、“拿优惠券买咖啡”。作者将图片题为《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还附上一句斩钉截铁的警告——“贪污腐败才是骆家辉大使的唯一出路”。这代表了普通民众对国内政府官员贪污腐败的一种反讽,而对比的对象就是骆家辉。试想,一个政府官员出国交流访问,骑着自行车出行,坐着经济舱,与民众深入交流,这本应该是很正常的表现。在中国,却成为刺激民众质疑政府贪污腐败的导火索。由此透视出,一些官媒党报所奉行的价值观是与普通民众的价值观是相脱离的,与普世价值更是相背离的。
中国的民智在开启,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民间论政氛围日渐浓厚,但是官方的回应手法与对外传播方式却没有多大进步。在外交领域,我国外交在世界上声音微弱,我们所“宣传”的东西不曾撼动西方,而美国一位外交官却能搅动中国舆论。其中深奥,除了美国文化外交的娴熟外,更显示我国文化外交的贫瘠。中美文化外交上的差异,体现的是文化内核的差异,一个在尊重多样性基础上践行普世价值,而另一个依然紧守着意识形态宣传不放,说着别人听不懂的话。
注释:
[1]、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24-25页。
[2]、光明网:警惕骆家辉带来的美国“新殖民主义”,http://opinion.huanqiu.com/roll/2011-08/1913897.html
[3]、环球时报:希望骆家辉好好做“驻华大使”,http://finance.huanqiu.com/data/2011-09/2026319.html
[4]、北京日报:从陈光诚事件看美国政客的拙劣表演,http://opinion.people.com.cn/GB/17807571.html
[5]、中国青年报:做好自己何必纠结骆家辉,http://zqb.cyol.com/html/2011-09/28/nw.D110000zgqnb_20110928_5-01.htm
[6]、李智:“软实力的实现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7期,第57页。
[7]、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