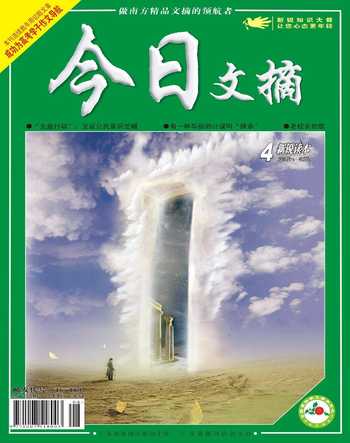老校长的歌
罗启锐
我一直不能忘记,念中学时一个盛夏的傍晚,天气火辣辣地炙热,我刚独自练习完三个多小时的越野跑,于灰蒙的暮色中,疲倦地走过学校的草坪,绕过校长宿舍侧门离开的时候,所看见的景象。
我看见我的老校长,坐在宿舍阳台外的一张旧藤椅上,默默地流泪。
老校长没有看见我,他大概没有想到,在这时分,还会有学生未回家,更会抄他宿舍旁的私家路下山。无论如何,即使当时的暮色已开始苍茫,我还是隐约看见老校长坐在一台古老的留声机旁,背负着一个朦胧而庞大的身影,像个小孩子般抽搐着,哭得非常难过。
顽固的草坪
我一下子看得呆了,也不知道该上前安慰他,还是装作没有看见。老校长在人前,一向是个幽默伟岸、挥洒自如的英国绅士,现在这种时刻,他大概会希望自个儿安静地好好哭一场吧。我不敢多想,便蹑手蹑脚地按原路折回草坪,快步走往学校的另一端,准备往石阶那边下山去了。
我慌乱地踏过草坪,心中只望自己可以快点消失,别让老校长知道有学生曾经偷偷路过,看见他偷偷流泪。只是那晚的草坪,却好像特别顽固茁壮,特别漫无边际,仿佛比我刚才二十多里的越野跑,更顽固茁壮,更漫无边际。而老校长的低泣声,却一直在草坪上追赶着我,寻找着我。
我脚步慌乱地走着,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逃过这些哭声,但觉它无处不在,恍惚就混合在炙热潮湿的盛夏空气里,网罗着大地。
许久之后,一切才终于平复下来,我再次感到大自然的宁静,生命也终于恢复了它的温柔。当我正要回过气来的时候,稍一定神,忽然听到一首我从未听过的老歌,一首老校长刚才一直重复又重复地播送着的老歌。
不知道刚才的我怎会完全听不到这歌,也许是因为老校长的哭声实在太震撼,太叫我不提防了,叫我只懂得没命奔逃——我的意思是,老校长曾经以他父兄般的严苛,责备过我;以他圣公会的基督精神和教义,原谅过我;以他恨铁不成钢的心情,放弃过我;可是,他从来没有以凡人的肉身,在我面前软弱过。
是的,我在老校长一切的严苛、教义与恨铁不成钢之前,一直顽劣地从不屈服,但那个晚上,我在他软弱的凡人肉身面前,被愣愣地杀了个措手不及,甚至有点早熟地顿悟过来。
哭泣的老歌
老校长于两星期前的一个清晨,安详地辞世,享年八十二岁,丧礼在情人节的当夜和翌日举行。我不知道他们选取这个日子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我记得许多年前,我早逝的哥哥离开时,老校长替我家打点了很多事情,包括那个小教堂内的丧礼。当时丧礼在妇女节后的第二个星期五举行,大概也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反正今天我明白,很多时候,即便是生与死,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更何况丧礼与丧礼发生的日子呢?
至于那首盛夏草原上的歌,我倒是在后来才知道,一直没有结婚的老校长,每次听到这歌,都会禁不住流泪。那是我在念大学时,跟一个与我从同一家中学升读上来的学生,于另一个盛夏的傍晚,在大学宿舍内,听一首他每次听到都会流泪的歌时,得知这个真相的。
今天,我当然知道,并且了解,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么一首歌,曾经令他快乐,如今令他心碎。正如每一对恋人,都有一首他们永远记着的歌,叫他们梦萦魂牵、肝肠寸断,只因这歌背后隐藏着的秘密,和一段随着歌声逝去、却又偏偏顽固地不断回来的心痛与相思。
我同样知道,无论我们如何相爱,无论生命如何相欺,无论铁最终成不成钢,一切都只会成灰,早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