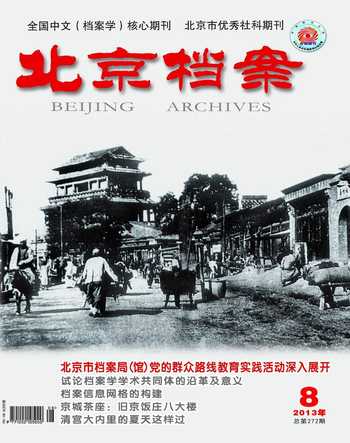导演的真性情
杨红军
多年来,我与戏剧界一些前辈及其家人常有接触,茶余饭后,海阔天空,云卷云舒,趣味盎然。但是,泉溪归海,话题归总离不开剧本、导演、表演等等。特别是一些著名大导演的工作细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中感受到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他们的性情及人格魅力。
儒雅智慧的欧阳予倩
1943年至1944年,正值日本妄图鲸吞中国,我军民撤退西南的艰难岁月,欧阳予倩策划发起了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来自桂、粤、湘、贵等8省28个剧团(队)1000余名戏剧工作者,历时3个多月,演出73个戏剧剧目,观众达10多万人次,声势空前浩大。
在西南剧展期间,当局规定凡是展演的剧目,必须办理报审手续,取得准演证才能公演。为了确保剧展顺利进行,欧阳予倩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巧妙斡旋与斗争。本来,曹禺根据巴金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四幕话剧《家》,其上演报批手续已经办好,广告登了,戏票也发了。但直到演出当天上午,准演证还发不下来。张客急忙派人到审查处据理询问,审查处推托说:第二幕中瑞珏枕边摆放《安徒生童话集》不妥,最好换成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欧阳予倩得知这种情况,想到那位审查处处长恰巧与自己是湖南同乡,于是立即打电话给他,严肃地批驳了审查处提出的换书意见,并软中带硬地说:“请你权衡一下利害关系吧,西南剧展的会长是省府主席,这点你是知道的。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而把事情弄僵,恐怕也不大好!”放下电话,又风趣地对秘书说:“你再去一趟,顺便带点东西(指戏票)塞塞他们的嘴巴。”这样,话剧《家》才得以与观众见面。
严格精细的孙维世
留学俄罗斯的孙维世,在担任中国实验话剧院总导演时,经常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的观念灌输给演员们,要求演员“戏路要宽,要演好千面人。”
1959年,实验话剧院演员石维坚已经在《一仆二主》、《桃花扇》中演过男主角。60年代初,剧团到山西省排《汾河湾》,起初没有他的任务。经他再三争取,孙维世才同意他演男主角B组、群众乙,并担任场记。这出戏在农村粗排时,观众和剧团对他的表演很赞赏。可是回到北京再细排时,孙维世却取消了他的B角,只让他演群众乙,继续做场记。石维坚心里有点打鼓,“是不是大家都认为我演得不错,而总导演孙维世不满意呢?”虽然心里琢磨,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演好群众乙,认真做场记,仔细看大家排戏。一天上午彩排即将结束,突然孙维世招呼石维坚:“小石,你来从头排一遍。”在事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要做到台词、走位都准确相当不容易,然而石维坚做到了,孙维世微笑着点点头。这部剧共四场,正式演出时男主角由AB角各演两场,这在剧院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来才知道,孙维世完全信任石维坚的演技,但考虑到如果只让石维坚演主角,那么另一个演员会永远失去饰演主角的机会,为了多给青年人锻炼成长的机会,所以做了如此特殊的安排。
敢说真话的焦菊隐
戏剧界的导演有“南黄北焦”之说,“南黄”是指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黄佐临,“北焦”指的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总导演焦菊隐。焦菊隐学在国外,回国后为北京人艺先后导演了《龙须沟》、《明朗的天》、《耶戈尔·布雷乔夫》、《茶馆》、《虎符》、《蔡文姬》、《武则天》、《胆剑篇》等古今中外诸多剧目。他治学严谨,勇于创新,是一位永无止境的探索者。他善于把中国戏曲艺术的美学观点和艺术手法,融会贯通地运用到话剧艺术当中,从而创立了自己的导演学派,同时缔造了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他曾设想把《白毛女》搬上话剧舞台,以全新的民族化形式呈现给观众。但“文革”彻底毁灭了他的理想。据说,江青说焦菊隐这个人很坏。于是他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第一批被关进“牛棚”,受尽折磨。1973年,北京话剧团(“文革”中北京人艺被改为此名)排了话剧《云泉战歌》,这是一出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戏。军工宣队让焦菊隐去看并让他谈意见。当时如果违心地投“上边”所好便可保身,这一点书生气十足的焦菊隐不是不明白,可他却坚持一贯地在艺术问题上不讲情面、不说假话,给这出戏的打分评价是:“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这一下可不得了,军工宣队立刻把这当成“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给他施加了更大的政治压力,对他批判升级。
把排练场当“练兵场”的金山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总导演金山,针对“文革”后排演场纪律松懈的状况,提出在排演场不要做与戏无关的事。他说:“这是个严肃的地方,不能松松垮垮,跷起二郎腿交头接耳,什么‘门口登记大白菜呢!‘嘿,商场来了一批飞鸽车等等。这些可以讲,但不要到这儿来讲。与戏无关的事,都不要到这儿来讲和做。过去(指‘文革前)排演场里在艺术上浓烈的探讨空气,以及严肃认真的作风等等好的传统,我们一定要拣回来。”在他心目中,排演场就是“练兵场”,练得好不好,“决定将来刺刀能不能见红”——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他也常用这类有时代特色的语言。他提出在工作时间不会客,不接电话。他还特别说明:“即使中央首长来了,我们也不要中断排练。你们想想,中央首长来到机床旁,工人是继续工作的,同志们,不要忘记,我们是在战斗!”有一天,他正带着大家对词。突然,一阵大头皮鞋踩踏地板的咚咚之声,干扰了大家的注意力。只见金山猛拍了一下桌子,怒吼道:“你干什么?”一位刚进剧院不久的学员站在那里,大家看着他,他也回头四顾,看着大家,显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金山余怒未消地说:“说你呢!这是排演场,大家正在倾注巨大的激情在对词,你知道不知道?”那位学员惊呆了,脸涨红了……事后,金山对几个副导演说:“这是位年轻的同志,很多事情他不知道,我不应怪他,但是你们有责任向他讲解过去的好传统,一定要向这位年轻同志解释清楚。”
在《于无声处》这出戏的效果处理上,金山在戏中其他的任何地方一次雷声都不要,只要求在全剧结尾处有一声惊雷。他说:“这一声惊雷代表着九亿中国人民的声音!”所以他提出这雷声是要从观众席的四面八方发出来的惊天动地的雷声。可当时剧院没有设备,只好用传统方法,多人做效果混合成雷声,但人们手上磨起了泡,还是远远达不到导演的要求。于是大家又想出另外的方案。这时夜已深了。金山有心脏病,医生规定他每天晚九时前睡觉,所以副导演劝他回家休息,并保证按他同意的方案连夜进行实验。他不同意,仍然坚持不听到这声惊雷,绝不离开剧院。人心齐,泰山移,终于人造立体声惊雷震响了!他向大家表示感谢后,才放心地离开剧场,这时已是凌晨3点多了。一声惊雷是这出戏的点睛之笔,正如曹禺在观看了金山导演的《于无声处》之后的来信中所说,不仅使演出“万分精彩”,显示了“大家手笔”,同时通过排演“传艺于将来,使后生得望门墙,祖国舞台艺术幸甚!”
性情浓烈的欧阳山尊
被人们称为“中国话剧的活化石”的欧阳山尊,曾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总导演。他平日里性情平和,风趣幽默不分长幼,常常令人捧腹大笑,但在拍戏时也会见到他的倔脾气,他发起脾气来也常常会让在场的人目瞪口呆。他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年代,深感遵守纪律的重要性,对排练时无故缺勤或迟到的现象深恶痛绝。有一件事,在北京人艺传为美谈。一天排戏时,有位女演员迟到了十分钟,而她恰恰是要第一个上场的人,欧阳山尊让众人耐心地静等“恭候”她一个人。当那位女演员终于走进排练场地时,他非常克制地对女演员说:“请你明天准时到排练场。开始排戏!”声调不高,不怒自威。第二天排练,这位女演员偏偏又来迟了,而且迟到的时间居然比前一天还长。欧阳山尊坐在导演席上,一言不发。大家眼见他呼吸急促,脸涨得通红,忽然他站起身来,走到那位女演员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请你明天准时到场!”这一惊人之举和咆哮之声骤然间震惊了整个排练场。意在威慑的这一举动,尽管让人看上去未免觉得有些滑稽,却也足见欧阳山尊性情中人的鲜明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