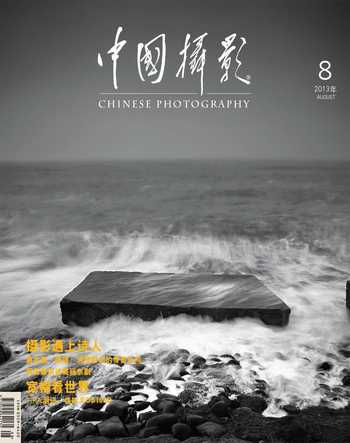消费时代的身份认同
唐晶



奥利弗·西博的摄影作品主要都是肖像摄影。“你现在是谁?”这一哲学性命题构成了西博所有作品的核心。在他不同的系列中可能表现方法有所不同,拍摄对象的国籍和拍摄地点可能有所不同,但他的作品始终都通过影像不断地向观者提出问题:你现在是谁?你如何认定自己?作为一个个体和作为社会的一个部分,你的个性特征如何?你认为应将自己展示为一种什么样的图像?
带着这些问题奥利弗·西博拍摄了大量有强烈视觉符号的亚文化群体,包括朋克、摇滚青年、哥特等等。因为亚文化以及与之紧密相连的青少年文化,其核心都指向当代消费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亚文化实际是消费社会背景下特定人群对自身的话语、行为和基本价值的一种认同方式,它与消费、大众文化和传媒息息相关。亚文化作为有别于主流文化的概念,其内容始终是相对的。亚文化群体成员有属于自己独特的价值与观念,而这些观念散布于主流文化之间,与主流文化有相通的地方。实际上一个亚文化群体的身份越趋向于被认同,亚文化就越来越接近于主流文化,并最终为之接受。它反映的是从个体对自身的认知到群体与个体关系改变的过程。爵士与摇滚乐都曾属于亚文化的范畴,但它们不断地被主流文化所吸收,直至成为主流文化的一个部分。
英国与德国战后几年,工薪阶层青年文化的兴起既是社会的动荡也是对传统社区文化的颠覆。以”泰迪男孩” (Teddy Boy)为先导,随后出现了光头党、朋克、摇滚、摩登派(Mods)和嬉皮士等等。奥利弗·西博敏锐地抓住了这一题材,在他1999年的系列《光头党/摩登/泰迪》(Skins/Mods/Ted)中,他采用了分类类型学的拍摄手法.在干净无其他杂色的背景前拍摄这些属于亚文化群体的人物,一个个拍摄对象被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下来。当他把这些类似的图像陈列在一起的时候,观众和被摄者之间建立了某种特殊的交流,被摄者本身的个性和身份的认定也逐步被推移到这种场景和氛围之后。
他同时期的另一个系列《练习室》(Ubungsraum)则将观众带入乐队练习的房间。这些空空的房间中没有人,只有练习用的乐器和简单陈设。但观众们看着这些乐器和私密的房间时不禁会去联想,那些使用它们的人会是什么样子?他们代表了怎样一种时尚与文化元素?或者这些乐器本身就是一种符号和代表?这个系列从一个侧面将流行文化与个体性格特征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接下来西博将他的镜头对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亚文化人群。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首府杜塞尔多夫不到60万的人口中就有3万日侨,这是一座深受日本文化影响的城市。在这里西博开始拍摄了很多玩Cosplay(角色扮演)[7]的年轻人,后来他又在美国和日本等地拍摄了更多的角色扮演者,并将这些集结成一本画册《角色盗窃者》(Character Thieves)。Cosplay作为日本动漫流行文化的衍生物,能勾起七八十年代人的共同回忆,也能满足更年轻一代对自己喜爱的身份角色和符号的幻想。在这个系列中,西博关注的并不是角色扮演者是否更像他扮演的那个人物或是角色的故事情节,而是“扮演”这个行为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这个系列在角色扮演者的居住环境或是附近拍摄,在这些日常生活的场景中,这些模特仿佛陷入一种思索或是困境。他们的服装和现实环境格格不入,周围的环境将这种反差衬托得尤为强烈。他们分裂为两个部分:一个日常生活中的自己和一个幻想中的自己。这些人物面临着一种身份与环境的双重错位:现实中幻想的自我和幻想中现实的自我,以及他人的个性和自我性格选择的重叠和冲突。
在其后的“日本亚文化”(J_Subs)系列中,虽然人物的服装并不像Cosplay那样充满视觉冲击力和戏剧性,但是西博更加强化了人物的思考空间与自由选择这一要素。这个系列的人物都面向四分之一或是四分之三的前方,并不与观众直接进行视线交流,这种方式带来了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双重自由。观看者避免了双方直视而带来的强迫性观看,从而能带着轻松的心态浏览图片上的每一个细节带来的符号特征,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观看的人物和物体。被观看者则处于一种恍惚失神的瞬间,在这个瞬间他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去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以及如何将自己展示给观众。这种不直接交流的方式似乎也隐隐如同亚文化在主流文化中的地位:它们往往是有自己独特群体和方式的小众文化,很多时候都晦涩于和主流文化进行面对面的直接对话。
在消费时代中,亚文化及其推崇的各种风格和偶像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消费。“我买了(什么),因而我就是什么”(I shop, therefore I am)。符号作为一种看得见的标志,当它不可见时,它是否还能起到作用呢?奥利弗·西博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他拍摄了一些盲人的肖像。在看不见的世界中,符号只存在于盲人的想象中,即使它不可见也同样能促成消费,这似乎从一个侧面论证了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定义。不过在《盲人》(Die Blinden)这个系列中,他没有要求盲人穿上特殊的服装来显示自己,而是简单地拍摄了一些背景干净的肖像照片。在拍摄过程中,视觉工作者(摄影师)和丧失视觉的人以及观看的人之间通过拍摄行为和图像形成一种交流。结合他以前的作品,西博聪明地将对视觉符号这一问题的答案交还给观众。
可以看到的是,无论在西博的哪一个系列中,人物都处于一种思索的状态。这种自由的空间赋予了人们想象的可能,也许这也是他把自己最新的画册命名为《幻想俱乐部》(Imaginary Club)的原因。在这个系列中,西博不再采用类型学的手法来排列照片,而是将自己这些年来在日本、美国、德国和加拿大等地拍摄的黑白和彩色照片混合排列在一起,那些偏离于主流社会的人物和各种街景、酒吧、乐队演奏交错出现,共同构建了一个“并不存在的文化范畴的俱乐部”, 由此来展示亚文化的朦胧幻影在全球化流行背景下是如何自我传播和改变的。
奥利弗·西博的肖像作品既不致力于探索人物背后的故事也不是刻意去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但他的作品却探讨了人本身的属性和需求:人们对身份的自觉意识、对人格统一性的追求以及对某种生活理想的趋同。而他选择的亚文化人群实际是将这一探讨放在当代社会的文化背景下来进行的, 间接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消费属性和消费行为的符号属性,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文化传播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