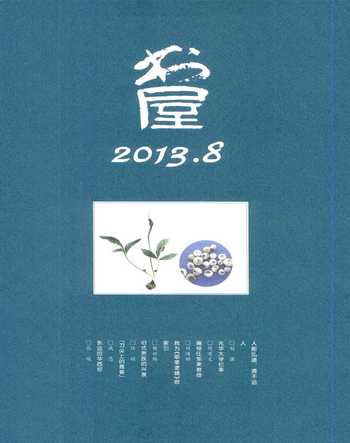字帖里的“私乘”
刘淑玲
2010年7月,河北教育出版社为父亲出版一本特殊的书《刘太馨小楷》。父亲晚年最大的爱好就是书写小楷,每日习写,从不间断。八十多岁的父亲撰写的蝇头小楷整齐温润,功力过人。但是,捧读这本书,最让我感叹的是记录在父亲字帖里的“私乘”。
我的祖父母有五个儿女:我的父亲、姑姑和三个叔叔。按照我们大家族的排序,我的三个叔叔分别被唤作四叔、五叔和老叔。祖母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我出生之前她就已经过世了,但是父辈口中时常提起她温和孝顺、善良坚韧,全村人有口皆碑,以致病重时探视者络绎不绝,病故后吊唁者不计其数,让我印象至深。祖母宽以待人、严以律己的作风对她的子女影响极大,父辈们也对她的言传身教念念不忘。2009年祖母百年诞辰之日,全家二十多口人聚在一起,举行了一个非常庄重温馨的追思会。父亲的字帖里就抄录了我的姑姑刘秀英和五叔刘大刚对祖母的赋诗追忆。其中有姑姑赋诗一首,名为《诉衷情》:“慈母百年诞辰临,心底思念深,贤妻良母交赞,堪模范人伦;众儿女,孝悌根,永记心,而今而后,更焕精神,以慰双亲。”姑姑刘秀英196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班。婚后,与姑父体弱多病的高堂老母和自幼瘫痪在床的弟弟同住。姑姑敬仰婆母、抚育小叔,尽心竭力。姑父的弟弟,我们小辈都称他小叔叔,除头部之外,四肢与躯干小而畸形,但是聪明伶俐。姑姑不但每日为他把屎把尿,还教他识字,使他能够读书阅报,解脱病中寂寞。每次用餐时间,无论多忙,姑姑总是让两个表妹把第一碗饭盛给奶奶和叔叔,我到姑姑家住时,也曾学着抢先给小叔叔端饭。小叔叔感念姑姑的养育之恩,还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文章《我有一个好嫂子》,着实感动。我上中学的时候,就记得《人民日报》曾刊载当时北京市妇联主任李钢钟接见姑姑的照片,我父亲把那剪报压在写字台的玻璃板下面留存了很长时间。姑姑还曾入围2008年度感动朝阳十大新闻人物,《北京晚报》曾发长文《长嫂如母照顾卧床小叔四十年》报道姑姑的事迹。
五叔大刚以“慈母百年诞辰纪念”为题头,赋诗如下:“慈兰荫嗣沐恩环,母祉流芳永世传,百代死生德为贵,年华夭寿命系天,诞先登岸心与若,辰错于参泪潸然。纪弘幻将旌旄列,念道愿修化性关。”五叔少年失母,生活历尽折磨,自学成才,后成中学名师,桃李满天下。他对母亲的高山仰止是其德行流芳。五叔不计个人得失,他的伯父患胃病,手术需要输血,其子孙数人回避不前,五叔毅然献血,保证了手术的顺利进行。五叔生性倔强,自认脾气不够温和。祖母姓兰,名弘道。已经年过七十的他写出“慈兰荫嗣沐恩环”、“念道愿修化性关”这两句诗用意十足,他想在母亲如兰芬芳的环绕中脱尽躁气,馨香永德。
在父辈之中,四叔太馥是一个最温和的人,自幼腿有残疾,一生坎坷。纪念活动中四叔给母亲写了长长的一封信,表达自己自幼让母亲操心、拖累双亲的内疚。父亲的字帖里没有篇幅抄录这封长信,但是他专门给这个弟弟题写了一首诗,称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为人处世礼为先,经过磨难真不少,不尤人来不怨天”,永远替别人着想。
老叔大正曾经是我父亲的骄傲。祖母去世时老叔还年幼,长兄为父,长嫂为母。老叔一直把我父亲看作是父辈,一生敬爱。老叔“文革”前曾经是唐山一中最优秀的学生,一心要上清华大学,但是正在备考之时“文革”开始,只能回家务农。恢复高考的消息刚刚传来,父亲就写信给老叔,鼓励他重拾书本,复习迎考。1977年,已经成为两个孩子的父亲的老叔重回校园。但老叔的英年早逝对父亲打击巨大,他在字帖里以《大正》为题,录下了他对这个才华横溢、命途多舛的弟弟的深深怀念。
父亲的这本字帖2010年出版,而2012年我们又迎来了祖父的百年诞辰纪念,祖父比祖母小三岁,祖母去世时他才五十二岁,而后独自抚养孩子们成才,又为孙辈的成长出力,到1994年,八十二岁时去世。父亲的字帖里没有留存祖父诞辰纪念会我的姑姑和叔叔们所写的诗文,但是它们也是这本字帖里的“私乘”,是生生不息的血脉,流淌不尽。
“自幼崇儒好古,贫困不忘读书,为人耿直刚正,克勤克俭一生”,这是我的父辈们联合送给祖父的诗,也是对祖父一生最准确的评价。祖父体质瘦弱,性情耿直,不善交往,自幼就酷爱读书,但是曾祖父认为从商才是正理,对祖父埋头读书不以为然,所以祖父从小就被送到商铺中去做学徒。虽然练就了一副铁算盘,可是祖父对经商毫无兴趣。
祖父一生读书都是自学,从未进过正规学校。他最喜欢也最爱读的是《四书》、《五经》。父亲说他崇儒尊孔近于迷信,每年正月初二对民国时期的所谓儒家传人江希张祭拜。每日中饭前带领全家人背诵《孝经》,而后用餐,如耶稣教徒之背《圣经》。祖母虽然目不识丁,日复一日,亦能随着背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等句子。祖父对我的父辈们说:“如不认真读书,学习四书、五经。即使搬来金山银山,我也并不喜欢。”正因为饱读诗书,建国之后祖父还做过正式的小学教员,只是祖母去世后精神不振而辞退。祖母去世对他打击极大,多人为他说亲、续弦,均被婉言谢绝。
祖父克勤克俭,即使再艰难从不张口向已工作的儿女要钱。父亲记得祖父只在车轴山中学要过一次钱四十元,是为外祖母做寿木,因为父亲的舅妈去世时,把为外祖母的准备的寿木先用了。1985年的一天,父亲曾贴着祖父的耳朵说:“如今家庭情况已有好转,手头应有几个钱,一为零用,二则谁有困难可以帮谁。”老人不以为然。同时,祖父节俭太过,常感吝啬,洗脸用水不过一杯,便后手纸剪成几厘米见方才用。他常说:“为父母者不可享受过度,十分聪明也要七分用,留下三分给子孙。”父亲的字帖里还留存了祖父的两则墨迹,是抄写《娄公德行》和《孝经》的片段,表达了父亲对祖父的怀念。
祖父的百年诞辰,五叔也赋诗一首,表达对祖父的敬仰:“亲上上达,一生蹇蹇卓卓,惟存昂昂之心志;知终终之,百年絅絅晔晔,永念厚厚之德恩。”五叔用《周易》、《论语》中之典故,展现了祖父的经历、节操和精神。祖父多灾多难的一生中,儒家思想与文化传统是他一直不变的信仰。他知道精神的归宿处,就要行到精神的归宿处,“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姑姑也为祖父赋诗如下:“严父天国位居尊,娇女凡间续做人;谆谆教诲犹绕耳,人间天国心连心;妈妈割爱先西去,爸爸衔泪抚儿孙;诗书教化胜朵颐,殷殷深情寄家门;种德锄经乃父志,希冀子孙勤耕耘;克己复礼牢牢记,格物致知日日新;父爱如山亘今古,永志难酬养育恩;晚辈身心俱茁壮,叩拜父母爽精神。”
祖父因自己未能升学,悔恨不已,决心供自己孩子念书,我的父辈们几乎全部都是教师。老叔在唐山矿冶学院毕业后本来是要留校的,但是那时冀东水泥厂筹建,他就奔赴了这个最需要的地方。除此之外,姑姑和叔叔们分别都在大学、中学任教。
父亲就是被祖父送进遵化县中,接触了很多新鲜事物。1944年暑假,在北京读书的铁珊表兄回家,主张把他带去上学。经祖父许可,父亲在北京西城二龙坑志成中学入学,并在学校入伙,住同兴公寓。
1945年暑假父亲回家后,日本投降,社会动乱,一直在家不能去京,就在家乡的燕各庄小学教书,后又在西龙虎峪小学初级复式小学任教,四个年级一人教课,一个教室不下百人。后来平安城高小招生,父亲带去的考生一举夺魁,当地传为佳话。1949年6月6日教师节,父亲当选为遵化县第四区小学模范教师。平安城中学刻印小报,曾约父亲写过《爱的教育》一文介绍经验。父亲这个初生牛犊从此在家乡小学有名气,1949年秋假,被调遵化城关完小,开始教五年级算数,监管总务。他深刻体悟到:只要教授得法,笨拙可以转化为聪明,并尝到教学相长的甜头,因此在县小学教师文化考试中,数学成绩名列前茅, 1950年被评为遵化县小学模范教师,而后到车轴山中学任教。1952年上半年,河北省培训中学教师,父亲被保送到北京河北师专生物科学习。看到解放后北京的变化,滋生着热爱共产党的意识,终于在1953年7月19日入党,后来调入河北师专生物系工作。而后在河北师范大学任教,先后任河北师范大学校长,河北师范院院长,直至离休。
1958年,国家选拔苏联留学生,父亲榜上有名。暑假到外国语学院留苏预备部报到,学习俄语,虽从字母学起,并不觉得吃力,他曾回忆说刘芷老师教学得法,对她讲得课至今记忆犹新,父亲学俄语进展不慢,半年以后,他就走到同班同学的前面了。此时又有大跃进,去京西山区参加劳动几个月,未得学习。1959年底,父亲被通知去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动物研究所攻读组织胚胎学,抵达莫斯科恰好是1960年元旦,坐上汽车市内灯火辉煌,大地白雪皑皑,相互辉映,另有一番情趣。休息两天而后北上,到列宁格勒,科学院研究生宿舍位于彼得工厂大街七号乙。不久得知,动物所为父亲聘请列宁格勒大学胚胎教研室主任拖金教授为导师,拖金发现植物杀菌素闻名,并获“斯大林奖金”,仪表堂堂,学者风度十足。
父亲进入实验室之后,由副教授顿都阿具体帮助开始学习切片技术,而后又为确定研究题目:在鸡胚发生过程中皮肤创伤愈合的研究。父亲观察的结果认为鸡胚早期发育中的外胚层细胞就是未来上皮层的基底层细胞,显微镜照片和细胞分裂率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据此写成文章投到解剖组织与胚胎学杂志,与谢尔扎诺夫和导师拖金教授的文章在同一期刊登。人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竟然是发表在苏联的大杂志上,父亲自然高兴万分。实验室工作量很大,制作切片很多,后来又用放射自显影的方法,常常通宵工作,还抱着字典看了不少英文文献。学习期间曾申请出差去北极海摩尔曼斯克,因中苏关系紧张未获批准。1963年10月14日上午在列宁格勒科学院的动物所会议室,学术委员会为父亲举行副博士论文答辩会,由父亲做简要报告,父亲的论文辩护人科诺里教授做长篇发言,评价很高,导师拖金教授介绍了相关情况,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副博士学位。10月21日,父亲就经二连浩特回到祖国。留苏期间,祖母过世,父亲未能回国守终尽孝,是他一生的至痛……
2009年12月,我有机会带着女儿到英国去访学,父亲激动万分。我也曾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进行出国之前的培训,因此,他的字帖里留存下两首诗:一首是《留学》,一首是《十二月廿日首都机场淑玲淑惠俩姐妹二人同日登飞机》。第一首诗:“父学俄语进外院,弹指一挥五十年;子学英语今又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第二首诗记录了也让父亲欣慰的巧合之事,同年在加拿大留学、定居的姐姐回国探亲,她回去时的机票恰巧与我出国在同一天,父亲和母亲专门从石家庄来,和姑姑一起到首都机场为我们送行,并为我们赋诗赞叹:“西欧北美各有志,巾帼自古比须眉。”我知道这是父亲希望我们能延续他的梦想。
父亲还在字帖里写道:“如今父母以下已有三代共三十五人,其中博士学位四人,具高级职称及大专以上毕业者十八人,他们岗位不同,各有建树,重孙辈亦有九人,个个活泼可爱,快乐成长,其中将有出类者。父母在天可以安息。”
父亲的字帖是他晚年的杰作,也是一个诗书之家的记录,它记载了一个普通人家的诗书传递与模范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