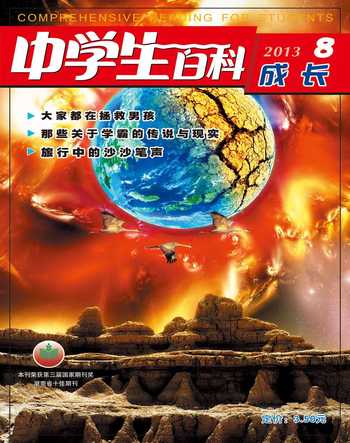太平
胡石柱
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与胡德夫先生靠得这么近。
说起《太平洋的风》,很多年轻人可能会首先想到去年韩寒那篇写台湾的博客。而实际上,我早在七年前就与这阵风邂逅过。那一年,台湾地区以电影《练习曲》代替李安导演的《色戒》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这部讲述一位听障青年骑自行车环岛的电影依然风靡海峡两岸。电影海报上的那句“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甚至被五月天写进了歌词中。
在这部音乐骑行电影的结尾,胡德夫先生坐在空旷的沙滩舞台上弹奏着钢琴,背景是蔚蓝而又深沉的太平洋,当时他唱的,就是这首《太平洋的风》:“最早的一件衣裳,最早的一片呼唤,最早的一个故乡,最早的一件往事,是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
隔着银幕,耳畔回响着那沧桑浑厚的嗓音、自由随意的吟唱,一种安静却又极其强烈的感动从我心底生发出来。第二天,我就在班上给同学们推荐了这部电影,并且记下了这位白发的歌者,后来上网搜索才知道,他是“台湾民歌之父”胡德夫。
之后会在一些音乐节的报道中看到胡德夫,不久前还在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上看到过他一次。窦文涛请他过来,谈钓鱼岛问题,节目中播放了胡先生的音乐作品《脐带》。这是两年前,胡德夫写给母亲的歌,穿插在这样的话题中,真是再贴切不过了。不管走了多久,走得多远,“我永远是您怀中的宝贝,视线里的焦点”。许多人说,这首歌是属于那种刺进心脏直达灵魂的,听到就想流泪。
时间行走至2013年,因为春节的临近,《潇湘晨报》主办了“未曾忘记——让抗战老兵过个好年”的公益演出活动,来了很多民谣歌手,王梵瑞、钟立风、川子,而作为压轴表演的就是胡德夫。仍旧是一袭白色披肩,缓缓地在钢琴前坐定,那熟悉的旋律在他的指尖跳跃流淌。一曲唱罢,他会说很多往事,他从小吃的湖南菜,他经历过的那些年代,他认识的老兵,以及心中的母亲。台下的我们,静默地听,静默地落泪。他的歌很难模仿,也不需要去模仿,那是岁月沉淀下来的印痕,是海风刻画下来的音轨,是稚嫩的我们无法企及的一个高度。
演唱会结束后,很多人在场外排队,拿着歌手的唱片等着签名。我手上拿着的是《大武山蓝调》,队伍在缓慢地挪动,胡先生很慈祥地在与前面的人不断地握手、合影。轮到我时,我竟然紧张得不知该说什么,慌乱中冒出一句:“我也姓胡……”心里顿时觉得丢脸丢大了。胡德夫先生笑了笑,对我说:“谢谢你能来。”并在CD内页上写下:“胡小弟指正——胡德夫。”我没想到,一位有着传奇色彩的伟大歌者,竟会如此之温恭谦逊。
或许我早就应该想到,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张开满背的刺,将物饰与头衔挂满一身。所有真正内心强大的人,都是朴素而内敛的。尝过了世间苦楚,也看惯了悲欢起落,锋芒早已尽收,平静深邃得像一面湖水。放过牛,种过菜,卖过水,打过杂工,为原住民争取过权利,经历过亲友的生死离散,生活的艰辛早就血淋淋地摆在那里。可是在胡德夫先生的歌里,我们能看到的意象,却是美丽的山谷、无垠的草原、南国的椰林和槟榔树叶、芬芳的玉兰花……这个星球自有人类寄居以来,从未停止过纷争,有智慧之人,自会用自己的方式去寻求内心的太平。
“最早和平的感觉,最早感觉的和平……太平洋的风徐徐吹来,吹进了生命的胜出……吹过真正的太平……”
编辑/姚 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