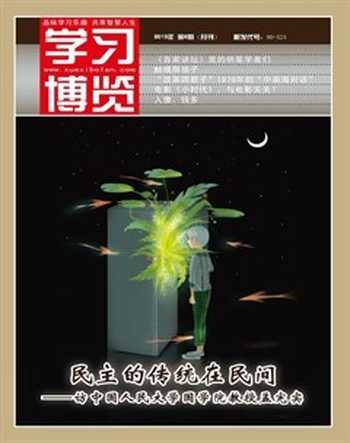丹青自白
陈丹青
谈相貌
有两句话我都相信,“人不可貌相”、“相由心生”。
譬如“文革”时大家都讨厌江青、张春桥,谁敢说呢,谁又真了解他们?可是电影里看他们的相,就是讨厌。还有,人跟人一照面,好感、恶感、反感、无感,一秒钟就有,事后接触,也大致是的。一见钟情是稀有的经验,一见反感,例子太多了。
“人不可貌相”,例子也多。我记得小时候在弄堂里、在乡下,善良忠厚的大人、大嫂,都长得一般,甚至难看。还有就是才华。我认识几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非常非常有才气。
一个社会得有一小群怪人。所谓“怪人”,会有异常出格的打扮,但其实蛮善良、蛮规矩,甚至有点孤僻、有点害羞。
谈身份
不要被人以为是个艺术家。我认识太多艺术家,原来我跟他们一样,我就是他们?特别受不了老要问你怎么定位自己,画家还是作家,还是公知?这种身份焦虑,我慢慢明白了,大概屌丝太多了,快点想有个身份、有个说法,公务员啊,科长、处长啊,至少部门主管吧。艺术家也这样,巴望有个说法、有张名片、有个头衔。
我是长期没有身份的人,年轻时连户口本都没有,很自卑,火车上最怕人问:小伙子你是哪个单位的,你做什么工作?我什么都不是,坐火车就是到山沟去啊。后来上了美院,一天到晚戴着校徽。结果很快出国了,又成一屌丝。美国结结实实教育了我:你就是你自己。现在我很骄傲:没有身份。画画算什么身份啊!可是你在中国没身份,意思是没单位、没职业、没钱、没权……这一关很难过的。我最怕看见年轻人自卑,可是我们的教育就是让你越来越自卑。
谈流氓
我总喜欢说自己是流氓。你耍流氓!这是流氓手段,其实是指无赖。旧社会,旧上海,流氓的定义就是“白相人”,“白相人”的定义就是黑道。
目前我看过最朴实的黑道定义,是杜月笙的儿子。记者问他,到底怎么看那代流氓?流氓是什么?他想了很久,只说一句话:“就是帮忙。”—你在这个地面上,本地人,外邦人,你进上海街面混口饭吃,要做小生意,要有地盘,尤其要有朋友,怎么办呢?要人帮忙。今天人家帮你,有一天你有力量了,兜得转了,你帮人家的忙。
白道不是。黑道有一系列规矩,白道也有一系列规定,玩儿规定的人,管人的人,吃官饭的人,都有交易,但轻易不帮忙,也轻易不拆台。清末民初,孙中山、蒋介石闹革命,都要靠“流氓”。
我相信每个省、每个小地方,都有杜月笙这样的人。草根里永远有这样的人,书都没念过,聪明、仗义、有办法、敢担当。
谈现代文化
所谓现代文化、现代文艺,两大摊:一摊娱乐(美国所有电影电视统称“娱乐业”),一摊时尚,两者都是大生意。这两摊没了,弱了,你谈什么现代文化?
当代艺术都要跟时尚界找灵感,为什么?古代也一样,文艺复兴那会儿,画家、雕刻家这一摊是最牛逼的时尚,创造经营整个景观。现在最有活力的人精,许多在时尚界。大都会博物馆、现代博物馆,每年有顶级时尚人物的专展。中国是两头不着调:美术馆是官府,不懂时尚,看不起时尚,时尚界也拿不出真东西、真角色。
不要把我当读书人,书架上这些书我顶多看过千分之一,以后也不会看,我得找个时候扔掉。
谈中国人
在一些小店里,我发现不少店员发现你是中国人,收钱交货,但眼睛不看你,他们显然在这样的人面前受了太多他不明白的遭遇,我不能说羞辱,因为他挣了钱。但他没见过这样花钱的人,这样来买东西的人。
我有一次在罗马的古董街里,古董店一家连着一家,便一个个走进去看,问其中一个店主价钱,店主不回答,最后说:“你进了我的店,甚至都不跟我打个招呼。”
这时我会倾向自责。所有我们在国外遭遇的事情,不管事由怎样,我大部分时候会同意鲁迅的态度,他会骂中国人,不会骂外国人。即便错在外国人,我也会先反省我们自己。
(摘自《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