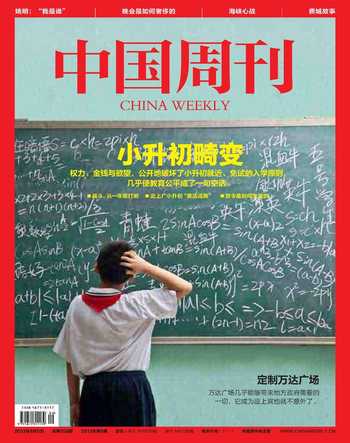月饼与“日饼”
孟繁佳

去西安参加一个月饼大会,在我旁边坐的是台湾来的烘焙业策划师黄泰元先生。黄先生的发言很耐人寻思,他说,余光中说乡愁是一张船票,他却感觉,乡愁是一块月饼。
会后,我和黄先生聊了很久,他说,台湾人喜欢饼,也会做各种饼。月饼只是其一,还有“日饼”。
我听了很惊奇,还真有叫“日饼”的饼吗?
他笑了笑说,不是真有叫“日饼”的食品,而是台湾人经常甚至每天都有买饼的习惯,“日饼”只是形容这样的现象。
在台中,我很喜欢阿明师的太阳饼,每次回台湾,总要买几盒带回北京给亲戚朋友们品尝。太阳饼味道口感很独特,像小时候吃的酥皮点心,但又感觉任何一点都超过小时候的味道。阿明师曾给我讲过饼的制造工艺,虽然记不住那些很复杂的程序,却感到他很用心地在做。
黄先生说,的确,像阿明师这样在台湾用心做一件事,却能坚守一辈子,甚至两三代人的人很多,所以你在台湾能看到很多百年老店。
我曾经在台湾的大街小巷看到许多这样的饼店,一边是老的铁皮屋,进出的都是上岁数的人,手里只拎着很简单的一种纸袋子包装,悠哉悠哉地走回不远的家。另一边是外装内饰都很精美新潮的西饼店,门口偶尔会有一两位俊美、衣着又很职业化的小美女,手里端着一个小餐盘,给路人分发着切成小块的西式糕饼。店堂里也大多是上班族和情侣们,在一角快餐椅上喝着咖啡或甜饮。
两种饼文化,在台湾街头就这么和谐相处着。
回家和老婆聊起月饼大会上和黄先生聊到的话题,我问她,台湾是不是也有一种老婆饼,她说,也有老公饼啊,那是从澳门传过来的。
她数着小时候爱吃的乡下饼,告诉我那才是真正台湾本土的味道。小时候的绿豆椪(台湾的传统月饼)、白雪月饼、蛋黄酥,到现在也只有在乡下的老店里才买得到。还有寿桃、面龟这些寿诞场合用的饼,都属于喜饼这一类的。
这让我想起台湾还有一种更为夸张的结婚用喜饼。娶媳妇至少要花上一二十万喜饼钱,让娘家买几百盒(吉百合)喜饼分送邻里亲朋,这在台湾大小婚礼也算是一笔很固定的开销。
大陆的饼分广式、京式、海派等传统味道的月饼,可又有多少保留了老月饼的味道呢?参加月饼大会的朋友大多抱着这样的慨叹,同时又崇羡台湾的饼健全发展。
黄先生对此有自己的看法。他说大陆的月饼只是缺乏文化的包装,尤其是传统工艺还停留在手工上的边远地区的老月饼。那些月饼保留了月饼文化的原汁原味,若加以现代营销手段,不难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其实,我倒觉得,市场空间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它给富有人情味的商品预留了一席之地。月饼本就是民族饮食文化中不能或缺的角色。
饼文化从几千年前就注定,是与一个民族兴旺相连的历史。饼,食与并。两块面皮合起来就是饼,这是比肩并立的饼。皮中有馅,这也是饼,吞并的饼。饼在古代有两种用途,适合储存和携带,可以随时充饥,打仗时用作军粮。在食物短缺的古代农耕社会,制作精美、外饰考究的饼多被用作祭祀祭拜的供品。
直到物质丰富起来,饼的文化中与军事和祭祀文化的关联便越来越少,更多的乡土文化却越来越浓重。这时月饼便从它的前身胡饼,借以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说,变成了中秋月圆时那一口浓浓的浪漫乡味。
月饼大概是两岸间最能解乡愁的食品了,记得那年与邻居家台湾老兵在聊天时,他曾无限幽怨地说过一句,这辈子大概再也吃不到妈妈小时候给我做的月饼了。他说,小时候家里穷,没啥吃的,恰逢征兵离家前的中秋,妈妈最后做了几块饼让他随身带着。打仗时,他没舍得吃,跑丢了一块。剩下的都发霉了,变成干饼,他带到了台湾。别人说黑黑的有着霉味的一块面坨儿,干嘛不丢掉,他说,哪里有霉味,不是一直有妈妈的味道么。
真正有霉味的,却是大陆的月饼,这些年被当成了厚礼和暗藏玄机的礼品,在社会上传递的就是腐朽的味道。搞不好那盒中月饼还真的可能变成了发霉的面坨儿。我问黄先生,今年中秋是否回台,他说有可能带一些大陆月饼厂商回台参观一下。我点名让他给我带回一些台中的老月饼,给老婆孩子,以解她们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