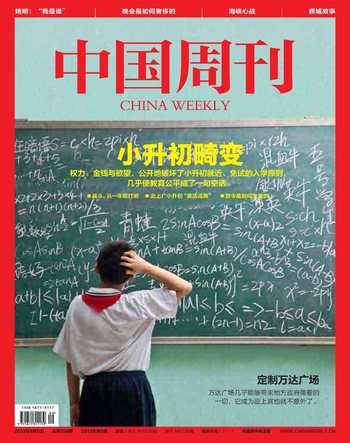费城故事
张亚利
延误了几个小时的飞机上,人们烦躁不安,几名乘客取出了乐器,奏响了动听的四重奏。
6月7日,一段机舱里的即兴演奏的视频获得中国网友大量转发和激赞,有人将其“浪漫”程度媲美“泰坦尼克号上的最后的四重奏”,尽管况味天差地别。
这纯属是一段小插曲,可这段意外的小插曲,让更多人知道了美国费城交响乐团2013年6月的“中国行”。
40年前,费城交响乐团首度来到中国时,人们关注的同样远远不是他们在舞台上的演出。
机舱“音乐会”
2013年6月7日,北京大雨,当天中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共计取消航班112架次,延误滞留一小时以上航班95架次。
赴澳门的一趟航班已经在首都机场停机坪滞留了三个小时,飞机上的乘客早已躁动不安。陈则宏也坐不住了,他是费城交响乐团的一位中提琴手,同机舱里还有两位小提琴手和一位大提琴手。他们刚刚完成在北京的演出,将赴澳门表演。
坏天气让飞机延误状况令人绝望。“等待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一位小提琴手就起身去找机长建议,希望在机舱里进行演奏。机长说,乘客们可能需要休息。等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候,机长说,好,你们去拉吧。”
大提琴手侧坐在椅子把手上,陈则宏和另外两名小提琴手则在椅座之间弯腿站着。机舱里响起了“美国四重奏”。优美的旋律很快让机舱安静下来。
乘客暂时忘却滞留机场的烦闷,开始为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的近距离演奏振奋,有人为乐手捧起了曲谱。
演奏持续了5分钟,陈则宏发现,乘客们平静了许多,可等候又持续了四个小时,中途又有人要求演奏,乐手们又表演了一次。
有乘客拍下了这段“机舱四重奏”,这段视频迅速在中国的网络和媒体上传播,中国网友纷纷“羡慕”,表示虽然忍受飞机延误之苦,也“值了”。
这段小插曲让很多人知道费城交响乐团正在中国演出,可很少人知道,乐团此次来华是为纪念首次访华40周年,并正式推出中国驻地合作五年计划的首年度活动。6月7日的“飞机即兴演出”事件之前,他们已在杭州、上海、北京巡演一周,并将赴澳门做最后两日的收官演出。
而早在2012年,费城交响乐团就在中国进行了为期10天的试点“驻站”表演。在北京,除了国家大剧院,他们还在天坛祈年殿、颐和园等古迹名胜区和社区、医院等户外场所举办了15次“小型音乐会”。
国家大剧院副院长杨静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从来没有外国乐团在北京进行如此街头的表演,这对我们意义重大,中国政府要求艺术家们走向普通老百姓。”
一些媒体则干脆套上了“走转改”、“下基层”等中国特色词汇,形容费城交响乐团的“壮举”。
飞机上的表演完全在“计划外”,是真正的“即兴”,却因“飞机延误”、微博传播,而成为费城来华驻站的最大话题。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竟然如此“平易近人”、降低“身段”?这对陈则宏来说却很平常,陈则宏14岁从台湾被推选到在美国寇帝斯音乐学院深造,21岁就进入费城交响乐团,成为该团最年轻的团员。他告诉《中国周刊》记者,从辉煌肃穆的剧院走向室外表演已是欧、美交响乐团近些年来的新潮流,有时免费,有时也卖票。“我很享受这样的街头表演,能够和观众产生真正的互动和共鸣。”
在机舱的即兴演出现场,77岁的美国人卜励德(Nicholas Platt)为乐手们充当了翻译。卜励德是美国前大使、亚洲协会名誉主席。这不是他第一次充当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人的纽带,40年前,正是他推动了费城交响乐团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乐团进入红色中国,那才是真正的“历史性”时刻。
曲目谈判
1973年的8月,36岁的卜励德接到任务,负责接待美国费城交响乐团即将到来的访问。6月,卜励德才刚刚搬进美国在北京成立的联络处,担任政治处主任。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驻北京联络处正式筹备。
刚刚“开张”的那个夏天,联络处就挤满了来自美国的各个团体。但费城交响乐团的来访,是一次最大型的、由政府资助的交流活动,也是真正意义上具有文化影响力的活动。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音乐事件。此次访问的许可,是由周恩来总理在我们会谈期间批准的。当时我们讨论了我们两个国家间最敏感的问题。双方一致认为,由世界上最杰出之一的交响乐团到中国访问演出,展现我们之间关系的突破性进展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将是一种恰当的方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后来回忆。
在卜励德接手之前,中美之间的谈判已经持续了几个月,商讨演出节目像是在制定条约,双方在访问的细节上争论不休。中国方面反对选用施特劳斯的《唐璜》和德彪西的《牧神午后》,因为它们情色颓废。中方商讨后提出选用科普兰的《比利小子》和任何莫扎特或舒伯特的作品,因为后两者“在政治方面保持了中立”。音乐会定在1973年9月中举行,可直到9月上旬,曲目都没有正式确定。
负责和卜励德直接对接的是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首席提琴家司徒华城。在最后时刻,他深表歉意地对卜励德说,一些演奏曲目还需修改。领导们想在音乐会中加入其它的作品,所以现在就是“贝多芬的第六交响曲、一组美式联曲以及黄河协奏曲,一首由革命委员会创作的主题音乐”。“我指出,花几个月谈判确定下来的曲目,并没有包含这样的组合。而奥曼迪对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的反感是众所周知的。”卜励德反对说。
尤金·奥曼迪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指挥大师,他也一样“专横”。卜励德任务“艰巨”。从上海到北京的飞机上,卜励德作为接机人员坐在他旁边,一路都在“战战兢兢”地向他转述中方的要求。“你知道,我讨厌贝多芬第六交响乐,甚至都没带乐谱。”
卜励德编了很多故事:“中国人喜爱主题音乐,能够表现农民在农村的生活。中国的革命是农民革命,觉得它能展现他们曾经在暴风雨中经历的挣扎和共产党统治下的新面貌。”大师最终做了妥协。
双方还临时达成一个新的时间表,在北京的演出,在三场基础上加演了一个特殊的领导专场,计划在9月16号演出。
音乐会开幕中场休息时,卜励德被告知“大师出了点状况”。在更衣室,奥曼迪心烦意乱、满头大汗,他端庄的奥地利妻子正用手绢呼呼地给他扇风。
“他们根本不喜欢我的音乐,”奥曼迪抱怨道。“他们这么安静,我从来没有遇到如此平静的反应。”
“我告诉他,刚才的观众反应一如我在中国见到的一样‘热情。他们不习惯喧闹的欢呼,而且中国人几十年都没有听过西方音乐了,他们在公众面前随时保持慎重。”
大师渐渐冷静下来,音乐会很成功。
9月16日,江青出席观看了费城交响乐团在人民大会堂的演出。江青身穿一件黑色真丝正装礼服,脚蹬一双露趾白凉鞋,每当乐曲演奏完,江青都会鼓掌,最后带头起立致敬。后来卜励德才得知,贝多芬第六交响曲正是她要求演奏的。“她对西方音乐的确有一定的了解,不过在看演出的过程中,她一直跟坐在旁边的人聊个不停。”在招待晚会上,江青发表了祝福讲话后,坚持同所有107位表演家一一握手。
40年前的“走基层”
1973年9月12日,费城交响乐团130位乐手、随行人员和乐器塞满了一架波音707客机,抵达中国。临行前,他们准备了矿泉水、卫生纸和餐巾纸,训练了筷子的使用方法。
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北京还处在“文革”末期的动荡之中,作为第一支进入新中国的美国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打开了一扇已经关闭了25年的大门。对于美国的音乐家而言,中国之行是一次忐忑又激动人心的“探险”。
乐手被细致地安置在每个房间,他们的名字用英文和中文写在门上,走廊里站着紧张等候客人的侍者,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随时补充房间热水瓶中的开水。
早起床的人们观察到严肃的中国人穿着睡衣在街道上练太极拳。古老中国的一天由此开始,这与他们想象中手持红宝书的“红色中国”有所不同。
他们迫不及待走向中国的街道,25年没有西方人在中国的街道上散步了,骑车的人停了下来,散步者愣在那里,不过,当团员们抛起自己的秘密武器—飞盘时,中国人也渐渐加入了。
乐队首席小提琴手诺曼·卡罗和其他几位小提琴手还加入了中国人购买炸油饼的长蛇队。中国人与他们握手,长蛇队伍被打乱,小提琴家们被推到了前面。
乐手们白天被安排参观长城、明代陵墓、颐和园和紫禁城,这些令他们大开眼界。初来时疲惫不堪的乐手们热情越来越高涨。在和中国乐手一起进餐时,一位团员幽默地对给他夹菜的中国乐手说:“少许弱音就可以”,引发周围一片笑声。
除了在北京的4场演出,费城交响乐团还在上海做了两场演出。上海的观众的反应比北京的要热情得多,人们走进剧院,又从门口将票递给外面的人,好让自己的亲戚朋友也进来听。
小提琴手帕斯奎勒在上海街头散步,一栋建筑中传来小提琴声,他跑上楼找到了正在练琴的学生。给这个诚惶诚恐的孩子上了一个小时的演奏课。
《费城问询报》前任音乐评论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在2008年发表的文章里详细回忆了这些有趣的“探险”细节。
而对中国乐手而言,这次短暂的交流却如一缕清风,却回味无穷。
今年82岁的赵昉曾是中央交响乐团的一位小提琴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当年的一场排练。
当时,中央交响乐团邀请费城交响乐团在北京老城墙边一座破旧混凝土建筑里参观。乐手们拿着有缺口的和用胶粘过的乐器,使用手写的、粘贴在一起的旧乐谱排练。这些乐手从1966年开始从事采煤和田间劳动,几个月前,他们突然被招回,重拾西洋音乐。赵昉虽然没有“下乡”,却一直在演奏《沙家浜》等革命样板戏,西洋乐也早已手生。
当时他们正在排练《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第一乐章,费了很大的劲儿仍“不成样子”。李德伦指挥完第一乐章后,转身邀请奥曼迪上台,代替他指挥第二乐章。奥曼迪脱掉外套,欣然上台。
《纽约时报》记者哈罗德·桑伯格(Harold Schonberg)记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中央交响乐团突然焕然一新,充满信心,演奏节奏极为精准……大家一起握手,交换关于乐器的看法,甚至拥抱,甚至可以看到中国人眼睛里的眼泪。”
中央乐团给他们的访客带来了一场用传统乐器演奏的中国音乐会,奥曼迪惊讶于中国音乐的技巧,琵琶—一个葫芦形的吉他、笙、二胡—两根弦的蛇皮小提琴。在幕后交流时,这些音乐家们告诉美国同行,在“文革”期间他们被送往乡下,在干校劳动,他们戴着柔软的手套摘李子,保护了他们那双宝贵的手。
费城交响乐团返回时,团员们依依不舍,他们带走了中国的乐器、对针灸的热衷和各种轶事。他们离开后,《贝多芬第六交响曲》再次被作为“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文化”批判,被临时召回的中国乐手也再次被下放到劳改农场。而中国乐手们则被继续“禁演”西洋音乐,直到文革结束。
2004年卜励德主持美国亚洲协会盛世时,中国音乐家谭盾告诉他,1973年9月16日的音乐会通过无线电向全国转播,当时他作为下放农村的知青也听到了,正是这段乐章坚定了他追随音乐的信念。
“这些都过去了,贝多芬第六交响曲依旧在。”卜励德对《中国周刊》记者说。
“中国男孩”
作为一名美国人,卜励德称自己是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1973年接洽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之前,卜励德已经和中国结缘超过十年。
早在1963年,卜励德就曾在台湾进修中文。1964年,卜励德来到位于香港花园路的美国总领事馆工作,这里的大陆部是观察中国的总部。
卜励德和同事负责“观察中国”。他们阅读能弄到的所有报纸,包括用来包鱼的报纸,收集带进香港的各个省的出版物,跳过华丽的辞藻,快速浏览《人民日报》的社论,分析细微的偏差和不能马上理解的叙述方式。
“文革”期间,卜励德则通过其他国家驻中国大使馆的朋友帮忙,从墙上扯下的大字报令他如饥似渴。
1973年5月,卜励德从香港来到达北京,为进驻北京美国联络处工作做准备。到达的第二天,他就买了一辆凤凰牌自行车,铃声响亮,到哪儿都骑着。脚踏在这个他曾“隔空”观察过很久的城市马路上,令他兴奋不已。
在回忆录《China boys》(《中美关系中的“中国男孩”》)里,卜励德摘录了自己多年前发回华盛顿的观察信息:“很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摘掉的路牌仍然没有归位,这让新来这座城市的人很难辨别方向。新路标逐渐取代旧路标,原来那些带有激进名字的路标将不复存在。”
“胡同给北京城带来无限乐趣,这里的生活也像以往一样继续着,尽管穿着开裆裤的孩子们随地大小便,人们随地吐痰,北京城还是像传说的那样干净。”
他还描述了老百姓的友好态度,被小伙子撞倒的女孩尽管气红了脸,还是很有礼貌地说:“你知道,这是你们的错。”其他人也很礼貌,给彼此让开地儿,不怎么咒骂车辆。大使馆的一个年轻秘书某天晚上骑自行车回家,有个人骑车追上她,转头面向她唱了一首不知所云但很好听的歌,然后掉头走掉……
不过,因为一次交通事故,卜励德很快返回了美国,憾别北京。此后,他担任过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驻巴基斯坦大使、美国亚洲协会主席等。不过,作为费城交响乐团与中国的“中间人”,他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重返中国
卜励德与费城交响乐团和中国的关系,被中美两国的关系所影响。1980年代末,随着中美关系紧张,卜励德与费城交响乐团已无可能重返中国。1992年,两国关系缓和,中美双方提出费城乐团再次访华,以示“融冰”,此次访华克林顿支持,江泽民题词,规格很高。
1993年3月,昔日的中国问题专家卜励德终于重返中国。两个月后,费城交响乐团也在时隔20年后,来到中国演出。此次访华,与首次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一样,都属于高层政府间促成。
2003年,费城交响乐团再次来到中国,此后多年,他们频繁来中国演出。而这些演出,更多与政府无关,属于纯粹的音乐合作、商业演出。卜励德多次随乐团访华,费城交响乐团仍然信任卜励德,卜励德帮他们与中国洽谈。作为文化交流大使,他的作用无可替代。
卜励德很了解中国,此时的中国与1973年已经大为不同。中国政府在弘扬软实力,庞大的剧院一座座建起,剧院需要高水平的演出。卜励德建议费城交响乐团展开中国驻站计划,进行多种交流,确保合作的深度和广度。
2010年,费城交响乐团在上海世博会开幕式上表演。费城交响乐团新上任的团长艾莉森对卜励德提到,希望在将来能和中国展开更加深入的合作。这次合作不只是乐团和乐团之间的合作,更多的,是商业诉求。
在此之前,费城交响乐团在美国的经营遇到问题,因为观众数量骤减、经营不善,这个昔日的老牌乐团步履艰难。2011年,费城交响乐团申请破产保护。不过,即使如此,在中国的驻站计划却没有终止,不仅签下了2012年的试点,还“酝酿”着更宏大的未来合作。
2012年4月,费城交响乐团宣布安全度过破产保护,5月底,即赴中国进行为期10天的“试点”驻站。
2013年,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启动了正式5年驻站计划的首秀。
费城交响乐团赴中国的雄心令美国媒体人不解,卜励德给出了答案:在过去的15年,中国如雨后春笋爆发出近80所音乐厅和剧院,城市和城市之间争相比较谁的建筑更绚丽,但音乐厅都缺乏世界级乐团的表演,因而又展开了对顶级乐团驻站名誉的争夺。
事实也证明了卜励德的判断,过去几年了,费城交响乐团在中国的演出售票状况一直不错,“尽管他们可能不是完全理解,其实在美国也是一样。但我相信他们是真的喜欢交响乐,而且对交响乐的理解也在进步。”
就这样,广阔的中国市场成了费城交响乐团沃土,乐手们频繁穿梭中国,他们的音乐奏响在中国的剧院中,也奏响在停机坪上等候了七个小时的飞机上。
那段在微博上流传的即兴演出的视频背后,是40年的积淀与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