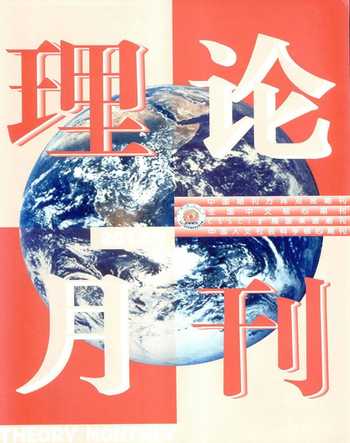论住房权及其立法保障
黄辉明 潘艳红
摘要: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第二代人权是二战后西方国家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第二代人权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住房权作为第二代人权被国际公约提出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立法保障,成为政府的法定义务。近年来,随着我国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故应该加强对住房权的重视和立法保障。
关键词:积极人权;社会权利;住房权;立法
中图分类号:D9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3)01-0082-04
近年来,随着住房市场化的过度推进,对于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保障严重缺位,高房价和住房问题日益演变为重大的民生问题。造成这種局面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对住房权作为基本人权的认识不足应该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必须加强对住房权的认识和立法保障。
一、作为积极人权的社会权利
在人权发展史上。有“消极权利”(negative rights)和“积极权利”(positive rights)之分。启蒙运动所提出的以个人自由和财产权为核心的自然权利,即“第一代人权”概念,属于消极权利。消极权利是指个人反对国家政府权力的权利,奉行不干涉原则,政府被认为只承担“守夜人”的角色,不可恣意妄为,干涉个人自由。第二代人权是西方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影响下迫不得已在某種程度上承认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权利,人们又称第二代人权为积极权利,因为这一代人权不再保护个人反对政府干预的权利,而是要求政府作有利于个人平等的积极干预。由守夜人转变成福利国家。
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大师,洛克可以说是第一代人权概念的奠基者。洛克为人们描绘了一个完美无缺的自然状态,认为自然状态乃自由、平等的状态。他说:“那是一種完美无缺的自由状态。他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并且,“这也是一種平等状态,在这種状态中,一切权力和管辖权都是相互的,没有一个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洛克认为自然状态虽然是自由状态。却不是放任的状态,它受自然法即理性调节。“自然状态有一種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理性,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这里,洛克提出了著名的四大古典自然权利,即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和自由权。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揭起人权的旗帜,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以“人权”反对“神权”和“君权”,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并以宪法和法律确认了这些基本人权。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成果就是对消极权利的确认。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1776年美国的《独立宣言》首先将“天赋人权”写进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权宣言。该《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建立政府”。1789年法国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则宣布:
“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天赋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这些权利是:自由、财产、安全以及反抗压迫。”此后,各国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人权相继被载入宪法,成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重要内容和象征。
虽然第一代人权概念对推翻封建专制功不可没,然而,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人们看到资产阶级所谓“自由、平等”的理想人权在现实中变成了贪婪的资产阶级特权。近代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体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权问题,普通公民缺乏享有基本权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保障;个人自由和财产权利并未能使人的尊严受到普遍的尊重;为保障人权而建构的政府体制并没有满足全体人民的权利诉求。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日益贫困。社会矛盾尖锐。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思考人权的深刻含义,反思不干涉主义,宪法不仅仅应当防止国家“积极作为”带来的侵害,还要避免国家“消极不作为”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在公民政治自由权领域,国家权力处于消极不作为状态,而在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方面,国家权力应当处于积极的作为状态。人权观念发生了社会化转向,产生了第二代人权概念。这些权利属于积极权利,成为国家的义务,应该得到政府的大力保障。以使得人们平等地享有人权。
雅克·马利旦就是战后新人权理论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人权的理性基础就是自然法,但是这種自然法不应像以往的思想家那样规定。自然法既是人类本性所要求的理想的东西,又是随着人的道德良知和社会经验的发展而发展的东西。由此出发,马利旦认为人权在新的条件下,应该包括和反映新的内容:“人不仅有作为一个人格的人和公民社会的人的权利,而且还有作为从事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社会的人的权利”,即人又拥有一系列新的社会权利,包括工作权、组织工会权、取得公平工资的权利、取得救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基本保险的权利,等等。而且,马利旦认为,新人权与旧人权是兼容并蓄的,两種人权之间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因为任何人权都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至少就这些权利的行使来说,是有条件的和受限制的。国际社会的一系列重要的人权公约,就是在这種思潮的推动下作出和签署的,而且马利旦本人参与起草了其中许多重要文件。
因此,二战以后,在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下,1948年联合国通过并发表了《世界人权宣言》,这是第一个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件。1966年联合国又通过并发表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这几个文件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和尊重,成为当代国际人权保护的基石性法律文件,被誉为“国际人权宪章”,在第一代人权的基础上确认了“第二代人权”。《世界人权宣言》纳入了积极人权标准的重要内容——福利主义主张。第22条规定:“每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有权享受社会保障,并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所必需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各種权利的实现,这種实现是通过国家努力和国际合作并依照各国的组织和资源情况。”
可见。第二代人权观点与第一代人权观点有了很大的不同。人权有了新内容,增添了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权利。这些权利包括:社会安全的权利、工作权和休息权、受教育的权利、生活保障的权利、参与文化生活的权利等。因而从纯粹个人的权利走向了社会化。很明显,这些权利不是保护个人以对抗政府或其他当权者的。反而要提请国家干预以保证每个人自由得以实现。后者可以说是实现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必要手段,这些权利赋予人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也就是说,它们将人从阻碍其作为人全面发展的限制和约束中解放出来。尽管这些社会性权利与古典的自然人权有着显著的不同,但为了所有的人都成其为人,要求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是完全正当的。而且,第二代人权与第一代人权并不是完全割裂的,第二代人权是实现第一代人权的基础。即自由的物质基础。
二、住房权概念的提出和界定
住房权属于第二代人权的范畴,住房权概念源自国际人权公约中“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的表述。自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宣布以来,大量的国际文书明确承认了住房权。
《世界人权宣言》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宣布:“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a standard of living adequate for the health and
well-heing of himself and his
family.including food,clothing,housing and medical care andnecessary social service”,即“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本人和家庭的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和必要的社会服务”,并在遭到失业、疾病、残废、守寡、衰老、或在其他不能控制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有保障。1966年《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进一步阐述并重申住房权。该《公约》第十一条第一款宣布:“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Covenant recognize the right of everyone to an adequate standard of living for himself and his family,including adequate food,clothing and housing and to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living condition”,即“本公约缔约国承认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并规定各缔约国将采取适当的步骤保证实现这一权利,并承认为此而实行基于自愿同意的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可见,这两个国际人权文件是在生活权(adequate living)的基础上提出住房权(adequate housing)的。但第一次单独将住房权“adequate housing”一同全面普及开来的是1991年12月12日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通过的《General Comment No.4(1991)The Right to Adequate Housing》,即《第四号一般性意见:住房权》。这是联合国系统第一次全面的运用了“adequate housing”一词,也正是因为这样一个文件使得住房权(或译适足住房权)在人权体系中被清晰界定并广为普及。
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976年生效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实施。由于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和人权委员会都任务繁重,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处理《公约》要求的各个国家提交的各種报告。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专门成立的"32作小组”由于政治分歧并没有起到预想的作用。所以,经济和社会理事会就于1985年决定设立一个独立的机构来帮助理事会“审查”国家报告。这个机构就是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它由18名专家组成,他们以独立身份参加会议。委员会工作方式除了报告审查以外,另一種工作方式就是“规范化发展”。其核心意思就是为理解公约提供一个“精确标准”。为此,委员会采取了颁布“一般性意见”的做法以阐述委员会自己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实体以及程序方面的理解。自委员会成立以来,已颁布了8项关于实体性权利的一般性意见,其中1991年12月12日颁布的《第四号意见——适足住房权》是第一个关于实体性权利的一般性意见。这主要是因为委员会在开始工作后,发现住房权是社会权利中较为重要的一種权利,而且发现人们对这一权利的认识很模糊。所以,委员会就致力于为人们的理解提供一種统一认识的基础。经过广泛讨论和研究,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于1991年12月12日通过的《第四号一般性意见:适足住房权》中对“适足住房权”的概念进行了全面的和权威的解释。
《第四号一般性意见》的第八条认为:“因而适足之概念在住房权利方面尤为重要,因为它有助于强调在确定特定形式的住房是否可视为构成《公约》目的所指的‘适足住房时必须加以考虑的一些因素。在某種程序上,是否适足取决于社会、经济、文化、气候、生态及其他因素,同时,委员会认为,有可能确定在任何特定的情况下为此目的必须加以考虑的住房权利的某些方面。”这些方面包括:
(a)使用权的法律保障。
(b)服务、材料、设备和基础设施的提供。
(c)力所能及。与住房有关的个人或家庭费用应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不至于使其他基本需要的获得与满足受到威胁或损害。
(d)乐舍安居。适足的住房必须是适合于居住的和安全的。
(e)住房机会。须向一切有资格享有适足住房的人提供适足的住房。
(f)居住地点。适足的住房应处于便利就业选择、保健服务、就学、托儿中心和其他社会设施之地点。
(g)适当的文化环境。
由此可见,住房权的含义是指人们有权获得住所,并能够有尊严地居住的权利。
也就是说,住房权首先是指人们“住有所居”,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栖息之所。
其次,居所必须满足一定的居住条件,适合居住。在这个栖身之所,他(她)能健康安全便利地生活而不受外界干扰,不论这个栖身之所的住房是他(她)自己购买的,还是租用的,或是政府廉价或无偿提供给他(她)的。
再次。住房权的实现形式包罗万象,包括租用(公共和私人)住宿设施、合作住房、租赁、房主自住住房、应急住房和非正规住区,包括占有土地和财产。然而不论使用的形式属何種,所有人都应有一定程序的使用保障,以保证得到法律保护。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
最后,住房权是对政府的权利,政府有义务为公民提供合适的住房和改善居住条件。
三、住房权的立法保障
由于第一代人权是为了反对政府专制权力的消极人权,因此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后所制定的近代宪法,如美国1787年宪法及其的权利法案和法国1791年宪法。一般都未提及住房权。战后,随着二代人权概念的提出和国际人权公约的倡导,一些国家纷纷在宪法里确认了住房权,或制定了专门的住房法律保障住房权。因此,住房权不仅被宪法确认为公民的法定权利,而且成为政府的保障义务,政府必须创造条件满足人们的住房权。
1978年《西班牙宪法》在第一章“基本权利和义务”第三节“社会和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第47条规定:“所有西班牙人有享受应得的和适当的住房的权利,公共权力根据总体利益协调地皮的使用,避免投机,创造必要条件并制定有关规定以使该权利付诸实现。社会分享公共部门在城建工作中的剩余价值。”1993《俄罗斯联邦宪法》第40条规定得更为详细:“(1)每个人都有获得住宅的权利,任何人不得被任意剥夺住宅;(2)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自治机关鼓励住宅建设,为实现住宅权创造条件;(3)向贫困者或法律指明的其他需要住房的公民无偿提供住宅,或者根据法律所规定的条例由国家的、市政的和其他的住宅基金廉价支付。”《南非共和国宪法》第二章明确规定“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其中第26条其第1款规定:人人有权获得适当居所,第2款规定:国家必须在现有资源的范围内采取负责任的立法措施和其它措施,以逐渐实现这项权利。第3款规定:未经法院审理所有有关情况后发布命令,不得将任何人驱逐出自己的家或者将他们的房屋拆毁。任何法律均不得允许任意驱赶。1982年葡萄牙宪法、1999年芬兰宪法、2004年瑞士宪法也都有住房权的规定。
公民住房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人权,由宪法加以确认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因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权威和最高的法律效力。没有宪法保障。任何人权保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些国家的宪法虽然没有明确地规定住房权,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住房权的否定。因为在这些国家,最高法院拥有宪法解释权。可以通过运用特有的宪法理论和有效的司法审查机制。保护主要通过适用和解释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来实现对住房权的间接保护,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一些国家进而通过制定具体的住房保障方面法律来保障公民住房权,如美国的《住房法》、《住房与城市发展法》;德国的《住房建设法》、《住宅促进法》;日本的《住房金融公库法》、《公营住宅法》、《日本住宅公团法》;新加坡的《建屋与发展法》等,为公有住房权的落实与实施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虽然我国宪法确认了公民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但我国宪法未明确提及住房权,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它表明我国对住房权的重视还未提高到根本法的高度。虽然宪法第39条规定了“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但这显然属于第一代人权概念,反对政府公权力的消极人权范畴,而不是住房保障意义上的积极人权范畴。近年来,宪法的修改不断加强了对人权的保护。特别是2004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首次以根本法的形式承认保障人权是国家的基本义务,这是我国人权事业的巨大进步和里程碑事件。住房权作为基本人权,应该得到宪法的确认和保障。
我国政府于1997年10月27日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2001年2月28日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加入该《公约》,2001年6月27日,《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自批准《公约》以来,中国始终根据本国国情,有计划、有步骤地实现《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2003年6月27日,中国如期向经社文权利委员会提交执行《公约》情况的首次报告。2005年4月27日至29日,委员会正式审议中国履约报告。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国履行《公约》报告的“结论性意见”,对中国贯彻公约方面工作予以积极评价。同时也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服务、住房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保护、贩卖妇女和儿童以及遗弃老年人等问题表示了关注。委员会还提出相关改进建议,希望中国政府在下次定期报告中列出国内生产总值用于教育、卫生和住房计划的比例。足见委员会对我国住房权问题的关注。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但公民住房权没有入宪。目前也还没有制定住房保障方面的法律。因此,通过宪法和立法方式保障住房权也是我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经济、社会和文化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联合国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基础上通过的两个姐妹公约。因为世界人权宣言内容包括第一阶段的公民和政治权利以及第二阶段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由于两个阵营的对立,再达成一个同时包括两阶段的公约是很难在国际上达成共识的。另外,像资本主义的美国会比较关心公民和政治权利,而社会主义国家则偏向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解决这个问题。于是撰写了两份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有义务履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不能让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福利走在我们的前面。因此,我们应该顺应时代潮流,积极主动地修改完善现行宪法,在根本大法中明确规定住房权,通过宪法保障公民住房权,引起人们和政府的足够重视,从而指导进一步具体构建中国的住房保障制度。
公民住房权入宪,这只是住房权保障的第一步,并不意味着公民住房权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了。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要转变为实有权利必须要构建的具体的法律制度。在当下中国,宪法权利还处在宣示的层面,不具备直接可诉性,宪法还不能直接司法化而作为诉讼和裁判的依据,我国的司法机关还不能直接适用宪法基本权利的条款。也就是说法院还不能受理宪法权利诉讼。因此,我们应该在宪法对公民住房权保护的指引下,建立起可操作的以公民住房权为核心概念的《住房保障法》。目前,《住房保障法》已被列入11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规划,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负责该法的起草工作。显然,住房保障法的起草如果缺乏宪法住房权的指引和制约,其合宪性值得质疑而缺乏效力根据。
“住有所居”自古以来是中国人以一贯之的要求和理想,但由于过去生产力的落后和剥削制度的缺陷,这一理想对劳苦大众来说始终难以实现。今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当家作主,“住有所居”有了现实可能性,成为人民政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目标。目前,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住房权,解决公民住房问题,抑制投机性购房需求,促进房地产市场的稳定,我们应该通过修改宪法明确对公民住房权的保障,并且以之指导尽快制定《住房保障法》,提供“广厦千万间”,让“天下寒士俱欢颜”,使得“风雨不动安如山”,这是国家和各级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在尊重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宪法精神指引下,切实加强公民住房权保障,努力实现人人“住有所居”,让百姓安居乐业,高房价问题不攻自破,和谐社会不远也。
责任编辑 肖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