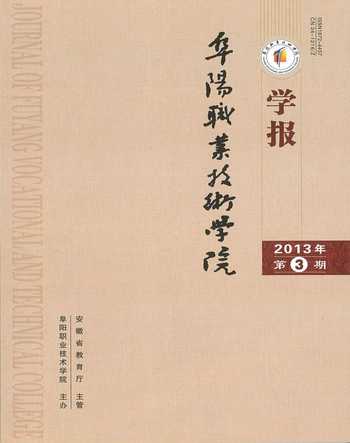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及其创新
丁立山
摘要:回顾20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的历程、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中国的纪录片,在“客观与再现”的创作理念下走向世界,又在“主观与表现”的创作理念下走向新的成功。同时,纪录片的创作者也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拓展视听的表现上有所追求,有所创新。纪录片创作的视点与视角是创作者首先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纪录片;创新意识
中图分类号:G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437(2013)03-0097-03
纪录片从诞生至今,虽然经历了不算太长的时期,但是,它却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程度。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较西方起步较晚,现阶段也已经呈现出兴旺的态势。
一、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发展历程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演进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解放后到80年代后期的格林尔逊式即画面加解说式纪录片,二是90年代以来的真实电影式即观察式纪录片。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是教化与指导。此时的纪录片的创作特征是:
1.重视文本根据作品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事先设计完整的“文本”,作为拍摄的基础。
2.依赖解说借用广播的语言,通过播音或解说,将思想直接灌输给观众,达到耳提面命的说教目的。
3.声画分离解说为主,画面为辅,多是声画不搭界,构成简单的“声画两张皮”的节目形态。严格地讲,这种纪录片的创作,与其说是纪录生活,不如说是揭示思想、宣传观念。对广大电视观众进行思想教化和行为指导。在其“形象化政论”的影响下,导致中国的纪录片维持了30多年的画面加解说的模式。尤其在“文革”期间,该模式大行其道,阻碍了多种艺术表现形式的探讨与追求,产生了内容单调、主题僵化、选材面窄、形式单一和表现公式化,“声画两张皮”的弊端。这一时期的电视纪录片《收租院》《丝绸之路》《话说运河》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纳入“思想教育节目”之中,或“通过介绍革命历史和先进人物事迹进行思想教育”,或“通过介绍锦绣河山和建设新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在第二个阶段,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发生重要变化,其创作理念是客观与再现。此时的创作特征是:
1.纪录过程生活本身体现为一种过程,电视纪录片一般以时间为顺序去纪录正在行进中的、未知生活结局的过程。在跟踪拍摄的过程中,就会跟出人物、跟出情节、跟出故事,完成客观再现真实生活的任务。
2.现原生态。电视纪录片开始重视纪录生活的原生形态,对真实的生活,不做太多的雕琢,不做太多的精粉饰,尽量保持生活的原汁原味,记录带毛边的生活。
3.声画并重我们生存的世界,通过光波的流动,传播图像;通过声波的流动,传递声音,这才有了我们这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因此,以记录生活为己任的电视记录片,当然不能忽略生活之声的记录。这声音,体现为“同期声”:当事人的现身说法;“现场声”:在屏幕上再现生活。故而有人说:电视纪录片“视同期声为艺术生命”。
二、中国纪录片的创新
1.创新与突破
出于对主题先行模式和“假、大、空”的反叛,纪录片走向了“新现实主义”,即主张真实描述人们生活的原生态,用小角度、情节化的描述来展现生存状态。在这方面,大型纪录片《望长城》作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探索。这部纪录片采用了“设定中心线法”的拍摄手法。所谓“设定中心线法”,就是在众多的被摄对象和拍摄素材中,依据作者的创作意图推出一条明晰的线路,使创作者和电视观众都能对此一目了然。整部作品以长城为贯穿始终的中心线,在这条中心线上系起了一个又一个长城两边中国人的故事。主持人在片中的出现,强化了观众的视觉感受,坚固了中心线的突出地位。《望长城》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领域里,做出了全方位的整体性的突破和创新,一位电视理论家称它为屏幕上的革命。《望长城》的创新首推同期声的“彻底”运用。总编导在策划阶段就明确提出“节目要创新,首先在声音上要有突破”。这时期,中国纪录片才开始在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创作水平等方面与西方优秀纪录片有了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架起与国际思维模式相一致的话语体系,并在亚广联等国际大赛中频频获奖。它在中国纪录片演变的进程中,给沿袭已久的“画面配解说”形态划上了一个明确的句号。之后一大批优秀作品脱颖而出,但把“新纪实”运用到极致并取得巨大成功的是央视《东方时空》中的《生活空间》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题材、拍摄方式的把握上以单一、简捷为主,注意抓取一段或几段有意味的生活流程,加以“过程化”的表现,使细节放大,过程“浓缩”,使“结果”在“过程”的展示中,逐渐地明晰、突现出来,使人感到顺理成章。
中国的电视纪录片创作,全方位地踏上了“客观与再现”的创作理念之路:如《沙与海》、《藏北人家》、《最后的山神》、《深山船家》,都是坚持“客观与再现”的创作理念而走向世界的。正是由于这些作品的创新意识,将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推向了高潮,故而有人将其称之为中国新纪录片运动。
2.“主观与表现”的创作理念
这种“主观与表现”的理论基础,一是台湾纪录片研究学者李道明所说:“纪录片一般是指有个人观点去诠释世界的,以实有的事物为拍摄对象,经过艺术处理的影片。”一是英国葛里尔逊的观点:“纪录片是对真实的创造性的诠释。”
在这种创作理论的指导下,纪录片创作者的主体意识,主观思想大大地提升,通过屏幕展现的客观事物来阐释创作者主观的思想感情、观念意识。这样,中国电视纪录片的创作理念,从纪录片的客观、再现原则,走向了主观、表现原则:
这种主观、表现原则的创作特征是:
(1)符号语言。较多的运用暗示、象征、对比、强化、隐喻等符号语言、修辞手段,寄寓个人的情思,抒发创作者的主观情感。
(2)寄寓含意。创作者赋予客观存在的事物以深刻的含意,具有了较强的可读性,进而激发观众的联想和想象思维,引发观众再创作的能力。
(3)理性印证。创作者所选择和记录的事物,都化作了创作者的主观思想、个人判断被印证、被阐述的过程。
遵循这种主观、表现创作理念创作的代表人物,当首推刘郎和张以庆。张以庆的电视纪录片《英与白》揭开了“主观与表现”创作观念的序幕,他将一只熊猫、一个人、一台电视机构成了一种生活存在,同时也作为一种载体承载了一些对生活现象背后的思考。
3.纪录片在拓展视听表现上的创新
由于韵律、色彩、运动和声音等都是画面整体布局的促进因素,它们每项元素都具有丰富细腻的变奏力和触媒性,同时,画面之间产生的无限联想与象征更是变幻莫测。从视听表现的美学本体论来说,影像构成的每种元素都具备拓展表现的可能。这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并无定式可寻。
纪录片既是对真人真事的真实纪录,又是由编导完成的一次新的创作行为。对应故事片编导所从事的“虚构性创作”,纪录片编导的创作行为可定性为“纪实性创作”。这种创作通常包括两个步骤:首先是有选择地采集原生状态的生活素材,然后是创造性地提炼、整合所拍摄的素材,借以构成具有艺术形式的视听文本,向观众提供一种包含审美价值的情感体验。在纪录片创作中,摄影机不仅仅是记载客观现实的纪录机器,亦是受创作者主观掌控的表意工具。摄影机镜头作为人眼的延伸,所有纳入摄影机取景框的外界物像都在创作者调控之下,诸如景别大小、角度变换、镜头运动、延续时间等因素,无一不受到创作者自身的价值判断、情感倾向、审美意趣以及操作手段的影响。所以,创作者应当具有创新意识,也应当允许创作者把自己的真情、激情与艺术个性融入作品,创作出风格迥异的作品,让中国的电视纪录片走向世界。
三、纪录片创作的视点、视角
1.视点
所谓视点是指纪录片创作者在观察、记录和体验拍摄对象时所采用的叙事角度和方向,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概念:一是从技术层面上讲,存在于各个镜头序列之中的机器拍摄视点;二是从创作理念上讲,创作者结构与表现视听文本的出发点。明确创作视点是纪录片工作的首要之义。
纪录片是对人物进行点、线、面的观照与思考,时间和空间从来都是作为创作的元素来结构叙事,生成文本,如果没有一定的空间范围(即主人公的生存外壳)贯穿人物行为,依托纪实进程,人物的型塑将流于平面,直接导致人本观照的社会坐标体系迷失,涉及主客体的互动全无,纪录片真实美学的流动韵律也将丧失殆尽。只要人类还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人事纠葛的乱絮之中,以标榜关注人的纪录片创作,就必须从还原人的生存外壳开始。
纪录短片《垄山映》,反映的是一个一家两代人修路的动人故事。在本片中,母亲一生修路的故事只是人物生活中单调的一条线索,只反映了她征服自然、坚持不懈的人生追求,但一旦还原人物的生存外壳,真正关注除去英雄主义色彩的真实的个人时,我们见到了儿子对母亲修路复杂的情感与态度,围绕资金问题家庭里所产生的矛盾等等。这便是生活固有的两面性。只有还原个体人的真实的生存外壳并予以平等观照,纪录片才能忠实于人物复杂矛盾的天性,复现个性鲜活的真实魂灵。
2.视角
视角,是一种发现,是主体思想的体现。纪录视角的改变使纪录对象的自在进入主体世界的理解性存在。从电视纪录开始的电视活动,如果在其纪录过程中能够改变审视纪录对象的视角,那么生活本身就有可能将主体既有的诠释予以反正,使原本看似无趣的东西变得意趣盎然或见微知著,进而获得艺术生机;也就有可能将其他艺术对生活的诠释反正为电视艺术对生活的诠释,将其他艺术的创造变成电视艺术的创造。“事物更可见,不是靠更多的光线,而是靠我注视的新角度。”电视纪录作为起点,其发展过程始终是一种“正在进行时”状态,这意味着纪录过程蕴含了纪录主体审视对象的多向度自由。视角的自由,实质上是心灵的自由。纪录对象有其存在的自然状态,而纪录主体有其审视对象的自由状态。对象的自然存在可能没有意味,但不同的审视角度却可能激发其意味的生成。
电视纪录,始终存在着主体视角同纪录对象自在状态的碰撞、冲突。不是主体从纪录的过程中去发现新视角并将新视角作为纪录轴线一以贯之;就是主体将自身对世界的主观理解变成纪录的中心,让纪录围绕对理解的表达而展开。前者,电视纪录是电视艺术创造的本体;后者,电视纪录是说明主体理解的材料。两者实质上正反映出主体诠释观念和纪录观念的持久交锋。在这种情况下,以纪录视角控制纪录过程是解决这一冲突的最好途径i纪录视角的改变不等于纪录对象的改变,但会让纪录对象离开其自在状态而进入理想状态——纪录过程从纪录对象枝节横生的自在状态中分离出来,集中于对象与主体的精神世界能够形成同构的方面。纪录片《龙脊》摄制组去广西龙胜民族自治县采访之前打算对那里实施“希望工程”的先进典型加以反映。但摄制组到了那里后,发现所谓的先进典型远不如现实的触目惊心更令人难以拒绝。那个小山村,坐落在一座名叫龙脊的大山里。纪录视角的转换和以此为推进逻辑的纪录过程,把“龙脊”的名称反正为对那片土地的新的诠释一一那些普通到也许永远不会为外面的世界所知道的师生正是支撑起现实生活的“龙脊”。
由此可见,纪录视角的变换能够让生活本身对主体关于对象的成见得到反正。成见是每个人在一定的个人经验、文化修养、生活环境影响下形成的观察、思考问题的习惯性角度和方法,它往往成为把握事物的先在定势和局限。艺术创造,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突破成见,提供认识对象、把握对象的新角度、新方法,亦即新鲜思维方式。从电视纪录开始,意味着纪录主体对现实时空的直接面对、审视和介入,这使得纪录主体可能直接从纪录对象本身出发,寻找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从而使关于纪录对象的成见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