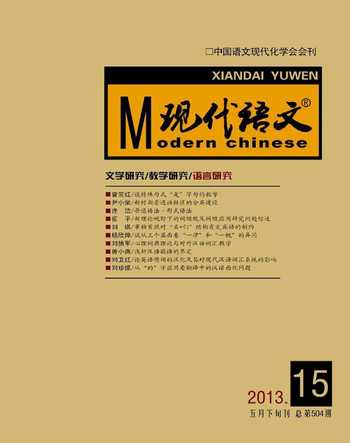《马氏文通》“动字相承”评析
摘 要:《马氏文通》“动字相承”的语法观念及研究方法主要体现在句法形式的突显、特殊句式的观照以及词性及其语法功能的探讨等诸多方面。马建忠充分借鉴西洋语法,不仅注重汉语的句法形式,同时也不忽略语义,这对后来的学者在某些实词、虚词、句式以及篇章的研究上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马氏文通》 动字 坐动 散动
一、前言
清人马建忠所著的《马氏文通》(以下简称《文通》)是我国第一部汉语语法学专著,它的问世开创了汉语语法学的新纪元。马建忠学贯中西,借鉴泰西语法创建了系统完备的古汉语语法体系。一百多年来,《文通》所体现出的语言观、语法观以及研究方法无不指引着后世学者的汉语研究道路。《文通》中随处可见马建忠超群的智慧以及他深邃的治学眼光,诸多论述在今天看来也颇具学术前瞻性,其精辟的论断及独到的见解令世人折服。在“动字相承”一节中,马氏仿照西洋语法,主要从语法功能上把动字(动词)分为“坐动”与“散动”。“一句一读之内有二三动字连书者,其首先者乃记起词之行,名之曰坐动;其后动字所以承坐动之行者,谓之散动。散动云者,以其行非直承自起词也。”
(1)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求贤诏》)①
(2)而谋动干戈于邦内。(《论语·季氏》)
(3)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4)季氏将伐顓臾。(《论语·季氏》)
以上例句中,句子若有多个动词,则位置居先者为坐动,后为散动,如例(1)的助动词“能”为坐动,“尊”“显”为散动;例(2)的“谋”为坐动,“动”为散动;例(3)的“恐”为坐动,“王之不好勇”一般被认为是小句作谓语动词“恐”的宾语,其中的“好”是全句的散动;居如者果一个句子只有一个谓语动词,那么其为坐动,如例(4)的“伐”。
结合《文通》的论述,学者们一般认为“坐动”主要指的是句子的核心谓语动词。“散动”主要是指非核心谓语动词,类似于英语语法中的动词不定式、分词、动名词以及英文语法中从句的动词。(宋绍年,2004)
在马氏的体系中,散动以及所在的动词短语可以用如止词(宾语)、起词(主语)、表词(形容词谓语或名词谓语)、司词(介词宾语)、偏次(大致相当于定语)等等。他看到了汉语中动词及动词短语具有多种语法功能,在句中可以充当多种语法成分。
对于《文通》中的“坐动”与“散动”,学界褒贬不一。汉语中没有类似英语的不定式、分词等,一些学者认为此类术语没有提出的必要,因此它们在后来的语法学著作中便销声匿迹了。这里我们讨论的重点并不是该术语在语法学界的流变问题,也不是要对这两个术语进行明确的辨析和区分。我们想探讨的是,尽管坐散两动的提出表明马氏的确借鉴了西方语法学,但他不是一味地简单模仿,而是从汉语实际出发寻求创新和突破,其语法观对我们现在的研究仍然具有启发意义。他在词、短语、句子甚至篇章等多个语法层级的探讨都为后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有关“坐动”“散动”体系的价值,学者多有论及。卢烈红指出:“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动词区分方法……只依据它们在句读中的语法功能”;此种区分的理论“可以运用于句子结构的分析”等。陈庆汉认为“‘坐动与‘散动的提出从客观上揭示了汉语动词的多功能性”。宋绍年认为“坐动”与“散动”这对概念提供了构建汉语句法系统的基础,并且“散动”概念是《文通》“读”理论的基础。王海棻(2000)、李春晓(2003)看到了马氏的层次分析观念。以上研究成果在此不需赘言,“动字相承”的语法观念以及研究方法还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体现。
二、句法形式的突显
马建忠具有很强的语法观念,这与传统小学的语法研究全然不同。他从语法功能的角度来区分“坐动”与“散动”就可窥见一斑。马氏在阐释几个动字相承的部分时,从句式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为“V1+V2”。V1是坐动,可以是助动字,也可以是有形动字;V2是散动,后乎坐动。如:
(5)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论语·季氏》)
(6)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孟子·梁惠王下》)
另一种情况为“V1+N+V2”,即“承读”一说。“或不然,而更有起词焉以记其行之所自发,则参之于坐散两动字之间而更为一读,是曰承读,于是所谓散动者,又为承读之坐动矣。”换言之:“坐动1+承读[起词+散动(坐动2)]”
(7)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孟子·公孙丑上》)
“见”字坐动,“人”字起词也,“入”字第二动字,上承“见”字,“孺子”为“入”字起词,“孺子将入于井”六字承读,即目见之事也。
“见”是整个句子的核心谓语动词,谓之坐动;后面的“入”是非核心谓语动词,谓之散动。但从“孺子将入于井”这个承读来看,“入”又是它的坐动,动词“入”具有双重身份。
《文通》接下来用句法形式来统摄具有不同语义范畴的动词的句子。除去“位移动字+散动”属于动字相连而不属于动字相承以外,其他几类句子具有某些相同的句法形式,主要分为:“感官动字+散动”“心理动字+散动”“请+散动”“使令动字+散动”等式。
(一)感官动字+散动
“凡动字言官司之行者,如耳闻、目见、心知、口述之类,则有承读以记所闻、所见、所知、所述之事者,常也。”主要句式和例句如下:
1.V1+N+V2
(8)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2.V1+V2
(9)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孟子·尽心上》)
例(8)中的“见”为坐动,“师”为起词,“师之出”为承读,“出”为散动,“而”后结构与前亦然。例(9)“爱”“敬”直承“知”,是坐动与散动紧随的情况。
(二)心理动字+散动
“凡动字记内情所发之行者,如‘恐‘惧‘敢‘怒‘愿‘欲之类,则后有散动以承之者,常也。” 主要句式和例句如下:
1.V1+N+V2
(10)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左传·成公十三年》)
2.V1+V2
(11)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
从《文通》所举的示例来看,“心理动字+散动”与“感官动字+散动”类似。需要注意的是“敢”“怒”“愿”“欲”等几个词的词性问题,后面会有所讨论。
(三)请+散动
“‘请字之后,其承读起词如为所请之人,往往置先‘请字。”主要句式为“N+V1+V2”。
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此类句子的语法形式有别于前面所讨论的内容,是否是马氏疏忽了?请看下面的例句:
(12)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孟子·梁惠王上》)
《文通》指出“王请无好小勇”类似于“请王无好小勇”。“王”是所请之人,应是“请”逻辑上的动作的接受者。整个句式比较特殊,把“王”提前了。如果我们按照句子的逻辑语义改变其语序,以“V1+N+V2”来理解句意也未尝不可。
(四)使令动字+散动
“‘使字后有承读,以记所使为之事,常语也。”马建忠在此把“使”分为动字和连字,关于它们的不同用法后面将会提及。主要句式为“N+V1+V2”。
(13)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孟子·公孙丑下》)
这四类句子中,虽然核心动词的语义范畴各异,但从句式来看却有共同性,都是坐动后承以散动的情况,特别是有马氏所强调的“坐动+承读”句式。马氏从庞杂的语料中析出这些语法现象绝非易事,并且“不以分类和举例为满足,他要尝试指出其中的规律”(吕叔湘,2009)。因此,“动字相承”的体例与内容体现了作者对句法形式的认知高度,同时也突出了以动词作为句法核心的研究方法,这与后来以至当今占主导的汉语语法研究相契合。马氏对汉语的研究绝不是照搬西方语法,也不是仅注重意义,是语言形式与意义的有机结合。
三、特殊句式的观照
“动字相承”对一些特殊的句式给予了观照,马建忠的观点相继被后来的学者们所继承和推阐,如兼语句、使字句、连谓句等。
(一)兼语句
在以上举出的承读式中,现在一般把V1是使令类动词的句子看作兼语句。王海棻认为:“《文通》把这类句子和‘[一般]动字+承读的句子完全等同起来,恐未必妥。后来的语法书把‘使[令]+承读称兼语式,而把另一类叫做小句作宾语。这两类句子的区别在于:‘兼语式的句子,兼语和它前面的动词结合得很紧,中间不能停顿,也不能加副词或副词性的修饰语。(《现代汉语语法讲话》)马氏将二者混同,是分类不细的表现。”她认为马氏的分类过于宽泛,感官动字、心理动字等后面跟承读不是兼语式,而是主谓短语作宾语,或者说坐动后面跟的是宾语小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马氏为何要把这些不同语义类的动词都放在一起讨论?兼语结构和动宾结构如何进行有效地区分?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否应遵循同样的标准?
首先,从句法形式来看,兼语句式和主谓短语作宾语极为类似,都是“V1+N+V2”。
(14)使人给其食用,无使乏。(《战国策·齐策》)
(15)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孟子·公孙丑上》)
(16)愿夫子辅吾志。(《孟子·梁惠王上》)
(17)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上》)
若按现在的观点,只有例(14)才是兼语结构,其他则为小句作宾语。
傅书灵曾着重谈及兼语结构与动宾结构。他认为兼语结构具有包容性,在“V1+N+V2”式中,V1为“看见”“听见”“愿意”等也可以把它们看作兼语式。文中曾举出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认为宾语小句的动词和带兼语的动词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有交叉。以下是赵先生的例子:
(18)我看见他在那儿写信。(两解)
(19)我听见他唱的很好。(两解)
(20)我愿意你别那样儿聋。(两解)
赵元任认为:“语音有时能帮助解决:‘他不念轻声,是小句作宾语;‘他念轻声,是兼语标志。”
可见兼语式与宾语小句可以根据语音停顿和轻重来区别。现代汉语尚可如此,但古代汉语只保留了文字书面语料,我们无法探知语言在实际交际中所传达的信息。仅从形式来看,它们的区分的确不是绝对的。这也是马建忠把诸如此类的句子归纳于此的原因。
其次,对于一个句式来说,我们不能严格地按照坐动的语义类别来为兼语句扩大内涵,缩小它的外延。在现代汉语中,除了使役类动词能作兼语之外,有人还认为有一类心理动词也能够作兼语,如“喜欢”“埋怨”等。“喜欢他诚实”“埋怨老师批评了他”“感谢同志们关心他”(宁文忠、靳彦山,2002)。既然现代汉语V1表示心理的这类动词可以归入兼语句,为何要排斥先秦汉语中类似的句子呢?
王力先生在讨论递系式(兼语式)的发展时曾把“我请他吃饭”这样的句子也归入其中。可见,《文通》把“请+承读”放在一起讨论也不无道理。王力先生认为:“递系式中的两系是一个整体,其中处在兼位的名词或代词既不能单纯地认为是宾语,也不能单纯地认为是主语。”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动字相承”中“感官动字+散动”“心理动字+散动”“请+散动”“使令动字+散动”都可以看作兼语句式,至少可以区分为典型性和非典型性。马氏的分析不是凭空而论,而是他重视句法形式的结果。
(二)使字句
马建忠认为“使”具有两种词性,分别为动字和连字。
1.“使”为动字
主要是指人名字作为施事起词,从语义上来说表使令。
(21)王使盖大夫王驩为辅行。(《孟子·公孙丑下》)
(22)薄太后乃使使承诏赦太子、梁王。(《史记·张释之列传》)
以上两例起词“王”“薄太后”皆为人名,是动作行为的发出者,表施事。马氏认为这是作动字的“使”。
2.“使”为连字
此种“使”字,“用以明事势之使然者,则当视为连字,而非动字也。”从语义上来说,“使”之前的事件与之后的事件语义上有直承关系,表致使,具有篇章连接作用。
(23)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孟子·梁惠王上》)
(24)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左传·隐公元年》)
例(23)的“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是“发政施仁”的效用使然,而与动字“使”前指人的施事起词相异。例(24)也当如是解。
问题的焦点之一就是“使”的词性问题。现在一般认为,无论是表“遣使、使令”义,还是表“致使”义,“使”都当为动词。马氏对“使”的词性的归类我们姑且不论,然而他的确看到了这两种“使”字句的动词语义的差别以及“使”对篇章连接所起的作用。“前有施事起词时使令诸字意义比较实在,动词性比较强,反之则意义较虚,动词性也减弱了,马氏的观察作为一种语义分析是有见地的。”(宋绍年,2004)
学者们从马氏的论述中汲取了充分的养料。李佐丰把《左传》的使字句分为“意使”和“致使”两类。他所说的“意使”即由于主使者的授意,受使者独立地去完成VP所表述的行为;“致使”是由于主使者的活动或影响,使受使者具有某种状态或活动,便构成致使。这种分类方法与马氏如出一辙。从现代汉语的研究成果来看,使字句有新的发展,两种语义类型仍然有沿袭先秦汉语的趋势,只是谓语动词出现了分野。李临定认为:“‘让‘叫和‘使都有致使义,但是侧重方面则有所不同:前者侧重于人,后者则侧重于事件;前者经常表示某人致使了某种动作,后者则总是表示由于某个事件而引起了什么结果;前者常和人的主观意志相联系,后者则不和人的主观意志相联系。”
文中马氏还着重分析了“位移动字+散动”以及“而”字句,这些句子中的前后动词都应是坐动,属于连谓结构,因为是“两动字意平而不相承者”,在此不作讨论。
四、词性及其语法功能的探讨
“动字相承”还涉及到助动词的句法功能、某些助动词的词性、虚词“以”的词性及功能的探讨等。
(一)助动词
“夫曰助动,必有所助之动字为之后焉。后之者,所谓散动也。”如例(1)中,助动词“能”被认为是坐动,其后的“尊”“显”为散动,“皆并承‘能字”。此说关涉到助动词和动词谁是核心谓语动词。
按马氏的体系,助动词是核心谓语动词,后面的动词是它的宾语,也即动宾结构,因为“散动直承动字,与止词无异”。这一论断对以后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德熙先生认为“助动词是真谓宾动词里的一类”,它的特点是“只能带谓词宾语,不能带体词宾语”,把此类结构看作动宾关系。王力先生曾给助动词下的定义为“词之帮助动词,以表示行为的性质者。”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来看,助动词之后的动词应该为核心谓语。今人一般认为助动词是修饰语,在句中作状语,助动词与动词应该是一个状中的偏正结构。
马氏从词类和句法角度来分析助动词的功能。既然助动词是动词里的一个小类,就应该具有动词的普遍语法特征,如果是及物动词当然就具有带宾语的功能。同时,助动词在早期是动词,其后经常带宾语,只是后来虚化,具有了独特的语法特征和意义。
另外,马氏把“敢、愿、欲”归入心理动字,而没有把它们归入助动字一节中。这三个词从语义来看都是表示人的心理和意志,并且多数的助动词都是由动词虚化而来,马氏把它们归入心理类动字是无可厚非的。我们认为马氏所举“‘敢、愿、欲+V”形式中这三个词应为助动词,而“‘敢、愿、欲+N+V”形式中它们仍带有明显的动词性质。马氏对此的讨论可归纳为:
1.“敢+散动”,“敢”主要是助动词,为“敢+V”式。可表有胆量做某事,也可用于反语。如:
(25)不敢输币,亦不敢暴露。(《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26)孤不敢忘天灾,其敢忘君王之大赐乎!(《国语·吴语》)
(27)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孟子·公孙丑上》)
2.“欲+散动”为“欲+N+V”式,仅有一例:
(28)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论语·公冶长》)
王力先生认为“欲”本为动词,后面可以直接带宾语。我们也认为此例中的“欲”仍为动词。因为“人之加诸我也”中间加入“之”已经使之名词化,整个“读”可以看作是“欲”的宾语;后面的“吾亦欲无加诸人”,虽然“欲”后跟的是动词,然而此小句应与上句对举,“无加诸人”可以看作是“吾之无加诸人”的省略形式,上下两小句“欲”的词性相同。
“欲”也有作助动词的用法。例如:
(29)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论语·先进》)
3.“愿+散动”,两式皆有。如:
(30)寡人愿安承教。(《孟子·梁惠王上》)
(31)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孟子·梁惠王上》)
例(30)中的“愿”应该是明显的助动词,后面紧跟动词。例(31)中其后续承读,仍然可以看作是动词。
(二)虚词“以”
马建忠把虚词“以”只作为介词看待。现在人们认为表连词的“以”仍是作介词。
(32)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庄子·养生主》)
(33)故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
例(32)中的“以”是典型的介词,后跟名词。例(33)作的“以”,马氏认为是介词,“以”之前的“脩文德”表示行为的方式或手段,“脩”是坐动;之后的“来”表目的,是散动。按现在多数人的看法,此类句子中的“以”是为连词,前后两项均为坐动。按《文通》的处理方法,马氏认为“来”承坐动“脩”之行。从语义上来讲,这两个动作确实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体现在句法方面,表目的的动词一般放在表行为方式的动词之后。宋绍年认为,马氏力求把前后项的语义关系突显出来。马氏的这种处理方式类似于英语中的动词不定式“to do something”,不定式常用作状语,表示行为动作的目的。
但马氏没有看到“以”在动作上的前后关联作用,特别是用在复句中可以明显地体会出来。如:
(34)晋侯秦伯围郑,以其无礼于晋且贰于楚也。(《左传·僖公三十年》)
此句连词“以”用来连接两个分句,后面的表示原因,前面的表示结果。这与“以”后面直接跟体词性的词或词组的句子从句法上来说有明显的区别,比较例(32)。
五、结语
在“动字相承”一节中,马建忠充分借鉴西洋语法,对汉语的句法形式给予了足够的重视。然而,马氏也并不是一味地模仿,很多方面都注重句法和语义的有机结合。这些探讨引发了后人对某些特殊句式的思考,如兼语句、使字句、连动句、“知见”类句、“N之V”句等等;还引发了对某些动词、虚词的讨论,如助动词的句法地位及其与后续动词的关系、“以”的词性及功能、“而”的功能等。尽管马氏在著述中尚有不少缺漏之处,但瑕不掩瑜,他立足于汉语的实际,构建了颇具创造性的汉语语法体系。一百多年来,《马氏文通》仍然是我们学习、研究古代汉语的宝藏。
注 释:
①文中例句未经注明者皆选自《文通》。
参考文献:
[1]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2]宋绍年.《马氏文通》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3]卢烈红.《马氏文通》“坐动”“散动”说评议[J].武汉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5).
[4]陈庆汉.《马氏文通》动词系统中的“坐动”、“散动”及其价
值[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6).
[5]王海棻.《马氏文通》研究百年综说[A].侯精一,施关淦主
编.《马氏文通》与汉语语法学[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李春晓.《马氏文通》析句方法中的层次分析观念[A].姚小平主
编.《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
[7]吕叔湘.重印《马氏文通》序[Z].马建忠.马氏文通[M].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9.
[8]王海棻.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9]傅书灵.也谈“N之V”结构[J].语言研究,2011,(3).
[10]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M].吕叔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1]宁文忠,靳彦山.兼语句与其他句式结构的区别——现代汉
语特殊句式辨析之二[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
[12]王力.汉语语法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13]李佐丰.《左传》的“使字句”[J].语文研究,1989,(2).
[14]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5]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6]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4.
(杨丹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00875;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 10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