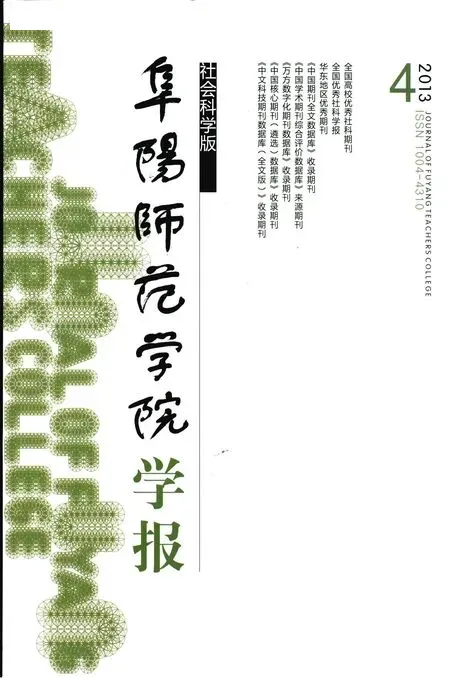论《我弥留之际》中本得仑家庭的解体
孔令云
(安徽工程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一、引言
威廉·福克纳是著名的美国南方作家。他的作品以精湛的写作技艺、深邃的人文关怀享誉文坛。他一生著作丰富,其中《我弥留之际》是他最好的作品之一。该故事讲述了南方穷白人本得仑家将女主人安迪的遗体送往杰弗生镇埋葬的故事。透过送葬之旅,福克纳刻画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展现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并以故事中本得仑家的种种遭遇折射人类社会的普遍危机,表现了作者深邃的人文关怀和哲学思考。
自《我弥留之际》出版以来,评论家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部作品。1930年代,受社会学影响,这部作品被看作南方穷白人的生活纪实。1946年出版的The portable Faulkner 在福克纳研究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强调了该故事背景的重要性。后期的沃伦和布鲁克斯进一步地提出的观点:这部作品实际上是整个时代的缩影,具有普遍性意义,已成为评论界的共识。另有学者和福克纳专家从其他视角解读这部作品:如原型批评、新历史主义、复调理论等等,有助于深刻地挖掘作品的特征和意义。不可否认的是,《我弥留之际》中高超的叙事手段、恢弘的历史背景和深邃的人文关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然而这部作品首先是一部家庭小说,并且作者福克纳始终强调对家庭的描写和思考。国内外评论家如Olgas Vickery,Bleikasten,Wadlington 和肖明翰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审视本得仑家,并提出了深刻和独到的观点,然而未从整体上研究作品中的家庭关系。本论文在细读文本的基础上,运用了文化研究和女性主义等文学理论,较为全面地研究聚焦本得伦家庭的解体,并提出家庭解体的三大原因为:亲人之间相互孤立、家庭中心的缺失和家庭成员的精神危机。
二、亲人之间相互孤立
本德仑家的送葬之旅曾一度被认为是“奥德赛式”的“史诗般”的旅程,因为从外表上看本德仑家齐心合力,战胜艰难险阻,成功地将安迪的遗体送到目的地。直到Bleiksten提出“《我弥留之际》中同时存在两个故事,一个发生在马车外,一个发生在马车内。”①[1]161此观点揭露了本德仑家暗地里的家庭关系:互相孤立,彼此隔绝。
(一)“我就是我”
作品一开始便隐晦地介绍了本德仑家两兄弟之间的不和。兄弟朱厄尔和达尔一前一后地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们一个沿着路走,一个穿过房子。达尔的心中思想朱厄尔和自己的不同。[2]1兄弟二人如同陌生人,坚持用“我”的方式走“我”的路,隐晦地宣告“我是我,你是你”(I would be I and you would be you)。
“我就是我”是女主人安迪的座右铭。事实上,它更是本得仑家的家族格言。“我就是我”表达了说话人视“我”为主体,别人为“他者”的观点,夹杂着“我”独善其身、拒绝同化的思想和愤怒的情感,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当安迪强大的“我”在丈夫安斯面前受挫时,她宣告“我就是我”来表明立场和表达愤怒。Wadlington 注意到愤怒是本得仑家人普遍的情绪,通常出现在“我”的想法和性格受到威胁和侵扰的时候[3]52。大儿子卡什擅长木匠活,并以此为傲。当他人质疑他搬运棺材的安排时,一向温顺的他也大发雷霆。
如前文所述,“我就是我”是本得仑家的家族信条。它摧毁了本得仑家的每层关系,并最终导致了本得仑家的解体。首先,自成一体和拒绝对话发生在丈夫安斯和妻子安迪的婚姻里。从夫妻俩各自的内心独白可以看出:他们都自私并固执地坚持自我,彼此貌合神离。丈夫安斯和妻子安迪都有鲜明的个性。安斯懒惰,喜欢用嘴巴操控人;安迪勤快,注重经历生活。安迪临终之时,在独白中回忆过去说:“他是他,我是我,让他成为文字的回音吧……他在我心目中早已死了,只是他不知道”[2]68。而安斯在妻子弥留之际,仍未为伴侣做丝毫的改变,他在独白中仍然坚持说:“上帝把人造成竖直的,就是让人呆着不动”[2]42。本得仑家每个人都在坚守“我就是我”。三儿子达尔看似最软弱,却固执地坚持“疯子般和诗人般”的人生,即使在一切压力下也拒绝改变:“他整天无所事事,只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坚持自我,致使他人的远离,他生活在自己的孤独中。”[2]24朱厄尔无所顾忌地在众人面前表现自己的独特和野性。当全家人都坐在运送安迪遗体的马车上时,他却坚持撇下家人,独自骑马。Wadlington 精辟地指出:“本质上,这个家庭的集体行动支离破碎。朱厄尔、达尔、安迪和安斯都极端地表现了这一事实。”[3]77
Bleiksten 指出“本得仑家最主要的特征是家人之间的隔绝和分裂”[1]115。本得仑家的每位成员坚持以“我”为中心,拒绝因他人改变和联合,致使至亲的家人成为陌路人,并最终导致家庭的解体。
(二)无处不在的秘密
本得仑家集体坚持“我就是我”,致使家人彼此隔绝,也导致了本得仑家处处滋生“不可告人”的秘密。安迪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秘密和自私的想法”。“本得仑一家习惯隐藏秘密,独自解决。”[1]23
福克纳认为写作手法应当完美地服务于作品的主题思想。《我弥留之际》中,作者将内心独白这一叙述手法运用到极致。整部作品是由15 位人物的59 篇人物独白串成。福克纳采用内心独白以淡化外在事件,强化独白者的内心活动,确切地说,透露他们秘密的思想和故事。因为较之为人所知的事件,在私底下发生的秘密是本得仑家的关键事件,是故事的主轴。本得仑家冒着极大的危险将安迪的棺材从洪水和大火中救出,即使烈日烘烧,秃鹫滋扰,也不放弃送葬之旅。然而,送葬之旅的完成却终结了这个家庭。这样的结局看似不合逻辑,充满讽刺,然而如果从本质上看送葬之旅,家庭解体却是必然,因为送葬之旅是家人实现秘密愿望的工具:葬在杰弗生镇是安迪秘密报复丈夫安斯的手段;为了一副新假牙和新妻子,丈夫安斯答应送葬;女儿杜威·德尔去杰弗生镇为要秘密地打胎,遮盖丑事;就连愚笨的瓦德曼也是为了香蕉和火车才去的。
值得注意的是,家人之间互留秘密,拒绝沟通已经成为本得仑家的传统。正如Bleiksten 发现“本得仑家家人从出生就继承了这个家庭特有的保留秘密的习惯。”杜威·德尔的独白深刻地反映了这一家族传统。当杜威·德尔发现自己未婚先孕,她试图向家人求救,可是“朱厄尔是啥都不管的,他跟我们不亲,所以不用操心,再说他也不喜欢操心。卡什只知道把一个个漫长、燥热、愁闷、发黄的白天全都用在锯木头钉东西上面。爹认为乡邻之间就应该这样互相帮忙,他一直忙于让别人来帮他干活所以他是发现不了的。我也不认为达尔会发现,他人坐在晚餐桌前,眼睛却越过了饭菜和灯,只看见自己的脑袋里在挖掘的地和更远处的那些窟窿。”[2]34。家人未曾真正注意和关心杜威·德尔的需要,所以她只能“孤零零地解决问题”。
三、家庭中心的缺失
现代心理学和生活经历都证明在家庭中,母亲是情感中心,父亲是权威中心,两大中心各尽其职才能维持家庭的稳定。然而本得仑家却存在一个讽刺性悖论:就身体而言,父亲和母亲都在场,然而从情感和责任上来看,他们却不在场。如同Howe 指出“兄弟们有个羸弱的父亲,并且彼此抢夺母亲。他们意识到母爱的缺失,便拼命地想占有母亲或拥有一个替代物。”[4]19
(一)情感中心的缺失
女主人安迪在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首先,小说题目“我弥留之际”中的“我”就是安迪。其次,家庭冲突的根源在于抢夺她的爱。再次,该小说主要讲述她的亲人对她生与死的反应。然而,作为母亲,安迪给孩子们产生的是消极的、毁灭性的影响。受各种力量的左右:父亲的虚无主义、环境的挫败和自身的孤傲,安迪拒绝做一个真正的母亲。“安迪作为母亲表现的是死亡而非生命,愤恨而非慈爱。儿女们一生都未得到母爱或被错爱。”[1]55
母亲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儿女们的夺母大战。安迪躺在病榻上,杜威·德尔好像是看守自己的领地,不许别人靠近母亲。卡什则专心做母亲的棺材,讨安迪的喜悦。而朱厄尔对安迪的掌控则更加极端和强烈。在他的独白中,他想象自己和母亲单独在山顶,他人想上山来抢夺安迪,他拼命地往下推石头来保留自己的母亲。达尔知道母亲不属于自己(motherless child),而私生子朱厄尔是母亲的最爱。作为报复,他用刻薄的方式去问朱厄尔他的父亲是谁,引得朱厄尔大骂达尔王八蛋等等。安迪造成了儿女情感上的空缺,导致了弟兄姐妹之间的嫌隙,甚至互相愤恨,并最终催生了家庭解体。
本得仑家的每个孩子的人生均以悲剧收场也源于母亲安迪的失败。安迪的强大摧毁力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二儿子达尔的悲剧命运上。未出生之前,达尔就是安迪憎恨丈夫的转嫁物。“接着我发现自己怀上了达尔,起先我还不肯相信,接着我相信自己会把安斯给杀了”[2]163。然后,安迪就就秘密地决定不再承认达尔是自己的孩子。母亲的抛弃使得达尔成为小说中最大的悲剧人物,一生都陷在“无我”和“无家”的痛苦中,受他人的隔离,并最终成为替罪羊和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他说:“我无法爱我的母亲,因为我没有母亲”[2]82。不仅如此,其他孩子们,如卡什、杜威·德尔、朱厄尔扭曲的性格和悲惨的结局都是母亲缺失的后果。
(二)权威中心的缺失
安斯是一位失败的父亲:懒惰、自私、伪善。安斯的失职导致了家庭里缺失了传统的权威中心,使得家庭不能有效地维系,并最终被摧毁。故事的结尾,安斯为了自己,另娶一位妻子,标志着本得仑家完全地解体。
Bleiksten 评论安斯是福克纳塑造最成功地恶汉,冷酷、固执、没有丝毫怜悯[1]23。福克纳把其描写成“鸡”和“鸟”成功地传达了他丑陋的个性。安迪描写他为“当时我也注意到他的背开始有点驼—他个子高高的,年纪不大—因此他呆在大车的驾驶座上看上去已经很像一只寒天弓着背的高高的大鸟了。”[2]162皮保迪说“他两条胳膊垂在身旁,头发翘起来,缠结在一起,像只洗过药浴的鸡”[2]50。值得一提的是,安斯的手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懒惰和无用:要么垂在两边,要么不停地搓着膝盖。“他的手笨的像鸟爪,想抚平自己弄出来的褶皱,可是褶皱却偏偏不断地在他手下到处出现,因此最后他只好放弃,两只手又垂回到身边,在大腿上蹭磨,手心蹭完了又蹭手背。”[2]57另外,亲人和邻舍对安斯的态度都是轻视、躲避和鄙夷。正如安迪所说:“他在我心中已经死了,只是他并不知道他死了。”[2]164安迪去世后,安斯命令女儿杜威·德尔不要哀悼,改去做饭时,她充耳不闻。
四、精神危机
本得仑家的解体不仅根源于家庭内部,同时也受到美国南方社会的影响。《我弥留之际》是一部美国南方小说,描写了美国南方独特的社会图景。小说中的美国南方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深刻的社会变革引发了严重的精神危机。在当时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本得仑一家陷入道德的沦丧、习俗的压制等危机之中。可悲的是,本得伦一家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而没能克服他们面临的精神危机,相反却被其异化,这个家庭也最终解体。
(一)道德的沦丧
《我弥留之际》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创作的。然而以本得仑家为代表的美国南方穷白人的经济处境更加恶劣。细读文本,可以看出本得仑家经济异常拮据。他们付不起电,只有一只煤油灯。另外,专家们说当时自制棺材已很少见,而安迪的棺材却是儿子卡什自己做的。卡什和达尔已过适婚年龄,却因贫穷找不到妻子。一位评论家精辟地指出,贫困的生活导致了穷白人精打细算(calculation),这是极端个人主义的表现[7]16。精打细算导致了本得仑家人计算利益和道德时,为了利益,牺牲道德。正如Watkin 所说:“本得仑家人屈服于环境而轻看道德。”[6]47安斯为了三块钱而让儿子们离开处在弥留之际的母亲。当达尔看出送葬之旅背后的黑暗时,他放火烧了马棚以毁灭棺材结束荒诞的送葬之旅。然而,当本得仑家面临经济赔偿时,达尔的亲人决定牺牲达尔而免于赔偿。在亲情和钱财的选择中,本得仑家选择钱财。卡什描述了家人如何“齐心协力”地捆绑自己的血亲做替罪羊:“杜威·德尔什么都没说,也没看他(达尔)。只是当疯人院来抓达尔,达尔反抗的时候,她一下子扑到她身上就像一只野猫的时候,以至于一个家伙不得不停下来拉住她。她就像一只疯狂的野猫抓着达尔,父亲和朱厄尔一下子把达尔摔倒,把他摁在地上,盯着他看。”[2]145这段描述赤裸裸地描写了家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掩饰秘密,而凶残地对待自己的亲人,此举令人胆寒心惊。当达尔被捆在马车上去疯人院的路上,不禁狂笑起来。这笑声充满了达尔对人性的失望和对亲情的虚无。
Brooks 认为福克纳对穷白人抱有同情,觉得他们是正直和有自尊的一群人[5]18。事实上,本得仑家还有整个穷白人的群体都已经被环境改变。正如Howe 指出,“美国南方穷白人是人类道德最堕落的一群人。”[4]47
(二)传统的压制
福克纳认为南方传统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生活,是罪恶的势力。《我弥留之际》中的人物都是南方传统的受害者,他们僵硬地、精确地信从南方固有的意识形态,并将其在落实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达尔说:“我们都是按着极其精确地方式去走路。”[2]27弗农也表现出男方传统带来的僵硬和死板。“弗农吐了一口痰,人一动也不动。他一丝不苟地异常精确地把痰吐在廊子底下的一个个小坑的尘土里。”[2]26其次,清教主义在南方的影响根深蒂固。福克纳评述《喧哗与愤怒》和《我弥留之际》的共同之处时谈到两部作品的写作基础都是清教对南方政治和经济的剧烈影响。清教主义催生了美国南方的妇女观和父权制社会的形成。这在《我弥留之际》中有很大地体现。作品中的妇女鲜有自己的声音,都是别人代其发言,如女主人安迪她只有一篇内心独白,读者获取的信息大多是周围人的介绍和评价。另外,福克纳在作品中谈到在男人的眼里,女人无非是做苦工的牛与马而已。
传统的、死板的南方传统的强大的辖制力诱发了南方人们人性总的黑暗,并导致他们痛苦和悲剧的生活。“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有这个毛病,所有的一切,气候以及别的一切,都拖延的太长了,他跟我们的河流,和我们的土地一样:浑浊、缓慢、狂暴;所形成和创造出来的人的生命也是同样的难以满足和闷闷不乐。”[2]51另外,为反抗荒谬的南方妇女观和父权制,安迪选择做一个失败的母亲,造成了家庭的悲剧。而当杜威·德尔发现达尔察觉到她和莱夫的不正当关系,她甚至想杀了自己的哥哥去掩盖这个秘密,因为这些秘密不能曝露在光中,尤其在满脑礼仪道德的美国南方。她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人呆着的话,其他的人都会知道的”[2]33。所以,她假借送葬之名去镇里买打胎药,并最终将最大的隐患—兄弟达尔送到疯人院。
五、结语
福克纳谈到《我弥留之际》时说“这是一部描写旅程和家庭的小说。”[8]134本得仑家庭的解体是这部小说的重要主题,也是作者福克纳所关注和思考的对象。细察本得仑家庭解体,得出孤立是本得伦家庭悲剧的根源之一。本得伦一家的悲剧产生于家庭成员以自我为中心,没有家庭意识,为了自身利益,不惜牺牲他人。同时,为了隐藏秘密,与人隔绝,甚至彼此伤害。因此,家庭成员不是相互依存,而是彼此孤立。其次,安斯和安迪却没有承担父母应有的责任。母亲安迪拒绝爱自己的孩子,而安迪利用父亲身份为自己赚取好处。安斯和安迪的失职造成了孩子们的悲剧,也导致了家庭的解体。再次,在当时社会和文化背景下,本得伦一家陷入道德的沦丧、习俗的压制等精神危机之中。通过对作品和当时美国南方社会现实的分析,可以得出本得伦一家是现代美国南方社会的缩影,它的解体是家庭内部和外部各种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
注释:
①文章中引用的外文文献均是作者的翻译。
[1]Bleikasten,Andre.Faulkner’s As I Lay Dying[M].New York: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73.
[2]威廉·福克纳.我弥留之际[M].李文俊,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
[3]Wadlington,Warwick.Reading Faulknerian Tragedy[M].Ithaca: Cornell UP 1987.
[4] Howe,Irving.William Faulkner: A Critical Study[M].Chicago: Ivan R.Dee ,Publisher,1991.
[5]Brooks,Cleanth.William Faulkner: The Yoknapawpha Country[M].New Heaven Yale UP,1978.
[6] Watkin,Henry “As I Lay Dying: The Dignity of Earth.”In Time and Place.Ed.John Hollanders.[M].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1986.153-62.
[7]刘国枝:荒野文学序列的<我弥留之际>[J].四川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3):15-19.
[8]肖明翰.威廉·福克纳研究[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7.
[9]孔令云,汪景峰.从“独白”走向“对话”——《我弥留之际》中的对话哲学[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1):91-94.
[10]刘晓琳.浅析《我弥留之际》的重要叙述者与主题[J].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8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