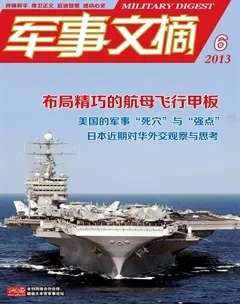左宗棠与福建船政的恩恩怨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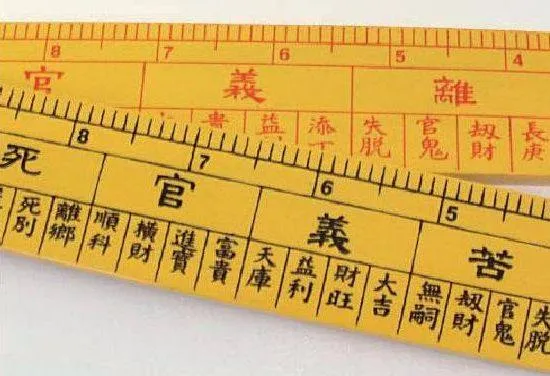


此一时,彼一时——左沈交恶谁之过
按道理来说,被曾国藩评价为“死党”关系的左宗棠和沈葆桢之间应该是亲密无间的,可最终却分道扬镳,酿成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悲剧结局。有人将左宗棠和沈葆桢交恶的原因归结到李鸿章对二人的挑拨离间、从中作梗。但事情真的是这样么?
左宗棠办船政的初衷绝不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而仅仅是要在规模上和场面上压倒他的政治宿敌曾国藩和李鸿章,船政筹办速度陡然加快也和曾、李师徒在上海黄浦江畔建厂造船不无关系。而船政初具规模后,左宗棠所谓的“军舰”也仅仅是平日运货、战时作战的“兵商两用船”,这与真正的海军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船政之父”左宗棠对他的“孩子”——福建船政,并没有尽到一个“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而沈葆桢对船政的态度则完全不同。他在福建船政最初的五年计划中就看出“兵商两用船”绝非中国海防所需要的军舰,并在自己的权责范围内对左宗棠的错误尽力予以修正。在他的脑海里,中国海防在利器方面的需求始终是清晰的——铁甲舰。沈葆桢和左宗棠的嫌隙因为以上两点分歧开始扩大。更要命的是,铁甲舰还有一个忠实的中国粉丝——李鸿章。由于当时主张购买铁甲舰的呼声在官场上来自少数派,同时沈葆桢和李鸿章还是丁未年科举的同年进士,所以沈葆桢和李鸿章很容易就走到了一起,在铁甲舰的问题上互为奥援,形成了南北同盟。
从左宗棠的角度看,他不但没有意识到铁甲舰对中国海防的作用,而且还对沈葆桢逐渐与李鸿章走近感到不忿。1874年,台湾事件爆发,日本台湾藩地事务局都督西乡从道率领炮舰“日进”、“孟春”带着3600名日本陆军士兵,分乘“明光丸”、“有功丸”、“三邦丸”等商船,在台湾琅桥登陆,进攻曾屡屡杀害遇难商船船民的牡丹社等生番土著。对此大为震怒的清政府态度强硬,命令时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立即组织舰队渡台,对登陆台湾的日军进行武力示威。
船政大臣手里的船是不少,但却没有可用之兵。本地绿营部队战斗力不值一提,达不到威慑的效果。沈葆桢只好拉下老脸向各省督抚请调陆军赴台协防。但令其失望的是:对于和本省毫无干系,又孤悬于海外的台湾,督抚们显然不愿意出力,拒绝了沈葆桢的请求,这其中就包括左宗棠。几乎陷入绝望的沈葆桢最后求助于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本沈葆桢对此并不抱希望,不料却意外收到了李鸿章爽快的回应:调原驻扎在江苏徐州的淮系铭军精锐唐定奎部十三营6500人,借给沈葆桢去台湾威吓日本人,并表示:如果兵力不足,淮军可以再出十九营赴台助防。得此喜讯的沈葆桢不吝感激涕零,自比“贫儿暴富”。自此,沈葆桢和李鸿章的关系就更近了一步,但也招来左宗棠对其的不满和嫉恨。
在与此同年的海防大筹议上,左宗棠力主对被阿古柏占据十年之久的新疆用兵,正好和提出购买铁甲舰的李鸿章撞个满怀。以当时清朝的财力,不管是购买铁甲舰还是对新疆用兵,应付一项已是勉强至极,更别说两者兼顾。而不论是左宗棠还是李鸿章,都视对方的行为为抢钱行为,丝毫不退让。此时的沈葆桢已是李鸿章的坚定盟友。在这场大论战中,沈葆桢坚决反对左宗棠为新疆用兵而向英国银行借高利贷的主张。左宗棠为此大为恼火,不得已去找了胡雪岩,为西征贷款做担保。左沈关系进一步恶化。
1875年后,沈葆桢离任船政大臣,北上就任两江总督。同时,因与李鸿章的亲密合作关系,沈葆桢之后的三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臣、黎兆棠均出自李鸿章的幕下。左宗棠眼见淮系势力渗透到福建船政,自己中意的船型被弃用不造,再回想起自己当年对沈葆桢有知遇之恩,对沈葆桢怒火满膛。直到1879年沈葆桢病逝后,左宗棠依然对其购买铁甲舰一事耿耿于怀。他在写给徐理卿的信中抱怨:“幼丹(沈葆桢)之明岂不知铁甲固无所用之耶?对于沈葆桢生前与李鸿章的合作,左宗棠更是愤愤不平,一有机会便加以抨击。1880年,他又在信中写道:“铁甲轮船英人本视为废物……船坞为各国销金之锅,罄其财而船终无用,李(鸿章)与丁(日昌)独无所闻,亦不可解。”而李鸿章对日意格所选船型“老旧”的批评,在左宗棠看来,也是李鸿章借批评日意格来抽他的大嘴巴。咽不下这口恶气的左宗棠伺机反扑,意图从淮系手中重夺船政的控制权。
公报私仇——造舰订单的惊人分配
左沈反目,与其说是李鸿章挑拨的“功劳”,不如说是左宗棠出于一己之利,忽视了沈葆桢的抱负和诉求,最终硬生生地将自己的“死党”推给了李鸿章。结合左宗棠在晚清官场上狼藉的人际关系和口碑,笔者认为:左沈交恶,主要责任在于左宗棠。
1881年10月28日,正当左宗棠作为军机大臣,成天在军机处吹嘘自己西征之功之时,晚清政府任命其为两江总督。左宗棠于1882年2月12日正式抵达江宁就任,奉旨办理南洋海防事宜。此时的船政大臣是李鸿章的幕僚黎兆棠,船台上正在建造的是船政所建的第一艘2800马力巡洋舰—“开济”号。
出乎意料的是,左宗棠对这条没有货仓的军舰表现出了极大兴趣,十分热心地表示将采用“开济”号的设计为南洋水师再造4艘同型巡洋舰。另外他和长江水师提督彭玉麟谋定要为长江水师建造一批小型炮舰,要求船政和江南制造局两大造船机构各自提出方案,以供他参考,择优而取,建造数量可能是10艘。这笔单子,用今天的话来说,简直就是一笔军火大单,不论对船政还是对江南制造局,都极具诱惑力。
就造船实力而言,福建船政局的能力在江南制造局之上,所以船政大臣黎兆棠对这笔大订单志在必得。在左宗棠就任两江总督之前,彭玉麟就将长江炮舰的设想责成江南制造局设计部门画出草图,并做出预算,每艘炮舰不含火炮的单价为16万两。彭玉麟给予首肯。而江南制造局提交的方案体量相当,但报价要比船政的方案高出2~3万两。这笔大单花落谁家,似乎已有定论。
但是左宗棠的决策却令黎兆棠甚至是远在天津的李鸿章感到失望。4艘“开济”级巡洋舰,福建船政只分得2艘的建造订单,另外2艘则由左宗棠通过他在西征时结识的德国泰莱洋行经理福克,转包给了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德国霍华德造船厂(这家造船厂现如今因建造了206、209、212、214等一系列性能优异的潜艇而闻名世界)。经过一系列“节约成本”的操作,霍华德船厂给出的不含火炮的报价为每艘27万两。这个报价虽比船政的报价每艘30万两低,但是如果算上舰艇建成后回航中国所产生的费用,这个报价还是要高于船政。而且中间商福克为了赚取差价,导致霍华德船厂承建的两艘名为“南琛”和“南瑞”的巡洋舰性能较“开济”号有了不少缩水。比如,两舰没有采用一台2800马力的主机,取而代之的是两台1400马力的主机,导致两舰的最高航速只能达到14. 5节,而非“开济”号的16节;两舰采用了较易被腐蚀的铁壳船体,而非“开济”号采用的双重木壳船体,导致“南琛”、“南瑞”两舰的总体质量不如“开济”号,更无法与船政承建的“镜清”和“寰泰”两舰比肩(“镜清”和“寰泰”在试航时时速分别为17节和18节,令在场的所有人瞠目结舌,要不是此时左宗棠已经作古,定将无地自容)。后任船政大臣裴萌森对“开济”级巡洋舰有过一段十分精彩的评价:“……矧三船皆为南洋代造,而制法则日新月异,复有不同。‘开济’之坚韧灵捷,既非‘南琛’、‘南瑞’所能及,而‘镜清’又胜于‘开济’,‘寰泰’又胜于‘镜清’,所谓进而益精,熟能生巧。南洋得此三船,洵足以壮东南海疆之声势矣。”
很明显,左宗棠将两艘“开济”级巡洋舰的工程承包给德国人,除了要还德国人福克在西征中出力的人情外,对福建船政的不满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另外,关于彭玉麟想要的小炮舰,即便福建船政的报价比江南制造局低,即便江南制造局已经有7年没有建造过一艘军舰,造舰能力值得怀疑,左宗棠还是决定将长江炮舰的工程承包给江南制造局,并声称江南制造局的预算高于福建船政的原因是“只期工料坚实、费不宜省”。对福建船政提交的物美价廉的方案,左宗棠则将其选择性地遗忘,左宗棠对船政的不满情绪再一次表现出来。当然,这些只是毛毛雨,真正的疾风暴雨随后而来······
“船政之父”的最后反扑——“开济”试航事件
1883年10月22日,福建船政承建的“开济”号巡洋舰建成,经过试航证明合格后,由南洋派来的管带何心川指挥北上江宁。不料,在航行过程中遭到飓风侵袭,根据管带何心川的报告,“开济”号上的抽水机均不合用,导致舰内积水,主机停转,只好就近靠岸。经过三昼夜的抢修,“开济”号才得以恢复动力,返回福建船政修理。时任船政大臣的张梦元竟要求何心川修改报告,绝口不提抽水机不合用,改为因飓风导致军舰受损。
左宗棠接到报告后立刻上奏朝廷,借此事对“开济”号的质量大加鞭挞,抨击福建船政“俨如居贾者以劣货售人,一出门则真赝皆弗顾。故一经风浪,百病业生”。随后又在“开济”号的技术参数上大做文章,称“开济”号设计吃水1丈7尺,实际却达到1丈9尺。设计航速每小时可航行百里,但是到两江实测只有九十多里。最后居然以“镜清”、“寰泰”的报价只有30万两,而当初建造“开济”号的报价为40万两为由颠倒是非,称“开济”号最初的预算为30万两,实际却耗费了40万两,明指福建船政背后有徇私舞弊的行为。之后,左宗棠感慨道“臣昔年奏设船政局,原为自强之计,具有深意”,“闻近年该局员匠愈趋愈下……均不似昔年规模”,遂要求严行申饬福建船政大臣,革退不力员匠,大有重夺船政河山的架势。
但是接替张梦元担任船政大臣,奉旨调查此事的何如璋却丝毫不给左宗棠留情面。一就任,何如璋便迅速展开对此事的调查,并很快得出了结论:10月23日“开济”号起航遇到暴风时,舰上原本有五台抽水机,完全可以应对舰内积水的情况。但是因管带何心川不熟悉机器,处置失当,导致舱底抽水机的密封橡皮被热水浸化,致使五台抽水机全部失灵,时任船政大臣张梦元要求何心川重写报告完全是出于好心,顾及两江总督左宗棠的情面。原本是官场的人之常情,更何况张梦元事后立刻给左宗棠写信告知实情,并要求其再派熟练的管带来接替何心川,左宗棠接到张梦元的信后表示知道此事,并就此事回了信,所以左宗棠以何心川的报告为由攻击福建船政纯粹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至于“开济”号技术参数偏差,何如璋的结论是左宗棠无理取闹:吃水竟用鲁班尺单位硬套工部营造尺单位;航速竟用英里单位
硬套法国的海里单位。而“开济”号的造价为何比“镜清”、“寰泰”高10万两,何如璋也以建造“开济”号时,船台扩建费、法国船型设计费等额外费用均要纳入“开济”号建造成本为由,毫不客气地加以驳斥,并称左宗棠颠倒是非、居心叵测。
面对骑虎难下的局势,左宗棠十分心安理得地将责任全部推给了何心川,声称他是受了何心川报告的蒙蔽,将何心川予以撤职了事,绝口不提张梦元之前写给他的告知实情的书信。事后证明,福建船政建造的“开济”号质量毫无问题,但是由于左宗棠起先制造的负面舆论,所有参与监造“开济”号的有功人员都没有按照惯例得到清政府的嘉奖。
纵观整个“开济”试航事件,左宗棠不可谓不知道实情,但还是对福建船政痛下杀手,全然不顾当年创办船政积攒下的情谊。可见,左宗棠这个“性情中人”缺乏大局观念,办洋务也只关心自己能够控制的部分。对于自己失去掌控的部分则漠不关心,甚至大加打压,即便福建船政曾经是他一手辛苦创办而起。这不得不说是由于左宗棠的性格以及为人方面的缺陷所引发的悲剧。
后 记
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因为消化不良病逝于福州,盖棺定论,对于左宗棠在创办福建船政所做的贡献,我们后人无疑是要肯定和纪念的。但是或许因为历史局限性,或许因为其个人的性格缺陷,其对船政乃至中国近代海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值得我们后人深思和总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于左宗棠这个“性情中人”,过多的吹捧或者一味的否定都是不可取的。毕竟他是那个时代造就的人物,身上有着那个时代给予他的烙印;他也是那个时代里的异类,不融入主流的后果便是难免在性格上形成偏激。这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贡献和阻碍都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左宗棠不暇自哀而我们后人哀之,也要哀而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