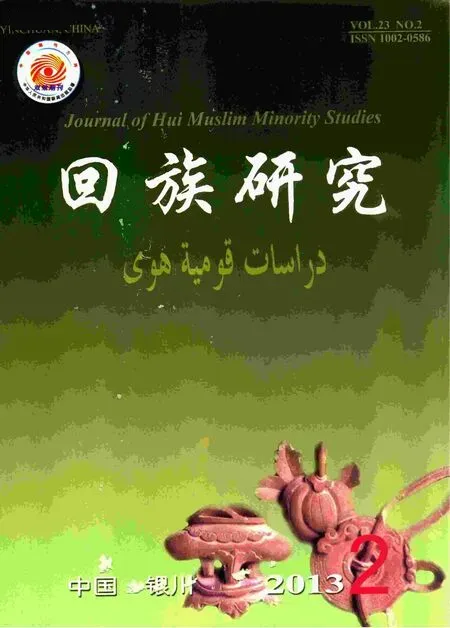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诸马与民国》序
杨怀中
(宁夏社会科学院,宁夏 银川750021)
1
书写西北诸马的著作不少。
这些著作中,能够站在少数民族的角度,来反观探索的却是少数。能够将这一群穆斯林军政群体在民族、宗教、教育、卫疆等诸多领域的积极面挖掘出来,并置于中华文化的层面上,予以客观审视体会的,更属凤毛麟角。
早在1965年7月16日,周恩来总理在对学界发表谈话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国民党军队将领的研究与看法:“作为实践中主体的‘人’,也不能不受环境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要写好国共双方的将领,还要深刻揭示这些将领与环境、与历史的真实关系。要不然,为什么同是黄埔学校的学生,有的成了我们的将军和元帅,有的却跑到台湾海峡那边去了。这一点写好了,作品就有厚度!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
西北诸马,泛指民国时代崛起于甘宁青等地的一群少数民族军阀人物。历史的车轮进入民国后,他们出自河州,兴起于乱世,各据一方,父承子袭,左右地方四十年,对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影响深远。
我在《回族研究》杂志工作期间,有幸陆续接触过研究者写作回族军阀人物的来稿。这类文章,涉猎诸马人物的方方面面,时有颇具分量的论述出现,令人欣喜。纵览之余,我自慨叹,对于诸马群体的认识与探索,并没有结束,甚至需要新的审视。我所说的这种重新审视,是指细致的爬梳,把更多关于诸马与那个时代的、尚有借鉴价值的东西,予以挖掘呈现,并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直面历史,知往而鉴来。
时至今日,可以说审视这群统治过西北的少数民族人物,观察、总结其政治作为,是今日之西北为政者、修史者、民族与宗教工作者,不可不问的学业。
2
选题的现实意义,致使对诸马群体的探索者,代不乏人。
仅以宁夏举例,吴忠礼、霍维洮、刘钦斌、杜力夫、胡迅雷、丁明俊等学者,皆有涉及,并且出版了一批有关西北回族军阀的图书。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我称上述诸位专家学者,可谓是这门学问的先行探索者。之所以这么认为,是因为诸马与民国,需要讨论的话题实在太多,限于种种因素,甚至是时代的关系,难于在一个时期内完成。总而言之,这类不属显学的课题,却总是需要时间,更是需要几代学人的接力而行。
限于时代的观念、思潮、禁忌,能够直面历史,知往鉴来,是需要勇气和自信的。这种勇气与自信,不仅来自于学人,更来自于当今社会。
2013年4月,青年学人王正儒捧来了他的《诸马与民国》稿样,求教于我。面对洋洋洒洒60 万言的《诸马与民国》,面对这个我关注了许久的话题,我的内心是喜悦的。这种喜悦,与书稿本身无关,首在青年人能够沉下心来,勤奋钻研。我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
通读全书,始终觉得有味。这部书稿中的诸马人物,是新鲜的。行文颇显章法,很流畅,不干巴,既有文献资料的依据,又有必要的判断。较之于先前的著述,这部史著是有着突破性的进展的。这种突破,重在资料的发掘与运用上。
早些年,正儒博士便在刊物上发表了与之相关的不少论文,又出版过专著《马福祥》,主编过《回族历史报刊文选》。这些著述的编辑与写作过程,使他接触到了大量鲜为人知的资料。直到此时,我才知他为写作《诸马与民国》业已准备了很长的时间。
这部书稿的前期工作,或说是辅助工作,显然是充分的。
3
这是一段长达近百年的西北史。
有清一代,中央政府对回族在内的诸少数民族的政策,糟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史迹昭昭,不作缀述。比如,清嘉庆年间,哲合忍耶穆斯林马达天在充军途中对儿子的谈话,颇能反应出受压迫者的凄惶与悲怆——
“行亏的官吏,把我充军到东,又充军到西。总有一天,他们的势力要消灭,一丝不存。须知!他们的国土上起了风暴,威严没有了,只有战争;地位没有了,只有粪土;自豪没有了,只有贫穷;高贵没有了,只有低贱。”
压迫继续,反抗不止。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西北回民的反清运动即在同治年间爆发。清军主帅左宗棠奉命西征,对河州回民进行了剿抚并举的政策,河州反清自卫的首脑人物马占鳌、马海晏等人,选择了受抚。马占鳌其人,接受清廷的收编以后,诚心实意效忠于清廷,成为了清廷安定河湟地区的得力助手,也使西北诸马开始了漫长的孕育期。
1912年,诸马人物在西北的时代悄然到来。是年秋天,马占鳌那一代人的后辈人,纷纷崛起于甘肃(时甘肃辖宁夏、青海)。马安良坐兰州,马福祥立宁夏,马麒定青海的势力格局,业已形成。
民国初期,内忧外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是靠拢于中央政府,还是亲近于外部力量从而独立,成为了未知。比如,库伦独立最终演成外蒙古的形成;又比如,英国人积极煽动怂恿支持西藏地方上层某些势力寻求独立。伴随着民国的到来,这一严峻的边疆危机浮现了!决定边疆命运、领土完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当时的北洋政府,而是边疆宗教人物,以及手握重兵的边疆武人。在西北,名重当时的人物里便有诸马。
延至20世纪30年代初期,诸马军阀的第二代关键性人物——马鸿逵、马步芳,分别确定并巩固了他们的统治体系,形成了“宁马系”、“青马系”的鲜明特征。1949年,解放军剑指西北,经略西北40年的诸马人物,在风雨飘摇中,选择了异国的隐遁。
这漫漫岁月中的历史演进,这段时光里的这些人物,必然会为我们留下启迪今日的种种智慧。
4
《诸马与民国》,体现出了作者的冷静与思考。
全书自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运动讲起,重点又起自民国建元,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在诸马人物漫长的时间跨度中,作者的阐述是全面而翔实的,系统而有侧重的。再看其持论,也多有中肯之言。
著者对于马福祥、马麒等老一代诸马人物,多所誉扬。然而,这种对军阀人物的誉扬,确有实据为依。譬如他们在抵制分裂、兴办教育、禁绝鸦片、创办实业等诸多方面颇有建树,并初步开启了西北地区近代化的进程。对于以马鸿逵、马步芳为代表的第二代诸马人物,著者认为他们坚持反共到底,无可讳言,但避开了斥责与谩骂。相反,著者对他们在地方上的教育、民族、宗教、文化、实业等在内的政治业绩,进行了细致的观察、梳理。
因此,这部史著,有很多值得圈点的地方。比如,资料翔实丰富,谋篇布局有章法。作者历时数年,收集了大量尚未公开的资料,既有档案资料,也有报刊资料,还有一些当事人的回忆资料。加之作者长期对于这一方面的研究,因而在资料运用上,驾轻就熟,详略有当。又如,文字流畅,生动活泼,又趋于客观,等等。比如,在谈到青海军在新疆的活动时,著者引文明确指出:
“北塔山之战,是中国的边防部队(指骑五军)成功挫败了苏联支持下蒙古国现代化部队入侵中国领土的企图。这场局部战争,当时引起了举国的关注,被称为中国西部的‘九一八’。战争起因是蒙古国向中国边境部队送达最后通牒,居然说北塔山在蒙古国境内,要中国边防军向南后退上百公里。战争一开始,奇台县城已经出现了平民为躲避战火而撤离的迹象。这场战争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中国的边防部队如果没有成功地守卫住北塔山边防,那么,整个的天山北坡都成为了战区,直接的后果是,今天开发西部的支撑点准东煤田有可能成为他人的宝藏。”
诸如这类客观翔实的分析与见解,不时便会在书稿中闪现。
5
《诸马与民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重在实践的意义,是对诸马研究方面较之前人的某些探索的突破。比如,书中涉及大量关于诸马处置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的案例。这些大量的案例,是过去的相关论述中所鲜有的。那么,这种论述对于今天的我们,似尚有启迪的价值,甚至是具有从中参考内容的。
作者引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里面的描述,记录了青海马步芳治下的穆斯林的心理动向——在一次穆斯林节日庆典上,西宁的教长向上万名穆斯林发表演说时称:
“‘第一,要把个人看小点,个人不要不知足,国家才可以安定,才可以太平;第二,要服从能干的领袖,不管他是汉人也罢,回人也罢,藏人也罢。要这样才可以团结,才有力量,才可以不受外国的欺侮。’范长江听到这位青海回教教长的讲话后,他认为‘他这话有多少理论的价值,暂不管它,不过,他这话确代表一种趋势,我们不能忽视’”。
当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得知,“有人自称回教领袖时”,大为吃惊,遂撰写启事,发表声明,表示惊异不已。表示均受各级政府系统之领导,并无另行组织。他在报纸上公开谈到:
“信教自由,载于宪法,但不可以宗教而作国际之活动,此稍有国家法律常识者,莫不知之,盖国际交际,固有外交之整个计划……夫领袖非自称所能成,现在的蒋委员长,人皆以领袖呼之拥之,虽妇人孺子,亦知蒋氏之伟大。”
《诸马与民国》读后,我以为其阐述是全面的,持论亦算公允。已是耄耋之年的我,能够读到这部与我人生旨趣相关的史著,且出自于青年学人之手,我是欣慰的。亦如著者王正儒所言,自己的著述,是几代学人智慧与心力的延续。对此,我是认同的。
这部著述,不周之处自然存在,容留来日再由著者修订。
“一个将领,可以写出一个朝代的兴衰。”那么,这群穆斯林军政人物之与民国、之与西北,其意义显而易见。
诸马人物与内地军阀人物的特殊性,在于他们的穆斯林身份,以及所处的穆斯林社会背景。因此,把他们的有关民族的、宗教的积极面挖掘出来,与今天的西北进行观察对照,是不无裨益的事情。著者能够如此下工夫并付出努力,精神是可贵的,意义是现实的。
今日之世界,和平发展是主流,但冲突与分歧依然并存。作者以西北历史为观照,认为宗教有责任亦有能力,为社会的发展、和谐、人心的安宁,作出应有的贡献。这部著述里的种种努力,是积极且可贵的。是为序。
(王正儒著《诸马与民国》,60 万字,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2013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