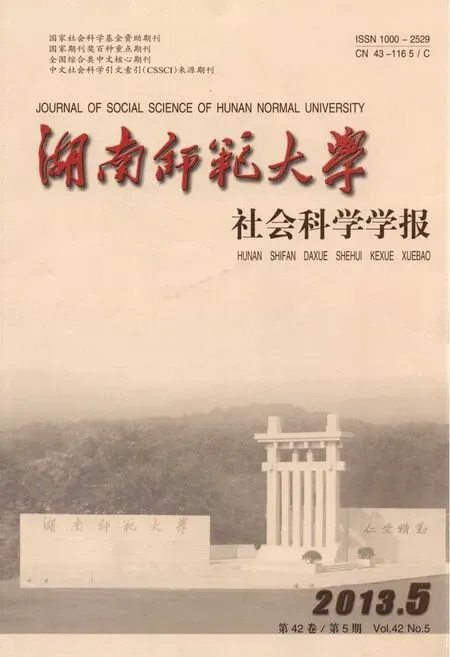王阳明人才观及其价值解读
左志德
“得才者昌”、“失才者亡”,人才是世之栋梁、治国之宝、执政之要,因而古今中外的政治家、思想家都比较重视人才问题。孟子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充分发掘、使用人才资源对政治家而言特别重要,它既考验政治家的智慧,又关乎各项事业能否顺利进行。一代大儒王阳明(1472~1529)堪称儒家人格的典范,他集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为一生,因而对于人才的价值更有其深刻的认识。他指出“(推贤荐能乃)天下治乱盛衰所系,君子小人进退存亡之机,不可不慎”(注:有关王阳明的言语均选自《王阳明全集》,红旗出版社,下同),他深刻认识到,在国家政治清明之时,用人得当则可以助推社会的发展,而危难关头用人得当与否则直接关乎着朝廷的生死存亡。王阳明在人才的评判、选拔、使用等诸方面形成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相比其他政治家而言,他的人才观及其措施更彰显着一定的独特价值意义。
一、人才价值观:“忠”为先,兼具“才”、“体”,达致理想人格境界
自古至今评价人才的最高依据不外乎两个维度:德与才。选人是唯德、唯才或是二者兼顾,这是用人伦理的重要内容。通常,用人的最高境界是做到德才兼备。一方面,“德”依赖于“才”来体现,无才,“德”显得空洞而无内涵;另一方面,“德”是“才”的内在要求,无德,“才”的施展便无正确方向。①事实上,德才兼备的人才判断标准已被历史经验所反复确证是正确的。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虽然有“智者德之帅也”(刘肋)、“唯才是举”(曹操)等偏重才的人才理念,也有西汉时期“举孝廉”的偏重德的荐官制度,但总的来看,智德双修是各代统治者选拔、使用和判断人才的基本依据和原则。如周公对统治者“以德辅天”的要求,西周对人才“六德、六行、六艺”的教育内容,司马光的“德帅才资”主张,朱元璋的“才德俱优者上也,才不及德者其次也。才有余而德不足,又其次也,苟二者俱无,此不足论也”的命题都无不体现了中国古代君王和思想家们所诉求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伦理观。
王阳明基本上接受了司马光“德帅才资”的观点并作了进一步发挥,主张判断人才的首要依据在于“忠”,“忠”是官员的首要德性,他说:“夫朝廷用人,不贵其有过人之才,而贵其有事君之忠,苟无事君之忠,而徒有过人之才,则其所谓才者,仅足以济其一己之功利,全躯保妻子而已耳。”(《卷十四·别録六》)显然,阳明认为,人才与否的首要标准是“忠”,“忠诚”与“才”、“体”相比,借用当代伦理学家罗尔斯的话语,就是具有词典式价值优先地位。忠,即忠诚。在王阳明看来,国家的兴旺和长治久安有赖于官员的忠诚,忠诚要求官员将个人的命运与朝廷的繁荣昌盛紧密联系起来,对百姓诚恳厚道,对朝廷尽心尽力。阳明给予了“忠诚”两个规定性:一方面要对国家忠心耿耿,一心为朝廷效劳,想朝廷之所想,急朝廷之所急。他说,“人臣于国家之难,凡其心之可望,力之可为,涂肝脑而膏髓骨,皆其职分所当。”(《卷十三·别绿五》)当然,在封建专制体制下,“忠”为绝对服从于君主的一种片面的道德义务。
在阳明看来,倘若没有“忠”的德性,“才”可能被滥用来谋求私利:这样的“才”仅足以“济其一己之功利,全躯保妻子而已耳”。王阳明进一步强调:“小人之才,如砒硫芒硝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于参芩耆术之间而进之,养生之人万一用之不精,鲜有不误者矣”。“小人”是相对于“大人”、“君子”而言的,通常而言,“小人”有两种类型:一是无德无才之人,一是无德有才之人。显然,阳明指向的是后者,在他看来,“无德”的有才小人很可能成为社会的毒品,弄得不好会遗祸无穷,借用老子的观点,就是“智慧出,有大伪。”(《道德经·第十八章》)
阳明的“忠诚”为先的人才观实质是坚持以德为先的人才评判标准,但它并非意味着阳明识人的“唯德”单一价值取向。在《全集》中,阳明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人才价值理念:“臣惟任贤图治,得人实难……何者?反覆边夷之地,非得忠实勇果通达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乱。有其才矣,使不谙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过刚使气,率意径行,则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于其地。故用人于边方,必兼是三者而后可。”(《卷十五·别録七》)可以看出,阳明评判人才标准的内涵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忠实勇果通达坦易”是“德”的要求、“谙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是“才”的要求、“耐其水土”是“体”的要求。德、才、体三者兼备的观点反映出阳明判断人才理念的进一步完善。
二、人才选拔观:破“时例”,不拘一格选人;信“公论”,保证“程序正义”
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有一定的特殊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而不能受拘于不合理的条条框框。在人才选拔方式的问题上,阳明践行了这一思维路径,是一个彻底的务实主义者。他在《边方缺官荐才赞理疏》中说:“今边方绝域,无可用之人……其豪杰可用之才,乃为时例所拘,弃置而不用。夫所谓时例者,固朝廷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无不可者。陛下何忍一方之祸患日深月积,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卷十五·别録七》)文中的“时例”意指明王朝当时选用、擢升官吏的惯例,而“破例”就是要在特殊时期打破这种惯例,不拘泥于僵死的典制,做到有破有立。阳明认为,当时的社会中并不缺乏人才,而是不合理的选拔机制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阳明如是说,不见得他要反对科举制,但是至少标识了他不拘一格用人的远见卓识。比如,伍文定是他手下的一位颇有将才且在平定宁王叛乱中立有大功的猛士,阳明十分赏识他的“质性勇果、识见明达”。他当时的官衔是副都御史,于是阳明向皇上建议,伍文定的官职由从三品直接擢升为从二品。由于阳明不拘“时例”的选拔观使得阳明在人才紧缺的条件下也能够找到合适人选,从容应对了各种危局。
“舍短取长”是他不拘“时例”这一人才选拔理念的进一步具体践履。阳明尽管希冀社会“满街皆圣人”,但他所说的满街圣人,仅是从良知本体而言的,而并非意指现实是“满街皆圣人”,他深知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的黄金律,他也不相信现实社会全是“全才”的存在。在他为官生涯中,他坚持“自己用人,权度在我,故虽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的选人原则,即不分出身贵贱、地位高低,只要有德又有一技之长者就可以“器使”,而非全才方可“器使”。思恩、田州社会经济比较落后且经历长年的战乱,许多干才战死疆场,阳明经营多年苦于找不到能够担当起治理一方疆土责任之人。为打破无人可用的困境,他大胆提出“用人之仁去其贪,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卷十·别録二》),表明他舍短取长、不求全的灵活用人观。选人应该注重大节而不纠缠于小节,观察人才要从大处着眼,从本质着手,看其是否有大德、大才。对于君主专制的社会而言,考量德看大节,则主要是看他们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四种最基本的等级秩序方面是否失德。大节有亏,不能为贤;反之,大节不失,虽有小过也不能为贤。舍短用长的选拔策略让阳明在危难之中笼络了一大批务实之才,这对治理地方、发展地方经济提供了极大的智力保障。
“因时制宜”是阳明打破“时例”,尊重社会管理客观规律,一切从实际出发来选拔人才的高超策略。破“时例”形式上是对上级君王的不惟命是从,“因时制宜”进一步彰显了阳明“不唯上、只唯实”的唯物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例如,在思恩、田州等少数民族治理的问题上,如何选拔地方官员阳明是煞费苦心的。他非常懂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古训,究竟在民族地区启用土官还是启用流官,这是阳明一直感到棘手的问题。当时朝廷的主要策略是实行“改土归流”,将土官统统撤换,全部委派流官来进行管理。阳明对此持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天下郡县之设,有大小繁简之别、中土边方之殊,流官土袭之不同,盖亦因其广谷大川风土之异气,人生其间,刚柔缓急之异禀,服食器用,好恶习尚之异类,是以顺其情不违其俗,循其故不异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卷十四·别録六》)意思是,不同的地方风土人情各异,人所养成的秉性也就有差异,因此对不同地方的民众实行治理时,则要袭其俗而遵其情。采用土官或是流官进行治理的道理也是一样,应当从实际出发,不能只听从朝廷的指令,需要灵活变通。阳明因地制宜、因时之治在田州设“土官”,而在思恩则设“流官”。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灵活贯彻执行上级君王的决策,不机械地照搬照抄“时例”;不唯命是从,客观上是以维护明朝统治有序稳定、社会长治久安为旨归的。同时,阳明不拘泥于朝廷的选拔规定,根据治理事物的需要交叉启用土官与流官,也凸显了阳明高超的领导艺术。
在选拔官员的程序上,阳明富有今天西方学界所倡导的“程序正义”的色彩,力主选拔官员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当然,他的“程序正义”并非内蕴着西方学者所主张的宁可牺牲实体正义也要坚持程序正义含义,在他看来,诉诸选拔官员的程序正义,是以选拔出“德帅才资”的官员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即程序正义要从属于、服务于实体正义而不是程序正义高于实体正义。阳明的官员选拔“程序正义”通过听取“公论”来实施,即以民众的评论和意见作为选拔官吏的重要依据。他非常清楚当时的用人弊端:吏部官员高居庙堂根本不了解文武百官的实际情况,仅凭一次次的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并非适合为官,在他看来,这种选拔程序是非正义、不合理的。事实上,由于主考官好恶所形成的偏科或因人员亲疏所形成的作弊更有可能选拔出恶性之官员。为保证选拔官员的程序正义,选出真正肯干事、能干事特别是能干好事的官员,阳明力主应该听取公论。他建议吏部选拔人才时先要充分听取公众意见再决定是否选用。他说:假若某人只有一人举之而九人不举,此人肯定不可以取用;假若三人举之而七人不举,用不用也基本可以确定;假若五人举之而五人不举,对他的考察就应该更加详细;假若七人八人举之而一二人不举,则其人之可用就不必怀疑了。阳明的听取公论的选人方法也反映了他的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唯物史观,但是他所听取意见的对象并非指向于“劳力者治于人”的劳苦民众,而是一些“劳心者治人”的当朝官吏,因此他并非真正的民本主义者。但是无论如何,阳明的选拔办法拓宽了人才选拔的视野,客观上约束了被选拔对象的言行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改善官员选拔过程的公正性,对那些无论是无德无才者还是无德有才者抑或是无才有德者,此举无疑增加了他们谋求一官半职的难度。
三、人才使用观:“久任其职”,增强责任感;“量行加增”以促廉洁
为增强为官者的责任感和廉洁性,保证他们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阳明提出了两种在当时环境下较为新颖的观点:一是让官员久任其职,以此激励其勤于政事,以增强责任感;二是提高在职官员的物质待遇,以促廉洁。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官员勤于政事、恪尽职守、脚踏实地为民为朝廷办事是天下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基本前提也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对于阳明而言,他相信,“政在勤而事在为,富凭人而不在天。利在民不可不言,私出己而不可不克”②。州郡守令和巡抚是治理地方事务的主体,作为政治家的王阳明,他深知只有他们处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奋勇向前,有责任重于泰山的意识;心存“民之所忧,我之所思;民之所思,我之所行”的“以百姓心为心”(《道德经·第四十九章》)的为民意识,才能确保朝廷“万寿无疆”。为此,他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治郡犹如治田”:“牧守之治郡,譬之农夫之治田。农夫上田,一岁不治则半收。再岁不治则无食,三岁不治则化为芜莽,而比于瓦砾。苟尽树艺之方,而勤耕褥之节,则下田之收与上等。……潮地岸大海,积无饶富之名,其民贡赋之外,皆得以各安地利,业俭朴,而又得守牧如退之、李德裕、陈尧佐之徒相望而抚掬梳摩之,所以积有今日之盛,实始于此。”(《卷二十九·送骆蕴良潮州太守序》)农夫种田,勤则下田变良田,懒则上田变瓦砾;官员治理地方也莫过如此,勤于政事,穷郡变富,反之,懒于政事,富饶之郡也会变为萧条荒芜之地。他在总督两广、江西和湖广军务期间,对地方官员的“偷惰苟安侥悻度日”十分愤慨,“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职,而有司之失职,独非小官下吏偷惰苟安侥悻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国宪,不恤民事,不以地方为念,不以职业经心。”(《卷十八·禁革轻委职官》)
那么如何让官员有勤于政事的为民意识和责任感呢?对此,阳明提出了“久任其职”的策略。阳明认为,官员任职不宜频繁调动,只有让其久任其职才能增强他们为官的责任心,才能避免产生急功近利思想。在他看来,官员治理好所属地方需要一个过程,发展好所辖地区经济也并非“一日之功”而需“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的恒久治理,因此考核地方官吏的行政能力时,应当做到任职地点相对固定、对其政绩考核的时间段相对要长一点。阳明在《山东乡试录》中指出:“今者徒据纸上之功绩,亟于行取,而责效于二三年之间,彼为守令者,无是亦莫不汲汲于求去,而莫有诚确久远之图,此则求之太速之使然耳”;“非久其职任则凡所举动,多苟且目前之计,而不为日后久长之谋,邀一时之虚名,而或遗百年之实祸。”(《卷十四·别録六》)显然,阳明在这里提倡考核官员要从长久计,不要让官员产生急功近利的念头。做官如果急于求成,必定会做出一些对百姓不负责任的虎头蛇尾的形象政绩,如他所说就会“多苟且目前之计”,如是,必然引起“膏泽未洽于下,而小民无爱戴感恋之诚;德威未敷于远,而蛮夷无信服归向之志”的不良后果。因此,“久任其职”是增强官员治理地方的责任感,乃至造福一方为旨归的。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足见公正、廉洁是官员的首要德性。阳明之“廉”建立于他对朝中官员贪腐现象的深刻认识,并对此深恶痛绝。追求名利的功利思想是滋生贪污腐败、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的源头。他说:“功利之毒沦侠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相矜以知,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其出而仕也,理钱谷者则欲兼夫兵刑,典礼乐者又欲与于锉轴,处郡县则思藩泉之高,居台谏则望宰执之要。故不能其事,则不得以兼其官;不通其说,则不可以要其誉,记诵之广,适以长其傲也;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闻见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卷二·传习录中》)在阳明看来,功利之毒膨胀了人们巧智、伪诈之术,腐化了社会风气,大部分官员完全被物所奴役,人性完全被异化。
事实上,“人”首先是作为一个自然生命体而存在的,在这个意义上,人和动物都有欲望等情感的表现,亚里士多德在分析人的德性并非自然生成而在于后天养成时首先强调人是情感性动物,“许多情感形式如欲望可能为其他动物所共有,但是如果把人的这些情感性的东西都去掉的话,人也就成为了很抽象的对象了。”③许多私欲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因而这些欲望是正当的、善的。作为凡夫俗子的官员有正当的“私欲”也自然成了他们的内在规定性,因而那些满足正当需求与实现才能所带来的享乐如培根所说的“促进和完善其本质的欲望”是一种积极的善。古希腊伊壁鸠鲁也因此将人之欲望分为三类,其中那些自然和必要的欲望,如对面包和水的欲望都是善的。④在阳明看来,官员之欲望同样有正当和非正当两类,每个官员都有“良知”,只不过被非正当的、非合理的“私欲”(即功利之毒)遮蔽罢了,“良知”是人的至善本性,是造化的精灵,但它常常因“私欲”所遮蔽,只有人人去除“私欲”,那么作为“天理”至善本性的“良知”才会“显现。”⑤正如他所说:“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扭怩。”“私欲”与“贪”相对应,是“廉”的对立面。阳明深知,官员一旦成为私欲的奴隶,他的“久任其职”用人谋略其结果势必是祸害一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理想更是付诸东流了。对此,阳明主张通过“收放心”以达“致良知”——“收放心”就是要“存天理、灭人欲”,使人心“纯乎天理”、进而达到“致良知”的理想境界。为满足官员那些正当的欲望,阳明建议朝廷“量行加增”俸禄。
在阳明看来,此举可以达到一石二鸟之目的:首先,通过从物质上提高官员的待遇,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以此增强官员工作的责任心。当时大部分官员薪水较低,连自己的生活都供不起,加之当时官场上的迎来送往之多、出入供奉之繁,使得大部分官员“穷窘困迫,计出无聊”,阳明体恤各级官吏的实际困难,因此他建议官府对官吏的俸禄“量行加增,使其禄足以代耕,以利于尽心职业”。事实上,阳明此做法形式上是客观为官员,使其“禄足以代耕”,然而,阳明并非是把人当做目的来看,作为官员的人只不过是达到维护朝廷有序安定的一种手段而已,因而“量行加增”以利于尽心尽职,在本质上、主观上均是为朝廷的。
其次,他还坚持认为,增加官员的薪俸还有助于官吏的勤政廉洁。基于他对当时官场现象的深刻分析,阳明认为,古代的官吏激励制度设计很不合理,因为不事贪图之人往往在任满职革之时负债累累,退休后不敢回乡,甚至只得退隐山林,而那些贪赃枉法之徒却衣食无忧,境况比清官要好得多。阳明说:“(官吏)例应所得,又从而才削之,使之仰事府育,且不能遂;是陷之于必贪之地,而责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资将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众乎?”(《卷十七·别録九》)在他看来,现实的社会物质力量对于道德操守如廉洁德性有很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因道德主体即每个个体官员有较大差异性。对于“上者”来说,处此境地,或可甘贫食苦刻励自守,而对于中人之资以及“下者”来说,此境地无疑成了“必贪之地。”⑥人皆有“好色、好利、好名等心”、“闲思杂虑”,与其回避这些人性弱点,毋宁正视它——“量行加增”薪水以促廉洁。
四、阳明人才思想的价值
总体说来,王阳明的人才思想是以儒学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及其人才评判标准为主,辅之以道家的人才评判和使用标准,其中既有继承传统的方面,又有结合现实突破传统的方面。他的这些实用主义的用人观点与方法,彰显了其不拘于古敢于打破传统勇于革新的精神,因而有一定独特的价值意义。
首先,按照阳明的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来选拔官员能有效保障官员的善行(注:“以德为先”原则并不是说要否定“才”,上面第一节已作阐述)。人的行为可能在四种情况下成为善或具有善性:一是有德性的品质而使行为是善的;二是没有德性的品质但完全是出于一种社会要求从而行为是善的;三是既不具有德性的品质也不是出乎社会的要求,而只是迫于社会舆论压力从而按道德要求行事使行为具有善性;四是一种歪打正着型即完全没有道德的品质,而行为恰好符合道德要求,从而这种行为也成了善行。⑦不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行为是否善并不在行为本身而在于行为者是否有德性,具体而言,人的行为是善的须有三个具体规定性:其一,行为主体“必须知道那种行为”,即行为主体必须知道自己在做有德的事,如果只是无意中做了“善”并不足以说明他是有德性的。其二,“他必须是经过选择而那样做”,即行为主体的行为善是一种自由意志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外在的强制、逼迫威胁作出的一种非自愿的行为,否则即使行为有善的属性也不能称之为善行。其三,“他必须是出于一种确定了的、稳定的品质而那样选择”⑧,即行为善是人的德性的自然流淌。
由此看来,阳明的“以德为先”选人原则与亚氏的这些观点有本质上的相似性。只有官员是一个德性之人,才能确保他在治理地方事务中一以贯之地行善事。阳明所处时期朝政混乱、朝廷危机四起,如他所说,朝廷处于“多难兴邦”、“屡经变难”、“民心骚动”、“宗室谋动干戈”风雨飘摇之中。作为一个彻头彻脑的君主专制的卫道士,为稳固、维护明朝廷统治,他深知更需要有德性的官员。有德性的官员浩然正气、大公无私、忧国忧民,其所行之事能给百姓带来福祉,一心忠诚于朝廷;反之,有才无德的官员则只会民脂民膏、利欲熏心,不仅恶化了朝廷与民众的关系,甚至在危难之刻,成了“窃国者”。
时至今日,阳明这一“以德为先”的用人理念也富有时代价值。事实上,人是一个情感和行为的动物,而德性关涉人的情感和行为,它以追求情感和行为的适度为目的,即德性是过犹和不及两种恶之间的中道,因而德性之人的情欲和行为都是善的。⑨因此,考察官员的德性是我们选官、用官的先决前提,当然,今天我们对于官员的德性的具体要求已完全不同于阳明的德性要求。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是判断一个官员德性的根本尺度,一切为了人民群众,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廉洁奉公,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则是这一根本尺度的具体规定性。
其二,阳明辩证性地否定了贵义贱利、弃利存义等正统儒家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利养廉的人才使用观。宋代吕祖谦在《官箴》中说,“当官之法,惟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这如同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德性一样,清廉乃官员之首要德性,它直接关涉到朝政统治的稳定、持久。然而阳明所看到的却是一个个官员利欲熏心、贪污腐化的官场景象,这也促使阳明不得不思考怎样去改变这种局面。⑩如上述章节所说,阳明的思想尽管脱离不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但是,他所主张的“灭人欲”并非一切欲望,而是一切非自然的过分之欲,同时鉴于现实的社会物质力量对于道德操守如廉洁德性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阳明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利养廉的用人观。
阳明这一做法有其一定的价值意义:一方面,增俸养廉的措施在主观上是对道德教育万能论的消极否定(就客观上讲,阳明并非是对道德教育万能论的否定,他一心一意希望通过“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教化使人人达致“圣人”的理想人格)。具体而言,它主观上辩证性地否定了贵义贱利.、弃利存义的儒家思想义利观。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非常反对讲利(物质或私利),义乃为人为官的立身之本,为人为官所行之事均应以义为准绳,“非义之义,大人弗为。”(《孟子·离娄》)。在孟子看来,如讲利,则必然引起危乱,因为利本身是矛盾的,而义则是和谐的。如果“后义先利”,将利看做是最重要的,则势必引起人人之利相冲突、官员之利与国君之利相冲突,结果是争杀篡权不止。反之,讲义,则人人彼此相融合,相济而互益了。[11]阳明从客观现实出发,主张通过一定的物质刺激而并不是诉诸于一切的道德教化来鼓励官员勤于政事、希冀杜绝腐败无疑在当时来说有它的进步性。另一方面,这一措施标识了阳明对人性观有了较前人新的看法。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韩非子的性恶论抑或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说,几乎所有古代思想家、政治家对人性的认识都是囿于这些基本观念中,而且它们都未涉及人性的自然性。事实上,人同动物一样首先是一个自然的生命体存在,有着自然的规定性,都有欲望和冲动的内容。也就是说,人的本性首先是他的自然欲求性。人的自然欲求性包括生存欲求、物质财产欲求等,它是人类行为根本的出发点,是推动个人发展和人类发展的基石,主宰着人们的一切社会活动。阳明由于其认识的局限性,因而不可能将人的这种自然欲求本性提升至思想理论层面,但是他的这一“量行加增”措施却真真切切表征了他对人性的自然欲求性的深刻认识。在他看来,满足了官员的正当的自然欲求有利于官员德性的提升,即责任心和廉洁德性的养成。这个认识显然是对的。当今许多西方国家高薪养廉政策的实施也证明了其合理性。
不过,按照现代民主法制的角度来看,阳明的观点似乎还是有失偏颇:官吏的廉洁与否跟薪酬的水平没有必然关联,官员的“廉”与“贪”主要与社会的法制是否完善、个体的道德水准的高低相关的。
当然,阳明人才观的价值不仅只是上述两点,在上面一、二、三节中均有简述,因而不再赘述。还要说明的是,阳明是君主专制的卫道士,因而他的人才思想不可避免的有相当程度的历史局限性——他的人才措施始终是以维护君主专制的统治者的利益为旨归的,他所说的“人才”,其内涵也只不过是那些代表君主专制利益的各类统治者,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才决不能相提并论。
注 释:
①⑦江畅:《德性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56页,第53页。
②张祥浩:《王阳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85页。
③余纪元:《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83页。
④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96页。
⑤刘立夫:《试论王阳明心学教育思想》,《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5期。
⑥陈立胜:《王阳明思想中“恶”之问题研究》,《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1期。
⑧⑨亚里士多德:《尼可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2页,第48页。
⑩赵玉强:《宋明理学的秩序重建向度及其内在理路阐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2期。[1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北京:昆仑出版社,2010年,第4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