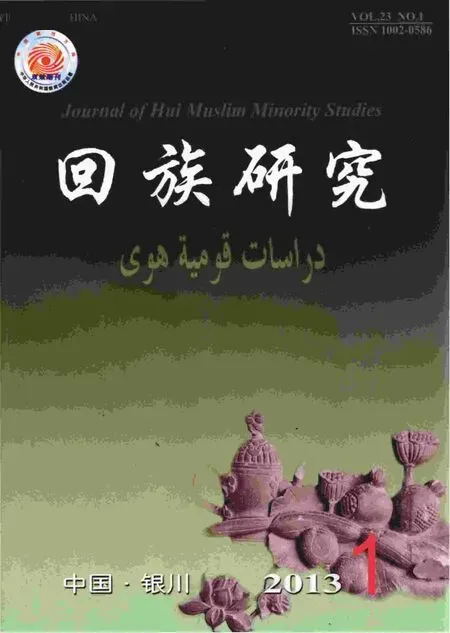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与清代回民起义之关系论略
王银春,李世荣
(宁夏大学 西夏学研究院,宁夏 银川 750021)
连绵不绝的回民起义①一直伴随清王朝统治始末。清顺治年间的米喇印、丁国栋发动的甘州起义;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苏四十三发动的循化起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田五发动的盐茶起义;同治年间的陕甘回民起义;光绪年间的河湟起义。清代西北回民爆发此起彼伏起义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笔者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的角度,对清代西北回族起义的原因做一些必要的探索。
一、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
清初,伴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前后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潮,西北回民最终形成了“大分散、小集居”之格局。这为此后反清起义奠定了基本的人口基数和地理格局。有学者认为:“某个民族的人口数量及其集居模式与社会动乱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并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爆发周期性的大动乱,大都发生在人口稀疏的边远地区,而非人口稠密的中心区域。”[1](P241)这一特征对于清代西北回族而言,则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第一,人口数量的增加。
自唐代以来,回族已经生活在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近400年之往来聚合,人口数量不断增加,而回族人口的真正壮大始于成吉思汗的大规模西征。伴随着蒙古帝国之西征,“阿拉伯、波斯及中亚各族穆斯林,沿着这条交通线,跟着蒙古军队,大量涌入中国。伊斯兰教大规模入华时期开始了,中国伊斯兰教兴盛发达的黄金时代来临了”[2](P13)。据统计,整个蒙古西征期间,被掳掠到中国的色目人总数当时在二三百万左右[3](P5)。蒙古统治者按其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各方面统治之需求,把俘掠而来并有一技之长的色目人别类分派到冶炼、铸钱、造棉、制炮等劳役部门,大多数则编入“探马赤军”,担负着戍边、守卫及随军西征等重任。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政府命屯聚各地的探马赤军就地落户定居,编入“村社”户籍,自此,回族取得了正式的户籍,这不仅标志着回族作为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已经形成②,而且也是回族人口迅速壮大的开始。一方面,伴随着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数日益增多,据《多桑蒙古史》记载:元成宗之从弟安西王阿难答镇守唐兀期间率所部15万士卒皈依伊斯兰教[4]。另一方面,回族一般严格遵守伊斯兰教之婚姻观,“与教外人嫁娶只有对方变更信仰才有可能,结果是其他族人改宗而回族人口大增”[5](P389)。因此,回族与当地居民融合繁衍而人口倍增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
西北回族人口究竟是多少?历代封建王朝对于回族人口均没有详细的数据记录或者相关文献保留。如果探究清廷眼里回回人口之数量,即便是依据现存少量当时官吏奏折的旁敲侧证,也只能还原一个大概的人口状况。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陶模曾奏称:“甘肃汉回错处,综稽民数,本汉少而回多,汉弱而回强”[6],清廷对陕甘人口普遍的看法是“陕则民七回三,甘则民三回七”[7]。回族人口的增长引起了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和严加防范,“甘省各属回民率多聚类而居……以杜逆回改扮汉民,混入甘境,煽诱勾结,数月以来,地方尚称安静”[8]。虽然上述对于陕甘地区回族人口的认识还很笼统,但同治以前,陕甘地区回民人口数量众多,在总人口中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应该是不争之事实。
学界对于清代同治以前西北回族人口数量的关注和研究由来已久,但由于现存史料所限,对于甘肃回民人口数量的研究极其薄弱。马长寿先生认为,“原在陕西省西安、同州、凤翔三府和乾、那、邺三州共二十多个州县里,住有回民七八十万到一百万,占全省人口的三分之一”[9](P1)。丁万录先生认为“陕西八百坊回民在同治年间大起义前总人口当不下一百二十万”[10]。胡振华先生在《中国回族》一书中认为,清同治以前,陕西的回族人口大约有150至200万。霍维洮先生认为“到清代后半期,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族人口应该不少于200余万”[11](P4)。路伟东先生在《清代陕甘人口研究》一文中,经过较为严格的考证认为,“同治以前,陕西回民人口峰值估计在二百万左右,大约占同时期全省人口总数的一成五,甘肃回民峰值人口数保守估计应该不会超过600万,这一人口规模大约占到全省人口总数的三成左右。两省合计,回民峰值人口仅占全部人口的二成五”[12](P255)。上述学者对清代同治以前陕甘回民人口数量的认识虽然差距较大,但综合而言,当时西北回族人口总数应不低于600万,且居住较为集中。
第二,分布格局的形成。
随着回族人口的壮大,尤其是14世纪以后,由于统治阶级的各种移民政策、律例定制以及各类战乱的影响,以致回族在全国范围内频繁迁徙,不断地改变着回族人口在空间分布上的格局,并最终形成“大分散、小集中”的集居格局。明代之前,回族的重大迁徙在历史上有两次:一次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和阿拉伯人的东来贸易,贯穿于整个唐宋时期。从空间分布上来看,这一时期的穆斯林主要集中在中国沿海城市及内陆都城地带,而其迁徙之轨迹经历了东来经商、往返旅居到长期定居三个历史阶段。另一次是蒙古西征时期。伴随着成吉思汗的西征,东来的穆斯林数量庞大且成分复杂,在空间分布上而言,元代回回人虽然散居于全国,但主要分布在西北和东南各省。明代的回族人口迁徙是回族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明朝时期,回族群体进一步壮大,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特点最终形成”[13]。回族人口通过不断迁徙与组合,至明代时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五大回回人聚居区:西北聚居区、云南聚居区、中原聚居区、华北聚居区和江南聚居区[14](P393)。尤以西北聚集区人口为最。明代回回人“大分散、小集中”居住特点最终形成并趋向定型化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二是回回人宦游、经商;三是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中政府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活动最为重要[14](P385)。几经历史变迁,回族人口集居态势最为明显的是西北的陕甘地区。
第三,非常态的人口变迁轨迹。
与历代中国人口变迁轨迹明显不同的是,西北回族人口变迁的轨迹极其复杂,这是一个非常态的轨迹。换句话说,西北回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及其集居格局的形成过程是一种被动的、饱含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过程。
首先,回族人口数量激增始于蒙古帝国之西征,当时俘掠的二三百万色目人绝大多数被编入“探马赤军”,参加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统一中国的征服战争,“在统一南北的大功告成后,探马赤军则被分布于西北、华北、西南及江淮流域的广大地区,在甘肃的河西走廊和宁夏、青海及河州一带,分布最多”[15](P2)。元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亲军”10万大军南下平大理国[16](P2)。在朱元璋攻伐元朝的战争中出现许多回族将领,他们大多随着战争举族而迁,大批江南回族进入云南,形成“南流浪潮”。至清代,清廷在征服和镇压的战争过程中,“又实行移民僻地等政策使陕甘宁青回族又一次大规模流动,形成回族历史上带着深重心灵创伤被迫进行的一次大范围移民”[17]。其次,统治阶级强制性的政治移民是西北回族人口变迁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明代不断推行政治性的强迫移民,人数众多的回族人口,不止一次地从甘肃的河西走廊迁到东南地区,“其种类遂蕃于江左亦”[18]。陕西渭河两岸的许多回民集聚地,大部分被强制安插到甘肃、宁夏等地。清代对于回族的移民政策更为残酷,这种移民的大致轨迹:由中原腹地迁往边疆,而在边疆又大都强制性地安插在偏远、贫瘠的地方。形成了在回汉杂居的边疆地区,汉人往往居于地理条件较好的平川,而回族往往居于地理环境恶劣的山沟的独特境况。再者,民族歧视贯穿于西北回族人口变迁的始终。民族歧视是回族人口变迁轨迹的一个独有现象。元代回回色目人的地位虽然较高,但这都是历代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惯用的羁縻政策。回回色目人“在有元一代,被统治被歧视的实际处境和被压迫歧视的具体事迹,大半都被掩蔽于两种比较复杂的历史现象之中”[15](P7)。明代对于回族的歧视更是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如明《大明律》中明确规定:“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从中国人为婚姻,务要两厢情愿。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入官为奴,其中国人不愿与回回、钦察为婚姻者,听从本类自相嫁娶,不在禁限。”
二、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与西北回民起义之关系
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与清代西北回民起义有着紧密的内在联系。
第一,清代之前,西北回族人口处在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之中,从人口角度而言,爆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因为人口基数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元末和整个明代以及清初也爆发过几次回民的反抗运动,但这些反抗运动往往是呼应同时期全国范围的农民起义。著名的回族将领胡大海、常遇春以及沐英等跟随朱元璋参加反元斗争。明末陕西回民马守应领导的回民起义,同样是从属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反抗腐败的明王朝[15](P11)。清初的甘肃甘州起义,其斗争的目的与当时全国各族人民抗清斗争基本相同,都是以反抗清廷的统治为目标,目的都是反对清廷的统治,带有鲜明的中国古代王朝更迭之际农民起义之特点。因此,没有人口基数支撑以及没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族群或者群体,就不具备大规模的单独反抗斗争行为。
第二,清初,由于西北地区回族人口的增加和集居格局的形成,加之统治阶级的歧视政策,回族的发展趋向于内敛型的发展——强调内部的一致性。
“康乾盛世”的出现,西北回族人口的增长已经基本上摆脱了以往依靠外来人口输入为主的模式而转向本民族内部的自我繁衍,尤其是婚姻趋向本民族内部通婚制促使西北回族社会强调内部的一致性成为一种常态。由此可以看出,人口增长模式的改变,意味着西北回族社会的发展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蹙变时期:就积极效应而言,大大增强了回族的民族意识。就消极方面而言,清代之前,回族普遍实行“族外教内婚”的婚姻模式,这种婚姻模式“既扩大了回族人口与婚姻的来源,又加深了与兄弟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从而成为充实回族社会文化内容的一条途径”[19](P131),然自入清以来,婚姻取向的内敛使回族大大减少了与外族交往的机会,间接造成外族对回族及其伊斯兰教缺乏更为直接的真实的了解而常常对回族的社会、宗教、风俗习惯乃至价值观念抱有深深的偏见和歧视,对这种偏见和歧视的抵制,又使得西北回族更加强调宗教意识以区别于他族。历史发展的轨迹证明,民族之间的融合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相互之间的通婚,因为婚姻对于构筑于两个不同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念之上家庭的相互了解的融合力是十分强大的。在实际的生活之中,双方家庭因为婚姻的纽带而趋向于求同存异,逐渐消除不必要的冷漠和隔阂,这就使得双方都拥有了一个广阔的生存空间。清代以来的西北回族社会,由于人口的增加和居住地域的相对集中,更重要的是,清代实行一以贯之的对回族的歧视政策,强化了回族内部的宗教文化认同,因而回族从以往的开放性族外婚制转向内敛性的族内婚制。加上宗教意识的加强必然会导致教争的产生,“清初以后,回族内部教派斗争的实质就是为了争取宗教权势和经济利益”[15](P54)。清代几次大规模的回民起义都与教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爆发的循化起义,就是因为甘肃循化及河州一带的花寺门宦与新兴的哲合忍耶门宦为各自遵循不同的宗教仪式而爆发斗争,当时的清廷对回族的压迫和歧视政策最终导致回民起义的爆发。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爆发的乙未河湟起义原因之一同样是教争问题,清廷为平息事端,罔顾事实,采取高压屠杀政策,激起回民的愤慨,长期累积的矛盾爆发,由教派之间的教争问题转化为反清起义。
第三,随着回族人口的增加和集居格局的形成,回族的壮大引起统治阶级的重视,但这种重视更多地表现为对回族的歧视和压迫。
终清一代,从本质上而言,清统治阶级对于回族始终采取的是民族文化上的不认同、民族身份上的歧视、民族事实上的压迫,即便是在西北地区民族矛盾还没迅速激化的乾隆时期也是如此③。首先,清廷对于回族的普通态度是“清政府根本不认为回族在政治上有什么特殊性,对回族犹如对汉族一样,实行直接的专制统治”[11](P21)。事实上,对于回族而言,不承认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本质上就是最大的歧视。其次,当时大多数官吏对于回族及其伊斯兰教始终采取歧视和压制的态度。例如雍正二年(1724年),山东巡抚陈世倌上奏雍正:“左道惑众,律有严禁。如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衹,另定宗主,自为岁年,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20](P76)显而易见,回族在他们眼里完全是“济恶害民”、一无是处,而回族之伊斯兰教也是“旁门左道”,足见其对回族及其伊斯兰教歧视之甚。再者,崇尚和遵循儒或佛的士人对于回族及其宗教由于缺乏了解而总是抱着隔膜和偏激态度。例如顾炎武眼里的回回:“惟回回守其固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乡闾,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21](P77)统治阶级如是,在民间社会,对回族的不理解导致的偏见和歧视更甚,这在流传民间的许多故事或者谚语之中有着深刻的反映。
第四,回族复杂的人口变迁轨迹在文化层面而言,导致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大大激发了其浓郁的宗教文化意识,也是推动历次反清起义的强大民族意识。这在回族的历次反清起义中有着直接的反映。
三、结 论
在传统社会,回族人口变迁的轨迹是一个非常态的过程。一方面,回族人口的增加和集居格局的形成是在充满战争的磨难、政治的强迫以及民族的歧视过程中得以完成的。这使得回族强调内部的一致性来应对狭小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清初,伴随着回族共同体的形成及民族意识的加强,要求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给予伊斯兰文化更为广阔的生存空间。但统治阶级对此要求缺乏应对能力,采取一以贯之的民族歧视政策来解决复杂的民族问题,最终导致回民起义的爆发。总之,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与清代回民起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准确认识清代西北回族人口变迁轨迹与回民起义之关系,无疑会对今天的西北民族关系的团结与稳定提供必要的历史借鉴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霍维洮先生在《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一书中,通过对清代西北回民反清运动的特征及运动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现象——“抚局”之深入分析,认为清代西北回民起义,实质上是一场反对清廷对回族政治压制的地方民族自治运动,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起义。
②回族究竟何时形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目前学界说法各异。回族作为一个事实上的民族,其形成,首先是建立在回族人口壮大和伊斯兰教的广泛传播基础之上的,而回族人口真正的壮大,始于13世纪成吉思汗之西征,此其一;同时,回族必然要拥有相对成熟的经济环境和民族文化,终元一代,回族已经形成以农业为基础、商业色彩浓郁的经济结构和以伊斯兰宗教文化为基础、儒家文化为主要外部文化环境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此其二;此外,一个正式土著民族身份之确立必然要有官方在法律上的认同,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回回民族正式编入“村社”户籍,自此回族取得了正式的户籍,这标志着回族在政治和法律上已经被中原王朝正式纳入土著居民的管辖范畴,此其三。因此,回族形成中国的一个正式的民族应该是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年),而在此前,回回民族在中国传统文化层面依然是化外之民。
③对于清廷是否存在对回民的歧视政策,李自然先生在《试论乾隆对回民的政策——兼评李普曼“论大清律例当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一文中认为,清代乾隆时期并没有歧视回民。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判断清代回民是否受到歧视,从根本上而言,是一个是否承认和保护伊斯兰教的问题。大量的史实证明,清王朝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并没有给予回族及其伊斯兰教应有之地位。
[1]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现代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2]冯今源.中国的伊斯兰教[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
[3]民族问题研究会.回回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58.
[4]多桑.多桑蒙古史[M].冯承钧,译.北京:中华书局,1962.
[5]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6]陶模.陶勤肃公奏议[Z].民国13年(1934年).
[7]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Z].回民起义(第四册)[M].神州国光社,1952.
[8]钦定陕甘新疆回匪方略:卷22[Z].
[9]马长寿.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M].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10]丁万录.陕西回族发展变迁的历史考察[J].宁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4).
[11]霍维洮.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组织化进程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12]路伟东.清代陕甘人口研究[D].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2008.
[13]韩永静.历史上回族人口迁移与数量变动[J].宁夏社会科学,2010(1).
[14]邱树森.中国回族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
[15]丁焕章,刘钦斌.中国西北回民起义斗争史[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3.
[16]杨兆钧.云南回族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17]马婷.回族历史上的五次移民潮及其对回族族群的影响[J].回族研究,2004(2).
[18]顾炎武.日知录:卷29[M].
[19]王永亮.西北回族社会发展机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2.
[20]傅统先.中国回教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
[21]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