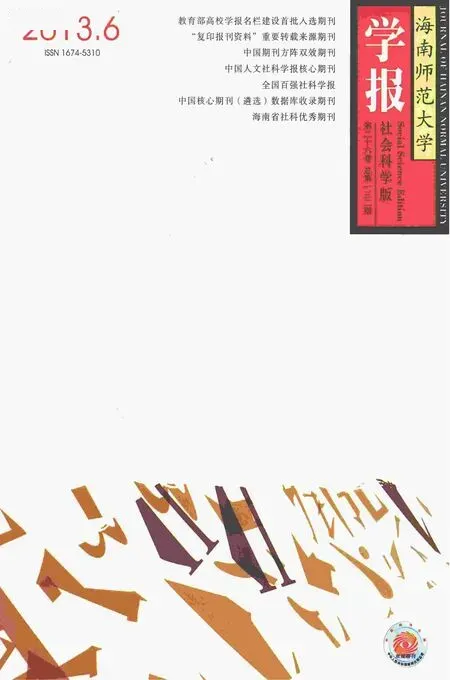双重幻觉与时代困境——论莫言小说《蛙》
夏小雨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小说《蛙》由三层文本构成:首先,叙事主人公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信表达了“我”的写作诉求,即通过“真诚的写作”来“赎罪”,从而“反省历史、反省自我”,使人类“避免许许多多的愚蠢行为”;其次,主体部分以第一人称叙事、写实主义手法讲述姑姑的故事,并在此过程中勾勒出60年中国历史在“我”与高密乡人身上留下的创痛;最后,“我”创作的“荒诞派”戏剧以一种匪夷所思的谐谑笔法,体现历史创伤的强大以及在此创伤驱动之下,世态人情的离经叛道和光怪陆离。
三层文本互相对话,互相补充,似乎可以还原出历史的本相;但事实上,文本之间同时存在着互相矛盾、互相颠覆的张力,继而将历史本相消解在叙事的不同声音中。正是在此张力之下,莫言的写作模糊了崇高与反讽的边界,致使小说所再现的历史一方面给人“逼真”的道德紧张感,另一方面,由于三层文本实则同出于蝌蚪一人之口,故而历史在受限的“垄断叙事”下,难免陷于主观的夸大与遮蔽,而这种潜在的虚构性落实到文本语言,便反过来构成了一种传奇演义式的声调,①较明显的表现如姑姑说故事“像评书一样引人入胜”,再比如两次提到肖上唇对历史的污蔑与捏造。从而内在地颠覆了“逼真”的写实主义要求。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内在颠覆,在主人公蝌蚪以“真诚的写作”来赎罪的写实主义要求下,《蛙》同时向我们暴露了这种“真诚”的虚伪性与“赎罪”的不可能——而这正如主人公自己所交代的,他有时候自己也分不清“是在如实记录还是在虚构创新”——历史真实在讲述与再现的过程中被有意无意地虚幻化。并且,我们很难说这种虚幻感究竟是源于历史本身的荒诞、浮幻、难以置信,还是源于叙事者的“不真诚”与叙事声音的不可靠。又或者,这其实是一种“双重幻觉”?
这里使用“双重幻觉”一词,是借用自齐泽克的意识形态理论。齐泽克所谓第一重幻觉是来自拉康理论背景,即,“(我们所体验到的)现实并非‘事物本身’,而总是已经被象征机制象征化、构成和结构了的。”[1]21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蛙》的“写实”对象实则是经过特定机制异化之后的现实。评论者在解读莫言创作时常使用“感觉化”一词,并将“感觉”视作我们与世界最基本也最直接的联系方式。这当然是毋庸置疑的,但如果我们仅将莫言作品中的感觉想象为一种“感性直观”,并进而停留在本能理论的范围内对之加以分析,那么这种“本质化”的处理方式可能会令我们忽视其“感觉”的历史内涵。正因此,在《蛙》的“感觉”中辨认非直观的、中介性的意识形态因素,或许能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知历史何以表象为如此“荒诞、浮幻”的面目。
如果说齐泽克的第一重幻觉乃是建立在“知”的层面,那么其第二重幻觉则无疑侧重于人们的“行”:在他看来,人并非不知道现实的虚妄和虚妄的根源所在,“他们很清楚地知道事情的实际状况,但他们仍然这样做着,似乎他们压根不知道。”[2]这用《蛙》中人物李手的话说便是:“这就是文明社会呀!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所谓“演戏”即明知是假,但还要自欺欺人地照着“剧本”行动。小说中“我”和小狮子将陈眉的孩子视作自己的孩子,便无疑是“明知故犯”地实践了一种幻觉;而最后的话剧更是将这种知与行的分裂以极端戏剧化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种知行的歧出,同时恰恰证明了我们所说的“叙事者的‘不真诚’与叙事声音的不可靠”。
值得注意的是,齐泽克将这样一种“双重幻觉”的本质理解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1]15。而这正是叙事主人公性格中懦弱、顺服乃至“犬儒”的核心。但不仅如此,通过以“犬儒主义”解释蝌蚪的行为、解释《蛙》文本中的意识形态机制,我们最终的目的乃是理解并评价作者本人的创作心理。莫言并不讳言主人公蝌蚪即自己的化身,而这也就是说,作者与叙事主人公之间保持着基本同一的立场,他们共享了这种犬儒的行为方式,同处于这一意识形态运作机制之中,并共同经受着痛苦而无可如何的时代困境。
本文正是希望能够把《蛙》放回时代的精神结构之中,尝试理解这一困境的内在成因,并从而探问小说表现/再现真实的限度与可能性。①感谢张业松老师在讲座“莫言与当代中国”以及“望道计划”第一讲的授课过程中开示的理解方式。
一 归罪对象的确立:个人与象征机制的互动
《蛙》讲述了历史中人如何作恶又如何赎罪的过程,而“赎罪”的第一步即是找到罪恶的根源、识别犯罪的动机并确立归罪的对象。值得注意的是,叙事主人公蝌蚪曾这样分析“文革”期间姑姑万心的犯罪心理:
她十分狂热,对曾经护过她的老院长毫不客气,对这黄秋雅,那更是残酷无情。我明白,姑姑其实是想以这种方式来保护自己,就像一个走夜路的人,之所以高声歌唱,实因为心中惧怕。
由此可见,在蝌蚪看来,姑姑犯罪的内在动因乃是出于惧怖。因恐惧而作恶,在此思路之下,我们可以这样重述《蛙》的主线情节。
以“生育史”为主题的《蛙》,其对生育的叙事实则与对“食”的关注紧密联系在一起。饥荒过后的生育高峰,用母亲的话说是“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而针对人民饱暖之后所施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姑姑的辩护理由则是“计划生育不搞不行,如果放开了生,……地球都要被中国人压扁啦”;甚至“我”在回应西方人对中国计划生育“有失公允”的批评时也说:“地球上的资源就这么一点点,耗费了不可再生。”在此,无论是对“生育”的鼓励还是控制,其合法性来源都在“国家”:既是因为国家人口的“缺乏”所以鼓励生育,又是因为人口的增长将导致国家资源的“缺乏”而控制生育。在这表面的自相矛盾背后,我们会发现,国家理由之下推动生育政策的真正驱力恰恰是人们对“缺乏”的恐惧。而这种恐惧,如果联系到小说一开始的饥荒,便完全不难理解了。曾有思想者将类似心理概括为“灾民理性”(任不寐:《灾变论——寻找另外一个中国》),其本质即是国人在一次次天灾人祸的创伤之后产生的一种生存性的恐慌,它相信生机是如此有限,以至于人必须通过抢夺与破坏他人的生存机会以维持个人的生命空间。
正是通过这一灾民理性的视野,蝌蚪既为姑姑的罪行找到解释与开脱的方式,同时或许也为特定历史环境下自身与乡民的种种罪行找到托辞。在现代中国,我们面对创伤断裂的历史,诚然需要并且应该为之找到一个理性解释的途径,无论是蝌蚪以“真诚的写作”来“赎罪”的愿景,还是莫言以及其他当代作家以小说再现并反思历史的努力,无不是基于这种心理;但在提供解释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警惕并避免一种简单的归罪机制。
避免简单的归罪,首先需要认识到:虽然《蛙》中叙事主人公蝌蚪为我们提供了一条解释罪行的途径,但我们必须承认,个人的灾民理性惟有在象征机制的运作下,经由意识形态的有效组织,罪恶才得以大规模地被发动。因此,为了理解罪行真正的内在动力,我们还必须深入个人与象征机制的互动过程。①齐泽克曾如此评价这样一种局限于本能领域的分析方式:“以无意识的力比多情结或直接借用‘死本能’的说法,为苦难与精神创痛提供一种精神分析式的解释方式,这会遮蔽毁灭的真正原由”,并会让我们最终陷于一种“无法和解的力比多困局”之中。见SlavojZˇiZˇek,“The Spectre of Ideology,”in Mapping Ideology,p.6.这同时是因为,“精神分析的对象并不是某种原始的本能冲动的主体,而是——正如拉康一再揭示的——现代的,笛卡尔式的科学的主体。”见Ibid.,p.29.而这互动主要表现为一个“确认”的过程。
深入这个确认机制,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小说中的两个主人公:姑姑和“我”。
(一)姑姑
在《蛙》的情节设置中,姑姑很晚成婚并且终生未育。通过叙事者蝌蚪的视野,我们未曾读到姑姑在男女之事上曾有过任何涉及个人欲望的表白。甚至,在姑姑与王小倜恋爱直至对方叛逃的整个过程中,叙事者也从未向我们明示两人间有过任何爱意。事实上,蝌蚪自承其“青春的大门”的“敞开”、爱的启蒙,是要等到日后见过王肝对小狮子的狂恋才完成的。在此,王肝对小狮子的爱欲颠狂,恰恰反衬出姑姑与王小倜的关系中爱欲的缺席。而这种缺席正可以呼应王小倜留下的日记中对姑姑的描述:“红色木头”。
“红色木头”这个说法当然带有非常鲜明的时代印记:“木头”固然暗示了姑姑爱欲的匮乏,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匮乏”与“红色”的所指直接相关。毫无疑问,“红色”所指向的正是一个庞大的象征机制。或许正是因为姑姑已经把她全部的欲望投射在这样一种红色理想之中,②王斑针对“文革”时期美学意识形态的分析中,同样指出在对“红色”理想的确认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因即是这样一种“对爱的对象(love-object)的力比多需求”。见Ban Wang,“Cultural Revolution:A Terrible Beauty Is Born,”In The Sublime Figure of History: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 - Century China(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03.故而她无法对一个并不具有象征意义的普通男子产生真切的、感性直接的爱情。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面对王小倜的叛逃,姑姑从未表达这样一种合理的情感:恋爱中被恋人抛弃的痛苦以及对另一方背叛恋爱关系的责备;相反的,她像是始终处在一种拟态的国家立场上批判对方的政治错误。这种批判更深层的心理正是认识到对方因为叛逃而失去了他在“红色”象征机制中的位置。所以相应的,为了重新确认自己在这个象征机制中的位置,姑姑不惜使用最为酷烈也最为极端的表述方式:“我恨王小倜!我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由此可见,姑姑正是在这种对党生死以之的忠诚关系中,既化身为“红色”象征机制的一部分,又实现了她作为“木头”所匮乏的强烈爱欲。意识形态询唤主体,而主体也通过回应这一询唤从而实现自身对“大他者”的欲望。③这当然主要来自阿尔都塞的著名理论,见Louis Althusser,“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Notes towards an Investigation),”in Mapping Ideology,pp.128 -132.正是在这回应的过程中,个体立场上升为国家立场:这就是为什么在此后推行计划生育的过程中,面对任何控诉,姑姑都能够毫无认知障碍地以国家理由为自我的正义性辩护。
然而到了晚年,姑姑每每对其曾经的罪行痛悔不已,甚而对那“忠诚关系”也有所埋怨:她认为自己“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这种短暂脱离忠诚关系的清醒状态,或许同样可以对应于王肝在小狮子嫁与他人后的情感表白:“爱情是一场病”,病愈清醒之后,“我只恋我自己。……甚至恋我的影子,我经常跟我的影子说话呢。”
当然,姑姑并没有取得与王肝同等级别的清醒,在短暂的埋怨之后,姑姑会继续为国家理由——也即她与欲望对象的忠诚关系辩护;也正因此,她无法为罪行找到归罪的对象,无法为屈死的亡灵正名,因而无法摆脱在梦魇、幻觉或现实中被象征化为蛙的婴儿们——那些被她夺去生命机会的婴儿成了她手上永远无法洗净的“腥臭的血”。而这也就解释了她在感到突如其来的罪恶与悔恨后,为何会投入民间艺人郝大手的怀抱:泥塑造人的幻觉正是在“象征化”地为她曾扼杀的那些生命招魂,并从中复现那个曾经作为生命给予者的自己——那个在“黄金时代”作为“送子娘娘”的、双手“芳香”的自己。
(二)“我”
与姑姑对象征机制的确认不同,叙事主人公蝌蚪的态度似乎始终有所游离。他当然没有姑姑那样的革命热情,更确切地说,他是那种只想过过日子的人:《蛙》中多次不加掩饰地写到“我”的欲望,而欲望的实现方式也常是扎扎实实的男女之事。相较姑姑,“我”更像是个普通人:难抑食色的本能冲动,也很难不被世俗的名利欲望所左右。
也正因此,“我”的确认机制更多地发生在本能与伦理的互动之中。伦理是个特别宽泛的提法,落实到小说中,“我”所面对的伦理困境大致可以具体化到以下几种情境:如何处置王仁美腹中的儿子、王仁美死后如何面对新任妻子小狮子、在陈眉怀上自己的孩子之后如何面对乱伦等一系列道德自责。
第一个困境:“我”曾一度很坚定地要王仁美打掉孩子,这当然是因为事关自己的党籍、职务(再加上一个“义正言辞”的理由:“涉及到我们单位的荣誉”);然而几次调停劝解失败之后,“我”又动摇了:“姑姑,要不就让她生了吧。”但在姑姑的一意孤行之下,“我”还是顺从了姑姑的决定并最终间接地酿成了悲剧。
第二个困境:姑姑想让“我”迎娶小狮子,但“我”起先是以不喜对方长相、对方是朋友意中人以及自己对亡妻的追思为由,看似构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伦理阻力,但是半推半就地,“我”开始发现小狮子“真是丰满啊”。这是本能战胜了伦理阻力;而与此同时,“我”又诉诸另一个伦理借口来掩饰这种本能冲动:“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如果不按,岂不是又把人家小狮子坑了?——我已经害了一个女人,不能再害第二个了。”这种伦理掩饰无疑更加暗示了“我”的虚伪性。更有甚者,“我”在完婚之后甚至连这种掩饰都放弃了:“当我的肉体与小狮子结合在一起后,心也同时贴近了。我无耻地说:狮子,我觉得跟你比跟王仁美更像夫妻。”这就是完全地屈从本能了。
第三个困境:首先,“我”在看似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小狮子“利用”而造成陈眉受孕(当然,这种“不知情”同样值得推敲)。紧接着,“我”先是处在种种道德自责中,然后渐渐被说动,甚而把陈眉腹中的孩子想象成是对王仁美腹中死去的儿子的补偿。这无疑又是一个以伦理掩饰本能的过程:一方面“我”的生本能让“我”渴望血脉的延续,另一方面“我”又必须将自己的行为正义化为一种“赎罪”的努力,并试图通过这个伦理化、象征化的过程,同时消除“我”对王仁美之死的负罪。而这种象征化的想象,更是以最为荒诞反讽的方式呈现在小说结尾:“我”最终将小狮子受孕的幻觉确认为一种现实,甚至在对杉谷义人的讲述中,毫无认知障碍地把小狮子说成“超高龄初产妇”,从而忽视陈眉分娩的客观事实。正是在这一颠倒真幻的确认过程中,“我”得以最终骗取伦理的正当性。
上述这三个困境共同展现了“我”在以伦理为目标的确认过程中,一再暴露出本能冲动,并继而在本能与伦理的“协商”下获得一种自欺欺人的正义幻觉。而这种幻觉逻辑足以帮助我们领会到当事人知、行的分离。我们看到:他明知所为出于本能,却宣称自己所行乃是出于道义;他明知背离道义,却托言一切都是在姑姑或小狮子的操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逆水撑船不如顺水推舟”——而这恰恰暴露出“我”的犬儒本性。
二 归罪机制的崩溃:亡灵归来与“虚妄”的“解脱”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试图将罪行还原到文本——历史的语境,从中我们同时能够感受到,象征机制如此庞大,以至于主体与象征系统的互动过程总是以主体的被淹没而告终。而主体性的失败同时导致原有的归罪机制的失效,体现在父亲的话中便是——“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也不知道该怨谁。”——既然受本能支配、被庞大机制操持的渺小个体不足以承担这些罪恶,那就只能归诸超越性的“命”,归诸无情的历史正义了:“……那是历史,历史是只看结果而忽略手段的,就像人们只看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埃及的金字塔等伟大建筑,而看不到这些建筑下面的累累白骨。”在此,“白骨”作为历史的内在构成始终潜伏于现实时空之下,并喻示罪行无法被象征机制消化,亡灵无法被告慰因而无法被安葬。①齐泽克曾将大屠杀与集中营这两件创伤事件视为20世纪“亡灵归来”的典型案例。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尚不能给予死难者一个体面的安葬,不能把由他们的死亡而造成的创伤整合进我们的历史记忆,那么这些“活死人”必将继续萦绕于我们当下的时空。见齐泽克:《邪目而视:透过通俗文化看拉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9页。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蛙》中我们能够反复读到这种“亡灵归来”的原型叙事。比如“我”在迎接小狮子“生育”的当下竟陷入噩梦,梦见母亲与亡妻王仁美,并在梦中极富象征意味地说:“娘,您能不能坐下歇会儿?你们这样来回转,让所有的人都不得安宁。”屈死的亡灵在梦中“来回转”正说明了她们仍萦绕在“我”的现实空间,②这句话中最富意味的暗示其实是:亡灵归来不仅让“我”不能安宁,更是让“所有的人”不得安宁。“所有的人”,当然也包括了历史在场中的我们。并同时喻示,“我”通过陈眉受孕产子的事实到头来无法令她们、也无法令任何人“安宁”。这最终迫使“我”在信中承认:“尽管我可以用种种理由为自己开脱……但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明白地意识到,我是真正的罪魁祸首。是我为了那所谓的‘前途’,把王仁美娘儿俩送进了地狱。我把陈眉所生的孩子想象为那个夭折婴儿的投胎转世,不过是自我安慰。这跟姑姑制作泥娃娃的想法是一样的。”确实,姑姑之所以制作泥娃娃,同样是基于这种无法摆脱的罪感。对此最具象征张力的表现当然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对蛙的恐惧:“蛙”既音近于“娃”,又音近于“娲”;“我”甚至相信人的远祖即是蛙;姑姑也曾几番自述其恐惧的原因。以上种种构成了一整个以“蛙”为图符的象征机制,其核心恰恰是民间的生育信仰与生育传说。正是因为姑姑早年的“罪行”冲撞冒犯了这个机制,所以她不得不面对亡灵一再以象征的方式归来的惧怖:她把这些“蛙”称为“讨债小鬼”并痛言“一个有罪的人不能也没有权力去死,她必须活着,经受折磨,煎熬,……用这样的方式来赎自己的罪,罪赎完了,才能一身轻松地去死。”
然而正如“我”在信中所说:
先生,我原本以为,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赎罪的方式,但剧本完成后,心中的罪感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变得更加沉重。……沾到手上的血,是不是永远也洗不清呢?被罪感纠缠的灵魂,是不是永远也得不到解脱呢?
“我”以写作召唤亡灵而赎罪的努力,恰恰可以对应于姑姑泥塑“造人”以还债的心理,两者最终只是象征界的挣扎而永远达不到真正的赎罪。那么既然罪感注定无法解脱,负罪者又如何在现世找到安慰?叙事主人公蝌蚪在此再度表现出犬儒的本性。他说:“一个自认为犯有罪过的人,总要想办法宽慰自己,就像您熟知的鲁迅小说《祝福》中那个捐门槛的祥林嫂,清醒的人,不要点破她的虚妄,给她一点希望,让她能够解脱,让她夜里不做噩梦,让她能够像个无罪感的人一样活下去。我顺从着她们,甚至也努力地去相信她们所相信的,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吧。”这里有两个层次:首先,“我”明知她们的都是幻觉,却在行动上顺从了她们;其次,“我”甚至要努力在认知上信服她们的“幻觉”。在前一个层次上,“我”尚且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旁观着她们的“虚妄”;而在后一个层次,则无疑“我”也努力将自己改造成虚妄的一员。这种看似荒诞的自我改造,其背后动力正如上引信中的自白所言:“我”也是被罪感纠缠而无法解脱的灵魂,“我”也需要这样的幻觉。
据国学博览馆副馆长邵馥萌介绍,国学博览馆不售门票,全部经营性开支一律由集团公司支付,将不定期组织大中专院校、中小学、企事业单位人士免费参观。国学博览馆将利用网络公众号这一载体,定期发布有关国学传统文化的主题学术文章,并组织国学传统文化的研讨和讲座,做国学传统文化相关课题的理论研究,以体现国学博览馆的宗旨“继圣贤明德之学,求知行合一之用”。
其实,在《蛙》中几乎所有人都需要并实践着这种幻觉——“世界就是一个大舞台,每天都在上演着同样的剧目。”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滥调,此处“世界大舞台”其实暗示了象征机制的两个必要前提:一是主体的主动“参演”,一是主体面对作为“脚本”的象征机制时的完全被动。这两个看似内在矛盾的前提,之所以能相安无事地共同维持这个机制的运行,其背后的动力正是一个整体性的犬儒主义意识形态:我们明知而故犯。
换句话说,我们明明已经感受到幻觉与现实间的差距,感受到意识形态的面具与个体的直观间的距离,甚至为这种距离而痛苦、愧疚,但我们仍会找寻一切理由保留这个面具。这是因为,离开面具和幻觉即意味着我们不再能将罪恶归诸集体、组织、国家,而不得不以裸露的个体的方式直面历史中那些未被安葬的亡灵。
三 《蛙》的主题:信仰的升降与民间的浮沉
无疑,《蛙》为我们深刻地揭示了当代中国的生存性绝望。但与此同时,所有时代的文学,绝望的主题几乎都通向一个信仰救赎的主题。《蛙》中化身“蝌蚪”的作者莫言正是把这个信仰放在了“生育”上。
这是真正伟大的事业,高尚的事业,甜蜜的事业……先生,我深深地被感动了,我的眼睛里盈满了泪水,我听到了一个最神圣的声音的召唤,我感受到了人类世界最庄严的感情,那就是对生命的热爱,与此相比较,别的爱都是庸俗的、低级的。先生,我感到自己的灵魂受到了一次庄严的洗礼,我感到我过去的罪恶,终于得到了一次救赎的机会,无论是什么样的前因,无论是什么样的后果,我都要张开双臂,接住这个上天赐给我的赤子!
这种信仰救赎的崇高体验无疑呼应了莫言写作《丰乳肥臀》后所说的“尽管文明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物质的进步也带来了道德的沦丧,但人类毕竟认识到了这些负面效应并力图矫正之,尽管人类无论多么进步也摆脱不了痛苦的折磨旧的痛苦消失新的痛苦产生但肌肉发达、骨骼匀称的男子和乳丰臀肥、花容月貌的女子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不息就是大自然的奇迹就是宇宙的至高无上的幸福。”①莫言:《〈丰乳肥臀〉解》,载于《光明日报》1995年11月22日。见杨扬编:《莫言研究资料》,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3页。
换句话说,《蛙》的60年生育史所见证的,正是生活世界中信仰的升降、确认与失落。最开始是民间自发的信仰,用母亲的话说就是“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传统社会里女人的“地位”、“尊严”、“幸福和荣耀”的来源,也是对生命“完整性”的确认。但这种信仰在“文革”中却被另一种“信仰”所替代:“我”曾看到红卫兵拆庙毁神、将送子娘娘扔入水中。这里我们可以读到民间信仰被放逐的过程。而时至今日,“我”又看到庙殿重起,送子娘娘被请回,这看似是民间信仰的复位与回归,实则内里已被换成市场经济逻辑下的异教信仰。一句话,生育史的变迁既见证了信仰的升降,也见证了民间的浮沉。当然,更确切的说法或许是,莫言作品中的“信仰”始终与“民间”保持着一种互相定义的关系。
这让我想到10年前莫言与大江健三郎(或许就是杉谷义人的原型)的一次对话。②《寻找红高粱的故乡——大江健三郎与莫言的对话》,载于《南方周末》2002年2月28日。见《莫言研究资料》,第77-85页。对话中,大江表白了他对文学的信仰:“我今年六十七岁,直到今天我仍顽强地认为小说写到最后应该写出一种光明,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信赖。”他肯定了莫言早期小说对这种信仰的表现,同时说道:“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文学是对人类的希望,同时也是让人更相信人的值得庆幸的存在。”他问莫言:“您在小说里是怎么表达的呢?”
有意思的是,莫言并不直接回答他的问题,甚至在整个对话中都没有出现“光明”、“信赖”、“希望”、“信仰”一类的字眼;相反的,在信仰的话题之下他再度谈起家乡和民间立场:他认为“作家要为老百姓写作”的口号应该改成“作为老百姓而写作”,“因为我本身就是老百姓,我感受的生活和灵魂的痛苦是跟老百姓一样的。”
我们要如何理解莫言的这个回答?他未能正面回应文学信仰的话题,是否说明了他不能相信这种“光明”的希望?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或许能够理解何以10年之后的《蛙》最终选择在犬儒主义的双重幻觉中消解“希望”本身。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莫言的回答其实已经完整表达了他的文学信仰,即,文学应该是贴着生活本身并内在于时代的;而如果光明与希望并非内在于时代的,那么文学家也不应把自己变成时代的“救世主”。如果我们把莫言答话的完整含义补全,或许是:作家不应“为(提供)老百姓(希望而)写作”,而应该“作为(同样无望的)老百姓而写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莫言的没有信仰,恰恰反映了他真正的信仰:这是对民间、对生活本身的忠诚。
这种忠诚在最好的时候,固然会成就写作者的真诚、勇敢;但在最坏的时候,它也可能会变成犬儒的和驯顺的,在反映现实的过程中失去文学的反抗性,在讽刺虚假意识的同时把爱、正义与善一并变成虚伪价值。身处时代内部的文学,又如何逃出后一种限度与危险所在?这不只是莫言一人需要面对的。
但限度所在,也或许正是可能性所在。最坏的犬儒式的“明知故犯”,或许反过来可以成就最好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吉诃德精神?
[1] SlavojˇZiˇZek.“The Spectre of Ideology,”in Mapping Ideology,ed.SlavojˇZiˇZek.London:Verso,1994.
[2] 〔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