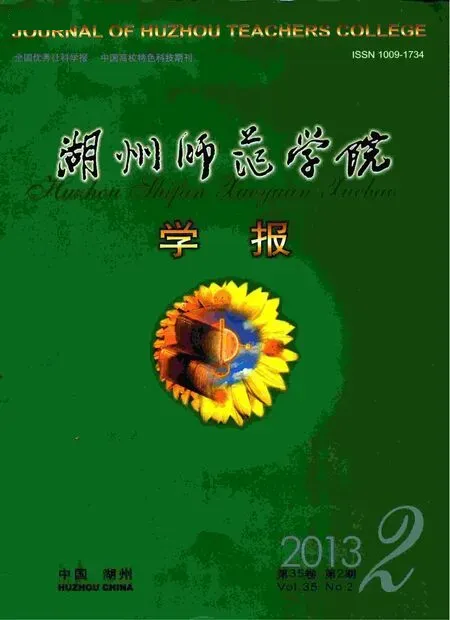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语言的词法偏误分析*
杨杏红,杨艳君
(闽南师范大学 中文系,福建 漳州363000)
使用域外的汉语教科书来研究汉语最有利的地方在于材料的口语化程度高,能够最为直接的反应当时语言的状况,如利用韩国早期汉语课本《老乞大》来研究元代的汉语;利用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课本来研究清末民初的官话和方言等。这些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我们就不一一例说了,但也有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即这些材料中的语言会不会存在着偏误,也就是材料的可信度的问题,因为这些书的作者毕竟母语都不是汉语。
有关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教科书的语言能不能用来研究汉语,李无未曾详细的分析了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的特点,认为一些较为经典的教材,如《官话篇》、《北京官话谈论新篇》等等,用来研究清末民初的北京官话是十分可靠的。但我们也注意到有一些教科书,如明治中期的北京官话课本《日英汉语言合璧》、《英清会话独案内》,限于作者的汉语水平和当时的时代特点,课本中的语言出现了一些偏误。在本文中,我们将以明治中期的这两本北京官话课本为基本材料,找出课本中出现的词法偏误,并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一、实词偏误
(一)名词
1.误用
例1:※這個表是箱子很好看。(It is a watch the case of which is very pretty.)
例1中,“箱子”应改为“盒子”,作者直接使用了日语中含义为“盒子”的“箱”这个词,错将二者等同起来,类似的偏误在该教材中还有不少。
2.残缺
例2:※別說糊塗□。(Oh!You don’t mean that.)
例2在句中空缺处添加“话”。“别说糊涂□”中“说”这一动作的承受者由名词性词语充当,“糊涂”为形容词,不能由“说”来发出,应在其后添加名词中心语“话”,句义才通顺。
(二)动词
1.误用
例3:※我告訴他說必去,我看見他不去。(...it seems likely that he will not go.)
例3应将“看见”改为“看”,句中把“看见”和“看”等同起来。“看”做动词还有“观察并加以判断”的意思,而“看见”只表“看到”,指看这一动作的结果,并不能与“看”等同。
2.重复
例4:※是得再改縫一縫。(they require to be altered.)
例4应将“改缝一缝”换为“改一改”或“缝一缝”。作者在选用句子中心动词时运用类似联想,即由“改”(altered)想到“缝”,二者并用使得句中出现了多余成分。
3.残缺
例5:※表是你的了,小心別□壞。(The watch is yours.but take care not to break it.)
例5应在空缺处添加“弄”这一中心动词。作者刻意简化句义表达的方式,回避结果补语而导致偏误。“弄坏”所体现的汉语特有的述补词组的格式是汉语学习的一个难点,汉语补语系统本身的复杂性易导致作者采取回避的策略。
4.位置不当
例6:※青馬是。(We take the black horse.)
例7:※A:還沒說。B:說那麼去。(went out to tell him so.)
例6应改为“是青马”。作者受到日语“主宾谓”结构的影响,把母语规则直接套入汉语句子。例7的B句应改为“去那么说。”作者对汉语相对更为灵活的语序知识掌握不全,加之受到英语“tell him so”省略人称代词后语序直译“说那么”的干扰,而把“去”放在句末;也可能是过度泛化了趋向补语位于句末的汉语语法规则。
5.“是”的过度使用
“是”在官话中,是一个用法比较复杂的系动词,在日本明治时期的北京官话教材中,有关“是”的偏误出现得比较多,这里我们具体分析以下几种情况:
(1)错用。
例8:※你們有什麼新聞紙沒有?——是,黑拉得嘎謝得和申報。(Yes,we have Hereld Gazette and shen-paw.)
例8将“是”改为“有”,作者受到英语答句“Yes”的影响,将其直译到汉语句中。
(2)多余。主要表现为应答时的多余,如:
例9:※你吩咐車沒有?——是,吩咐了,兩點鐘的空夫。(Yes,I have ordered it for two o'colock)例9应去掉“是”,在英语中,一般疑问句的答句格式“Yes,…”的影响,将其直接套用到汉语是非句的答句上。
(三)形容词
1.误用
例10:※下雨的時候兒必蒸。(When it rains,the atmosphere loaded with damp.)
例10蒸”应改为“潮湿”,作者直接借用了日语里的“蒸し”这个词语而使用到汉语中来。
2.残缺
例11※褂子穿第二□的。(I shall put on my second-best overcoat.)
例12※請坐,老□沒見了。(I have not see you for a long time.)
例11、12应在空缺处依次添加“好”“久”两个形容词。作者对汉语“修饰语+中心”语的偏正结构规则掌握不全而导致遗漏,此外,作者仍受到英语的影响,在例12中“long”译为“老”而忽略汉语选用久来形容时间的长短。
(四)量词
主要表现为残缺:
例13:※有什麼緣故分十二□月。(What give rise to the division of the year into twelve months.)
例13在空缺处添加量词“个”。作者过度泛化如“十二天”等无须添加量词的特殊结构,未能辨别“十二月”与“十二个月”在表意上的差别,将二者等同起来。
(五)代词
1.误用
例14:※他現在往這麼來哪。(He is coming.)
例14“这么”应改为“这儿”或“这里”。汉语的不同的指示代词的具体含义不同,在句中的作用也不同,作者在运用时采用类推的办法,将其不适当地套用,从而造成偏误。
2.残缺
例15:※老爺在家裡麼,□見一見。(I wish to see him for a while.)
例15应在空缺处添加“我”。日语中人称代词省略称代词的省略非常普遍,而汉语使用人称代词的频率相对要高得多,这样就产生词类的偏误。
二、虚词偏误
(一)副词
1.误用
例16:※可以乏了。(Very tired.)
例16中“可以”应改为“可”或“很”来表示程度之深。作者因“可”和“可以”字面上的相似且在表示转折义上常常可替换使用而过度类推,造成误解。
2.重复
例17:※那是最妙極了。(That would be very nice.)
例18:※英國話亞細亞地方尤其很有用處。(The English language is very useful,especially in Asia)
例17应将删去“最”或“极了”。在英语虚拟语气和表程度的“very”两方面的影响,选用汉语中表达最高级的程度副词,但又因过度泛化这一规则而导致最高级结构表达的杂糅。例18“尤其”和“很”表意重复,应人删去一个。
3.残缺
例19:※我□忙。(I am busy.)
例20:※他上陣一點兒□不慌不忙。《英清會話獨案內·兵要常語》
例19应在空缺处添加“很”等词语。日语、英语中的形容词常单独作谓语,而汉语中一般要加上程度副词,这样句子才完整。例20应在空缺处添加“也”,这样句义才连贯。汉语中有很多类似固定结构的格式,如该句中的“一点儿也不……”,但日语中没有类似对应表达。
4.位置不当
例21:※我想這個時晨(辰)最人多。(I thought thia line was very popular)
例21语序应改为“我想这个时晨(辰)人最多。”作者对汉语语序位置不明,在讲日语里副词可直接修饰名词的规则迁移到汉语中。
(二)介词
1.误用
例22:※從這個,還有什麼呢。(Then,what follow next?)
例22“从”应改为“除了”,汉语介词含义丰富且用法多样,很容易出现类似的错误。
2.残缺
例23:※那時候說什麼□拜年。(In what terms did you exspress yourself on that occasion.)
例23空缺处应添加“来”,表示“用在动词结构和动词之间,表示前者是方法、方向,后者是目的”,缺少“来”则句义不通。
(三)连词
1.误用
例24:※我母親還是姐姐元旦受了好些個拜年。(My mother and my sister received many calls on new year’s day.)
例25:※雖然乏了,又是跟我一塊兒出去了。(...however we gent out.)
例24“还是”应改为“和”或“跟”。“还是”只用于疑问句中,且表示选择关系。作者过度泛化了“还是”,错将其用于并列关系当中。例25疑问句应将“又是”改为表转折义的连词“但”或“但是”等。
2.残缺
例26:※不是這個□那匣子裡的紙。(This won’t do.The paper inside that box is what I want.)
例27:※是主戰的多□是主和的多。《英清會話獨案內·兵要常語》
例26应在空缺处添加“而是”,例27应在空却出添加“还”。作者由于未能掌握汉语中由连词构成的一些固定结构,如这两例的“不是……而是……”、“是……还是……”。
(四)助词
1.误用
例28:※您看著新聞紙麼。(Have you seen newspaper?)
例28“着”应改为“了”。日语跟英语词形变化来表示动作发生的时间,而汉语则是通过动态助词和时间词来表达这一语法意义,作者出现偏误是对汉语动态助词过度泛化的结果。
2.残缺
例29:※好大□月亮。(It is a delightful moonlight.)
例30:※天要下雪□。(It looks as though we are going to have snow.)
例29应在空缺处添加结构助词“的”。日语的形容词、动词、副词、名词、连体词等可作定语成分修饰中心语,作者因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例30应在空缺处添加“了”。两例中分别用“要”、“快要……了”来表示一种即将发生的新情况,需要加上“了”表意才完整,作者由于对汉语动态助词及相关结构掌握不全,产生偏误。
(五)语气词
1.误加
例31:※你找什麼了。(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例32:※你想什麼了。(What are you thinking about?)
例31、32应将“了”改为“呢”。作者将陈述表语气的“了”过度泛化,对其进行不适当地类推,将其错用在表进行时态的疑问语气的句中,使时态和语气都出现了偏误。
2.误用
例33:※好麼。(Very willingly.)
例33中的“么”改为表示陈述的语气词,如“啊”“的”等。作者对汉语语气词含义及用法掌握不全,过度泛化常见的疑问语气词“么”,错将其用于陈述句中。
三、偏误产生的原因
(一)语言内部原因
偏误产生的内部原因主要是从第二语言习得的角度来说的,其原因主要是“语言迁移”。语言的迁移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产生偏误主要是负迁移而引起,负向迁移一般认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母语负迁移,即把母语的词汇或者语法迁移到目的语的使用中,造成偏误;另一类是目的语负迁移,也就是对目的语的规则掌握得不是十分的牢固和清楚,往往类推了一些规则,从而造成偏误。但我们从日本明治时期北京官话课本反映出的情况来看,除了上面的两者之外,还有一类也比较典型,即“媒介语负迁移”,主要是在学习某一种目的语(在本文中为汉语)的时候,因受其他自己熟知的第二语言的影响(在本文中是英语)而产生的语言偏误。这一类负迁移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出现,这当中有其社会和个人的原因。
(1)由母语负迁移引起的偏误。这两本教材是以母语为日语的作者编著的,这就不可避免地使教材本身体现了作者受到日语干扰而残留的痕迹。我们都知道日文中有大量的汉字,而且很多汉字的基本意思是相同的,这种似是而非的情况,使得汉语相对于其他语言,对母语为日语的来说更容易产生偏误。粗略统计,仅就以上经过筛选的例子产生偏误的原因来看,由母语负迁移引起的约十分之二,且这类偏误在日语名词转化为汉语名词、日语和汉语都具有的类似意义或功能的表达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例1“这个表是箱子很好看”中拿日语中的“箱”直接替代“盒”;又如“下雨的时候儿必蒸。”出现的“蒸”是直接迁移日语中的形容词“蒸し”导致的;如例6“青马是。”则是把日语的语序弄到了汉语中。
(2)由目的语引起的偏误。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最容易出现的错误是目的语负迁移,作者将其有限的、不充分的汉语知识,用类推的办法不适当地套用在编写的汉语教材中,造成了许多偏误。在上面的例子中,由汉语知识过度泛化引起的偏误接近四分之三。如例3“我告诉他说必去,我看见他不去。”中“看”和“看见”的混同;我们从这些例子可以见出作者并未十分重视汉语知识的规范性。
(3)媒介语(英语)引起的偏误。这两本教材是中日英三种语言相对照的课本,这是教材的特点所在,也揭示了作者受到英语译文影响的客观原因,如例9“B:说那么去。(went out to tell him so.)”是直接按照英语语序排列而造成的偏误。
通过上面的内容,我们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域外的汉语教科书是存有偏误的,如果要用这些材料来研究汉语,一定要进行详细的甄别,找到哪些是偏误,哪些确实是当时的口语,和现在的北京话存有差别。我们在课本中看到了大量“所”的副词用法,如“葡萄所熟了”“天所晴了”此类的句子,但是我们判断这并不是偏误,应该是当时北京官话口语中特殊的表达式。因为日语和英语中都没有类似的用法,而北京官话中虽然没有类似的用法,但是汉语方言中是有的(详细内容我们将另撰文说明)。当然,类似于这样的特殊用法,正是那个时代官话的特征,也体现了使用域外教材研究汉语的意义。
(二)社会成因
1868年,日本迎来了历史上具有巨大转折意义的明治维新时期。而当时的中国处于清朝晚期,正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明治初期,日本传统汉学的研究影响了语言的研究,产生了几本较为经典的汉语教科书,如《官话指南》,语言的偏误几乎没有。而到了明治中期,经济和政治地位不断发生的变化,使得日本人改变了对中国和汉文化的尊崇态度,他们还野心勃勃地谋划着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这两本教材出版的时代,“日本的中国语教育开始降温”[1](P26),这时教材的编写主要是为了商业交往的需要,这从书中的内容可以看出。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英清会话自学入门》书末附有军事用语,然却没有英语翻译,从中已可见日本在明治中期政治态度。因此,我们认为:教材中出现的偏误,不仅是作者汉语水平不够的个人因素,也是当时特定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我们认为教材中出现的偏误中的绝大部分理应是可以通过校正的程序和交流的方式得到订正的。比如例(1)中提到的“箱”,只要懂北京官话的人都可以指出其用词欠妥当。此外,如例13漏掉量词等都是极容易察觉的较低级的偏误。显然,作者在编教材时并没有秉持着严谨的态度,其根源于当时日本对中国国力和文化的轻视,教材中汉语的部分只是一个附属,没有具体的实用价值。
其二,《英清会话独案内》课本的最后附录了“兵要常语”,共20页,为在战事中经常使用的语言,这一部分的内容没有英文的翻译,几乎没有很明显的语法错误,表达也相当顺畅自然,可见,作者有意在这一部分下了大工夫。当时日本人来华进行的游历大多是“以调查和探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地理、风土、人情等为目的的‘勘察记’或‘踏勘记’”[2](P9)。可见,当时的汉语教材是为“大陆政策”服务的,而不是为了让日本国民学汉语和汉文化。如此一来,他们也就自然不会把当时的汉语当成我国盛唐时期的汉语来对待,没有了崇敬和学习的激情,失掉了了文化和地位上的平等与尊重,汉语教材的整体质量大打折扣是可想而知的,出现大量偏误也是正常的。
其三,这两本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将汉语、英语和日语三种语言合在一起,这么一来汉语句子中所出现的偏误就多了一种来源。作为日本学生的汉语教材,其媒介语英语因代表了西方文明的强劲势力,对偏误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作者在教材编写中有多处偏误是由于直接受到了英语的语序和句式的影响。
其四,明治中期日本的汉语学习和研究面临着“窘境”。明治时期40来年,据六角恒广考察,出现的汉语课本共300多本,明治早期的课本很少,但很为经典,如《官话指南》,而大多数是明治30年之后出版的,从我们的考察来看,这两个时期的课本语言很少偏误。明治中期(明治18年——明治28年)的汉语课本并不多,大概十来本,而且基本上都是多语对照的课本,课本中汉语的偏误明显偏多。当时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家——吉川幸次郎写过一本书名为《我的留学记》,他在书中提到了自己当时因从事中国文学研究遭到蔑视和耻笑,他说“我在三高时,想研究中国学问,就有人反对,甚至有人对我提出忠告说‘你还是不要做那样的事吧。”[3](P13)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当时社会的潮流是学习西方,英语理应受到重视,而汉语的研究和学习则沦为旁支,这大概也是造成的当时官话教材偏误较多的原因之一。
[1]六角恒广.中国语教本类集成[M].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1992.
[2]六角恒广.刘洪顺译 日本中国语教学书志[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2000.
[3]吉川幸次郎.我的留学记[M].钱婉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