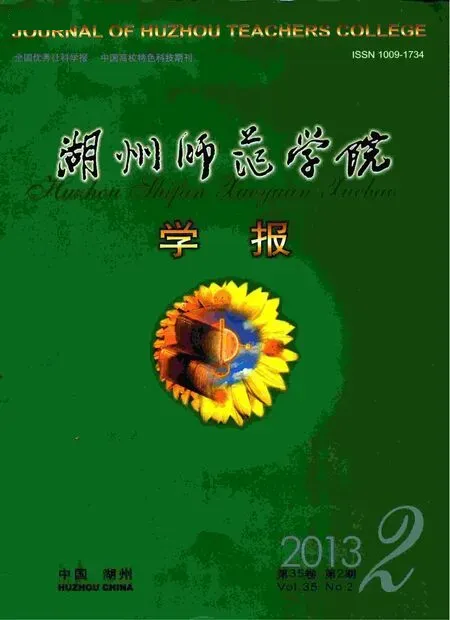上海租界的“亭子间人物”*——对周天籁《亭子间嫂嫂》人物群像的解读
张 梅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周天籁,一个在现代文学史上鲜为人知的名字,却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了风靡一时的《亭子间嫂嫂》,陈亮在给这部小说的序文中写道:“这部小说,刊在《东方日报》,居然大为轰动,社会上,上中下三等人士,都关心了《亭子间嫂嫂》的遭遇,今天看过,明天非得一早去买报来看不可”[1](P3),由此足见其受欢迎之程度。同时,在贾植芳教授主编的《海派文化长廊》小说卷中,也收录了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能这样有人情味地写下等妓女生活,新文学史上还没有过”[1](P2)。这部小说主要描写了二三十年代上海红灯区会乐里一个暗娼的生活,亭子间嫂嫂与狎客之间的周旋以及每个狎客背后的社会故事都成为小说表现的对象,也让我们在嬉笑怒骂之间感受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租界内下层市民的生活状态。
一、亭子间嫂嫂:“娜拉”式的生存困境
亭子间嫂嫂顾秀珍,是一个兼具侠骨柔情与圆滑机警的上海租界下等妓女,会在马路上拉客人,也会在栈房里等候挑选,但她又是特别的,在她看似风骚圆滑的背后,却隐藏着一颗倔强而又自尊的心。这样一个美貌的女子,因为生在错误的时代错误的环境中,注定只能在苦难里沉沦。顾秀珍多次逃离不幸的婚姻和爱情,她勇敢地反抗,但最后仍然失败了,就像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逃走之后仍然没有出路可言,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顾秀珍的精神世界都不足以支撑她“逃走”后过上理想的生活。曾经有很多为狎客都提出要救顾秀珍脱离苦海,给她全新的生活,也有几位已经付诸行动,但最后顾秀珍仍然在凄惨中死去。
(一)喧嚣都市挤压下的生存空间
周天籁将顾秀珍置身于动荡时期的上海,顾有着惊人的美貌,却没有文化,不识字,这也让几次三番想搭救她的客人无能为力,其乡下还有抽大烟的残废父亲,工厂倒闭之后,别无专长的她又能怎么办呢?正如朱先生所说:“假使说我有力量,挽救了亭子间嫂嫂,善后问题如何呢?”“留为自己的女人,法律所不容”“介绍她去做女职员吧,她又目不识丁”“送她回去吧,乡下又没有田地吃用何处来?”[2](P31)唯有供她上学,而后替她介绍个结婚的男子,方可真正救其脱离苦海,但这又谈何容易,所以她只能继续其神女生涯。
即使是做妓女,亭子间嫂嫂也时时处处面临着危险。因捐不出照会,所以顾秀珍只能做暗娼:“上海除了正式发给花捐照会的生意女人,真是一百个当中只不过一二成,其余都是私做的,都是偷偷避避不能看见天空一样,到晚上才出世的”[2](P31),暗娼则随时都有被抓的可能,而审讯她们的则是顾秀珍口中的“外国人”。加之在弄堂里等生意时,如果碰到下雨天,脏乱的弄堂就会变成一个发酵场,臭气熏天,而这些下等妓女还不得不站在雨中像货物一样等待挑选。在《上海掌故》中提到:“上海的妓院,大部分设在弄堂里,名目繁多,有什么书寓、长三、和么二堂子、向导社等等,以分高下。最下一等的就是‘马路天使’,华灯初上,在西藏路一带拉客,直至次日临晨”[3](P100),顾秀珍也经常迫不得已做“马路天使”。
此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也是促使顾秀珍沉沦的一个外部力量。一件事物之所以会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环境和价值。在李永东老师的《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中就提到,租界当中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调,这必然会“加剧租界色情事业的发达和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租界内最为世人所诟病的就是卖淫事业的发达”[2](P40)。在不同的海派文学作品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这样的现象,各省男子抛妻别子、远离父母只身来到上海闯荡、求学,希望在这个繁华的大都市觅得第一桶金,从此飞黄腾达,一家团聚于大上海。可是这个过程是十足艰难的,缺少家庭温暖,事业又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和精神上窘迫的状况必然会对人的心理产生一定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租界社会。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买淫”市场,所以才会有妓女的产生,她们有钱可赚,用自己的身体来养活自己。顾秀珍们没有文化,没有技能,社会为她们提供了这样一种谋生的手段,使其可以在上海立足。
传统社会一直坚持的婚姻观也是造成亭子间嫂嫂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作品开始之初,朱先生为顾秀珍想得最后出路就是嫁一个适合的男人,而顾秀珍自己也从未放弃过追求婚姻的权利。可见,传统的婚姻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幸的是,作为妓女的亭子间嫂嫂,在追求婚姻的道路上可谓困难重重,最后也是因着急于给肚子里的孩子找个父亲才会过早的结束了生命。她可以从容离开薛景星,偷偷逃离石春波的大公馆,自己选择结束不幸的婚姻,但是在肚子里怀了不知父亲的孩子之后,顾秀珍的理智和果敢则完全失去了,她只想给孩子找个父亲,所以才会饥不择食选择了韩江汀,并不惜变卖自己全部家当供韩吃喝嫖赌来维持这段婚姻,但最后却落得个人财两空,自己也在凄楚中死去。究其原因,还是传统的婚恋观在左右着顾秀珍,如果她选择自己生活,凭着她从石春波家里和各个客人那里得来的首饰钱财,完全可以将孩子生下。她心里盘算离开石春波时,也想道:“念万赡养费如果不给我分文,我偏偏争一口气,这断命钱不要,只需席卷我的细软首饰也可过半世把了”[2](P649),可她还是选择将生活的希望寄托与一个不相熟的男子,以致被抛弃最后惨淡离开人世。当然,顾秀珍面临的这些生存困境在当时的上海是具有普遍性的,所有的“亭子间嫂嫂”都会面临这些问题,这是那个时代和社会造成的。
(二)喧嚣都市下的精神荒原
在大上海这样一个浮华的环境当中,顾秀珍的精神世界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社会的影响。她看不起短衫班,认为这样的人没有能力养活自己,“拨开短打长衫不谈,一个水果店伙计,出息有限,决不能维持一个家庭生活,所以他的良心好到一百分,也没有力量来讨我,总之这都不是我的对象”[2](P34),却从不曾想过自己也去做工养活自己,维持家庭,在她的心目当中,女人是没有必要在一个家庭中担任赚钱的角色的。她的潜意识中并没有将自己与社会底层市民归为同等地位,她想嫁得是一个“正正当当的生意人”,过至少是中产阶级的生活。她还怕吃苦,北平来的狎客许耀明最初说要带顾秀珍回北平时,她有这样一段心理活动:“亭子间嫂嫂心上砰的一跳,一个人家种有三四百亩田园,家中老少都要下去做,叫我哪吃得消,我上海的苦头还没有吃饱,特为老远跑到北平去吃这种苦,我真不是在发痴,当真我茄要嫁男人,我情愿一辈子过孤独日子的”[2](P254)。由此可见,顾秀珍并不认为通过劳作养活自己是一件高尚的事情,她将在上海吃的苦与即将在北平吃的苦拿来做比,殊不知这已经注定了她的神女生涯只能继续下去。“女性对男性的物质和精神依附,作为既定传统的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已成为人类的常规文化心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生活”[5](P74-77),顾秀珍作为一个下等妓女,亦不能免俗,她不可避免的将自己依附于男权社会。所以,顾秀珍有机会跳出自己生活的圈子,却不愿过苦日子,最终还是跳不出来。
顾秀珍可谓是妓女中的“佼佼者”,她将揽客的方式,对待不同客人的态度,跑公司与跑栈房的不同以及过关门节等都搞得一清二楚,整日周旋与各色人中间,时而千娇百媚、温存无限,时而狠下杀手、宰客无情,时而正义凛然、直言进谏。此外,她扮少奶奶可以派头十足,以假乱真,扮女学生也可以清纯逼人,难辨真假,周天籁企图将亭子间嫂嫂塑造成一个全知全能的角色,勇敢地与社会抗争,在嫁人不可得之后试图主宰自己的命运。但是她缺乏明确的道路和精神指向,所以只能到处碰壁。她是洒脱的,或者是因为受伤太多进而麻木了,她可以忍受男人没钱之后将其抛弃,比如与薛景星的婚姻,也可以在自己男人不在意时卷款潜逃,比如石春波。但是逃走之后的顾秀珍又能去哪里呢,处于租界内的上海人每天只能在外国人的管辖范围内苟延残喘,何谈人生理想,何谈精神出路,即使有知识的文人尚且精神困苦,经济窘迫,何况一个下等妓女呢?几次从不幸婚姻中挣脱的顾秀珍,只能回到那个小小亭子间,重操旧业,社会也没有提供给她们生存的条件,女性仍然要依附于男权社会,受尽压迫和歧视。
纵观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我们不难发现大批形色各异、有血有肉的妓女形象。提到周天籁对底层妓女的关注,自然会想到对底层社会关注最多的作家老舍,无论是《月牙儿》当中的月牙儿母女,还是《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都对妓女的苦难经历予以深刻描写,以此批判现代城市文明中的道德沦丧和精神荒漠。与周天籁和老舍形成鲜明对比的,当属沈从文。在上海租界糜烂颓废的社会氛围中,沈从文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田园气息。他笔下的妓女形象均闪现着人性的光芒,她们比城市人淳朴善良,也更有情有义。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同样面临生存的艰难,《柏子》、《丈夫》、《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妓女》等作品中的妓女多是为了生计而出卖肉体,她们面临的同样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沈从文用一种人文关怀的态度将这种对立和矛盾融汇在湘西淳朴的民风当中,跟老舍和周天籁直击问题根本的表达方式相反。同样,郁达夫的《茫茫夜》《回归线上》等作品也有此类妓女形象。
除了为生计的底层妓女之外,还有一类妓女形象也活跃在作家笔下。她们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比底层妓女生存环境稍有提高,不会受巡捕的骚扰,在金钱上也有一定的稳定性。《亭子间嫂嫂》中,周天籁就曾隐晦的提到过这一类妓女,她们有经营执照,定期纳税,也有相对固定且身份地位较高的客源。另一种就是所谓的高级交际花,她们不为生计操劳,大多接受过五四新思想,但在这种新旧文化交迭的状况下,被物欲蒙蔽了心智找不到出路,反而深陷精神堕落的泥潭不能自拔。曹禺《日出》笔下的陈白露、茅盾《子夜》中的刘玉英、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微龙等即是如此,她们因习惯物质上的优渥生活而不得不开始出卖肉体或继续出卖肉体,以至于走向穷途末路。这类形象虽然侧重的是精神层面的问题,但表达的主题是一样的,同样是对现代城市文明对人性的冲击,对黑暗社会的控诉。
二、亭子间狎客:上海知识分子的“沉沦”与“拯救”
陈思和在写给《亭子间嫂嫂》的导言中这样认为:“作家使主要场景集中在半间小小的亭子间里,这有点像演话剧,透过小小的一角场景来展开上海社会的各色人物和黑道白道各色事件”[1](P4)。在《透过轩窗看炎凉——周天籁散文随笔编选后记》中也写道:“这部小说以朴实无华,精粹洗炼的文字,将一位风姿绰约,伶牙俐齿,不幸沦落风尘,而又良心未泯的亭子间嫂嫂顾秀珍,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作品单线结构,通过她——一个社会底层的暗娼不断地与形形色色的狎客周旋,和盘托出一个病态繁华的都市市民社会”[6](P318)。在顾秀珍的小小亭子间中,接待了至少四十位客人,在这些狎客中,有大学生、报社编辑、生意人、和尚、白相人、伙计、画师各色人等,加上亭子间嫂嫂出外在栈房里接的客人,又有大教育家兼慈善家、大家族遗少等人物,在这里我们将其统称为“亭子间狎客”。不得不说,从顾秀珍接待的这些狎客身上,我们可以窥见上海市民世界的一角。下面笔者选取知识分子作为对象,从沉沦与拯救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上海知识分子的沉沦
在上海租界,知识分子的比例很高,但是面对家国沦丧、生存艰难的现状和大上海繁华都市的诱惑,很多知识分子选择了沉沦。上海租界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调,间接导致上海租界娼妓事业的发达,男子嫖娼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是再正常不过的,甚至花甲之年仍流连于烟花之地的,也不乏其人,道德的界限在这里似乎没那么明显了。有学者认为:“从价值观念的驳杂看,在租界化的上海,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为人准则难以带给生命的酣畅而受到严重的挑战”[4](P85)。在周天籁的《亭子间嫂嫂》中顾秀珍所接待的就有这样的客人。六十一岁的沈老先生在上海一家顶大的银行里面做杀老虎,自称年轻时就是风流才子,现在老了,还是喜欢偶尔叫个家人子出来玩玩,而且要是年轻漂亮的。在顾秀珍之后,他又会换别的栈房找新的人家人,可谓年龄虽老,但精力依然旺盛。另有一位大教育家沈梦白,在上海教育界颇有名声,儿女皆有成就,年过半百,却仍喜欢寻花问柳,最讽刺的是,父子同嫖一女,可谓颠覆伦理纲常。文中的朱先生也感叹道:“足见社会上越是文明的人,他的私生活越是不堪设想,这一位是以教育家名于时的,谁知道他开口教育闭口道德,原来一到晚上便换一副人格,实行猎艳工作,这岂是一般人知道的呢”[2](P109)。
上海租界是一个男性文化统治下的社会,不论中国还是外国,最初来上海闯荡的男子当中,以青壮年居多。青年人敢于冒险,渴望在冒险中寻求刺激,当然这也和上海当时的社会状况有关,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上海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模仿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更加刺激着初涉上海滩的中国男子。所以顾秀珍的客人小孙就选择铤而走险,在公司的账上舞弊,得了钱之后就跑到亭子间嫂嫂这里风流快活。小职员经受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宁愿违法也要享受一番,如果说他只是为了追求理想中的资产阶级生活的话,那么大富翁石春波的投机则完全是为了寻求刺激。石春波是顾秀珍的第二任丈夫,是江南大富豪,家里娶了几房姨太太,花钱如流水,但作品中也提到他有段时间天天忙着做投机,最后吃了个大亏,这让他心灰意懒。
上海租界的中青年男子大部分都是来自外地,来到上海之后,首先会被这个有着“东方巴黎”之称的大都市所震撼,对一切事物感到新奇,并努力追逐。但不久之后就会发现大上海充满了太多的诱惑,这是一个物欲与肉欲的世界,而且时时在自己的国土上面临外国人的欺压,精神上的幻灭和民族自尊上的打击使这些人开始选择逃避。邵茜萍是一个报社编辑,大好青年却终日沉迷于花街柳巷,当顾秀珍苦口婆心说他是国家栋梁,希望他出人头地,做正气有为的青年时,邵茜萍“双手拥抱了顾秀珍只是一阵的颤抖”,顾秀珍知道“他是受了刺激”[2](P676),这刺激是因为顾秀珍的劝说让邵终于敢面对自己的内心,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也说:“以后我想做一个正气有为的青年,专心经营金融事业”“何尝不明白在外面荒唐,终究不会有好结果,耗费金钱,耗费精力,甚至误下公事,给友人背后批评”[2](P677)。虽然这样说,但是邵茜萍过后仍然没有收敛,可见积习非一日可改。况且,大上海又有多少个邵茜萍呢?来亭子间嫂嫂这里“白相”的至少有三分之一与邵属同一性质,可见中青年沉沦,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二)上海知识分子的欲拯救而不可得
亭子间嫂嫂的客人中有多位大学生,表明上海污浊的社会环境也影响到了象牙塔里的莘莘学子。他们用家庭供给上学的钱出来“白相”,作品中的薛景星、王先生、陆大新等,都是在校大学生。他们一方面在大学里接受先进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社会的腐蚀,既想寻求改变现状的出路,但自我的力量又太渺小,不足以使改变目前的社会状况,故而只能在矛盾中痛苦的挣扎。他们受西方男女平等思想的影响,欲救顾秀珍脱离苦海,但自身力量有限,又无明确的思想指导,最后拯救计划只能宣告破产。
薛景星是亭子间嫂嫂的一个“好客人”,只有二十三四岁,在上海读书,他极其爱护尊敬顾秀珍,对她的遭遇深表同情,并想尽办法让顾的生活好一点,并没有因为顾秀珍妓女的身份而轻视他,甚至把亭子间嫂嫂当成《茶花女》当中的玛格丽特。他是一心想改造顾秀珍的,他租偏僻一点的洋房,是为了防止顾秀珍再和“恶劣的环境接近”,还教顾读书识字,预备渐渐改变其环境和生活。但是薛景星的计划最后因家里不再供给用度而宣告失败,美好的理想最终幻灭了。薛景星与顾秀珍分开之后,选择沉沦,其实很大原因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失败,对未来感到迷茫,他想有一番作为,可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染缸,任何在里面的人都会被涂上颜色。他最后在顾秀珍的资助下终于选择回家了,他的改造计划失败了,自我的理想也破灭了。
《亭子间嫂嫂》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是十七岁的中学生许永明,他所代表的是初进社会的青年人,没有过多的受到那个社会的污染。他自因为反对父亲为他定下的婚姻,故而辗转写信给顾秀珍,想要与之结为夫妻。他自称是一个“极有志气的青年,将来要脱离家庭,完全自立的”[2](P756),乍看之下,十七岁少年向一个暗娼求婚,是有点可笑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物形象是也代表着青年学子对旧家庭、旧制度的反抗。这个求婚最终因为顾秀珍的拒绝不了了之,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只是把顾秀珍看成反抗他家庭的一种工具,无关感情,当然也就不可能给顾秀珍幸福。
诸如此类的知识分子,在接受西方新的思想之后,都试图运用到实践中,但是他们没有明确的思想指导,只能在暗夜中独自摸索,这期间难免会有失败,可只要他们仍在努力,仍在挣扎,就有希望。张恨水《夜深沉》中的宋信生,《傲霜花》中的唐子安、华傲霜等重庆知识分子,与上海知识分子面临同样的困境。上海知识分子大多是因战乱避祸而远离家园,初到上海,租界里灯红酒绿的奢靡生活对他们造成强烈的冲击。他们一时间无法接受租界里的种种新鲜事物,必然产生排外感,怀念家乡又不得归,故而一部分人选择浑浑噩噩的生活,就如邵茜萍一类,而另一部分则迅速投入到租界的投机氛围中,如薛景星一类。而张恨水笔下身处重庆的知识分子,同样是因避祸来到异地他乡,生活上的困窘和随时面临轰炸的精神紧张,让他们不堪承受,文人的地位也急速下降。此种情况下,有人选择保持文人的节气,坚持做人的信仰,如唐子安,即使生活落魄,也在落魄中追求精神的安逸;而有人承受不住经济上的困境和文人地位的迅速下降,如洪安东、华傲霜等,选择弃文从商,做投机生意,从而获得生活的安逸和精神的满足。
三、亭子间文人:朱先生的独特视角
“上海租界特有的文化精神不只是使作家能够在这里生活和创造,同时也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他们怎样在这里生活和创造”[4](P63),周天籁在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上海租界时期的文人形象,他与顾秀珍毗邻而居,见证了顾秀珍沦为暗娼后直至死亡三年的辛酸生活。结合朱先生自身的生存困境,从文人视角加以关照,又会对租界内的社会生活有新的认识。
“因为上海在开埠以来在国内所占据的独特的文化、政治、经济地位”,“上海再度成了混乱年代、恐怖年代文人寻找栖身之地的避风港”[7](P2),外来文人初涉上海滩,大都居住于上海的亭子间。“亭子间”是上海弄堂房子中的一间,主要位置是石库门房子中灶间上面的一间,一般用于堆放杂物或者佣人居住,可想而知,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也是极差的。知识分子们初到上海,这个大都市首先带给文化人的除了震撼,继而就是深深的失落感,加之亭子间生活空间的狭小更增加了他们的“孤傲激狂”。李欧梵曾说:“‘亭子间’事实上成了上海文化生活的附属物,以至于后来成了作家的形容词,‘亭子间文人’和‘来自亭子间的作家’,他们的住所不仅说明了上海作家的社会经济状况,而且也表明了他们的生活方式”[8](P38)。
在《亭子间嫂嫂》这部作品中,有两个主要叙事视角,一个是顾秀珍,一个就是朱先生。朱先生是在香港经营商业失败后被一家书局聘请担任主编而到上海的,妻儿都在故乡安徽,自己以文字为生,生活境况并不好。他同情亭子间嫂嫂的遭遇,总是在关键时刻给予其帮助和支持,也曾想过改变顾秀珍的生活境遇,预备“一两年之内,利用夜里工夫,赶成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大约可卖两三千块钱,将这笔钱作为改善亭子间嫂嫂的生活境遇,也许可以够了”[2](P32)。但是靠文字赚钱并非易事,况且他还要供给家乡亲人的开支,可谓自顾不暇。身处上海租界的知识分子在当时是被边缘化的,并没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也是周天籁可以将朱先生和顾秀珍同时作为作品叙事视角的一个因素。
朱先生的生活状况其实就是当时很多上海租界作家生活的真实写照,居于亭子间,凭笔杆子赚钱,辛苦养家,没有亲人在身边嘘寒问暖,其实他们也是出于社会底层的一个群体,至少在当时来说是如此。朱先生曾经多次搭救顾秀珍,并在其危难时刻予以帮助,但毕竟文人的力量有限,无论财力还是势力,都不足以将顾秀珍拯救出苦海。当然,他也有过自私的时候,会担心因帮助顾秀珍而给自己惹麻烦,造成不必要的困扰。朱先生曾不止一次提到万恶的社会制度,说明他认识到造成自己和顾秀珍悲苦命运的社会根源,但却无力反抗。在顾秀珍死后,朱先生对想要报仇的排门板说:“你有三万徒弟也无所用,你要替她报仇,除非先从改良这万恶的社会着手,否则你还是免开尊口”[2](P869),故事也以此结尾,这是朱先生的遗憾,更是作者的遗憾。
朱先生在生存和精神上的困境似乎也暗示着周天籁当时的困境,周天籁开始创作之初是写儿童文学作品的,并且也很受欢迎,但是上海租界沦为“沦陷区”之后,他毅然开始创作社会小说,用自己的笔去记录上海经历的种种。面对上海人民经历的种种磨难,他想要寻求一条帮助他们的道路又不可得,所以只能在挣扎中用文字记录心声。周天籁的创作还不同于南下作家,南下作家群初到上海,环境的改变,地位的下降,家国的沦丧对这些作家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对国耻家丑的感触远比周天籁来得强烈。而周天籁毕竟没有经历过颠沛流离的日子,对整个社会现象的认识也就没有那么深刻,也不可能对社会的卖淫现象作出深刻的剖析,他在作品中不止一次提到改变“社会制度”,改变“万恶的社会”,他的认识也仅限于此。陈思和在导言中也提到:“周天籁是个通俗小说作家,不可能对社会的卖淫现象作出深刻的剖析,但作为社会平民的一员,写小人物在卑贱和污秽中的人性之光,常常是小说中最令人心动的地方”[2](P6)。
“如果说市民社会是上海城市发展的基本社会形态特征,如果说街巷里弄万种风情是市民社会的基本审美属性,那么,迄今为止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作家是周天籁”[9]。如此评价周天籁或许有些夸张,但是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周天籁作品是了解上海风情,研究上海语言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
[1]陈思和.亭子间嫂嫂·导言[A].周天籁.亭子间嫂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2]周天籁.亭子间嫂嫂[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3]蔡耕编.上海掌故[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4]李永东.租界文化与30年代文学[M].上海三联书店,2006.
[5]艾璘,朱一菁.《亭子间嫂嫂》的社会文化指照[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2(3).
[6]朱鸿召.透过轩窗看炎凉--周天籁散文随笔编选后记[M]//周天籁.浪漫浪漫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
[7]章清.亭子间:一群文化人和他们的事业[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
[8][美]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M].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9]朱鸿召.最能代表上海风情的作家(代前言)[M]//周天籁.浪漫浪漫集.上海:文汇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