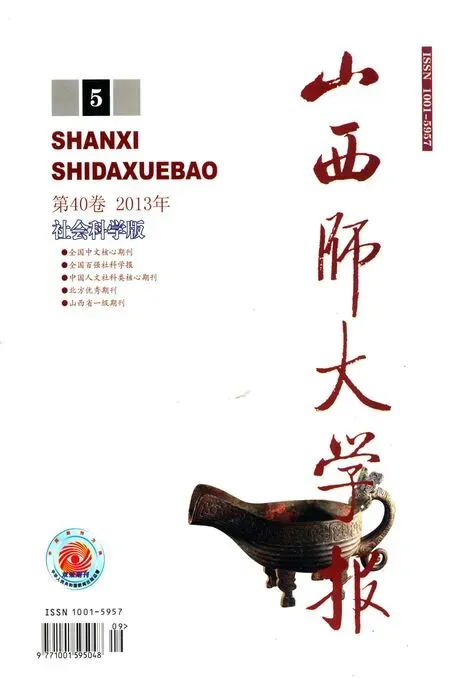话语与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伦理学略论
汪 怀 君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青岛 266580)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言语行为是交往行为的基本表现形式,因而,交往行为就是通过语言而达成相互理解的活动。在日常交往过程中,当人们对客观事实与现存规范的合理性产生质疑时,所采用的方法就是通过话语的论证,重新获得共识并取得相互认同。因此,话语理论是交往行为理论的继续,它是对哲学范式转换的进一步证明。从语用学意义上说,话语具有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的双重意义,因此对活动内在合理性价值规范的探讨就成为伦理学的主要任务。在交往行为中,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理解”是交往行为的中心概念,而交互主体之间的交往性理解与共识又是在理想的话语情境下达成的。
一、交往伦理是“话语”活动的伦理
交往是人的存在方式与生活样式,人的社会性决定了人不能没有交往行为,不能脱离各种交往关系而存在。人或者与客观事物打交道而与人发生间接的关系,或者与人打交道形成直接的交往关系,即主客关系与互主体关系。互主体关系由于涉及到人类精神沟通问题而成为现代人关注的焦点。主体间通过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理解使彼此间的关系得到协调与优化。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主体孤立生存,进行独白是不可能的,交谈、讨论、辩论或商谈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人都必然参与一个最低量的不可抗拒的交往活动。从根本上说,所有的社会文化与生活样式都是以交往关系为基础的。哈贝马斯通过批评怀疑主义者阐释了话语伦理交往行为的理论基础:“通过拒绝论证,怀疑主义者比如说并不能否认他在参与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否认是在交往行为的各种联系中成长的,并在其中再生产他的生活。他甚至不能间接地否认这些。一句话,他否认道德,却不能否认他自己可以说整天驻留于其中的生活关系的伦理。如其不然,他就不能不以自杀或某种精神病为出路。他不能不在交往的日常实践中不住地以‘可’与‘否’表态,他不能不以其他言词摆脱这种实践;只要他一般地保持生活,他用缄默的和动人的方式为显示他似乎能够脱离交往行为所编的鲁宾逊故事,作为一种想象的实验安排,就是永远不可想象的。”[1]100由此看来,人就是交往行为及其生活形式中的人。
语言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进行商谈与论辩不可缺少的媒介,但语言并不是人类交往的唯一工具,表情姿势、手势语言也是交互活动的中介。哈贝马斯通过考察米德的理论,发现“由表情中介的内部活动向由象征性中介的内部活动的过渡,同时意味着规则指导的行动,即通过著手确立意义惯例方向时,能够得到解释的一种行动的构思”[2]22。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活动是合乎规则的交往,意义的同一性是在规则的运用中形成的。交互主体对语言符号内含的规则及其意义的认同,保障了人类交往的有效性。因而,与以表情姿势为中介的交往活动相比,语言符号交往活动更反映了人类的社会性特质。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在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产生于意识发展与交往的需要,起初仅仅是作为工具而存在。语义学、句法学是语言学家关注的重点,他们力求通过加强语词与造句的精确性,来保证语言的正确有效性。奥斯汀、塞尔提出语言的最小单位不是语词或语句,而是被完成的某种言语行为,自此“言语”或者说“话语”的意义就在语用学层面扩展开来。哈贝马斯关于普遍语用学的重建理论把语言与日常生活中的运用紧密联系起来,揭示了话语建立人际关系的实践功能。话语不仅仅是工具,也是人的存在方式。话语是交往主体生存的土壤,它是人们进行交往的最基础条件。不仅人类的交往离不开话语,而且生活世界结构的再生产也依赖于话语的建构性作用。
哈贝马斯认为,随着世界观的解中心化与价值领域的分化,一方面分化的理性在面对外部自然、社会以及内部自然时,依靠精确化、明细化来提高效率,通过展示理论能力与实践能力高扬人类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合理性的分化意味着文化知识的承继由世代相传的传统模式改变为自觉学习的现代模式,这一模式的改变既加速了文化知识的更新速度,也有着瓦解文化传统精神内在的融合力与凝聚力的趋势。理性的分化所带来的非中心性、多元化与多样性,削弱了其对社会整合的统一性力量,理性必须不断为自身找寻合法性的根源与根据。
交往行为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非强制的共识。汪行福认为共识有两种:一是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的共识;二是通过理性的论证获得的共识。日常交往只有以前反思的直观知识为背景才是可能的。通常人们在交往中总是默许已有事实的存在和规范的正当性。但是,当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对情境本身理解的分歧,而是对用于理解情境相关知识本身产生了分歧,人们就会中断交往,进而讨论这些知识本身的合理性。为了克服日常交往中的意见分歧,恢复中断的共识,交往必须上升到话语层面,让交往行为的合理性要求在论证过程中接受批判性审核。话语是日常交往在理论论证层次上的延伸。也就是说,在后传统的现代意识形式中,不能靠传统的权威,也不能靠外在的强制来解决意见分歧。论证本身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实践形式。[3]184—185从这个意义上说,交往伦理对道德原则与规范的探讨是通过话语论证来获得的,“神灵”的启示与孤立的“自我意识”不再是价值规范的根据与来源。因此,交往伦理可以说就是“话语”活动的伦理。
二、话语伦理的中心概念:“理解”
以语言为中介的交往是话语交往,主要指交往主体在生活世界的基础上,以文化传统的前理论知识为背景,围绕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社会世界三个世界中一个主题进行论辩的过程,以达到理解与共识为根本目的。话语交往之所以具有合理性,不仅因它关涉三个“世界”,而且更为主要的在于它是一种以“理解”为导向的行为。“理解”是话语交往的中心概念与本质特征。在现代多元化社会,这种“理解”由传统主体对客体的目的—工具性理解转变为交互主体间的交往性理解。交往性理解以主体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承认为前提,是对伦理关系的肯定与协调,因而,“理解”也就构成了话语伦理的中心概念。哈贝马斯在界定“理解”的本质时指出:“理解……它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的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所理解。”[4]3广义的理解包括对客观事物的事实性理解、对价值规范的正当性理解、对交往主体的意向性理解。而无论从狭义还是从广义上看,哈贝马斯都把“理解”看作是展开于主体间的交互性的意识活动,即参与的主体之间彼此的信任、默契与合作。
从目的性理解到交往性理解的转变是以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论为基础的。传统认识论主张真理符合论,把真理观局限于主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认为凭着主体的感官经验与先验统觉就可以获得对客观事物本真的认识。“真理”就是对外在自然与客观存在的事实描述。哈贝马斯认为,“真理”就是话语主体在交往中所形成的共识。这样,真理共识论就将真理观扩展为主体与主体之间通过相互理解与相互沟通所形成的对事物的共同性认识。传统认识论强调外在力量的“统识”作用,同一性优先于差异性;而现代性意识强调主体间内在的“共识”作用,在差异性中寻求同一性。
目的性理解与真理符合论是相辅相成的,“理解”是主体对于客体事物意涵的了解,理解事物是为了实现一定的功利目的,倾向于将事物看作工具与手段加以掌控或控制。不仅如此,主体将这一思维模式用于人类同伴身上,人类自身也成了被奴役的对象。在此种意义上说,目的性理解不是真正的理解,甚至是扭曲的理解,它不仅造成了对外界自然的对象化的片面性认识,而且技术操作性的行为模式侵蚀到人类的日常交往,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精神沟通的障碍。交往性理解受益于真理共识论,“理解”是对行为意义的交互主体性理解,理解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主体间的相互认同与意见一致。哈贝马斯说:“理解过程以一种意见一致为目标,这种一致依于以合理推动的对一种意见内容表示同意。意见一致不能加于另一方,不能通过处置加于对方:明白可见地通过外在干预产生的东西,不能算作达于意见一致。意见一致总是基于共同的信念。”[1]134交往性理解是主体间依据共享的知识背景,基于共同信念所形成的理解,它既充分尊重人的主体性自由,以主体间的相互信任、相互包容解决心灵沟通问题,同时又将这种共生共荣的心态扩展到外在自然,充分认识到其对人类的先在性与限制性,于是,外在自然作为人类理解的对象也被纳入主体间的话语论辩过程。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性理解是由话语论证来实现的。他把论证分为两类:理论话语与实践话语。前者以科学知识的真实性为论证主题,后者以道德规范的正当性为论证主题。科学知识不再是外在于人的,它的真理性以及对现实社会的价值与意义都要受到交往主体的检验;道德规范也要体现人的普遍意志,它的正当性以及对实践活动的规约能力也要受到交往主体的质疑。而论证过程要求充分的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认识问题转化为自由问题,理论话语上升到了实践话语的层面,并像实践话语一样具有了伦理的意涵,在话语层面上认识论与伦理学相关联,这也是话语伦理的本质特征。可以说,在目的性理解中交往主体是以第三者的态度,也就是以客观化的态度来考察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他只能对事态作出客观化的论断,这种论断往往以暴力性形态压服于他人身上;在交往性理解中交往主体是以参与者的态度,也就是以交互主体性的相互对待与相互批判的态度就某一论题进行对话与商谈,在主体间非强制的相互作用中,不断进行否定与创新并达致共识。这里体现了两种不同的行为调节模式,也就是哈贝马斯所区分的“同意”与“影响”。“‘同意’不应该是在一方的强制之下被另一方所接受,他是基于‘共同的信念’,获得一致性的认识,它体现了行为中的互主体性;而‘影响’是基于一方对另一方外来干预,或是欺骗、谎言、威胁、利诱,或是心灵影响,它体现了行为中的主观性、主体性。”[5]86交往性理解不是通过强力与权威,而是通过商谈与讨论来实现的。
三、理想的话语沟通环境
话语伦理以达到交往性理解为目标,就是寄望于交互主体通过没有任何强制与暴力压制的交往与对话促成交往行为的合理化。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承认和重视社会中所存在的共同规范,这些规范影响和约束着每个人的言语与行为,它们是社会伦理关系不受干扰和破坏的前提,是建立社会伦理秩序的合法性基础。话语伦理认为,规范的求证及其对人际关系的协调,是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排除了外在的权威强制与内在的心理压抑,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与理性共识来实现的。
在哈贝马斯看来,知识的内在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知识有两种类型,即技术—实用知识与道德—实践知识。前者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而后者在人类交往关系、交往结构方面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现代工业社会,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异化了人类自身,要摆脱这种扭曲现象,就要通过交往合理化,使“道德实践合理化”。道德实践的合理化意味着主体自觉运用社会规范及对意义的理解来规约自己的行为。道德原则与社会规范之所以获得交往主体的自觉认可,作为协调行为的共同规则,关键在于它们是由对话、商谈、讨论、论辩的论证过程得来的。一个人只有通过对话充分论证了自己要求的正当性,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行为是符合普遍性社会规范的,他与别人的交往才能正常发生,交往双方才能达成协调一致的行为。哈贝马斯为我们找到了一种改变人类生活状况的新途径,那就是话语论证与言谈论辩。话语交往主体之间取得相互认同的唯一方式就是论证,举出理由,也就是摆事实、讲道理,使对方信服。这里不存在任何强制,只是以较好的论证来达到较强的说服力。主体之间既不受外界的压力,也没有内在的强制,完全是处于自由、自主、自律状态,而且相互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
交往主体作为参与者拥有均等的机会,他们通过阐述言语行为,进行陈述、解释、论证和反驳,以使各自的主张与观点置于批判检验之下,只有具备了上述前提条件,才能实现合理的共识。这些交往的必要前提就构成了哈贝马斯所说的“理想的话语环境”。具体说来,每一个参与话语论证的人都必须遵守下述要求:(1)一种话语的所有潜在者均有同等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任何人都可以随时发表任何意见或对任何意见表示反对。(2)所有话语参与者都有同等权利作出解释、主张、建议和论证,并对话语的有效性规范提出疑问、提供理由或表示反对,任何方式的论证或批评都不应遭到压制。(3)话语活动的参与者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即表达他们的好恶、情感和愿望。因为,只有个人陈述空间的相互契合以及行为关联中的情感互补,才能保证行为者和话语参与者面对自身采取真诚的态度,坦露自己的内心。(4)每一个话语参与者作为行为人都必须有同等的权利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即发出命令和拒绝命令,作出允许和禁止,作出承诺或拒绝承诺,自我辩护或要求别人作出自我辩护。因为,只有行为期待的相互性才能排除某种片面要求的行为义务和规范判断,为平等的话语权利和这种权利的实际使用提供保证。[6]152
在理想的话语环境中,以话语的有效性要求为讨论的对象,交往主体的意见不受限制,除了更有说服力的充分论证之外,不存在任何强制;除了平等地寻求共同真理之外,一切其他的思想动机都将被排除。主体认可对方或承认规范是语言沟通、以理服人的效果,而不是策略干预、权力与地位的影响。理想话语环境的突出特征就在于对话空间的开放性与包容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介入话题讨论之中,自由地进行质疑与诘问、反驳与辩护的相互批判,体现了参与者的理性自律性与道德自主性。交往主体商谈与论辩的权利是任何人都无权剥夺的,但对各种要求的提出也就隐含着对义务与责任的承担。就存在性质来讲,理想话语环境的观念蕴涵了一种理想的生活形式,抽离了理想的生活形式,理想话语环境的实现是难以想象的。哈贝马斯有时认为,理想话语环境无意界定理想的生活形式,也不提供个人生活历史的具体尺度,而是立足于程序理性,通过论证程序来解决问题。理想话语环境的假定,一方面是现存生活形式的构成要素,另一方面又预示了理想的生活形式。因此,它既内存于任何的生活实在之中,它的实现又意味着超越了任何现存的社会秩序。理想话语环境经常被批评为不可实现的乌托邦,但乌托邦理性的批判绝不意味着放弃对理想化的追求。哈贝马斯认为,有乌托邦的理性精神指引比陷于虚无或陷于狂妄的无知要好得多。
[1] Jürgen Habermas, Moral Consciousness and Communicative Action, MIT press, 1990.
[2]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第二卷)[M].洪佩郁,蔺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3] 汪行福.走出时代的困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反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4] (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
[5] 艾四林.哈贝马斯[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6] 章国锋.关于一个公正世界的“乌托邦”构想[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