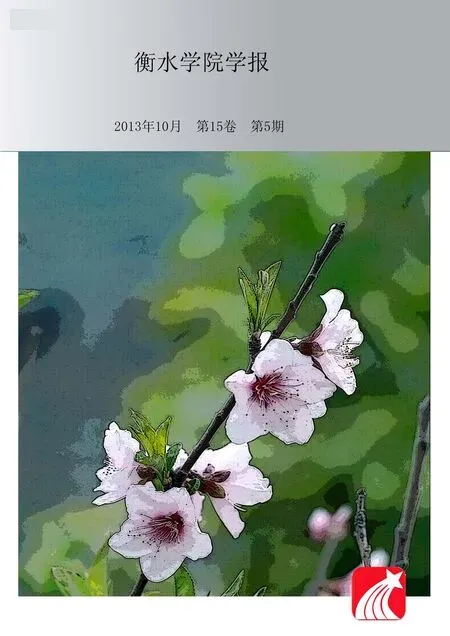从社会调查看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人口状况
王毅林
从社会调查看民国时期华北地区的人口状况
王毅林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从李景汉和当时其他学者的调查入手,考察华北地区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增长类型,从而引出对人地关系的探讨,并且以后者为重点。同时,从人地关系的分析中,还可以得知农民并非是一个愚昧、落后的群体,他们对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潜藏着一种朴素的智慧。
民国时期;华北地区,人口状况;性别比例;增长类型;人地关系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特殊处境,人们对于政府和教会的调查早已心存忌惮,他们的调查能否反映实情,自不必多言。但并不是民国时期所有的社会调查都与实际相差甚远。基于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定县的几年实践中取得了人们信任,使得李景汉在当地的调查尤为可信。所以,我们拟从李景汉和当时其他学者如卜凯、许仕廉、吴顾毓、刘容亭等人的调查入手,考察华北地区人口的性别比例和增长类型,从而引出对人地关系的探讨,并且以后者为重点,因为前两者会通过农民的生存方式,即人地关系反映出来。同时,从人地关系的分析中,我们还可以得知农民并非是一个愚昧、落后的群体,他们对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的安排都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他们的生活中潜藏着一种朴素的智慧。
一、性别比例与增长类型
在民国时期关于人口的众多调查中,性别比例也如同这些调查一样,众说纷纭,每100名女子与男子的比例从120到130,甚至高到150以上。根据1928年李景汉对定县东亭乡62村515家的调查,男女比例为105.7。1930年,又进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调查,得出男女性别比例为106.2。同时,根据许仕廉对几项调查的整理,我们可以看到华北几个地方的男女性别比例,即清河家庭人口为111,清河南区为108,定县大王耨村为113.8,燕京485学生家庭为104.7。可见,华北地区确实存在男多女少的问题,但是性别比例不至于太过悬殊。
除了性别比例,判定人口的增长类型,可以让我们对人口是否增长过快有一个明确的判断。1890年瑞典人口的年龄分配,被认为是一种标准的年龄分配。所以,李景汉把他调查中的人口年龄分配与瑞典的人口年龄分配作了一番比较,认为定县的人口增长类型属于稳定类。当然,李景汉并没有毫不客气地把自己的结论推广至整个华北地区,而是谨慎地指出:“此种现象能否代表华北人口情形,尚待此后他处亦有同样调查的参考。”
那么,我们就从其他学者的调查中,考察一下华北的人口增长类型。吴顾毓把自己在邹平的人口调查和人口统计学家孙得博(Sundbeg)对人口的分析比较之后,指出:“约略可以看出邹平的人口是在静止的状态中。”同时,吴顾毓把邹平和瑞典的人口年龄分配对比后得出:“邹平人口年龄分配上的表现是有病态的。”他所说的病态指的是“邹平人口的寿命短促,年老人不多”。我们认为,这主要是由于社会整体的医疗卫生条件差所导致的,并非人口自然特性上的病态。
此外,刘容亭对山西的调查也指出:“按各村户口比较,更足以证明人口生产率增高之迟缓。”许仕廉也发现:“若用人口塔表示清河家庭人口、清河南区人口与定县大王耨村人口,下层大,再渐渐自下向上缩小,大约成塔形,此图式很是人口常态。”并且,从许仕廉的文章中我们可以得知,这里的“人口常态”,即是指人口增长的稳定型。
虽然没有对华北地区整体的统计资料,但是我们从学者们所作的华北地区几个小范围的调查中,可以粗略地看出,华北地区的人口增长类型属于稳定型,并非有人惊呼的人口增长过快。例如,由于受太平天国这场农民战争的影响,“103年后的1953年进行人口普查,结果发现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山西、甘肃六省的人口还低于1850年”。虽然只有山西省属于华北地区,但也足以说明人口增长的缓慢。
二、人地关系
谈论人口是否过剩的依据是当时当地的社会生产条件能否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华北地区人口是否过剩,本质便是土地分配中的人地关系问题。首先还是看李景汉在定县的调查,全县人口约40万,平均每人约合田地4亩。
但是,仅仅从人均4亩地,我们无法得知这一土地占有情况能否满足人们基本的生活需要。所以,就需要其他材料的补充。农民的主要收入当然是农场的盈余,其次是各种副业的收入。李景汉通过调查农民家庭的生活费用,得出平均每家一年的收入为281.14元,而把全家一年的食品、燃料、衣服、应酬等费用加起来,得出平均每家一年的支出是242.64元,如此,则平均每家每年盈余38.5元。但是,这只是年景较好的情况,并且从李景汉的调查数据中,我们得出食品费和燃料费这两项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占家庭全年总支出的77.29 %,足见农民生活水平之低。
民国时期的其他调查,如杨汝南的调查,平均每家占有的田数为26.97亩,平均每家人口5.46人,我们可以得出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数约为4.94亩;根据卜凯在河北盐山县的调查,平均每家农场面积为24.5亩,平均每家的人口为5.35人,所以平均每人占有的耕地数约为4.58亩;董时进的调查显示,平均每人占耕地约4.7亩。
关于这3项调查所涉及的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否高于定县,我们不好妄加推断。但是,李景汉的调查中也指出:“从前定县常遇旱灾,土壤又属平常,因此农作物产量不丰。”定县的耕地生产能力应接近华北地区的平均水平。并且,李金铮在做了严密的考证之后得出,定县地区“人均2.53亩即可维持农民最低粮食消费”。因此,上述3项调查所涉及的地方,即使耕地的生产能力全部低于华北的平均水平,农民生活也不至于衣食无着。并且“现钱进款作物中,以小麦为主体”。尽管华北地区农民耕种的主要作物是谷子,其次才是小麦。但是,谷子主要用于家庭内部消费,小麦价值较高,主要用于出售,家庭只留小部分作为过节和应酬等方面之用。可见,农民对于农作物的种植分配,是一种根据自身需要的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安排。
前面关于华北人地关系的讨论都是考察农民经营农业的收入与支出,我们也尝试从用于划分阶级的农民成分上作进一步讨论。对阶级的划分实质上是关于农民土地占有情况的区分,而这也就是在讨论最大多数的农民是否可以从自己所占有的一定数量的耕地上获得维持日常生活的生存资料。在李景汉的社会调查中,我们看到1931年定县的自耕农所占的百分比为62.53 %,自耕农兼租种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占24.18 %,自耕农兼租出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占4.73 %,完全的地主占0.73 %,佃农占4.65 %。由此得出,前三者所占的百分比之和为91.44 %,即自耕农与半自耕农之家占了绝大部分。另一项调查中,自耕农所占的百分比为63.42 %,半自耕农为24.15 %,自耕农兼租出一部分土地的农民占4.76 %,地主占0.51 %,佃农占4.32 %。前后两项调查中各种成分所占的百分比大体变化不大。因此,我们可以说定县的绝大部分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基本可以自给。
此外,吴顾毓在邹平的调查也指出:“只看本籍户:无田者和有无田不明者所占的百分数是很少——只有8 %左右……在土地分配上,是没有什么因为不均而发生所谓土地与资本过于集中而有的人口过剩。”卜凯的调查显示,完全占有自有地的田主所占百分比为71.3 %。另外,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颇好,没有地主无理压迫佃农的事情……没有听说有佃农抗租或霸种,或地主欺诈或威吓的事情发生”。这也就保证了地方的相对安宁,“家家有土田,人人有职业,固不足为富有,亦可称为小康”。由此我们断定,华北地区农民的大部分为自耕农、半自耕农,农业生产基本可以满足他们生活的需要。而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佃农这两个利益对抗的群体之间也可以保持良好的关系。整个农村社会虽然仅处于赤贫线之上,但社会内部的各个群体之间可以维持一种相对和睦的关系。
除了以上纯粹的数字考察,我们还可以从数字之外进行分析。其中的道理,就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一种现象——“逃荒”。“对于以农立国的中国来说,土地资源的短缺必然造成了物质资料再生产的严重不足,从而产生大量的相对过剩人口,他们必须在农业之外去寻求生存条件”。在赛珍珠的《大地》中我们也看到,遭遇荒年之后,王龙一家人被迫选择了“逃荒”到南方的大城市去。农业社会不同于商业社会的谋生手段即在于:商业社会要求人们向外发展,以物品在不同地区之间的价值差额来获取利润;而农业社会则要求人们守定一块土地,通过辛苦的耕作获得“食”,农闲时从事纺纱、织布等副业获得“衣”,而就地取材一般就可以解决“住”,至于“行”在农业社会则是可以忽略的,最理想的状态即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既然农村社会要求人们“安土重迁”,而“逃荒”又是走投无路的选择,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如果人们没有选择“逃荒”的生存方式,那是因为当地的农业生产还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求。而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时,“农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和白银外流压缩了信贷,给农村家庭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同时,定县在“民国22年内,人民往东北及他处谋生者有八千人之多;23年内,竟达一万五千之众”。此中缘由,自无需多言。
三、结语
性别比例的讨论使我们看清了华北地区存在着男多女少的问题,但不是处于令人惊叹的悬殊状态。增长类型的探讨,我们认识到华北地区的人口增长处在高出生率、高死亡率的缓慢增长之中。与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相比,这种人口的自然状态对增长缓慢的作用更大。并且,农民的家庭人口与其土地占有规模是一种正比例关系。可见,农民对家庭人口数量的选择并非盲目的,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潜藏着一种朴素的智慧,支配着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人地关系的分析,使我们了解到当时土地的生产能力还可以维持大多数人的基本生存,而只占人口少数的地主和佃农之间也保持了一种相对和睦的关系。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逃荒”行为,也可以反证人地关系处在相对和谐之中。但是,当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到中国,并影响到农村地区时,定县外出谋生的人数骤增,更证明了我们对“逃荒”的运用是合理的。
[1] 李景汉.定县社会调查概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许仕廉.中国北部人口的结构研究举例[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3] 吴顾毓.邹平人口问题之分析[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4] 刘容亭.山西阳曲等二十二县五十个乡村人口概况之调查[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5] 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一八五○年以来)[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6] 杨汝南.河北省二十六县五十一村农地概况调查[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7] 卜凯.河北盐山县一百五十农家之经济及社会调查[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8] 董时进.河北省二万五千家乡村住户之调查[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二编:乡村社会卷(下).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9] 李金铮.也论近代人口压力:冀中定县人地比例关系考[J].近代史研究,2008(4):139-149.
[10] 李景汉.定县土地调查:上[J].社会科学,1935,1(2):441-449.
[11] 刘容亭.山西霍县安乐村五十一个农家之调查[M]//李文海.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人口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12] 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J].历史研究,1999(6):149-156.
[13] 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3)[M].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105.
On Population Status in North China of the Republican Perio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Survey
WANG Yi-l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Starting from the investigations of Li Jinghan and other scholar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sex ratio and growth type of the population in North China, and explores the man-earth relationship. The latter is the focus. Meanwhile, it shows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man-earth relationship that peasants can not be regarded as a group of innocent and underdeveloped people. On the contrary, they arrange thei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reasonably to some extent. There is a kind of simple wisdom hidden in their lives.
Republican period; North China; population status; sex ratio; growth type; man-earth relationship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10.3969/j.issn.1673-2065.2013.05.022
K258
A
1673-2065(2013)05-0100-03
2013-03-10
王毅林(1987-),男,河南安阳人,南京大学历史系在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