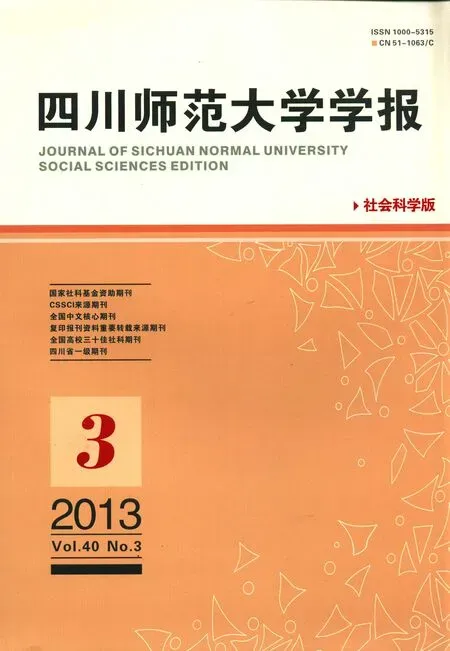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田 利 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田 利 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6)
1935年5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地区并将川陕苏区扩大到茂县、汶川、松潘、理县及大小金川流域,红军在所占领地区瓦解土司政权,解放“娃子”,夺取土司控制的粮食,分掉大土司的土地房屋,赢得了各族民众支持,但却遭到了川西北土司土官一致强烈的对抗。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转战并进入康北地区以后,将打击土司的政策调整为联合或者中立土司的政策,以致康北地区出现了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的情况。这一政策转变,直接原因在于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根本原因则是红四方面军面临着严峻的生存问题。当然,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以及康北的客观形势使红四方面军不可能与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
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康北;红四方面军;土司政策;政策调整
从地理范围及行政区划看,民国时期的川西北主要包括汶川县、茂县、松潘县、理番县及懋功、崇化、绥靖、抚边屯等处,而康北地区即现今四川康区北部,包括道孚、炉霍、甘孜、瞻化、泰宁、雅江等县,时为康区的一部分,后隶属西康省。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尚有土司土屯部落115个、土司土官114人,至1940年代,它们分别以姻亲关系、栓头关系、政教合一等方式分属于卓克基土司索观瀛为首的土司集团、苏永和为首的头人土官集团、华尔功臣烈饶布登为首的川西北草地部落集团[1],对川西北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康北地区的大土司有德格宣慰司、孔撒、麻书、竹窝(朱倭)、林葱4个安抚司及百利长官司,东北角还有巴底、巴旺两个宣慰司[2]3,在晚清赵尔丰“改土归流”不久,即因政权更迭、政局动荡,康北土司大多恢复,民国政府更是鞭长莫及,“不得不承认土司头人的权利,以维持自己的统治”[2]13。
1935年5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突破国民党军的土门封锁线后,相继占领茂县、理番县全境及松潘、汶川的部分地区,中共川陕省委移驻茂县,6月中旬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至7月初形成了包括茂县、汶川、松潘、理番县全境或部分在内的川西北苏区,构成为川陕苏区的一部分①[3]。8月底9月初,张国焘与中央就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发生分歧后率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并在10月下旬至11月发动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战斗失利后被迫向康北地区转移,1936年2月又发动康(定)、道(孚)、炉(霍)战役,攻占了康定、炉霍、甘孜,到4月初已建立起东起懋功、西至甘孜、南达瞻化和泰宁、北靠草地的康北苏区。在川西北苏区,红四方面军各部积极推行苏维埃阶级政策,打击豪绅地主及大土司、大土官、大喇嘛,这一政策虽然赢得了各族民众的拥护,却使川西北土司“一边倒”地反对红军[4]。而在康北苏区,红四方面军将打击土司的政策调整为联合或者中立土司、头人、喇嘛的政策,使康北部分土司喇嘛支持红军或保持中立,对康北红色政权的建设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就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及康北对土司的政策及演变原因、影响作一探讨②。
一
自1935年5月开始到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实施打击土司的政策,具体表现如下。
第一,瓦解土司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及藏羌回民族革命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川西北初设松理懋茂汶屯殖督办署,为邓锡侯所部第28军防区,1936年改为四川省第十六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其政权结构相当复杂,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屯政权、土司政权并存。国民党政府对土屯守备和土司所属地区的管辖徒有虚名,守备、土司是实际统治者,大土司甚至就是土皇帝。对此,邓锡侯在《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中说:“以夷制夷”的土屯制度使“夷民受封建制度束缚,生活沦于牛马,智慧锢蔽”,他计划“将现有土司、守备等名义一律废除,财政两权悉集县府,而于屯土酋长酌授官阶,仍加优礼”,但这一计划因“‘剿赤’军兴未及实施”[5]57,60。1935年5-6月间,红军进入川西北后推翻了国民党政权,瓦解了土司土屯政权,改变了川西北原有的政权结构,建立了一套红色政权体系③[3]。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完全剥夺大土司、大头人、大喇嘛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宣布撤销土司政权、取消土司制度[6]24,废除土司、取消等级制度[7]275。
第二,打击土司经济,将土地财产分配给百姓及娃子。
川西北民族地区盛行的土司经济制度,实质上就是农奴制领主经济。土司掌握了大部分土地成为农奴主,农奴没有土地,只能耕种土司的土地,向土司纳粮服役,接受苛刻的摊派。土屯经济的性质是封建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的过渡形式。屯守备掌握名义上属于国家的土地,并分与屯兵耕种。屯兵向屯守备缴纳正粮,承受屯守备的役使,份地收入则代替了国家发给屯兵的饷银。
针对土司土屯守备的残酷剥削压榨,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政府实行没收土司土地财产分配给百姓的政策。中共川康省委要求中共党组织及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没收土司头人的土地、牛、羊、马匹、茶叶、粮食等分给穷苦的藏羌民众[8]27。《回民斗争纲领》要求回族民众:“没收本族统治阶级的土地、牲畜平分给回族穷人!”[8]112《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章》号召百姓:“不交土司租,不还土司的债,不当娃子,不当差,把土司和土司管家的土地财产,分给格勒、格巴得沙。”[8]42自1935年5月开始到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实行了土地革命,汶川、理县、金川及梭磨、卓克基、松岗、党坝的农民分到了土司头人和寺院的土地[9]。土地革命改变了农奴制经济关系,也改变了建立在这个经济关系上的土司制度。
第三,消灭土司武装,建立藏羌回民族革命军。
大土司不仅拥有土地、农奴,而且拥有不可小觑的土司武装。中国边疆学会的佘贻泽说:川西北三大土司杨俊扎西、苏永和、索观瀛总计有枪11500支[10]154。《松潘社会调查》也说:“总计松潘所属生熟番有枪支不下二万余支,战斗力甚强,此次与我军协剿‘赤匪’,异常得力。”[11]247另据1938年四川第十六行署上报的《四川省第十六区夷族分布各县种类人口壮丁枪支数目查报表》统计:川西北土司拥有枪支11201支④。几种数据虽有出入,但都说明了川西北土司有枪不下万支,武装力量相当强大。
红军长征到达川西北后,各土司一致支持国民党政府与红军为敌。对此,红军一面坚决打击反动土司的武装力量,一面组织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苏区建立了大量革命武装组织,形成了地方革命武装系统。这个系统从横向上分为金川独立师、丹巴独立师、绥靖回民独立连、绥靖番民骑兵队、格勒得沙革命军,从纵向上独立师下辖团、营、连,格勒得沙革命军军部直辖一个营,往下每县设一个营。上述武装力量属于脱离生产的地方常规部队,任务是保卫根据地和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各县建立的游击队是不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地方武装组织,由地方苏维埃领导。地方所属茂县建立的“番(羌)民游击队”,在队长安登榜的领导下为红军筹粮、“扩红”做了大量工作,安登榜牺牲后,该游击队编入了主力红军。张国焘对少数民族革命武装的迅速发展感到兴奋,他说:“此间番民工作大有进展,已组织番民游击队数百人,群众大半回家(按:藏族民众因害怕红军躲进深山老林),现正组织格勒得沙(即番人)革命政府和革命军,主张格勒得沙独立自由平等,取消封建主剥削。革命政府包括大小金川十八土司区域,北至阿坝、毛尔盖,东至松、茂、汶,西至雅龙江,南达木坪、康定,番人对此极为热烈。”[12]443
第四,夺取土司控制的粮食,剥离土司控制的人口。
川西北地区属高山峡谷及草原地带,耕地稀少、贫瘠,粮食出产少、产量低。粮食筹集问题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极其严峻的大问题。就如耕地、人口、草山大多为土司控制一样,川西北粮食多数集中在土司手中。因此,红军筹粮,首先以夺取土司头人控制的粮食为主要目标。中共川康省委要求没收土司头人的牛、羊、马匹、茶叶、粮食,部分分给穷苦的少数民族群众,“大部分供给红军”[8]132。
红军在筹粮过程中非常注意夺取土司头人的粮食,尽量不损害普通民众的利益。1935年7月18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关于收割番民麦子问题的通令》,严格规定:各部队粮食极端困难、不得不收割地里成熟的麦子时,要先割土司头人的,最后在迫不得已时才准收割普通藏族同胞的[8]307。红军长征在川西北期间所获得的20万头牲畜、2000万斤粮食给养[8]109-110,除了民众的贡献外,大多取自土司头人。
数百年来,土司制度下的藏羌民众多被土司所控制,缺少人身自由,他们领种土司份地,向土司纳粮、当差,甚至当娃子。对此,红四方面军对土司控制的人口采取剥离政策,号召百姓“不交土司租,不还土司的债,不当娃子,不当差”[8]42。在争取民众脱离土司控制中,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建立少数民族的革命政党、革命政府和革命军,培养提拔使用少数民族干部。1935年6月5日,《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指出:建立广泛的少数民族穷苦民众的群众组织“番人革命党”非常必要[8]21。不久,中共川康省委不仅提出要立即组织“番人革命党、回人革命党”,而且强调它的组织基础是工人、雇工、娃子、丫头、贫农和贫苦的牧民[8]27-28。《西北特区关于少数民族工作须知》强调:要建立回番民族自己的政府,要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8]14。西北特区委员会还强调:“应当用一切方法动员番人参加红军,同时组织番人自己的红军、游击队、自卫军。这些民族的军队中间,必须以本族的穷苦群众做领导骨干,同时要设法选择穷苦番人中的积极分子到红军大学训练,培养成番人军队中的干部。”[13]78-79上述材料都强调了以少数民族的穷苦群众做基础和骨干来建立少数民族的革命政党、革命政府和革命军,其目的固然是为了推进苏维埃革命,但更重要的是把土司控制下的穷苦民众解放出来。
事实证明,红四方面军的这一做法是成功的。格勒得沙革命党自中央党部部长孟特尔以下的各部部长均由藏族积极分子担任,该党在川西北发展了300名穷苦民众为党员[14]85。格勒得沙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克基,副主席杨海山、孟兴发、马显文都是藏族或回族劳苦民众,中央政府各部或职能部门负责人及成员以及下辖的绰斯甲、卓克基、党坝、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等县级革命政府或特区政府成员绝大多数为劳苦的藏族民众,格勒得沙革命军主要成分也是藏族劳苦民众,总兵力千余人,总司令为卡格尔·江根[15]369。1936年1月成立的丹巴番人独立团有800余人,他们也都是藏族劳苦群众[12]314。
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还积极吸收藏羌回族民众中的积极分子直接加入共产党和红军。中共川康省委提出:在少数民族革命党里面,中共“要吸收积极斗争的分子加入共产党,树立党在番人革命党内的领导骨干”[8]27-28。西北特区委员会决议:“应当用一切方法动员番人参加红军”[13]78。
历史证明,红四方面军的这一做法也是成功的,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期间有不少藏羌回骨干分子加入共产党和红军。如藏族青年克基参加红军,并被推选为格勒得沙中央政府主席;藏族女青年杨秀英参加红军后,担任中共大金省委保卫局通司,后出任格勒得沙中央政府妇女部长;羌族泥石工张振福不仅自己参加红军,还动员一批羌族青年参加革命。藏族青年孟特尔、孟兴发和羌族青年袁大祥不仅加入了红军,还加入了中共。据不完全统计,1935年,川西北总人口不过30万人,参加红军的藏羌回族民众有5000人,理番县藏族杨金莲全家、党坝格尔威村高福贵全家都当了红军[7]113。对于不能参加共产党、革命党、革命政府、红军、革命军的少数民族群众,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则动员他们脱离土司头人控制,筹粮、打草鞋拥护红军。中共川康省委指示:“特别要组织番人在红军路过的地方烧茶煮稀饭,收容沿路彩病号和掉队的,掩埋路旁尸体,帮助红军医院搬运彩病号等”[8]28。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党组织在川西北全方位的组织动员,使不少民众摆脱了原有的对土司头人的人身依附关系。
二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为什么要采取打击土司的政策呢?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决定了必须打击剥削阶级的土司。
苏维埃革命来自苏俄。中国苏维埃革命实质上就是工农革命,它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就是由无产阶级政党组织领导贫苦的工农群众对剥削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进行的革命仍然是苏维埃革命,它要求红军及中共党组织动员藏羌回民众推翻土司喇嘛等剥削阶级的统治,建立苏维埃革命政权。这一点在川西北民族地区滞留时间最长的红四方面军的革命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1935年6月5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制定的《西北特区委员会关于党在番人中的工作决议》,要藏羌民众揭穿本民族统治阶级,即土司头人的假面具;要中共党组织及红军领导少数民族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汉官统治阶级,推翻土司头人的统治[8]75。中共中央也赞成红四方面军领导人的主张。8月5日,中共中央沙窝政治局会议认为,少数民族苏维埃革命的基本方针就是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及反对土司喇嘛等剥削阶级,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13]87。
可见,中共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在川西北民族地区苏维埃革命的主要任务:其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其二,是打击作为剥削阶级的大土司、大喇嘛,实现民众自由与平等。
第二,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认为藏民族内部的矛盾斗争实际上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反对剥削者压迫者的大土司大喇嘛的阶级斗争[9]。
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川西北藏民族,认为藏区存在严重的奴隶制等级制度,土司头人土官是残酷的剥削者、压迫者,是国民党军阀统治藏族民众的工具,他们出卖藏族民众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成为了国民党军阀统治的附庸,而黑头娃子、丫头、穷苦的农牧民是被压迫被剥削阶级,土司头人对他们有生杀予夺之权[12]491。至于活佛和大喇嘛是反革命的,他们用所谓“宣化”来欺骗民众,他们是国民党政府及土司土官利用来统治藏族民众的工具[13]72。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党组织最后强调,藏民族内部存在尖锐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就必须反对土司喇嘛。
第三,川西北严酷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使红军意识到要建立政权、要筹到粮食、要扩充兵员就必须打击土司喇嘛、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
川西北气候寒冷、人口稀少、土地贫瘠、粮食产量很低,有限的粮食和人口多数被土司掌控。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12万大军的粮食消耗是相当惊人的⑤。能否筹到粮食并补充兵员,是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红军筹粮、扩军必然同土司头人发生尖锐的矛盾和激烈的斗争。对此,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藏族土司头人为了保护他们的粮食,“往往集中数百人与我们的搜粮队对抗”[16]431。他和徐向前都强调,必须大力向藏羌各族和喇嘛做工作,他们最怕红军占他园地、吃他粮食,千方百计地前来抢夺,要想办法“不使土司再有联合,鼓动番众对我”[17]239。可见,红军为了生存、为了补充兵员,就不得不同土司斗争。
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苏区鼓动藏羌回族民众推翻本民族的统治者、剥削者,实施打击土司头人喇嘛的苏维埃革命政策,赢得了各族民众的拥护。这表现在:他们积极参与苏维埃政权建设,如黑水瓦钵梁子区苏维埃政府从主席、副主席到委员7人全部由当地藏民组成[6];他们积极参加土地革命,当苏维埃政府没收理番县左耳沟一带地主、土司、头人的土地分配后,贫苦藏民非常高兴,一个藏民喜悦至极,说要将土地证“藏之在我佛法经书中的神位头上,留为我永世万代的命根”[12]71;他们积极为红军筹粮,红四方面军在“四土”地区时,当地民众为红军筹粮200万斤[18]83,276;他们积极拥护红军,踊跃参加红军,如理番县有185位藏族、157位羌族民众参加了红军[7]113。
川西北的土司土官原本同国民党政府有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时有冲突发生,比较典型的是1931年2月至12月川军第28军邓锡侯部三次攻打黑水,三次被藏族基郎头人贡让、麻窝头人苏永和、根基头人仁真南木耳甲父子打败[19]755-756。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后,实施打击土司的政策,致使川西北土司土官转而与红军为敌,并参与国民党军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川西北土司土官及大喇嘛围堵红军的几次事件值得注意。其一,川西北三大土司土官苏永和、华尔功臣烈饶布登、索观瀛带头参与围追堵截红军。1935年夏天,苏永和率黑水各部落土司土官进攻路经黑水的红军,最终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松潘战役计划,绕道自然环境极其恶劣的草地北上[20]560;杨俊扎西之子麦颡第十五世大土官华尔功臣烈饶布登率土骑兵数千人两次堵截红军;索观瀛率众三次围攻“四土”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均被击败,但红军也遭到了相当的伤亡,后来索观瀛逃往绰斯甲躲藏[4]。其二,不仅土司土官头人攻击红军,喇嘛僧众也围攻红军。寺庙喇嘛围攻红军的事件不在少数,其中发生在1935年6月19日的“杂谷脑事件”最为典型。这次事件中有杂谷脑喇嘛寺、四门关喇嘛寺等不少寺庙中的喇嘛参与了叛乱,理番全境、“四土”地区、茂县、懋功及黑水部分地区屯兵、寺庙兵、土司兵、民团6000余人一起行动,他们烧毁桥梁、栈道,断绝交通,袭击红军驻地,杀害过往红军及地方工作人员,围攻各地苏维埃政府,暴乱历时一周,红四方面军在遭受较大损失的情况下才将其平定下去[13]263。其三,川西北土司土官喇嘛“一边倒”地围追堵截红军[4]。据笔者考察,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115个较大的土司土官中,除羌族土司安登榜外,绝大多数土司土官支持国民党军“围剿”红军,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土司土官直接参加了围追堵截红军的军事行动⑥。
三
红四方面军打击土司的政策,后来在康北地区发生了变化。
1935年12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主张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卖国贼蒋介石”之流的卖国活动,会后毛泽东的报告进一步强调:“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21]1511936年1月16日,陕北中央致电张国焘告知瓦窑堡会议的精神,指示: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一切反日反卖国的分子,不论他们代表那一阶级,那一政治派别,那一社会团体,那一武装队伍,都可加入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电报还告诉张国焘:为了结成民族统一战线,“苏维埃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许多政策改变为更加适合于反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
况”[12]319-320。
按照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执行的打击土司的政策就应作相应调整,但这时的张国焘已经另立中央并下令通缉毛泽东、周恩来等,他自然不会承认陕北中央、更不会理睬陕北中央的指示。有鉴于此,就在陕北中央致电张国焘的当天9时,共产国际派来解决红一、四方面军分裂问题的代表张浩(林育英)致电张国焘,一方面告诉张国焘可代转他给共产国际的意见,另一方面告诉张国焘准备向他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12]321。很明显,熟悉张国焘的张浩,深知张国焘不会接受陕北中央的指示,张国焘的意见只会向共产国际倾诉,所以特意告诉张国焘可代为向共产国际转达他的意见。
为了避免张国焘狐疑,1月24日,张浩再电张国焘,强调共产国际认为中央红军长征已经胜利,共产国际完全同意陕北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同时主张张国焘处改称中共中央西南局,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张国焘对陕北中央的意见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12]328。同一天,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张闻天也致电朱德,表示同意张国焘成立西南局,直属驻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同陕北中央并存,只“发生横的关系”⑦。1月27日,张国焘连发两封电报给张浩、张闻天,一封要求“以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12]331,一封表示“我们讨论了你们十二月二十五日的决议,原则上一致同意”[12]330。第一封电报标志着张国焘已决定放弃他的“第二中央”,只不过不服毛泽东为首的陕北中央的领导而只听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挥;第二封电报标志着红四方面军接受了瓦窑堡会议决议。
张国焘一直拒绝陕北中共中央的领导,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颇有意见,他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十天左右时间就明确表示放弃“第二中央”,接受陕北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呢?这当中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当时唯一正确的政策这一原因外,还有下面几个重要原因。
第一,张国焘南下川康边区建立根据地的计划失败。张国焘的大举南下,使川西北的茂县、汶川、松潘、理番等县相继丧失,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的失败,使他“打到成都吃大米”的企图无法实现,从而进退失据。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指出:“百丈决战,是我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也是张国焘南下方针碰壁的主要标志。”[22]473与此同时,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及红四方面军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接受共产国际和陕北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张国焘十分孤立,“孤家寡人的张国焘,被迫‘急谋党内统一’”[22]476。
第二,红四方面军面临极大的困难。这表现在:其一,红四方面军人数锐减。目前研究红四方面军历史的权威著作、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一书,两处提到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时的人数:一处讲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时,全军“总计约十万人”;另一处讲红四方面军到达甘孜整编时,全军“总计共六个军十九个师四万余人”[23]320,352。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有相似的说法⑧。可见,红四方面军南下后,人员损失之大实在惊人。其二,红四方面军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官兵多饥寒交迫、疲惫至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讲:百丈关战斗空前惨烈,红军杀敌15000人、自损10000人,“敌我双方都打到筋疲力尽的地步”[22]471。大军云集,不可避免地形成“与民争粮”的矛盾。藏族土司不仅组织武装反对红军,还煽动、威胁群众不与红军合作。红军部队常以野菜充饥,大量减员,有生力量日渐削弱,宝兴、天全、芦山一带不产棉花,部队不得不以棕榈制成的衣服来抵御高原的严寒[23]345。
第三,共产国际政策的调整及张浩的正确影响。早在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已把原来的世界无产阶级苏维埃革命的政策调整为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不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并派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张浩回国向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人传达,这才有了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召开。从前述张浩给张国焘的两封电报中不难看出,共产国际已经毫不动摇地承认了陕北中央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张国焘可以不听陕北中央的,但他不能不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
其实,此时的张国焘已成“骑虎”之势。他的“第二中央”并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并得到批准。众所周知,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作为中共老资格政治局委员的张国焘当然明白这一点。据徐向前观察:张国焘怕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他的“第二中央”,让他难以收场,特别是王明、博古等人都是共产国际的“宠儿”,斯大林决不轻易否定他们的主张,因此张国焘“对此颇有顾虑,要给自己留条退路,便不敢把事情做得太绝”[22]474。
当然,张国焘的转变同张浩的正确影响也有关系。张国焘对身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张浩较为信任。更重要的是,张浩没有“强迫”张国焘服从陕北中央的领导,还同意代为向共产国际转达他的“意见”;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定他的“第二中央”,而是同意作为“西南局”同陕北中央一起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领导;张浩还做通了陕北中央的工作,陕北中央同意只和张国涛发生“横”的关系,这给足了张国焘“面子”。
在这些因素的触动下,红四方面军开始全面实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策略,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改变打击土司的政策。1936年2月7日,红四方面军及中共金川省委提出:不论阶级、部落、土司、头人、活佛、喇嘛、阿訇,不论什么军队、派别、宗教、民族,都可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同时强调“给一切革命的小头人小喇嘛以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革命的大头人大喇嘛选举权”,改变对大头人及大喇嘛的策略,不没收大头人大喇嘛的财产,以便联合他们[14]451-452。3月,红四方面军总部发布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正式提出了联合或者中立土司、头人、喇嘛的政策策略[12]455。在实际的行动中,红四方面军比较注意争取土司喇嘛的支持。徐向前说:“根据党的统一战线策略,我军放宽了对土司、喇嘛的政策,尽量通过和平谈判,令其停止武装抵抗。”[22]482张国焘也说:对于藏人的抵抗,“我军多数是用政治方法来解决”[16]437。3月27日,张国焘、徐向前在致陈昌浩的电报中强调:“寿灵寺被俘大小喇嘛应优待之,并令其写信甘孜与各地喇嘛寺不与我打,大大宣布我军对喇嘛政策。”“三十军或乘胜速取多酉或先利用喇嘛办外交,与军事并进。”[12]401遵照红四方面军总部的指示,红军经过激烈战斗攻下寿灵寺后,对被俘的喇嘛不杀不辱,还让他们住在寺内照旧念经做佛事,在自己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还分给他们粮食。4月,在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川康省委的领导下,组建了藏族历史上第二个革命政党——波巴依得瓦革命党。革命党公布的《波巴依得瓦革命党党纲》,提出了打倒汉官、军阀、英日帝国主义,废除等级制度,解放奴隶,取消苛捐杂税等十大主张[12]465,却没有像《格勒得沙革命党党纲》一样明确提出“废除土司制度”[12]457。红四方面军政策的调整在当时的报刊文章中也可得到印证。1936年6月《川边季刊》第2卷第2期刊文指出:“自‘赤匪’窜康北道炉、甘、瞻后,即大肆提倡僧民合作,四出派人宣传‘不杀人’,‘不违康人习惯风俗’,‘极力保护喇嘛寺’,并迫令甘孜孔撒土司德钦汪母、香根喇嘛,集合附近喇嘛头人组卜巴临时政府,印发传单。”[24]711
事实正是如此。进入康区后,由于红军调整了对土司头人喇嘛的政策,康北地区藏族土司头人喇嘛并没有像川西北地区土司头人喇嘛一样“一边倒”地支持国民党军、与红军为敌,部分土司头人喇嘛保持中立,一些土司喇嘛甚至支持红军[9]。波巴共和国建立后,共和国中央政府驻甘孜孔撒土司官寨,孔撒土司为副主席,德格土司大头人夏克刀登任军事部长,甘孜寺的活佛香根督巴等参加了波巴共和国政府的工作[15]362。
应当指出的是,由于1930年代中期中国尚处在苏维埃革命时期,在西部地区,阶级矛盾还是社会主要矛盾。因此,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红四方面军,对土司政策的调整呈现了三个特点。
第一,政策调整有限度。红四方面军没有根本放弃苏维埃革命的阶级政策,没有根本改变打击大土司大头人大喇嘛的方针,而仅仅是策略上的有限调整。1936年2月7日,红四方面军及中共金川省委虽然提出改变对土司头人喇嘛的政策,但这种改变是要看土司头人喇嘛大小及是否革命,小头人小喇嘛可以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大头人大喇嘛虽然财产不再没收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使是革命的大头人大喇嘛也仅仅是有选举权而没有被选举权。作为政策调整最终完成标志的《关于少数民族工作的指示》讲得更清楚:对土司头人的宽大政策必须根据当地情形与阶级分化的程度确定,否则便是右倾错误[12]455。《波巴依得瓦革命党党纲》仍然规定:“废除等级制度”,“解放奴隶,废除奴隶差役”[12]492。在是否没收土司土地的问题上,张国焘甚至说:“甘孜工作的同志提出不没收土司的土地,是不对的。因为如果这样办,那么解放农奴便无从说起了。”[12]470
第二,对土司采取了区别对待策略。张国焘确立了红四方面军对土司的政策界限,那就是:中立一部分,利用一部分,反对反动土司。他认为,只讲废除土司制度和不反对土司都是呆板的机械的,反动土司我们毫无疑问地要反对,“可是有的土司愿意参加反对汉官、军阀的斗争,甚至赞助波巴的独立,并不反对我们,并且有号召能力,当我们运用民族统一战线时,当革命还是在开始时,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利用他呢”?他甚至主张“个别例外的分子还可以吸收到政权中来给他一个虚名”[12]470。
第三,始终由贫苦的民众掌握实权。张国焘认为,在革命开始时期,利用一部分有名望有号召能力的土司作为争取群众暂时的桥梁是可以的,但条件是他们要忠实于波巴独立解放运动,不妨碍群众斗争的发展。他说:对土司“正确的办法是一面利用这些旧人物,同时不使其掌握政府的实权,提拔大批可靠的基本群众的代表去实地掌握政权”;他警告,“在甘孜,现在是大批旧人物办事,孔撒女土司任波巴全国大会筹备会的委员长,日(白)利土司付之,督巴香根为秘书长,这种办法,如果不积极树立政权的下层基础,那么就有一种危险”;他还说,我们不一定要去机械地废除土司名义,但一定要把他们的实权夺取到新的政权中来,对于土司本身可采取发优待费的办法去优待他;总之,“根据群众阶级斗争的深入程度,根据群众组织力量的如何,才能逐渐改变我们对待土司的办法”[12]469-470。
纵观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土司政策及其演变,我们不难发现,除了政权的革命性质及共产国际政策的直接影响外,红四方面军自身的生存问题是决定红四方面军对土司采取打击还是联合政策的最根本动因。1930年代中期的川西北粮食、可耕地、人口很少且多被土司、头人、喇嘛控制,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时有10万之众,所需惊人,不打击土司喇嘛就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民众动员、扩大红军、甚至生存都是大问题。1936年初,红四方面军同原来相比减少了60%,仅剩4万余人,生存压力大大减轻,与土司喇嘛的矛盾便有所缓和⑨,这不能不说是政策转变的客观基础。但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认识上的偏差,再加上康区客观的社会形势,红四方面军还不可能同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这正如张国焘自己所言:“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16]436
注释:
①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成立于通江县城,1935年5月进驻茂县,6月移驻理藩县薛城、杂谷脑,下辖中共茂县、汶川、理番、松潘县委及茂县西一区、黑水特一区特委。中共川陕省委具体领导茂县、理番、汶川等县的中共地方党组织,组织召开了茂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茂县、理番、汶川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并将根据地扩大到“四土”及大小金川流域,直至1935年7月下旬中共川陕省委被中共川康省委取代。基于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建立的川西北根据地是川陕苏区的一部分。
②关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对土司政策的问题,涉及红四方面军的社会政策、政权建设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是较为重要的问题,然学界缺少研究。就笔者所知,目前仅有温贤美《红军长征与民族团结》(《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和胡本志、魏筱雨《怀念格达活佛》(《民族团结》1997年第2期)两文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笔者对此问题较为关注,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其中《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2期〕主要探讨川西北土司对红军的政治态度,《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主要从红军瓦解土司政权的角度论述红色政权的建立,重点分析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早期实践,《苏维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4期)主要论述土司及民众对红军苏维埃革命的态度与反应,本文侧重于研究针对土司的苏维埃革命政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演变。
③据笔者研究,这个政权体系先后包括1个大区级政权、5个省级政权、17个县级或特区政权、38个区级政权、140个乡级政权、181个村级政权(见拙文《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
④《四川省第十六区夷族分布各县种类人口壮丁枪支数目查报表》,第93-97页。四川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行署档案,全宗号8,目录号1,案卷号1017。
⑤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12万人左右,每人每天口粮按1.5斤计算,每天需粮食18万斤,一个月若30天、需粮食540万斤。川西北地区面积达83426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小省,而人口却只有30万人左右,只相当于中国东部人口密集地区的一个中等县,红一、四方面军特别是在川西北滞留九个月之久的红四方面军大量筹粮、扩军,必然使土司与红军之间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见田利军《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2期〕。
⑥据《四川省第十六区夷族分布各县种类人口壮丁枪支数目查报表》“备考”一栏记载,1935-1936年,川西北115个土司土官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达101个、占87.8%,其中积极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占58%、在半数以上,除羌族土司安登榜外,未见其他土司土官喇嘛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红军的史料记载。
⑦《中央为党内统一解决党的组织问题致××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9页。根据电文中的内容推测:“××”应是朱德。
⑧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第411页言: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时,全军“总计不下十万之众”;第483页说:到康区后,红四方面军全军“共五个军四万余人”。
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录了康区活佛的一段话:“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刘文辉。”(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张国焘认为活佛的观感描绘了当时红军在那一带的真相,也正好佐证了笔者“生存问题决定政策问题”的观点。
[1]田利军.民国时期川西北土司土屯部落变动考[J].贵州民族研究,2010,(5).
[2]四川省编辑组.四川省甘孜藏族社会历史调查[G].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
[3]田利军.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
[4]田利军.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2).
[5]邓锡侯.四川松理懋茂汶屯区屯政纪要[M].1936.
[6]中共阿坝州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阿坝州党史研究资料:第10辑[G].1984.
[7]阿坝州党史研究室,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阿坝州志之红军长征在阿坝(1935年4月—1936年8月)[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8]周巴.红军长征过阿坝革命文化史料汇编[G].马尔康: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化局,1997.
[9]田利军.苏维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4).
[10]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M].正中书局,1944.
[11]马大正.民国边政史料汇编:第28册[G].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12]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13]陈学志,范永刚.红军长征过阿坝革命遗址荟萃[G].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14]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
[15]中共四川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红军长征在四川[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
[16]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17]中央档案馆.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G].北京:学习出版社,1996.
[18]马尔康县志编纂委员会.马尔康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19]阿坝州地方志办公室.阿坝州志:民族志[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
[20]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3.
[2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2]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中)[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
[23]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
[2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录[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1993.
Red Fourth Army’s Policy and Its Change for Chieftains in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 and North of Xikang in the Mid-1930s
TIAN Li-jun
(Colle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6,China)
Fourth Front Army of Chinese Workers’and Peasants’Red Army which entered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 expanded Soviet Areas in Sichuan and Shaanxi province to Maoxian, Wenchuan,Lixian and the great and small Jinchuan Watershed in May 1935.The Red Fourth Army collapsed the chieftain regime,liberated slaves who were called wazi,seized food controlled by chieftains,redistributed fields and houses of chieftains and won local peoples’support, but suffered consistently intense confrontation from chieftains in the northwest of Sichuan.After they fought into the north of Xikang area in early 1936,Red Fourth Army changed the policy which combated chieftains into association with them or keeping neutral so that some local chieftains and lama supported or remained neutral.The direct cause was policy adjustment from the Comintern,but the primary one was that Red Fourth Army was confronted with severe issues for survival.Certainly,these which Soviet revolutionary policy of inertia and objective social situation in the north of Xikang province did not make Red Fourth Army bring about the real alliance with chieftains.
the mid-1930s;the northwest of Sichuan;the north of Xikang;Red Fourth Army;policy for chieftains;policy adjustment
K264.4
A
1000-5315(2013)03-0168-09
[责任编辑:凌兴珍]
2012-12-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川西北民族地区土司土官研究”(批准号:11YJA770046);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四川省中共党史学会党史资助课题“红军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康北土司的政策及其演变”;四川师范大学校院共建科研创新团队“中国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
田利军(1964—),男,四川新津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