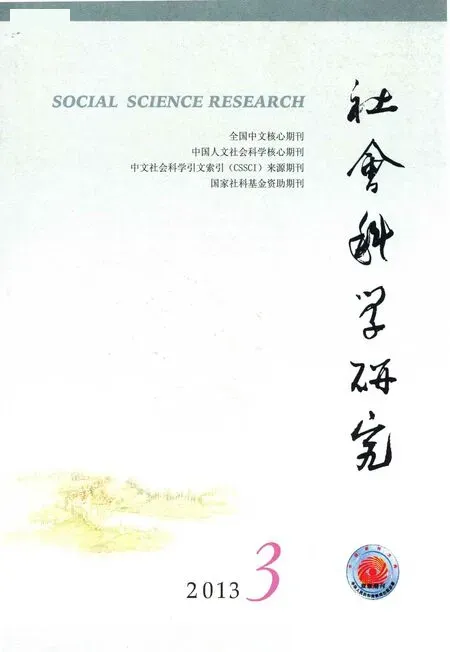先秦祭礼与祝祷文体
刘湘兰 周 密
先秦时期,人们非常重视祭祀,祭祀的范围很广。《尔雅·释天》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薶。祭山曰庪县,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是禷是禡,师祭也。既伯既祷,马祭也。禘,大祭也。绎,又祭也。周曰绎,商曰肜,夏曰复胙。”〔1〕在这些纷繁复杂的祭礼中,必然要发布祈福禳灾的文辞。这是祭祀仪式最重要的部分,是人神交流,达到祭祀目的的主要手段。最初,这些文辞仅是口头创作,到文字发明之后,便形之于简牍,最终流传下来,并成为后世祝祷文体的源头与典范。
先秦祭祀仪式十分庄严隆重。在国家、氏族的大型祭祀活动中,各级人员之间具有严格的组织分工,形成了各司其职、各掌其辞的制度;而且不同的祭祀仪式需要配合相应的祭辞,彼此之间不得混淆。这些祭祀制度对先秦文体的分类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由于祝祷文体为祭祀所用,其文体创作带有鲜明的功利性与目的性;文体形态受祭祀礼仪的影响较大。一些祝祷文体之间形成了功能对应关系。先秦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影响,体现了礼制与文体之间的互动。学界目前主要从考古学、文化学等角度探讨盟誓文、史诗等文体的发展,关于先秦祭礼对文体分类、文体形态、文体功能对应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却少有涉及。①目前学术界对先秦祭祀与文体的关系进行研究的成果有:陈梦家《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考古》,1966年第5期)、吴承学师《先秦的盟誓》(《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吕静《中国古代盟誓功能性原理的考察——以盟誓祭仪仪式的讨论为中心》(《史林》,2006年第1期)、张树国《“口诵史诗”与“舞蹈史诗”——论周秦汉唐史诗形态及与郊庙祭仪之关系》(《齐鲁学刊》,2011年第3期),等等。故本文就相关问题略论于下。
一、先秦祭礼与文体分类之萌芽
祠当为辞,谓辞令也。命,《论语》所谓“为命,裨谌草创之”。诰,谓《康诰》、《盘庚之诰》之属也。……会,谓王官之伯,命事于会,胥命于蒲,主为其命也。祷,谓祷于天地、社稷、宗庙,主为其辞也。……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此皆有文雅辞令,难为者也,故大祝官主作六辞。〔4〕
这“六辞”正是六种文体。这些祭辞或关乎国家命运,或用于社稷宗庙,或累列死者德行,各自有相应的运用场合。大祝根据不同的祭祀目的创作不同的文辞,形成了不同的文体样式。而作“六辞”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亲疏、远近”,处理人、神、鬼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不得混淆。这种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对不同文辞的选择,突出了文体特征,导致了文体分类现象的萌芽。
也有一些祭祀仪式,虽没能显现出祭辞的文体独立性,没能直接促进文体的分类,却为后世文体的确立及分类提供了历史依据。如瞽矇在不同祭仪中所掌“六诗之歌”的行为,就为《诗经》风、雅、颂三大诗类的区分提供了历史渊源。
在祭祀中,瞽矇的职责是诵诗、咏歌。《周礼·春官》曰:“瞽矇掌播鼗、柷、敔、埙、箫、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5〕在这则材料中,出现了歌、诗两种文体。歌体是合乐的,要击拊、鼓琴瑟而歌;而诗体用于讽诵。从《周礼》来看,瞽矇既掌“讽诵诗”,又掌“九德、六诗之歌”。前者之“诗”是指不同于歌的独立文体,这是没有疑义的。而后者“六诗”的含义却有所争议。何谓“六诗”?《周礼》有明确记载;
(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大祭祀,帅瞽登歌,令奏击拊,下管,播乐器,令奏鼓朄。大飨,亦如之。大射,帅瞽而歌射节,大师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大丧,帅瞽而廞,作硕匶谥,凡国之瞽矇正焉。〔6〕
我们可以从文体发生的角度来考察这“六诗”。贾公彦云:“大师是瞽人之中乐官之长,故瞽矇属焉而受其政教也。”据文献,教授“六诗”时,大师要“以六德为之本”,郑注曰;“所教诗必有知、仁、圣、义、忠、和之道,乃后可教以乐歌。”贾疏云:“凡受教者必以行为本,故使先有六德为本,乃可习六诗也。”即先要考察瞽者的道德品行是否合乎要求;继之要考察瞽者喉音与律吕是否相合,即“以六律为之音”,郑注云:“以律视其人为之音,知其宜何歌。”贾疏云:“大师以吹律为声,又使其人作声而合之听,人声与律吕之声合谓之为音。”可见大师在教授“六诗”时,对所授对象进行了严格挑选。这说明大师所教“六诗”具有特殊性,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诗”。
大师所授“六诗”用于大祭祀、大飨、大射、大丧等重要的祭祀大典中。所谓“大飨”是祭祀五帝先王的仪式,《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飨帝。”郑注:“言大飨者,遍祭五帝也。”〔7〕《礼记·礼器》又曰:“大飨,其王事与?”郑注:“盛其馔与贡,谓祫祭先王。”〔8〕“大射”是为选择合适的人员参与祭祀而举行的射礼。《周礼·天官·司裘》曰:“王大射,则共虎侯、熊侯、豹侯,设其鹄;诸侯则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则共麋侯,皆设其鹄。”郑注:“大射者,为祭祀射。王将有郊庙之事,以射择诸侯及群臣与邦国所贡之士可以与祭者。”〔9〕大丧,《周礼·天官·宰夫》曰:“大丧小丧,掌小官之戒令,帅执事而治之。”郑注:“大丧,王、后、世子之丧也。”〔10〕
以上这些通过诗词、图片、表情包和恶搞视频等表达个体政治态度的案例,不过是网民以戏剧化形式参与政治事件的冰山一角。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进步,更多戏剧化的形式将出现在网络政治参与当中。个体对政治事件的戏剧化表达,丰富和活跃了政治参与的形式与内容,是网络政治参与娱乐化的重要表现。
当大师主持这些仪式时,瞽矇唱诵的内容、唱诵的方式、所配之乐各不相同。举行大祭祀与大飨时,大师率“瞽登歌”,伴随着“击拊”、“下管”、“播乐器”、“鼓朄”等演奏行为进行祭祀。大射时,瞽“歌射节”,因射礼要展示武力,类似于征战,故大师要“执同律以听军声,而诏吉凶”。以歌律来预言征战之吉凶,在先秦应是常用的方法。如《左传·襄公十八年》记载晋楚之战,“楚师多冻,役徒几尽。晋人闻有楚师,师旷曰:‘不害。吾骤歌北风,又歌南风,南风不竞,多死声,楚必无功。’”杜氏注:“歌者,吹律以咏八风。”〔11〕在举行大丧时,“瞽而廞,作匶谥”,郑注云:“廞,兴也,兴言王之行,谓讽诵其治功之诗。”贾疏云:“帅瞽者,即帅瞽矇歌王治功之诗。”〔12〕可见“六诗”是融音乐、文辞、仪式于一体的具有不同风格与功能的“诗”体。在不同的祭祀中,大师与瞽矇要选用适合于祭祀目的的“诗”。而大师与瞽矇的选择,又说明风、雅、颂、赋、比、兴这“六诗”在祭仪中各自有特定的功能。郑注曰:“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雅,正也,言今之正者以为后世法;颂之言诵也,容也,诵今之德,广以美之。”〔13〕即是对这“六诗”功能的解说。
虽然《周礼》“六诗”并不是文体形式,但时人对唱诵“六诗之歌”人员的特定要求、不同祭祀场合下的祭辞风格与内容、“六诗”功能的差异,必然让人们认识到不同文辞之间的差异性。当文辞逐渐脱离了祭仪、音乐而单独流传下来,随着文体体制的成熟,用于祭祀的文辞发展为在日常生活中皆可吟诵的诗歌。《周礼》“六诗”中的风、雅、颂,就由祭祀时的表演形式转化为诗歌之体裁,即《诗经》中的三大诗歌体制。由此产生了最初的诗体分类。
概言之,在年复一年的祭祀仪式中,各类祭辞的功能与特征一再得到强化,并为时人所接受。时日既久,这些文辞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规范与模式,文体由此而形成。当人们在不同的祭祀场合对不同文辞作出选择时,这一举动又促进了文体分类的萌芽。当然,这种现象不限于祭礼。在先秦其他行为场合下,也促进了文体的发生与分类。如《周礼·春官》记载“士师之职……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二曰诰,用之于会同”。〔14〕士师所职“誓”乃是誓师之辞;“诰”是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对诸侯的告诫之辞。《尚书》记载的《甘誓》《汤誓》《大诰》《康诰》即是此类文体。另《尚书》又有典、谟、训、命,皆是在特定行为场合下使用的文体。这种因礼仪制度、行为方式的需要而创制文辞,是先秦时期文体分类意识形成的重要机制。
二、先秦祭仪对祝祷文体形态之影响
祝祷文辞是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祝祷文辞的内容依祭祀目的而定,其文体形态则要适应祭仪的需要。上古祭辞简单质朴,这固然是因为上古语言文字不够发达所致,但与上古简单的祭仪也不无关系。 《礼记·郊特牲》记载伊耆氏作“蜡祝辞”曰:“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15〕贺复徵认为此类蜡祝辞“报成功于岁终,又以祈来年之始,故祝之之辞如此。”〔16〕此篇“蜡祝辞”篇幅简短,语言直白,不假修饰。而《礼记》记载的上古蜡祭仪式也非常简单,可以推知祭辞与祭仪之间存在形式上的关联。
周朝祭仪较为繁缛,祝辞种类也趋于复杂。根据所祭对象的不同,使用的文辞也各不相同,故《周礼·春官》有大祝“六辞”之别。同样,周朝对祝文有文辞方面的要求。据郑氏注,大祝所作六辞“皆有文雅辞令”。刘勰也说:“祝史陈信,资乎文辞”〔17〕。刘永济认为先秦巫祝“二者乃先民之秀特,而文学之滥觞”,“祝以作六辞为职,亦择善为文辞者任之”〔18〕,皆可考见周朝时祝文的写作,要求修饰辞令以达到最佳的祭祀效果。《周礼·冬官·考工记》中的“祭侯辞”,是为天子举行射礼而做,辞曰:“惟若宁侯,毋或若女不宁侯,不属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强饮强食,诒女曾孙,诸侯百福。”〔19〕这篇祝辞从其内容看,可谓是恩威并重,文辞虽然简短,但文风庄重典雅,表现了强大的威慑力。《祭侯辞》的文辞风格正适应了射礼的需要。
周大祝所作“六辞”,现存文献很少,其文体形态到底如何受祭仪的影响难以考知。下文将考察用于宗庙祭祀的颂诗,以说明祭仪对“颂”文体形态的影响。颂诗的文体功能,据《诗大序》云:“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也。”〔20〕《文章流别论》曰:“颂,诗之美者也。古者圣帝明王成功治定而颂声兴,于是史录其篇,工歌其章,以奏于宗庙,告于神明。”〔21〕颂诗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美盛德之形容”,既是形容先祖盛德,故其文辞要求详赡富丽。
但同为颂诗,《商颂》与《周颂》却存在较大的文体差异。《诗经·商颂》是现存最古老的宗庙祭祀颂诗。《国语·鲁语》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①《国语》卷5《鲁语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216页。关于《商颂》是商诗还是宋诗,是《诗经》研究史上讼论了两千多年的问题。先秦典籍以《商颂》为殷商时作,而汉初齐、鲁、韩三家诗皆认为是春秋中叶宋人正考父所作,毛诗又认为《商颂》作于殷商时期。此后毛诗所论为世人认同,郑玄《诗谱》、孔颖达《毛诗正义》、司马贞《史记·宋微子世家索隐》等都持“商诗说”。清代中叶,魏源、皮锡瑞、王先谦力主《商颂》为“宋诗说”,王国维《说商颂》更是举卜辞与《商颂》相互印证,力主“宋诗说”,于当今学界造成重要影响,几成定论。不过,当今学界也开始对“宋诗说”提出质疑,并坚持“商诗说”。如梅显懋《〈商颂〉作年之我见》(《文学遗产》,1986年第5期)《正考父作〈商颂〉新考》(《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常教《商颂作于殷商述考》(《文献》,1988年第1期)、陈桐生《〈商颂〉为商诗补证》(《文献》,1998年第2期)等论文对魏源等人的论证进行了驳斥。另袁行霈《中国文学史》也认为《商颂》为殷商中后期的作品。本文立论从《毛诗》,认同《商颂》为殷商时期所作。正考父所献《商颂》共十二篇,其数量在当时而言已相当可观。从现存五篇《商颂》来看,其文辞以四言句式为主,文风典雅庄严,或抒情、或叙事、或祈福、或追忆,文体形态已发展得非常成熟。《商颂》的这种文体特征与商代宗庙祭仪有很大关系。殷人祭祀重视以歌、乐、舞祭神与飨神。据《礼记·郊特牲》记载,“殷人尚声,臭味未成,涤荡其声。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声音之号,所以诏告于天地之间也。”〔22〕所谓“殷人尚声”是指殷商社会崇尚歌唱、器乐、舞蹈三者一体的表演形式。“涤荡其声”大意是指歌唱之声回环往复,旋律起伏很大;“乐三阙,然后出迎牲”,即指用乐器演奏音乐,依音乐的章阙进行歌、舞,音乐进行三阙之后,始迎祭牲;同时祝颂唱祷之声响起,以示诏告于天地众神。殷人在祭祀过程中重视歌乐舞的传统,在《商颂·那》里有所体现。其文曰:
猗与那与,置我鞉鼓。奏鼓简简,衎我烈祖。汤孙奏假,绥我思成。鞉鼓渊渊,嘒嘒管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於赫汤孙,穆穆厥声。庸鼓有斁,万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怿。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顾予烝尝,汤孙之将。〔23〕
《那》为祭祀成汤的颂诗。在这篇颂诗中,频繁出现了鼓、管、磬、万舞等字眼,为后世展现了钟鼓齐鸣、歌舞升平的祭祀场景。颂诗便是在这种宗庙祭祀场合下用来歌唱的文辞,故当祭仪越繁复,所需颂诗的章节自然也越多。现存五篇《商颂》共16章,154句。其中《那》、《烈祖》、《玄鸟》各1章,各22句;《长发》7章,共51句;《殷武》6章,共37句。《商颂》章、句趋多,且章、句篇幅各不相同,似是依乐阙长短而定。可见随着祭仪的繁缛,颂诗的文体形态也趋于繁复。
而到了周代,祭祀传统有很大变化。周人祭祀喜用柴燎。《周礼》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祼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郑注曰:“禋之言烟,周人尚臭,烟气之臭,闻者槱积也。”〔24〕与“尚声”的殷人相比,“尚臭”的周人在宗庙祭祀中,更多是用血牲、黍稷、醴酒等以享神灵,而不是运用大规模的歌乐舞形式。周人祭仪的特点对《周颂》的文体形态也产生了影响。《诗经·周颂》“清庙之什”为祭祀周文王的颂诗,共10篇,每篇1章,共95句;“臣工之什”为诸侯助祭宗庙之作,也是10篇,每篇1章,共106句;“闵予小子之什”为“嗣王朝于庙”之作,共11篇,每篇1章,计137句,皆篇幅短小规整,文辞简要,缺少回环复沓之韵律。
《商颂》与《周颂》除了篇幅大小、章节安排存在差别外,二者文风也迥然不同。《商颂》回环往复,再三致意,且韵律协和、节奏鲜明,颂文叙事详赡,极尽铺排,语言典雅,渲染了一种庄严热烈、气势磅礴的氛围。从整篇作品的节奏韵律来看,很符合歌诵配乐的需要。而《周颂》却相对简朴些,不论叙事还是抒情,诗歌均缺少跌宕起伏的韵致,每篇内容也相当简略,较少铺排、反复。《商颂》与《周颂》的文体差异,正是缘于商、周二朝祭祀仪式的不同。
三、先秦祝祷文体的功能对应特征
由于祝祷文体用于人类与天地山川神祇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行为目的的相互对应,导致了言说方式的对应,反映到文体上则是有些祝文之间存在着功能对应关系。如“祝辞”与“嘏辞”即是一对功能互相对应的文体。在先秦文献中,祝、嘏常联称。《礼记·礼运》记载“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与其先祖”。“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谓大假。”“祝嘏辞说,藏于宗祝巫史,非礼也,是谓幽国。”〔25〕“故先王秉蓍龟,列祭祀,瘗缯,宣祝嘏辞说,设制度。”〔26〕郑注:“祝,祝为主人飨神辞也。嘏,祝为尸致福于主人之辞也。”〔27〕也就是说,祝是主人向神或先祖请求庇佑之文,嘏则是祝者代神或先祖向主人致福之文。祝辞与嘏辞是人神交流互应的文体。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以司祝作为中介,传达人、神旨意。
《仪礼·少牢馈食礼》对祝嘏祭祀的仪式与文辞皆有记载。“少牢馈食礼”中祝嘏祭祀仪式比较复杂。简言之,司祝先代主人作祝辞,祝文曰:“孝孙某,敢用柔毛刚鬣,嘉荐普淖,用荐岁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飨。”司祝传达了祝辞之后,再迎“尸”,司祝再代“尸”答以嘏辞,文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无疆,于女孝孙,来女孝孙,使女受禄于天,宜稼于田,眉寿万年,勿替引之。”〔28〕因为祝辞与嘏辞作文的指向性是对应的,二者所体现的情感特色也相互对应。《礼运》有“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谓大祥”之语,郑注云:“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各首其义也。”孔疏曰:“首,犹本也。孝子告神,以孝为首。神告孝子,以慈为首。各本祝嘏之义也。”〔29〕也就是说,人向神乞求赐福的时候,要本着子女对父母那样的孝心;而神灵赐福于人类时,也要表现如父母般的慈爱之情。
祷文与祠文也是一对功能相互对应的文体。祷文是向神告事求福之文,而祠文则是得福之后,用器物报答神灵庇佑之恩时所用的文辞。这就是郑玄所谓“求福曰祷,得求曰祠。”祷、祠在先秦典籍中也时常联用。《周礼·春官·大祝》云:“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郑注:“弥,犹遍也。遍祀社稷及诸所。祷既,则祠之以报焉。”贾疏:“以其始为曰祷,得求曰祠,故以报赛解祠。”同书《小祝》云:“小祝掌小祭祀,将事侯禳祷祠之祝号,以祈福祥,顺丰年,逆时雨,宁风旱,弥灾兵,远罪疾。”〔30〕《丧祝》“掌胜国邑之社稷之祝号,以祭祀祷祠焉。”贾疏:“祷祠,谓国有故,祈请求福曰祷,得福报赛曰祠。”〔31〕《小宗伯》“大灾,及执事祷祠于上下神示。……凡王之会同、军旅、甸役之祷祠,肄仪为位。”〔32〕
《荀子·大略篇》记载商汤祷雨辞,曰:“政不节与?使民疾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宫室荣与?妇谒盛与?何以不雨至斯之极也!苞苴行与?谗夫兴与?何以不雨至斯极也!”〔33〕《墨子·兼爱》也记载,商汤之时,天下大旱,成汤贵为天子,不惮以身为牺牲,以辞取悦于上帝鬼神,做祷辞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34〕两篇祷文皆言辞谦卑,反躬自责、祈求告罪之意溢于言表。这是祷求上帝怜惜天下众生,赐降甘霖的文辞。如果祷告灵验,那么必须再次举行祭祀,以示报答之情。
《诗经·周颂·丰年》是秋冬报赛祠文,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35〕再有《载芟》与《良耜》,《毛诗序》认为《载芟》是用于“春籍田而祈社稷”之文;《良耜》则是“秋报社稷”之辞,是一组祷、祠文。不过,因为《载芟》与《丰年》都有“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句,〔36〕故人们认为《载芟》其实也是报赛祠文。这些颂文记载了周人将丰收的黍粟酿成美酒,以祭祀先祖,以报赛享神,对神灵的庇荫表示感谢,同时又祈求来年再获丰收的美好愿望。行文高亢、热烈、欢快,充满了丰收的喜悦与来年的希望。可见,求福之祷文与报赛之祠文,因其祭祀目的的不同,其文风也迥然有别。
先秦祝祷文体既可用于祈福,也能用于诅咒。这也是其功能对应关系的体现。上文所言祝嘏文、祷祠文皆是用于祈福的文体。而诅文却用于陈述仇敌之罪恶,请神灵降祸于仇敌。黄叔琳认为“诅骂亦祝之一体。”〔37〕《文心雕龙·祝盟》记载“黄帝有《祝邪》之文”〔38〕,王兆芳《文体通释》认为诅“主于酬人罪恶,请神加祸。源出黄帝《祝邪文》,流有秦王《诅楚文》。”〔39〕黄帝乃传说中的人物,其《祝邪文》自然难以征信。《诅楚文》是北宋时发现的战国时期秦国的石刻文字,是现存最早的诅文。其内容为秦王陈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的罪恶,祈求天神制克楚兵,复其边城。文曰:
有秦嗣王,敢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鼛,布愍告于不显大神巫咸及大沉久湫,以底楚王熊相之多罪。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是戮力同心,两邦有壹,绊以婚姻,袗以斋盟。曰:叶万子孙,母相为不利。亲卬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而质焉。今楚王熊相,康回无道,淫佚甚乱,宣侈竞从,变输盟制。内之则虢虐不辜,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置诸冥室椟棺之中;外之则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诅盟。卫诸侯之兵,以临加我,却刬伐我社稷,伐灭我百姓,求蔑废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恤。祠之以圭玉牺牲,逑取彳吾边城新隍,及邘长亲,彳吾不敢曰可。今又悉兴其众,张矜意怒,饰甲底兵,奋士盛师,以逼彳吾边竞。将欲复其凶迹,唯是秦邦之羸众敝赋,鞟革俞栈舆,礼使介老将之,以自救殹。亦应受皇天上帝及不显大神巫咸、大沉久湫之几,灵德赐克剂楚师,且复略我边城。敢数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诅,箸石章以盟大神之威神。〔40〕
该文痛陈楚王熊相犯下的累累罪行,甚至将商纣的罪恶“刑戮孕妇,幽刺亲戚,拘圉其叔父”都强加到了熊相身上。全文极具鼓动性、煽动性。纪昀认为刘勰所谓“善骂”之诅文正是“《诅楚文》之类。”〔41〕
祝祷文体的这种功能对应关系,在文体发展史上是非常独特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祝祷文体作为人神交流的文辞,撰写的功利性与目的性非常强。文辞的发布方式与祭祀行为密切相关,因行为指向性的对应关系产生了言说方式的对应,从而导致文体功能的相互对应。
综上所述,先秦时期的祭礼对祝祷文体的发生、分类、形态及功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祭祀活动的繁荣、巫祝高水准的文字驾驭能力,促进了祝祷文体的发展。而不同祭祀场合对所需祭辞的特定要求,又增强了人们的文体分类意识。大祝所掌“六辞”、大师所教“六诗”即体现了先秦祭祀活动对文体发展与分类的推动作用。祝祷文辞作为祭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体形态随着祭仪的需要而发生变化。《诗经》中的《商颂》与《周颂》在内容、风格、篇幅等方面的差异,正是缘于商朝“尚声”与周朝“尚臭”祭祀传统的差异。祝文与嘏文、祷文与祠文、祝文与诅文等文体受制于祭祀目的的需要,形成了功能相互对应的特征。这些独特的文体现象,体现了古代礼制与文体的互动关系,值得学界进一步探讨。
〔1〕邢昺.尔雅注疏〔M〕.清阮元.十三经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1980.2609.
〔2〕〔3〕〔4〕〔5〕〔6〕〔9〕〔10〕〔12〕〔13〕〔14〕〔19〕〔24〕〔30〕〔31〕〔32〕贾公彦.周礼注疏 〔M〕.十三经注疏 〔Z〕.816,808 -809,809,797,796,683,656,796,796,874,926,757,811,815,767.
〔7〕〔8〕〔15〕〔22〕〔25〕〔26〕〔27〕〔29〕孔颖达.礼记正义 〔Z〕.十三经注疏 〔M〕.1379,1442,1454,1457,1416 -1418,1425,1416,1417.
〔11〕孔颖达.左传注疏〔M〕.十三经注疏〔Z〕.1966.
〔16〕贺复徵.文章辨体汇选〔M〕.景印四库全书:第1402册.171.
〔17〕〔38〕詹锳.文心雕龙义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55,371.
〔18〕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7.33.
〔20〕〔23〕〔35〕〔36〕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Z〕.272,620,594,601-602.
〔21〕李昉.太平御览〔Z〕.北京:中华书局,1960.2647.
〔28〕贾公彦.仪礼注疏〔M〕.十三经注疏〔Z〕.1201-1202.
〔33〕王先谦.荀子集解〔M〕.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331-332.
〔34〕孙诒让.墨子间诂〔M〕.诸子集成〔Z〕.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6.76-77.
〔37〕〔41〕黄叔琳.文心雕龙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57.105,105.
〔39〕王兆芳.文体通释〔M〕.北京:中华印刷局,1925.25.
〔40〕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