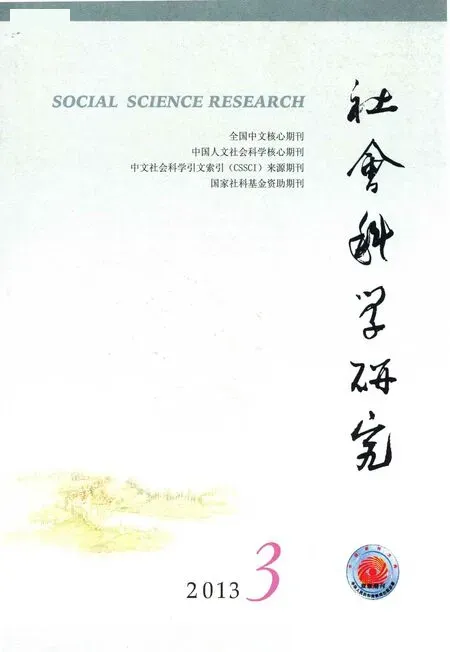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①
郭书愚
光绪三十年 (1904)②本文所用的清季史料皆为阴历,其中有无法精确对应到阳历年月者,故以下所述皆依照当时人的做法和习惯出以清帝年号纪元及阴历日期。又,本文以下引用作者全名时一概不尊称先生,谨此说明。,湖广总督张之洞饬令在湖北兴办存古学堂,力图以学堂这一“新”形式来保存国粹,此后各省纷纷“参仿”兴设。该校成为清季官方在“新教育”体系中尝试保存国粹的主要形式,有全国性的办学规模和长久影响。③详郭书愚《清末存古学堂述略》(博士学位论文)第二章,四川大学,2008年,49-92页。唯张氏为该校“殚心竭虑,筹计经年”,至光绪三十三年 (1907)五月,始正式进呈《创立存古学堂折》。〔1〕
而在光绪三十一年 (1905)八月初,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奏准“立停科举”,并饬令“各省督抚、学政责成办理学务人员,注意经学暨国文、国史”。此外,“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各省督抚学政每三年保送举贡至京师考官职,以便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2〕此后不久,豫、湘、赣等省相继有以上述政令为据并“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湖南方面更明确提出参仿湖北存古学堂办理,清季的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由此而与立停科举有了较直接的关联。且上述三省的办学方案皆先于湖北的拟办存古学堂规划进呈中央政府,不同程度地影响到此后保存国粹办学进程,更直接关涉到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的区别这一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重要面相。
张之洞在奏设存古学堂时即“特别声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3〕罗志田教授已指出,张氏此言意在明示存古学堂“与‘书院考课’这一旧形式的根本区别。存古而必出以‘学堂’的新形式,且划清与书院的界限,恰是其‘新’之所在”。〔4〕关晓红教授在研究晚清学部时,也注意到学部对湖南奏设景贤等学堂持否定态度。〔5〕关教授并在考察“科举停废对士子命运与乡村社会的实际影响”时,将“参与考职和优拔贡考试”作为“科举停废后乡村士子的实际出路”之一进行论述,是目前所知对这一官方举措最详实的研究。①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乡村士子——以刘大鹏、朱峙三日记为视角的比较考察》,《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关教授另有《科举停废与清末政情》(《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终结科举制的设计与遗留问题》(《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清季停罢科举的链式效应》(《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等文与本文论题直接相关,相当值得参考。笔者在考察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时,曾述及学部对豫、湘两省奏设尊经、景贤等学堂提案的批驳。②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但整体看,清季立停科举与保存国粹相关的面相未得学界充分关注,迄今未见专门以此为题的研究论著。本文拟以相关档案、清季报刊、时人文集等资料为据,重建清季豫、湘、赣三省兴设尊经、景贤、达材、明经等学堂的相关史实,进而考察这些学堂与张之洞兴设存古学堂方案的异同,希望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我们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一、河南尊经、湖南达材、江西明经等学堂的兴办进程
光绪三十一年十月,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奏请在省会设立尊经学堂。③这里及下段所述详《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会奏遵旨拟设尊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以保国粹而广师资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六日,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28-530页。此举的直接缘起和重要依据是同年八月四日得到谕准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 (以下简称《立停科举折》)。
河南方面的奏折开篇即引当年八月四、六两日关于各省一律停止乡会试、岁科考试,专办学堂的上谕,进而提出,袁世凯等人《立停科举折》奏请饬令各省切实遵办的“切要办法”,第一条即“尊经学”。若“坐令四方老宿,皓守穷经,而不能证明心得,以为国家致用,良足惜也。况当此振兴学务之际,设绩学老成之士,因不合时宜,废然自弃,人皆目经学为迂疏,不复专心致志,以蕲通作述之精意,第恐舍本逐末,不数年而国粹荡然矣。然则为今之计,尤以培植穷经之士,以保存国粹为先务”。河南省城原有大梁书院,光绪三十年改为大梁校士馆,“今科选既停,诸生应归师范学堂肄业”。而袁世凯等《立停科举折》原奏内又有“拟令各督抚学政每三年一次,保送举贡入京肄业”一语,故“拟即改大梁校士馆为尊经学堂,专考取通省举贡入学肄业,暂以百人为额”。学员“毕业时,择其最优者,咨送学务大臣考验合格,量予奖励,并升入学堂各分科,为日后递升通儒院地步,仍由臣等随时考察,习知其学问品行。将来三年保送时,亦可有所选择,不至滥举”。显然,河南方面拟办尊经学堂是因应中央政府停废科举政令的办学努力之一。④河南省城原有明道书院,“向由学政调取各府州县高材生前来肄业”。陈、王二人在拟设尊经学堂的奏折中,并以科举既停而“以前生员仍奉旨量予出路”,呈请将明道书院改为“师范传习所,专调各县绩学生员考取肄业,暂习简易科”。
在湖南,士绅的“存古”热情较高,且发端更早。光绪三十年下半年,在籍工科给事中冯锡仁、候选道张祖同、江苏候补道程龢祥等人即联名公呈署理湖南巡抚陆元鼎,认为前任湘抚赵尔巽光绪二十九年 (1903)奏准将岳麓书院改建高等学堂,是“变通往制,改弦更张”。岳麓书院为“先贤遗迹所留。若付之不甚爱惜,士林恫之”。且该书院“为全省士子聚集之所,各属每年来学者众,寻师访友,通声气而便取资,莫此为善。今废弃之后,风气隔阂,全省血脉为之不灵,于外郡县人士尤多未便,非另行设法通筹,奚以慰儒林之觖望”?岳麓书院东北旧有屈子祠,本在高等学堂校址外。冯氏等人呈请扩充其堂舍,缮葺其墙垣,“略仿令德堂之例”,创建“岳麓爱礼堂”,“聊寓告朔饩羊之意”,并“彰存古之义”;延请“品优学粹、夙孚众望者一人为堂长;学生以百数十名为率,斋舍约广容三百人。未经取额,亦准住堂”。该堂“参用通儒院新章”,“专崇正学,以扶世翼教为主”。“经术文章,培成根柢,进而究当世之务。在在以适用为依归,亦可研习乎声光化电之途而推之实业”。〔6〕
陆元鼎批示指出,岳麓书院为“千余年讲学名区”。“岳麓爱礼堂”意在“存古迹,延道统,讲朴学,储通材,一举而数善备,于湘省政教颇有关系,应准立案”。所需开办经费“由官筹拨一万金,以为之倡,另筹常年经费五千金。倘有不敷,由诸绅自行筹补”。堂名则“改题‘岳麓景贤堂’,似于高山景行之意,较为关合”。①陆元鼎:“批湘绅请建岳麓爱礼堂文”,时间不详,附在冯锡仁等《湘绅请建岳麓爱礼堂公呈》,时间不详,《湖南官报》第863号,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专件”,41B页。此后不久,又有二十余位湘绅联名呈请建“岳麓景贤堂”,“专收中年以上成材,普订学科、精研实业、分门肄习国文学,兼涉外国历史、理化、政治、法律诸科。意在参用通儒,酌遵新章。将来卒业后亦可备师范之选”。②冯锡仁等:“请建岳麓景贤堂公呈”,时间不详,引在《前署湖南巡抚陆奏湘绅建立岳麓景贤堂片》,时间不详,《东方杂志》第2卷第4期,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教育”,69-71页。联名公呈请建“岳麓景贤堂”的湘绅包括“在籍工科给事中冯锡仁,翰林院编修汪槩,翰林院庶吉士谭廷闿、苏舆,内阁中书陶觐仪、李铭勋,工部郎中蔡枚功,候补道孔宪教、席汇湘、程和祥,候选道张祖同、杨肇、陈翼栋,二品荫生龙绂瑞,甘肃宁夏府知府黄自元,四川候补知府刘庆咸、徐树锦,候补盐运判郭焯莹,举人张柏基、郑先亨、李光第、王礼祺,候选教职陈善澄、王先慎”。至光绪三十年十一月,陆元鼎在奏报筹办湘省学务情形时,专门附片具陈设立岳麓景贤堂事宜。〔7〕
另一方面,湖南省城原有孝廉书院和校经堂。前者为“通省举人肄习之所”,光绪三十年时任湘抚赵尔巽将其改为达材校士馆,于举人外添选贡廪增附监入馆肄业,仍“课经义治事”。后者原由学政“调取高材生肄业”,赵尔巽任湘抚期间将其改为成德校士馆。③本段及下三段所述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护理湖南巡抚庞、学政支会奏遵旨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东方杂志》,总第3卷第3期,光绪三十二年三月,43-49页。冯锡仁等人呈请创建“岳麓爱礼堂”时,时任湘抚陆元鼎正拟设法扩充“额少人多”的达材、成德校士馆。④陆元鼎:“批湘绅请建岳麓爱礼堂文”,时间不详,附在冯锡仁等《湘绅请建岳麓爱礼堂公呈》,时间不详,《湖南官报》第863号,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专件”,41B页。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申报》有报道说,湘绅黄敬舆、孔静皆等拟禀请官方将达材校士馆改为“养粹学堂,取保存国粹之义。悉遵奏定学堂章程,拟订简明规则”。⑤《孝廉堂拟改养粹学堂 (长沙)》,《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第1张第3版。该报道还提到:达材校士馆添招的“生监一班”与原招举人“每月课奖微有分别”,具体办法“大致半皆仍照旧章,略仿学堂章程,课试各门科学”。
光绪三十二年 (1906)一月,护理湖南巡抚庞鸿书、学政支恒荣会奏《遵旨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拟将达材校士馆改为“达材学堂,仿河南尊经学堂办法,专收举人五贡入学肄业,暂以百人为额”,毕业时“择其最优者咨送学部大臣考验合格,量予奖励,并升入大学各分科,为递升入通儒院地步”。另将成德校士馆、岳麓景贤堂分别改为成德学堂、景贤学堂,作为中年以上“通省旧学生员”专研中学之地,毕业时“均拟仿照湖北存古学堂并参酌河南尊经学堂章程,分别奏请奖励”。时衡永郴桂道谭启瑞等人详请将衡州府旧有船山书院“仿照湖北存古学堂章程办理”,庞鸿书、支恒荣“亦令参照省城三处学堂规则,专收该管府州属生员,名为船山学堂”。
与河南奏设尊经学堂折类似,湘省奏折开篇也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六两日令各省一律停止乡会试、岁科考试,专办学堂的上谕,进而提出,“科举既废,旧学寒畯,不乏穷经之士。以彼频年研计于中学,素有根柢,果其专心致志,不难入室升堂。且皆为国家昔年奖励之人才,当此学务振兴,亦岂忍令其皓首无归,中途废弃”?达材校士馆等“酌改学堂”以后,官方平时即可“考察习知”这些科举出身者的学问品行,以备将来考拔考优时“有所选择,不至滥取”。其为旧式读书人“宽筹出路”、为科举停废后保留的优拔贡考试作准备之意,实与河南拟办尊经学堂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尊经学堂“专考取通省举贡入学肄业”,而湖南的办学规划则将举贡生员皆纳入其中,且拟办四校分工明确,办学地点也扩及省城以外,俨然已是一整套面向科举出身者的办学方案。由目前掌握的资料看,如此恢宏的办学规模,即便是在整个清季官方有关“存古”的办学努力中,也鲜有它例。
豫、湘两省奏折除都以袁世凯等人所奏《立停科举折》为据外,还皆声称拟办各校与《奏定学堂章程》“相吻合”。湘省奏案更明确提出达材等校章程是依照奏定大学堂、通儒院、高等学堂章程,以及河南尊经学堂、湖北存古学堂各章程“参酌订正”而成,所有“应办各事宜”也“悉照奏定章程办理”。但学部在审查时即发现湘省奏案实际上颇多“与定章歧异”之处 (详后),故于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奏准饬令湘省将景贤学堂改办高等学堂,将成德、船山两校改办师范学堂,仅达材一校准“如原奏所请,招考举贡生员,肄习经、史、理、文各学。惟须先行补习普通 [课程],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庶将来升入分科大学,得以划一学程”。而河南尊经学堂“与湘省办法大同小异”,也应“改办师范学堂,以归一律”。〔8〕
学部虽然对达材学堂网开一面,但明确要求将该校纳入《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普通学制中,而不是专意“养成经史国文之资”。这为江西方面类似的办学努力提供了寻求避免学部批驳的办学思路。先是在光绪三十一年下半年,南昌举人胡其敬等人禀请用赣省“各属旧有宾兴、采芹、公车”等款项开办“孝廉存古学堂”,以便为“年齿已长”的“旧学之士”宽筹“进身之阶”。江西巡抚胡廷斡则认为,袁世凯等所奏《立停科举折》内已有专门举措可令“年齿已长”的“旧学之士”“不患无进身之阶”;且“伦常礼教、经史词章,学堂中无不备具”,不必“另立名目,致涉歧趋”。胡其敬等所禀“应无庸议”。〔9〕至翌年四月,也即学部奏驳豫、湘两省奏案大约一个月后,江西方面“援照湖南达材学堂成案”开办明经学堂。
与豫、湘两省的做法不同,江西方面是在明经学堂已正式开办后,向学部详呈该校“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准予立案。详文中说,该校“选录本省举贡生员入堂讲习。立学宗旨于保存国粹之中寓恤寒畯之意,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普通 [课程],以备升入大学分科”,同时“依中学程度增入讲经一门。盖因学堂取义显揭明经,循名核实,理似应尔”。如此“既系参照高等 [学堂]讲授,而肄业之举贡又皆国文夙有根底”。①“江西明经学堂详呈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转详咨部立案文”,引在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学部官报》总第26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页。
但学部注意到明经学堂“补习普通”仅一年学程,其科目设置及钟点配备较《奏定学堂章程》的规定“多有缺陷”(详后文),故饬令赣省将明经学堂所有学生“按其年龄学力分拨入师范学堂或中学堂肄业。所有经费亦移作扩充师范学堂及中学堂之用”。〔10〕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底,江西提学使林开謩以“各学堂均有经学一科,不必专立学堂,致多糜费”为由,札饬将明经学堂“即行裁撤。所有各学生业已分科考试,未取者各自回籍,另谋学业;已取者量其程度,分拨高等学堂及优级、初级师范各学堂肄业。所有该堂校舍以及经费即将医学堂移入接管”。〔11〕江西明经学堂在付诸实施一年多后以失败告终。
湖南达材、景贤、成德等校后来的办学运转也不太理想。就在学部饬令湘省改办的当月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湖南达材学堂正式开学。但该校并未照学部的意思,“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而是仍按湘省原奏方案,“分经、史、理、文四科为四班。举贡三年毕业,生员五年毕业,皆以能著有成书为据”。〔12〕至宣统元年 (1909)八月,时任湖南提学使吴庆坻也指出,达材学堂“聘订教员,选取学生均按 [光绪]三十二年原奏章程规定,以视鄂省存古学堂,范围不无广狭之殊,学科亦有疏密之判”。故湘省虽早有“存古专校”,但“办法未甚完全”。〔13〕
景贤、成德两校同样未按照学部奏令办理,而是皆改为法政学堂。光绪三十二年秋,湘抚庞鸿书奏准将岳麓景贤堂改为高等学堂“景贤法政分校”,拟翌年四月招录三百名学生,在“荷池精舍”正式开学。〔14〕据“景贤法政学堂”庶务长凌广文所述,该校原以“经费不敷,不能建筑校舍,又念诸寒畯向学情殷,不可不稍筹津贴,因照旧书院办法,以千六百金为正课生膏火,千金为正课、附课及随时投考生奖品”。至宣统元年,湖南咨议局“提议复裁膏火,拟用堂课,期于逐渐改良”。翌年五月,湖南提学使吴庆坻照会该校“实办法政”。①吴庆坻:“详湖南巡抚杨文鼎遵限筹设存古学堂文”,宣统二年十二月,附在吴庆坻《移奉抚批筹设存古学堂拟将成德达材两校合并改办文》,《湖南教育官报》,第13期,日期残,“文牍”,50A-52B页。同年六月校方通告,“非裁奖金,无以为延聘教员、印刷讲义之费;非加甄别,则校址狭隘,正课三百名端坐听讲,将不能容”。②“景贤法政学堂庶务长凌广文为学校改良事通告学生文”,宣统二年上半年,引在无作者《景贤学堂改良之通告》,《申报》,宣统二年六月廿八日,第1张后幅第4版。可知“岳麓景贤堂”在学部奏准饬令湖南方面将其改办师范后的近四年时间里,既没有修建“堂课”所需的校舍,也没有延聘讲课之教员,而是在“景贤法政学堂”的名目下照其既有的“书院办法”运作。
至于成德学堂,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的《申报》有报道说,“成德法政学堂”学生毕业后遗有学额,吴庆坻除“将本届备取优生二十名补入外,其余由考优、考职取列头场各生及在校未经毕业诸生中考取”,已于当天“行开学礼”。〔15〕后吴氏拟将达材、成德两校合并,改办“湖南存古学堂”,但与湖南咨议局未达成共识,加之吴氏本人宣统三年 (1911)初离职而同年三月学部颁行的《修订存古学堂章程》又与湖南办学方案歧异,皆直接影响了湘省整合改办存古学堂计划的付诸实施 (详另文)。
在河南,同样是在学部奏令改办的当月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巡抚瑞良即向学部电告尊经学堂改办两级师范学堂的计划。③参见瑞良《抚院覆学部推广师范电》,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河南教育官报》,总第3期,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文牍”,26B页;学部《咨覆抚院推广师范文》,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二十九日,《河南教育官报》,总第3期,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一日,“文牍”,19B-20B页。至宣统元年初,曾供职于河南学务公所的代理辉县知县戴宗喆以御史李灼华“请复岁科试之奏,持论甚大,所见甚远”,禀请河南巡抚吴重憙通饬各州县设“存古小学堂”一处,各府厅设“存古中学堂”一处,省会设“存古高等学堂”一处,以“存先圣之道统”。吴重憙则认为《奏定学堂章程》对中学“已加意注重”,如果各处学堂“遵章切实授课,断无蔑古荒经之虑”。豫省学务“尚未发达”,若“分等普设”存古学堂,“其知者以为国粹之保存,不知者以为科举之复燃。流弊所趋,不独无以兴未兴之学,即已成立者亦必立时解散,群以存古为名,相率弃学”。且豫省此前拟设的尊经学堂与戴宗喆“原禀所称存古学堂用意略同”,而被学部饬令改办师范学堂;后湖广总督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内也有“河南尊经、湖南景贤各学堂均系规仿鄂省而误会者”等语,故“此项偏重古学之学堂揆度现情,断在不应提议之列”。④吴重憙:“批示河南提学司如详饬知戴宗喆文”,时间不详,附在孔祥霖《详覆抚院遵议辉县戴令宗喆禀请广设存古学堂文 (院批附)》,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河南教育官报》,宣统元年总第45期,同年六月一日,“文牍”,368B-372A页。
吴氏的意见得到署理河南提学使孔祥霖的鼎力支持。孔氏进而强调,“若置经、史、文集数种,聘一从前工贴括者主讲其中,名曰‘存古’,实诬古矣。且如此则直曰‘复书院’可矣,何必强名为‘学堂’?若仿江、鄂 [存古学堂]体制为之,断非一府一州一县所能举”。当时已有上谕明令官员“当以李灼华等为戒,勿蹈故辙”。戴宗喆禀文引李灼华请复岁科试奏案为据,“未免显违谕旨,应予申饬,以为无识妄言者儆”。况“前次河南请设尊经学堂与湖南请设景贤学堂,先后均经部驳有案。乃不二三年间遽请自省城以至府厅州县广设存古学堂,匪惟无此财力,即有之,其能免学部驳诘耶”?〔16〕
由于资料所限,戴宗喆拟办存古学堂的具体设想尚不清楚,唯戴氏“分等普设”存古学堂之议,意在建立省会、府厅、州县三级的一整套中学人材培养体制,较张之洞等人仅拟在各省省会设一所高等专门性质的存古学堂的方案远更恢宏,恐怕已属当时中央政府担心并试图避免的“存古有碍新机”倾向。且戴氏试图将存古学堂与科举联结,也与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的思路异趣,正是当时中央政府竭力反对的做法。⑤详郭书愚《清季中央政府对保存国粹学堂的态度演变》,《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2期。另一方面,吴、孔二人皆提到河南此前拟办尊经学堂被学部奏驳的情形,孔祥霖更是将戴氏的方案与尊经学堂归为一类,从一个侧面提示着拟办尊经学堂未果对豫省后来的存古努力确有影响。实际上目前所知河南方面至宣统二年 (1910)仍未按学部《分年筹办事宜清单》的统一规划,设立存古学堂。〔17〕
二、尊经、达材、明经学堂与湖北存古学堂的异同
将现存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与张之洞兴设湖北存古学堂的饬令、奏折和课表章程细加比照,不难发现豫、湘两省的办学设想在立意初衷、招生思路、学程模式、科目配置、考试规章、管理方式、师资规模等方面皆与张之洞拟办湖北存古学堂的规划明显异趣。
在招生方面,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与湖北存古学堂皆面向具有科举出身者招生,但其具体的招生思路明显歧异,正体现出办学初衷的不同。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原拟“选取高等小学毕业者升入,特以目前小学尚未造有成材,应就各学生员考选,不拘举、贡、廪、增、附皆可”。〔18〕显然,该校所以“就各学生员考选”,是因高等小学“尚未造有成材”而采取的权宜之计。正因是权宜之计,故而对举、贡、廪、增、附生一视同仁,皆给予同等的应考资格,以便在尽可能广的范围内网罗到具有天资且诚挚“存古”的高材士子。①为达此目的,张之洞在实际招生时甚至“悬一特别之格,招考举贡考职、生员考优之正取、备取并各师范学堂毕业生,列为优待一项”。他还示谕:存古学生凡“入堂以后,如果于所认习之学科曾经用功、具有门径者,准其于定章七年毕业之期减一二年以示优异”。张仲炘:“详署理湖北提学使王寿彭文”,时间不详,引在瑞澂“湖广总督为存古学堂事咨学部文”,宣统三年四月,晚清学部档案,台北:“国史馆”藏,目录号195,案卷号135。其招生的初衷既是考选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入学而非面向旧式读书人群体,则其办学旨趣自然也不是为旧式读书人在科举停废后“宽筹出路”。实际上,按照张氏的设想,存古学生毕业后应送入京师大学堂肄习进而递升入通儒院,说明该校的实际定位就是力图在《奏定学堂章程》颁行后补入清季“新教育”体系的新式学堂。
前文说过,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的前身皆是完全面向旧式读书人的教育机构。豫、湘两省奏请将其改办学堂,上述招生思路仍在延续。且各校招录旧式读书人,对科举出身皆有明确而具体的要求。河南尊经、湖南达材学堂“专收举人五贡入学肄业”,成德、景贤两校以湖南全省中年以上“旧学生员”为招生对象,而船山学堂则专收衡、永、郴、桂四府州属生员。②本文以下所述河南尊经学堂办学预案,湖南达材、成德、景贤、船山四学堂办学设想,除特别注明外,分别参见“河南改设尊经学堂章程清单”,附在《河南巡抚陈夔龙、学政王垿会奏遵旨拟设尊经学堂及师范传习所,以保国粹而广师资折》,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六日,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528-530页;“湖南达材、成德、景贤、船山各学堂章程”,附在《护理湖南巡抚庞、学政支会奏遵旨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东方杂志》,总第3卷第3期,光绪三十二年三月,43-49页。科举出身的规格和等级成为湘省四校在招生方面分工的基准,与湖北存古学堂在招考时对科举出身一视同仁的权宜之计明显异趣。③学部已注意到豫、湘两省拟招学员“非学堂积累而升”且“学生之修业无异,而以举贡生员分别校舍”的做法,并在《湘省学堂与定章歧异奏请改正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28-130页)中明确指出其与“奏章不免歧异”。
在学程方面,湖北存古学堂学生一入校即分经、史、词章三科,各科主课皆是“先博后专”的研习思路。④本文以下所述湖北存古学堂办学方案除特别注明外,皆参见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五月,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4387-4389页。而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校倡导学员“首尊经学”、“精研理学”、“博览史学”、“保存文学”、“兼通艺学”、“预习政学”,各学科固有轻重之别,但学员既然要参加优拔贡各场考试,毕竟不能取一入校即分科专精一门的模式。河南尊经学堂规定:“学生一入校,即将其三年内拟治何经、著何书、考何政、习何艺,分晰亲注于册”。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在科目的设置和具体要求上,豫、湘两省皆要求学员“精研”理学,而理学并没有被张之洞纳入湖北存古学堂的教学授受范围。张之洞将“博览古今子部诸家学”列为湖北存古学堂课时最重的“通习课”,意在“优游治经史者之心思,增助治词章者之风骨”。而豫、湘两省办学章程不仅没有列出类似的科目,甚至整个章程都没有只字提及任何有关“子部”的内容。“算学”、“舆地”是湖北存古学堂两门兼讲中西学的“通习课”。但在河南尊经学堂章程中,二者都不是独立的科目,“舆地”因“与史学相表里”被附在史学科目中,“中国传统算学”则是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出现在“兼通艺学”的条目中,整个章程没有提及“西算”。
此外,张之洞拟为湖北存古学堂各科学生开设“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外国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各实业、工商各实业”等西学“通习课”和体操课。河南尊经学堂章程虽列有“兼通艺学”和“预习政学”的条目,但前者仅言及“六艺”而没有提到“西艺”,后者也只是说“通经原以致用,授政不达,虽多奚为?”没有明确提及“西政”。在湖南达材等学堂章程中,“艺学”和“政学”则要具体明确得多,前者被界定为“农、林、渔、牧、工商各实业”,而“凡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则为“政学”,这样的表述应是参仿湖北存古学堂的“农林渔牧各实业”和“工商各实业”两门西学通习课而成。唯湖北存古学堂的西学通习课为所有学生的必修课,意在“开其腐陋,化其虚矫,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长”。〔19〕而湖南方面要求达材等学堂的学员“各择[政学中]一门加意考习以储心得”,意味着“政学”成为选修课目,正有鼓励学生专长一门之意。
在考试方面,豫、湘两省章程皆规定每月“试以经史策论及各体文、政治及西国艺学”。按,“策”、“论”作为传统考试形式也出现在清季“新教育”体制中,并非科举与学堂的根本区别所在。①《奏定学堂考试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509-510页)即规定,高等一级学堂及京师分科大学的毕业考试分内、外场。内场“比照拔贡、优贡例,只考两场”,每场“出论策、考说各二题,头场以中学出题,经、史各一,经用论,史用策;二场以西学出题,西政、西艺各一题,西政用考,西艺用说”。外场“试以策论、考说文字,应就学生已习之中国经史文学及西学各科学中,分场发题考问”。有关晚清“策、论”等考试形式,参见刘龙心《从科举到学堂——策论与晚清的知识转型 (1901-1905)》,《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8期,2007年12月,105-139页。相关面相 (诸如晚清“新教育”体系对科举“策”、“论”等考试形式的承继和变通等)似尚有相当的考察空间 (详另文)。但由具体的考试内容看,豫、湘两省的考章更多考虑的仍是学员参加优拔贡考试的需要,而与《奏定学堂考试章程》的规定相去甚远。②光绪二十七年 (1901)十月一日政务处、礼部在《会奏变通科举事宜折》(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32-36页)中提出,全面废止“八股文程式”而代之以“策”、“论”、“义”。优拔贡考试头场改试“中国政治史事论”及“各国政治艺学策”,二场“改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若以此为参照,前引豫、湘两省的月考规章似不乏针对之意。尤其河南尊经学堂章程没有将“西政”、“西艺”纳入学员的研习范围,却将“政治与西国艺学”列为学生每月必须参加的考试项目,如此“学考分离”,说其是以优拔贡考试为指针,应不为过。
值得注意的是,与河南尊经学堂相比,湖南拟办达材等学堂有较多参仿湖北存古学堂之处。湘省奏折明确提出,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将经心书院故址改为存古学堂,法良意美”。“今日环球各国学堂皆重国文,凡礼教风尚及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以保全为主。中国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系人伦,忠孝至行、平治大猷皆由此出。即列朝子史,事理兼赅,各种词章、军国资用亦皆经术之绪余,文化之辅翼,未可听其废弛”。此言明显是“酌改”张之洞札饬设立存古学堂的公文而成。③《护理湖南巡抚庞、学政支会奏遵旨改设学堂以保国粹而励真才折》,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东方杂志》,总第3卷第3期,光绪三十二年三月,43-49页。张之洞在札饬设立存古学堂的公文(《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湖南官报》,第891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时政录要”,33A-34B页)中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至本国最为精美擅长之学术、技能、礼教、风尚,则尤为宝爱护持,名曰国粹,专以保存为主……中国之圣经贤传,阐明道德,维持世教,开启聪明,尊贵种族,固应与日月齐光,尊奉传习。即列朝子史,各体词章,军国资用,亦皆文化之辅翼,宇宙之菁华。岂可听其衰微,渐归泯灭!”此外,奏折对“中学日微”以致新式学堂“鲜教国文专门之教员而中师渐绝”的忧虑,也是张之洞创设存古学堂相当强调而河南奏设尊经学堂没有提及的面相。①张之洞在札饬设立存古学堂的公文(《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湖南官报》,第891号,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时政录要”,33A-34B页)中说:“新设学堂学生所造太浅,仅可为初等小学国文之师。至高等专门学、普通中学、优级师范、高等小学皆无教国文专门之教员。倘高等以下各学堂之中学既微,中师已断,是所有国文之经史词章无人能习、无人能教。然则将来所谓大学专门岂非徒托空言!既无周秦传经之名师,安有两汉立学之博士?窃恐不免有经籍道熄、纲沦法斁之忧,言念及此,不胜大惧。”不仅如此,前文说过湘省章程对“艺学”、“政学”的界定明显参仿湖北存古学堂,而湘省章程还列有“兼通舆地学”和“兼通算学”条目,为尊经章程所无。前者似是删减湖北存古学堂“舆地学”课程内容而成,后者基本与湖北存古学堂的“算学”课内容相同。
在校务管理方面,河南尊经学堂提出“皇太后、皇上万寿圣节、圣诞辰及端午、中秋均照《学堂管理通则》放假一日”,但以校内无洋教习为由,不拟采用西式星期制作息,而“遵国家朔望谒庙之制”,每月朔望,全校师生按照《学堂管理通则》的规定“行礼”,礼毕后放假。类似的行礼程式也见于湖南达材学堂章程中 (具体的行礼日期略异)。但湘省章程也没有照西式星期制作息和放假的相关规定。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之洞不仅为湖北存古学堂拟订了一整套星期制的课程授受和课时配置方案,而且相当注意利用新式学堂在“管理”方面的长处,摒除旧日书院积习。张氏明确提出,存古学生“须规矩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与现办文武各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20〕
实际上,豫、湘两省拟聘师资的规模皆远不足以实施一整套课程授受方案。尊经学堂拟设“教务长、监督、庶务长、文案官兼会计官、监学官兼掌书官各一人,教员二人,斋务长四人”。教务长“须聘德行道艺为士林所推服者充当,教员须明习各种艺学”,每月由教务长命题,考“经史策论及各体文”;由教员出题,考“政治及西国艺学”,两考“均由教员核阅,送教务长评定甲乙”。湘省章程提出“聘堂长一人并委监学一人、科学分校教员四人、斋务长一人、庶务长一人、管书斋长一人”。②这里所谓“科学分校教员”中的“科学”意指“众科之学”,而非今日通行的“科学”(science)之意。每月考试由堂长命题,“分校教员”核阅后送堂长“评定甲乙”。学生每旬所交札记也由“分校教员”核阅后送堂长评定。湘省拟聘教员人数较尊经学堂扩充一倍,但即便如此,仍与张之洞所拟湖北存古学堂总教4人、协教4到6人、分教6到10人的师资规模相去甚远。〔21〕整体看,豫、湘两省拟聘师资似乎更多考虑月考命题、核阅试卷和札记所需,而非象张之洞设计的存古学堂那样进行日常的西式学堂课程教学活动。
通过上文比照,可知学部在奏驳时所言河南尊经,湖南景贤、达材等学堂“外标学堂之名,仍沿书院之实”,大体即是其与张之洞兴办存古学堂方案的区别所在。〔22〕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特意申明湖南景贤等学堂、河南尊经学堂“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毫不相涉”,固然有避免学部批驳的考虑,但若说豫、湘两省拟设保存国粹学堂的预案原即“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而较疏离于清季“新教育”通行的西式“学堂”办法,也明显不同于张之洞拟在存古学堂中施行的“学堂教人之学”,应不为过。〔23〕
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不同,江西明经学堂是在学部奏驳豫、湘两省奏案后设立的。江西方面提出,该校“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历史、地理、算学、格致、图画、东语、英语、体操等“普通课程”。上述各门暨讲经一门,由江西教务处派员“到堂授课”。③“江西明经学堂详呈章程及课程表格并请转详咨部立案文”,引在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学部官报》总第26期,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页。学部“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罗振玉提交的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显示,该校光绪三十三年聘有“监督、监学官、监学兼斋务长、文案官、会计官、检察官、杂务官”各1人,司事2人,教员9人;学生定额120人,当时在校71人;“教学科目”为“伦理、经学、国文、历史、地理、心理及辨学、西语、东语、法学、兵学、算学、格致、理财、体操、图画”,确是参仿《奏定高等学堂章程》中“第一类学科”的课程设置规定而成 (个别名目略有变化)。①罗振玉:《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报告书·江西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时间不详,《学部官报》总第34期,“京外学务报告”,288B-289A页。《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570-574页)列出的“第一类学科”三学年课程包括:“人伦道德、经学大义、中国文学、心理及辩学、兵学、体操、英语、德语或法语、历史、地理、法学、理财学”,章程并要求有志入经科大学的学生加“物理、算学”两课。这样的师资规模和一整套教学授受方案显然与河南尊经、湖南达材等学堂迥异其趣。
唯《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规定的“第一类学科为预备入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商科等大学者治之”,并非专意为保存国粹而设,学员也不是仅以经、文两科大学为升学之阶。②张之洞等:《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570-574页。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的三年学程中,“经学大义”、“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史”三门的课时钟点数仅占总课时数的约20%,前两门为“通习课”,“历史”虽为“主课”,但“中国史”仅开设一年,其余两年皆授“外国史”。学部饬令湖南达材学堂“先行补习普通 [课程],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讲授”,实是有意将其完全纳入《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序列中。这使江西明经学堂面临两难局面:《奏定学堂章程》拟订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已相当饱满。③《 奏定学堂章程》(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291-339页)规定初等小学堂每周30学时,自高等小学堂至高等学堂,每周皆为36学时。若完全按照学部要求办理,则学员前三学年俨然已和就读于“高等学堂第一类学科”的新式读书人没有什么不同,谈不上以研习中学为主旨;若坚持“保存国粹”的初衷,则很难得到学部认可。江西方面决定明经学堂“一切学科程度按照定章高等学堂第一类讲授,并先行补习普通”课程,唯因“学堂取义显揭明经”,故“增入讲经一门”而未及其余中学科目,这几乎是最大限度向《奏定学堂章程》倾斜以避免学部批驳的做法,其“保存国粹”的办学原意已大打折扣。
不过,学部审核明经学堂章程时发现,“补习普通”学程的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较奏章仍多有“缺陷”。该学程实际仅一年,总计1200课时,尚不足《奏定中学堂章程》规定的“普通学”课时数的三分之一。学生如此“补习”,“于普通各学万难毕业”。其“算学”课程“于补习时并未及几何、三角,而正科第一年遽语以解析几何,学者何能领悟”?如果在一年补习学程中“加入几何、三角二门,则既有算学,又有代数,以一年二百四十点钟平均计算,每门才六十点钟,仅两月之程度,所得有几”?此外,该校声明“注重大学分科第一类之经学、政法、文学等科”,实际却并未照章开设“法制理财”课。以上各条若通通照章办理,则“各门补习期限至少须延长为三年,庶几程度相合”。〔24〕罗振玉在“调查”后明确表示,该校虽“意在保存国粹,用意至善,但经学渊源即夙有根柢者亦不能于三四年中遽能养成专家,况在堂更须修普通学科,则养成经学专家更无可望”。也即是说,明经学堂在《奏定学堂章程》内兼顾普通学科的“养成经学专家”方案根本不具有现实的可行性。④罗振玉:《奏派调查江西学务员报告书·江西明经学堂调查总表》,时间不详,《学部官报》总第34期,“京外学务报告”,288B-289A页。罗振玉曾在光绪三十三年八月私下向刚刚奉旨主管学部的张之洞提出“国学浩博”,湖北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恐成效难期”,得到张氏的“首肯”。可知即便是七年学制且“专力中学”的湖北存古学堂,罗、张二人仍担心其存在“国学浩博”与“年限至短”间的矛盾。罗振玉:《集蓼编 (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73年,21页。
按“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济”(张之洞《劝学篇》中语)的确是困扰清季“新教育”的一大难题。张之洞倡设存古学堂是因“各学堂经史汉文所讲太略”。〔25〕唯“各学堂经史汉文功课”所以会“晷刻有限,所讲太略”,归根到底是《奏定学堂章程》更多向西学课程倾斜,中学课程受到相当程度的挤压。在总课时相当饱满的情形下,兴办保存国粹的学堂势必需要突破《奏定学堂章程》以西学为重心的课程配置取向。故张之洞明确提出,《奏定学堂章程》“务在开发国民普通知识,故国文及中国旧学钟点不能过多。此次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于普通各门止须习其要端,知其梗概,故普通实业各事钟点亦不便过多,以免多占晷刻。两法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①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1762-1766页。实际上尽管湖北存古学堂的西学通习课已被精简压缩到相当程度,但该校仍然出现“钟点已多,讲堂已满”的问题。故张氏虽然认为“洋文为将来考究西籍之基,为用尤大”,但只能在存古学堂附近设“外国语文学堂一所”,准许学有余力的存古学生“附入该学堂,自行兼习”。这可能是该校与前文所述豫、湘、赣等省办学努力的根本区别所在:张之洞将存古学堂定位在“新教育”体系中而又独立于《奏定学堂章程》规划的学制外,二者是“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的关系。而河南尊经、湖南景贤、江西明经等校则竭力将科举停废与《奏定学堂章程》相联结,试图在《奏定学堂章程》的规章内既安排科举停废后的“善后举措”,又“彰存古之义”,且明显以前者为重。②袁世凯、张之洞等在《立停科举折》(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530-533页)中提出科举停废后应“尊经学”、“崇品行”,皆是指各省办“新教育”时要“注意”并“认真遵办”《奏定学堂章程》中有关“尊经学”、“崇品行”的内容,实际并未将“保存国粹”与宽筹“旧学应举之寒儒”的出路联结在一起。折中更特别声明,已入学堂者不准参加废科举后保留的优拔贡考试,意在强调这些考试与“新教育”的界域,防止其对“新教育”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善后措施”在实际运作中,却事与愿违,对“新学界”产生相当大的冲击,详另文。
进而言之,前文所述还涉及到清季保存国粹办学努力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清季“新教育”中的存古学堂与传统书院最核心的区别究竟是什么?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即便将西学纳入教学或考试范围,仍与当时通常的“学堂办法”“判然不同”。而存古学堂即便将西学课程精简压缩到相当程度,甚至完全没有西学课程,也可与其它新式学堂“无异,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③张之洞在光绪三十三年夏主管学部后与罗振玉的私下谈话中说,此前所拟存古学堂课程,若“不加科学 [课程],恐遭部驳”,并对罗氏提出的兴办“略如以前书院”的“国学馆”计划赞许有加,甚至允诺“当谋奏行”,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张氏或许未必将存古学堂视作最佳的保存国粹办学方案,至少是可以接受一个“不加科学[课程]”的存古学堂。罗振玉:《集蓼编 (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21页。这可能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是否以及在何等程度上接纳西学或非存古学堂区别于传统书院 (尤其晚清不少书院旨在“讲求实学”且已不怎么排斥西学)的核心标识。张氏自倡设存古学堂之初即强调该校要加强对学生的管理,以新式学堂在“管理”方面的长处克服“旧日书院积习”。湖北存古学堂从开办预案到实际运作皆没有完全否定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 (尤其是张之洞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整体上看,该校力图在“新教育”内探寻一条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国学传习之路。这样的尝试或未必成功,但在那个激进趋新的时代,可能较本文所述豫、湘、赣三省的办学努力更易被接受且更具可行性 (详另文)。④实际上即便是存古学堂,仍然被不少时人质疑和批评,甚至被塑造成“迂腐庸陋”、“窒塞新机”的“形象”。详郭书愚《清季在野一方对以官办学堂保存国粹的反应》,《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6期,154-161页;《“新旧交哄的激进时代”:以张之洞和存古学堂的“守旧”形象为例》,《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44-54页。
当然,传统书院在晚清的演进及其与“新教育”的内在关联是一幅精彩纷呈的复杂历史图景。清季时人言说中的“书院”也多有其特定所指,或不宜一概而论。即或是同一人在不同场合所言“书院”,也有可能是意指完全不同的面相。张之洞在《创立存古学堂折》中说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而在私下晤谈时对罗振玉提出的“略如以前书院”的兴办“国学馆”方案赞许有加,即是明证。⑤罗振玉提出,“各省宜设国学馆一所,内分三部,一图书馆,二博物馆,三研究所。因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研究所”应“选国学有根柢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诸生有著作,由馆长移送当省提学司,申督抚送部。果系学术精深,征部面试。其宿学久知名者,即不必招试,由部奏奖”。罗振玉:《集蓼编(雪堂自述)》,《罗雪堂先生全集》,第5编第1册,21页。依循“从细节入手认识整体”的思路,尽量落实到具体的人和事进行史实重建,相关问题尚有相当宽广的研究空间。
〔1〕〔3〕〔20〕〔23〕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 (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九日)〔A〕.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M〕.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1762-1766.
〔2〕袁世凯,张之洞,等.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四日)〔A〕.璩鑫圭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Z〕.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530-533.
〔4〕罗志田.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其观念异同〔J〕.近代史研究,2001,(2):75-76.
〔5〕关晓红.晚清学部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186.
〔6〕冯锡仁,等.湘绅请建岳麓爱礼堂公呈 (时间不详)〔J〕.湖南官报,第863号 (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一日):“专件”41A-B.
〔7〕前署湖南巡抚陆奏湘绅建立岳麓景贤堂片 (时间不详)〔J〕.东方杂志,第2卷第4期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教育”69-71.
〔8〕学部.湘省学堂与定章歧异奏请改正折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J〕.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28-130.
〔9〕无作者.禀设存古学堂批词 (江西)〔N〕.申报,光绪三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第1张第3版).
〔10〕〔24〕学部.咨覆赣抚明经学堂学生应请转饬拨入师范学堂肄业文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J〕.学部官报,总第26期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一日):“文牍”313A-320B.
〔11〕无作者.学使饬裁明经学堂 (江西)〔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五日 (第2张第11版).
〔12〕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光绪三十三年下学期一览表〔Z〕.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光绪三十四年上学期一览表〔Z〕.湖南省官立达材存古学堂宣统元年上学期一览表〔Z〕.时间皆不详,晚清学部档案〔Z〕.台北:“国史馆”藏.目录号195,案卷号141.
〔13〕吴庆坻.详覆抚部院遵议湖南九年筹备事宜请咨部立案文 (并表折)(宣统元年八月)〔J〕.湖南教育官报,总第11期 (出版日期残):“文牍”29A-B.
〔14〕无作者.投考法政之踊跃 (长沙)〔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八日 (第2张第11版);无作者.景贤法政学堂开学 (长沙)〔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三日 (第2张第11版).
〔15〕无作者.成德法政学堂开学 (长沙)〔N〕.申报,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2张第12版).
〔16〕孔祥霖.详覆抚院遵议辉县戴令宗喆禀请广设存古学堂文 (院批附)(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二日)〔J〕.河南教育官报,宣统元年总第45期 (宣统元年六月一日):“文牍”368B-372A.
〔17〕孔祥霖.详报学部宣统二年本省办理学务情形拟具重要大概事宜折呈请示文 (折附)(宣统三年四月十九日)〔J〕.河南教育官报,宣统三年总第89期 (出版日期残):“文牍”755A-761A.
〔18〕〔19〕鄂督张设立存古学堂札〔J〕.湖南官报,第891号 (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九日):“时政录要”33A-34B.
〔21〕张之洞.致江宁缪筱珊太史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三日)〔A〕.苑书义等编.张之洞全集〔M〕.9665;张之洞.致苏州曹叔彦中翰即元弼 (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发)〔Z〕.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档案〔Z〕.甲182-419.
〔22〕学部.湘省学堂与定章歧异奏请改正折 (光绪三十二年三月一日)〔J〕.东方杂志,第3卷第6期 (光绪三十二年七月):128-130.
〔25〕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184,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