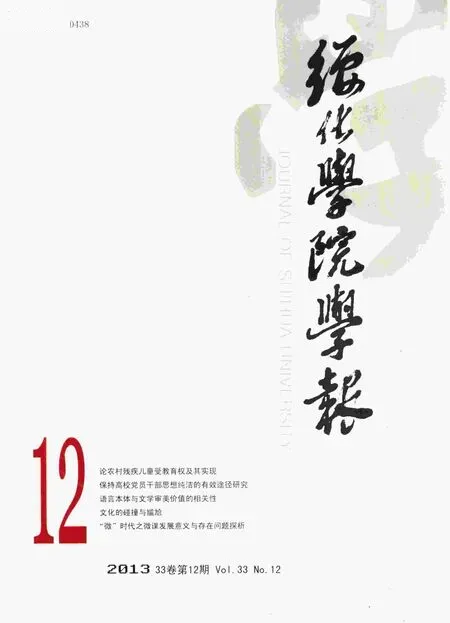浅析曹雪芹与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苏瑞琴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两千年以来,中国女性一直在各种不合理的社会规范和束缚下,悲惨地过着自己的一生。女性无法获得经济上的独立,因而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更意识不到自身的独立价值,她们心中的意识即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生活。
在这样一种窘迫的环境中,文学作为反映社会的载体,古代文学中的作品很少能有人从女性的角度去认识社会,去体验属于女性自已的生活;大部分作品中的女性都是男性统治下的温顺“羔羊”,仅为男权社会中的点缀而生存。《红楼梦》却突破了这点,它对于两性关系的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大观园中的女性不再是荣宁两府的点缀,她们用自身的美丽反衬着男性文化的衰退,作为主角的她们首次展现了自己悲伤却美丽的人格。《红楼梦》一句“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就将其中的女性意识完整体现。
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权运动日趋高涨。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张爱玲成为一个具有明确女性意识的作家。这位宣称《红楼梦》是她“一切的源泉”的女作家,继承和发展了渗透其间的女性意识,并把女性意识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女性悲剧的心证意证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开宗明义:此书是“使闺阁昭传”之作。他没有着力描写家族荣辱与时代浮沉,只是在写“花招绣带,柳拂春风”的大观园中的闺阁琐事。他着力开掘女性的自然美、诗意美,怀着理解同情之心写所有的女性。尽管如此,结局仍是“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即美丽的灵魂消逝。
张爱玲,这个早慧的乱世才女,秉承《红楼梦》的传统,以女性为主角,用悲凉的笔调描绘着她们颓败的人生,描绘着渗透其间的种种无奈与无可挽回的失望。张爱玲延续着曹雪芹“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剧故事,书写着女性人生的永恒悲剧。
不同的时代,相似的身世,是张爱玲继承曹雪芹悲剧意识的原因。张爱玲曹雪芹都有着贵族的血统,出生于显赫的家族,亦同样的衰败。荣华无常,功业易逝,他二人同有感悟。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屡屡感慨“生于末世”,张爱玲亦哀叹“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是要成为过去”[1](P135)。个人的经历让她困惑,让她哀叹,且让她由哀叹个体命运上升到感怀“乱世”的悲凉。
正因为如此,女性作家张爱玲对于红楼梦的女性悲剧有特别的感悟,可谓“心证意证,斯可云证”。《红楼梦》中女性悲剧在于女性的自然美被封建伦理道德异化,诗意美被世俗化,纯真美被污染。以男性为主的社会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标准,像盐溶于水一样无声无息地渗透到女性生活的每个角落。红楼梦中大多数女性,无论是主子还是奴才,无论有棱角,有叛逆性的,还是温顺和善,顺应世俗安排的,“无不与痛苦相始终”[2](P3)。张爱玲正是在这种深沉悲剧意蕴中构画着同样的女性悲剧世界。
在《经楼梦》和张爱玲作品中有众多身份地位经历性格不同的女性。贾府有个老太太,张爱玲小说里也白老太、姜老太、匡老太……她们时日不多,在不多的时日里她们主要的生活就是媳妇来请安,儿子来盘算自己剩余的钱;之外,就只有回忆。她们似乎被尊敬的活着,却又一无所有,只余寂寞,直至生命的消逝。
贾府有王熙凤王夫人这样壮年的太太和奶奶,在曹雪芹眼里只要进入男性世界的女子就会受到男人的污染,就会失去她们的自然纯真之美。张小说里亦有壮年的太太和奶奶,依附于男人,渴望情感,可是哪一位的情感不是千疮百孔呢?俊俏的郑太太一辈子都在生孩子,从一毛头到七毛头,生命的过程就是单调的繁衍传宗接代过程,唯一的支撑点就是选女婿,“那是她死灰的生命中的一星微红的炭火。”[3](P136)借这一点炭火的温暖来弥补无爱的生活。梁太太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嫁给一个年逾耳顺的富人做小,嫁给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等他死。“他死了,可是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4](P36-37)她为了“补偿”,毒害了一个又一个的女孩替她“抓牢”男人。后来,在与世隔绝的“皇陵”生活中,她被时代抛却与忘怀了。
曹雪芹歌颂着贾府里那些天真美好的年轻女孩子,她们的青春自然、诗意、纯真,是贾宝玉心中的至宝,但这些女子仍然摆脱不了失去珍贵品质,最终被社会世俗化的悲剧。在张的小说里,“青春是不稀罕的,她们有的是青春……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5]。白流苏离婚,是因为终于认识到了这点,所以决定走出去,想要争取一些真正有意义的东西。但结局是因为一次战争,一座城市的陷落,她赢得了一辈子的名份。此时的名份,这样一个结局,却依旧惆怅和苍凉。纯洁而有个性的葛薇龙最终成了交际花。“人生中一切厚实的,靠得住的东西”[4](P36-37)都不复存在了,她已经没有希望,未来只荒凉恐怖。其他女子的结局形式不同,实质相同。她们期望的幸福从未到来。张爱玲仿佛在永远验证着女性的悲剧,幸福和指望都是虚妄,寂寞才是永恒的。
《红楼梦》之所以持久地震撼着读者的心灵,原因之一就在于它的悲剧性,在于它是“悲剧中之悲剧”。张爱玲自觉继承发扬了曹雪芹表现女性悲剧命运的传统。张爱玲经历的时代,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正被“五四”革命扫荡,新生活新文明尚未最后形成,她笔下的女性,和大势已去的旧时代一起浸泡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悲剧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成为《红楼梦》与张爱玲创作的共同精神理念。
二、女性悲剧的内因外因
曹雪芹和张爱玲都从生活中看到女性的悲剧命运,看到在传统伦理道德下的女性过着怎样悲惨的生活。他们意识到这种不幸命运的必然与无奈,也意识到这种生活逻辑的不合理;与此同时,他们又从不同的立场与倾向上反映这一必然的不合理性。
《红楼梦》里的女性有皇妃有夫人小姐有丫环,曹雪芹用心刻画的是她们的美好。她们的诗意美,写诗作画,赋琴葬花;她们的自然美,嬉戏游玩,不为世俗所纷扰;她们或绰约婉丽,或飘逸淡雅,或才情卓异,或志行超群,无不个性鲜明风姿各异。作者以“凡日月山川之精秀,只钟于女子,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的观点,描写了这个女儿国欣欣向荣、百花盛开的春景。事实上,几千年的中同封建文化早已将女性为男性文化所同化,只是曹雪芹尽可能用美,用温情脉脉的面纱去遮饰现实中女性的缺陷。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世界亦十分丰富,笔锋却与曹雪芹偏多褒扬之情不同。她小说中的七巧丧夫了母性,小寒的爱有些畸形,梁太太极端的物质主义,流苏丧失自尊而得来的婚姻保障,……她以敏锐的眼光去剖析女性,揭示出因女性自身的缺陷而造成的种种不幸。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不再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的完美亮丽,而是挣扎于黑暗现实并终究被黑暗吞噬。
两者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最主要的原因是男性视角和女性视角的不同。作为一位男性作家,总与女性世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距离之外关注着女性的生活。他以局外人的立场宽恕谅解着女性被同化后的污点,始终同情和关爱着她们善良美丽的一面,并把女性悲剧的成因归结为外因,是这个以男权为主的社会让女性失去本有的美丽,并试图籍此来折射男性世界的虚伪与污浊,投射出男性面的临种种矛盾。作为本是女性的张爱玲,更易于用一种挑剔的眼光去关注女性,去揭示女性自身现状的弱点,她以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来深刻揭露女性本质的失落,她将矛头直指女性自身的沉沦与混沌。正是基于此种看待女性世界角度的不同,导致他们创作倾向的不同。
曹雪芹笔下的女儿们具有美丽的神性光辉,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美丽早已不复存在。曹对女性充满了怜悯,怜悯她们生活在男权中心意识统治下的社会,感伤其生存处境的艰难而卑下。张亦深知这是女性悲剧的外因,但更令她痛心的是女人自己的顺从与软弱。“女人当初之所以被征服,成为父系宗法社会的奴隶,是因为体力比不上男子。但男子的体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不曾为禽兽所征服呢?可见得单怪别人是不行的”[5](P68)。张爱玲作为一名女性,清楚地知道外因是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内因,是女性自愿附庸于男性,从属于男性,不坚持自己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存在的价值,因而被男性奴化,被社会异化。在这样一种深刻自省的女性意识的关照下,张爱玲对女性命运,对女性生存境况有更清醒的认识。女性若不知晓自己独立的生命价值,于这滚滚红尘中有的只能是永恒的悲凉。她通过小说,通过那些不幸且安于不幸不思改变的女子,来对痛苦拷问女性的灵魂,深反思长期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批判着生活在现代却依然保留着传统封建伦理道德的女性。
《传奇》中女性有大家闺秀,受过西洋化教育的知识女性如白流苏;有小家碧玉,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属于小市民女性如曹七巧;有以追求爱情为目的如葛薇龙;有以获得经济利益为主的如淳于凤;有只想拥有一个正式婚姻的如霓喜。尽管家庭出身、教育程度、生活背景和生活经历都各有所异,她们的灵魂却被只能依附于男人这样的奴性意识所束缚。近代社会女奴时代已经结束,女权运动正在兴起,但她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她们仍一如既往地生活在传统的甘为男性附庸的卑微生活中,仍然将全部的心思放在男性身上。女性自我的生命没有希望、没有光亮、没有前途。
女性自我的价值是什么?张爱玲在《谈女人》中曾明确表述:“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男子偏于某一方面的发展,而女人是最普遍的,基本的,代表四季循环,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女人把人类飞越太空的灵智拴在踏实的根柱上……超人是男性的,神却带有女性的成分。超人与神不同。超人是进取的,是一种生存目标。神是广大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5](P71)女人独立的存在价值即一种具有神的同情慈悲、了解、安息等特点的女性原则。有这些原则的女子,对生命充满赞美,对真正的爱无限向往,且对人世悲凉有着广博的同情与慈悲,代表着生生不息、绵绵不绝、坚强独立的自然母性。这才是真正健康的女人,这样的女子才能促进两性关系的健康和谐。
然而现实中,传统男权文化结构中的女性失去了这样的健康,两性关系也在这种迷失中失去了应有的色彩,依附男性成为一个女人存在的全部意义。因此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将男人比喻为太阳,将女人比喻为月亮,这成为两性关系固有的模式。“张爱玲却以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对‘太阳和月亮’这一传统的两性关系模式做出否定性的审美价值判断。”[6](P132)在《霸王别姬》中,虞姬这一形象正是如此。张爱玲借虞姬说出了自己对女性生存境况的认识:“十余年来,她以他的壮志为她的壮志,她以他的胜利为她的胜利,他的痛苦为她的痛苦。”这样一种依附地位,让虞姬痛苦,于是小说中虞姬“开始想起她个人的事”,于是她选择了自刎,并在逝去的一刻说“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通过姬别霸王这一绝决的情节,张爱玲表明了女性渴望自由独立的生存意识;也向所有女性发出了呼声:“我比较喜欢这样的收梢”,我选择过我自己的生活。
“‘饮食男女’被古礼推重是因为这两项活动都是建立在伦常基础之上的‘人之大欲’,非‘饮食’不足以续命,非‘男女’不足以繁衍。”[7]在《红楼梦》和张爱玲的世界里,女性无疑象征着整个民族文化的精魂。她们作为男性文化的对立面,受害者,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色彩。曹雪芹期冀用一方净土——“大观园”来保护这些拥有真性情的女儿们,期冀能在传统封建道德文化之中保存一些灵性;然而“幽微灵秀地,无可奈何天”,显示了女性悲剧的必然与无奈。他将一切罪源归于男性文化,批判的矛头直指封建传统道德。张爱玲虽同样批判传统伦理,但她深知一切的罪源在现代社会中已失去了原有的力量,更重要的是残留的已习惯的奴性意识让女性世界最终只能绝望。曹雪芹呼唤社会的觉醒,张爱玲则渴望女性的觉醒,他们用女性的悲剧——“千红一哭,万艳同悲”警醒着所有女性的心灵。
[1]张爱玲.《传奇》再版序[A].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2][清]王国维.《红楼梦》评论[A].姚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上部[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
[3]张爱玲.花凋[A].金宏达,于青编.张爱玲文集:第一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136.
[4]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二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5]张爱玲.谈女人[A].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6]姜欣.论张爱玲文学创作中的女性意识[J].云南社会科学,2005(6).
[7]高方.《左传》婚恋叙事与春秋文化精神[J].求是学刊,20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