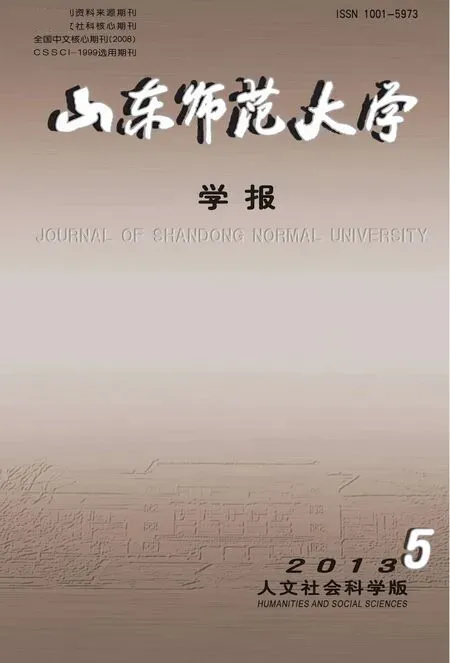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的中国意义*①
张宇飞
( 山东省政府 研究室, 山东 济南,250011 )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的中国意义*①
张宇飞
( 山东省政府 研究室, 山东 济南,250011 )
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以宪法的原初意图或者原初含义作为解释标准,旨在维护人民主权、多数民主、宪法权威以及司法克制等传统价值。中国特有的人大释宪体制与原旨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种释宪体制缩短了解释者与文本作者的“社会距离”,在探求宪法原意方面具有天然优势,而且我国的宪政框架之内对人民主权原则的推崇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宪政体制并不存在对民主不信任的西方式难题。实践中,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及宪法性法律的解释也表明,原旨主义背后的理论基础与人大释宪体制契合更为紧密。
原旨主义;人大释宪;司法审查;宪法解释方法
作为一种以制宪者意图或宪法原意为标准的解释方法,原旨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宪法解释实践与理论中都存在并发展着,特别是在美国司法审查实践与理论中,原旨主义更是一个无法绕开的议题。这一域外发展起来的理论与方法在特定宪法审查制度下蕴含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我国人大释宪制度下,原旨主义是否仍然凝聚着诸多宪法适用的理论价值,是否仍有借鉴价值与发展空间,是本文重点探讨的问题。
一、中国宪法解释体制的特点
从世界范围来看,宪法审查体制以司法审查模式为主,在这一模式下,由司法机关进行违宪审查并解释宪法。有人统计了194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其中有173个国家宪法规定了不同形式的宪法审查制度*该学者将所有类型的宪法审查制度都统一称之为司法审查,笔者对此并不赞同。尽管大多数宪法审查模式是以某种司法形式进行的,但是如果将其都一概称之为司法审查,显然其预设的前提已经决定了研究的结论。参见张千帆:《从宪法到宪政——司法审查制度比较研究》,《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1期。,在这173个国家中,采取司法审查模式的——包括普通法院审查与专门法院审查(如德国宪法法院)——国家有144个,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另一份统计尽管对宪法审查的分类标准不同,但也大致印证前一统计的客观性:在被统计的179个国家中,普通法院模式的宪法审查机制占据45%,宪法法院模式的宪法审查机制占32%,宪法委员会模式占7%。*林来梵主编:《宪法审查的原理与技术》,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年,第6页。在司法审查模式下,宪法解释类似于法律解释,由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结合案件争议解释宪法条款的含义,这种模式下的宪法解释是一项较为纯粹的法律技艺演练。
我国宪法确立了与众不同的宪法审查体制以及依附其上的宪法解释机制。1954年宪法和1975年宪法并未就宪法解释权的归属作出明确规定。1978年宪法在第25条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规定中,首次明确将解释宪法的权力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第67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仔细对比两部宪法关于宪法解释权的规定,仍存在细微区别。1978年宪法第2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三)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而现行宪法第67条则是这样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下列职权:(一)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四)解释法律……”两部宪法关于宪法解释规定的区别在于:其一,1978年宪法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并列规定,而1982年宪法则将二者分开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一变化反映了对宪法解释性质认识的变化,即它同法律解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地方,不宜并列一起规定。其二,1978年宪法中,解释宪法位列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的第三项,而1982年宪法则将其提至第一项,足见对宪法解释与宪法监督的重视。在1982年宪法起草之前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曾确定了九大类重点修改与讨论的题目,其中就包括如何保障宪法的实施,以吸取文革十年宪法权威荡然无存给社会造成巨大破坏的教训,在修改过程中曾提出设立宪法委员会的方案。从公布的资料来看,尚无从获知1982年宪法修改时对宪法解释的准确看法,但是从条文规定来看,将宪法解释与监督宪法实施并列规定,与1978年宪法呈现较为明显差异,可见宪法解释已经引起修宪者的注意。
宪法第67条是关于宪法解释的唯一规定,它主要解决了宪法解释权的归属问题。有关宪法解释程序的规定则蕴含在立法法第90条、第91条之中。根据这两条的规定,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要求,由常委会工作机构分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其他国家机关和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以及公民认为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同宪法或者法律相抵触的,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进行审查的建议,由常委会工作机构进行研究,必要时,送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查、提出意见。这一过程中,对法规的合宪性审查必然会涉及宪法解释的问题,因此这一规定也可视为宪法解释的启动程序,尽管尚不够完善。
以上规定构成了我国宪法解释的基本制度。从宪法以及立法法有关规定看,我国宪法解释体制具有以下基本特点:
第一,我国宪法解释属于抽象解释。这一特点既不同于司法审查模式下的具体解释,也不同于宪法法院与宪法委员会模式下的抽象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最高权力机关的常设机构,它既不是纯粹的立法机构,更不具备司法机构特征,人大常委会对宪法进行解释是一种纯粹的抽象解释,与具体案件无关。宪法解释一经做出便具有普遍效力,这与普通法院模式下宪法解释的个案效力不同。不论是司法审查制度下那种因具体案件而启动宪法解释又终于具体案件的解释进路,还是德国宪法法院体制下既可以进行具体解释也可以进行抽象解释的模式,都与我国宪法解释体制完全不同。即使是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也与我国宪法解释体制大相径庭。有不少学者认为法国宪法委员会模式与我国最为接近,在设计我国宪法审查制度时多主张以其为蓝本,甚至1982年修宪时也曾考虑过设置宪法委员会。但是,这实际上是对宪法委员会模式的误读。法国宪法委员会被认为是“一门对准议会的大炮”,控制议会及其立法的目的显而易见,尽管它兼具政治机关与司法机关两种性质,但是不论从其组成人员来看还是从其职权以及决定的效力来看,更多人倾向于认为它是一种司法审判机关。*朱国斌:《法国的宪法监督与宪法诉讼制度——法国宪法第七章解析》,《比较法研究》1996年第3期。尤其是2008年法国宪法修改之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在2008年之前,根据法国宪法的规定,各法律公布之前,可以由共和国总统、总理、国民议会议长、60名国民议会议员或60名参议院议员,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这是一种典型的抽象审查,也是一种事前审查机制。而2008年宪法修改拓宽了提请审查的渠道,在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当某一条款明显侵犯宪法保障的权利和自由时,公民可以提出异议,并交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进行审查,如果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可提请宪法委员会审查。这实际上赋予普通公民提起违宪审查的权利,只不过这一请求须经由最高行政法院或最高法院提请。从宪法解释的角度而言,尽管仍属于一种抽象解释,但是这种抽象解释却是源于具体案件,在解释宪法过程中不可能不考虑所审查条款的具体争议背景。法国宪法委员会在宪法解释过程中遵循的解释规则或者原则也显现了它的司法性质,例如“明显判断错误原则”、“合宪性推定原则”等等*方建中:《论法国宪法审查中的谦抑技术》,《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这些因素都使得法国宪法的抽象解释实际上是一种司法的抽象解释。
第二,人大释宪模式下解释者与文本作者具有高度同一性。之所以采用“解释者”、“作者”这样的表述是为了避免陷入关于制宪权主体、制宪机关、制宪者、宪法批准机关等诸多概念的纷争之中。1954年宪法是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在之前的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制定宪法的决议,决定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而此后宪法的修改都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所以有学者指出:“从宪政实践和宪法的原理上讲,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制宪机关的地位是十分明确的。”*韩大元、林来梵、郑贤君:《宪法学专题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11页。从实践来看,全国人大实际行使着制宪权与修宪权应无异议。根据宪法规定,我国宪法解释主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尽管宪法没有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明确赋予全国人大,但是基于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关系,以及全国人大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权性质,全国人大实际上享有宪法解释权也行得通,而且,宪法还规定了全国人大有权改变或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决定的权力,实际上这已经暗含着宪法解释的权力,因为不适当决定当然包括违反宪法的决定,而判断是否违宪则需要宪法解释。所以,从这一层面来看,如果宪法解释机关是全国人大,而制宪机关也是全国人大,那么宪法解释者与宪法文本作者就合二为一。*当然,这种同一性并不是指物理意义上的同一性,即完全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群人。这样的同一性既不可能实现也没有意义,只要制宪一代人逝去,就永无同一性而言。以此来质疑同一性的判断,本身就是个伪问题。退一步而言,即使否认全国人大的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为其常设机构与全国人大之间也具有高度的同一性,不仅在人员上有部分重合,而且在历次宪法修改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实际上也参与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所以,在人大释宪模式下,解释者与文本作者之间具有高度同一性——如果不能说完全同一的话。这一点与其他国家的释宪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不论是美国模式、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释宪者毫无例外地都不同于宪法文本的作者或者制宪者。释宪者与制宪者的分离,根本原因在于宪法解释也即宪法适用,而适用宪法的权力通常都交由一个中立的、独立的机构来行使。即使是英国这样一个坚持议会主权的不成文宪法国家,也于2009年10月1日成立最高法院,实现司法权与立法权的分离,这一分离的结果就是法院从议会手中分走最终的司法权(当然就包括法律解释的权力)。
第三,人大释宪是一种政治行为而非法律行为。法律当然不可能独立于政治体系之外,但是现代法律之所以称得上现代就在于它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形成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法律行为建立并主要运行在法律共同体内部,共同体成员分享一套专门化的价值、知识与技能。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一共同体存在一定的知识壁垒和准入门槛。因此,法律行为不仅是由专门人员操持,而且还具有一套特定的程序、方法与技术,这种行为的全部目标如拉伦茨所言“是发掘规范内的一体性及其一贯的意义关联,另一目标则是针对不同的案件情境将规范具体化”*[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20页。。人大释宪具有典型的政治而非法律性质。由一个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解释宪法,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由责任制之中的政治官员而非独立、中立的司法官员*这并非预设了宪法解释的司法审查模式。不论是普通法院法官、宪法法院法官还是宪法委员会委员,本质上都是一种司法官员。解释宪法,至少就目前情形来看,他们并不具有共同的、专业化的知识与经验。当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解释宪法的能力——是否具有解释能力是另外一个问题,还需要另外的逻辑与依据来判断——而是说他们解释宪法所依赖的知识与技能与司法释宪模式迥然不同。
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从根本上说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的。全国人大不仅是最高立法机关,而且还是最高权力机关,所以,从宪法对全国人大的权力配置逻辑来看,最为重大的、最为重要的权力——而不仅仅限于立法权及其有关的权力——都归属于全国人大。在这一逻辑下,修改宪法、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的权力自然归属于全国人大,之所以将解释宪法的权力明确配置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是出于技术性的考虑。因此,在这种逻辑下,解释宪法不仅甚至主要不是一种法律行为,而是一种体现最高政治权威的权力。从另一方面也可以佐证这一判断,从我国宪法解释实践来看,姑且承认存在宪法解释实践的话,主要集中于国家权力的组织、配置与运行方面,而非基本权利领域,这是有别于与西方宪法解释实践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西方国家,不论哪种宪法解释体制下,阐明宪法含义的活动都紧紧依附于解决争议、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根本目的之上。尽管宪法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权力配置与权利保障,关注权力运行领域的宪法争议当属宪法解释的份内之责,但如果宪法解释在两方面存在明显失衡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此种宪法解释的政治性多于法律性,因为政治并非以解决争议、保障权利为根本特征。此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基于职权主动做出解释,这与其他国家被动性的宪法解释有所不同。这些特点皆说明我国的人大释宪更接近政治行为而非法律行为。
二、人大释宪模式与原旨主义解释方法的契合
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在司法审查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它是克服司法审查的反多数主义倾向的重要方法,这也恰恰是原旨主义理论证立的主要论据。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之所以主张原旨主义优于其他宪法解释方法,并不在于原旨主义对宪法的理解和解释更为正确,而在于这一方法能够将法官有效控制在代表人民意志的宪法文本之内。但是如果转换至中国语境,人大释宪是否还存在类似于司法审查的“反多数主义”问题,如果不存在,那么人大释宪体制是否更倾向于选择原旨主义解释方法?或者说,人大释宪模式与原旨主义是否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关系?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由宪法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它决定了我国宪法解释体制的基本架构与特点。人大不仅是代议机关而且还是权力机关,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宪法解释职权不能被简单地等同于立法机关解释宪法的体制。在这种宪政架构下,人大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是全权性质的机关,至少从制度设计来看它被赋予了充分的信任与权威,因此,这就不同于司法审查制度下对立法的不信任。由于人大同时还是立法机关,对人大信任与尊重的逻辑的自然延伸就是对立法原意的尊重。在这种意义上而言,原旨主义在人大体制下的制度基础或许更为坚实,换言之,人大释宪体制也许更易孕育原旨主义的解释方法。
从我国宪政结构与内在机理来看,并不存在对多数主义的怀疑与警惕,恰恰相反,我国宪政模式建立在对多数主义的绝对信任基础之上。宪法构建的宪政框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居于基础地位以及最高地位的全权性机关。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而后再将一切权力赋予人民的代表机关——全国人大。也就是说,将人民手中的权力首先移转至代议机关,这是我国构建我国宪政框架的逻辑第一环;这一逻辑的第二环就是,由最高代议机关将人民整体赋予的权力进行分配,分割为立法权、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军事权等权力,并将这些权力配置于不同的机构。所以,我国宪法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其他一切价值都附属于这一价值。正如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在我国,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宪法修改草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我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内容和根本准则。”*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59页。而人民主权原则的实现途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主权的化身与象征,除了人民之外它不受任何约束,当然,这只是一个实定法意义上的判断而无关价值评判。刘少奇在1954年宪法草案报告中曾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统一地行使最高国家权力*刘少奇:《关于中华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而毛泽东则形象地把全国人大比喻为“如来佛”*1954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插话。转引自蔡定剑:《宪法精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年,第300页。。宪法不仅将最重要的权力——如宪法修改权、立法权、人事权、重大事项决定权、监督权等——全部赋予了全国人大,而且还规定了一条开放性的条款“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从而赋予全国人大一种开放性的最高权力。从宪法审查范围来看,现行宪法与有关法律实际上排除了法律和基本法律违宪的可能性。在立法法确立的法规审查体系中法律并未被纳入可以进入程序的审查范围之列,而只是确立法律之下的法规、规章的合宪性与合法性审查。之所以将法律排除在审查范围之外,背后的逻辑就在于对多数主义的信任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全国人大的最高地位。加之在实践操作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通过修改宪法或者制定、修改法律的方式以保证法律符合宪法,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与过半数通过并没有实质意义上的区别,所以有人坦言“无所谓合不合宪法”*洪世宏:《无所谓合不合宪法——论民主集中制与违宪审查制的矛盾与解决》,《中外法学》2000年第5期。另外,翟小波也持同样看法,见其所著《代议机关至上的人民宪政——我国宪法实施模式的解释性建构》,《清华法学》2007年第2期。。
所有这些都表明,从宪政架构角度而言,我国并不存在西方式的对议会民主或者多数暴政警惕的问题。相反,正是对人民主权原则的推崇以及对人大制度的信任才构建了现有的宪法审查及解释体制,人大释宪体制本身就是这种理念的逻辑展现。基于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民主的充分信任,才将宪法解释权赋予代议机关而不是其他机关,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反多数的可能性,西方语境下宪法解释的反多数主义困境在中国语境下是个伪问题。即使苛刻地认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民主基础与全国人大的民主基础不同,那么如果按照制宪意图来解释宪法的话,其主要功能也是在于保证“小民主”(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服从于“大民主”(宪法),而非“反民主”(法官解释)服从于“民主”(宪法)。
进一步而言,人大释宪模式下解释者或许更倾向于选择原旨主义解释的方法。这是因为立法者眼中的法律与法官眼中的法律并不一样。对于法官而言,法律文本是其工作的基础,法律对于法官的意义就在于它是解决纠纷的依据或者指南,正如日本学者棚濑孝雄所说:“审判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纠纷的解决。”*[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页。当一起宪法争议提交法院时,法官的任务不是像语言学家那样仅仅以探究文本含义为目标,而是必须要解决提交上来的争议,布伦南法官坦言,“不像文学批评家,法官不能仅仅品尝文本内在的模糊性,而是要必须解决它们”*William J. Brennan, JR.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temporary Ratification,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Debate Over Original Intent, ed.by Jack N. Rakov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4.。所以,以纠纷解决为导向的宪法解释常常会背离宪法原意,如果法官从制宪原意中不能获得答案或者获得的答案无法解决纠纷时,他将不得不转向其他方法来解释宪法以求得对宪法案件的圆满解决。这也是实用主义者常常持有的论调,尽管它并不为实证主义者赞赏,但也的确是事实。而对于立法者而言,法律是其得意的作品,创作这一作品的过程就是理性建构的过程,所以,立法者思维的最大特征是理性建构与抽象归纳,编织一套抽象的法律语言体系来覆盖社会生活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人大释宪是一种抽象解释,这种抽象解释脱离了具体案件的语境,既有利也有弊,弊在于因为没有经验佐证难以发现真正的问题所在,而利在于使解释者完全投身于文本而不是具体纷争,加之如前所述的立法机关特有的理性建构与抽象思维能力,他们共同推动着解释机关更为单纯地以探究和发现文本原意为解释目标。
反过来说,不仅人大释宪模式趋向于选择原旨主义解释方法,而且原旨主义解释方法在人大释宪模式下更为有效,原因就在于人大释宪模式的特殊性之一:解释者与作者的高度同一性。原旨主义以探究制宪者原初意图或宪法文本原意为基本特征,而这一解释进路的有效性主要取决于解释者与作者之间的“社会距离”,解释者与作者越接近越有可能理解作者的意图。如果解释者能够在思想、心理、时间、空间等多个维度完全进入作者的世界,那么可以说解释者完全理解了作者意图,这也就是施莱尔马赫所谓的“重建作品的心理世界”。当然,在伽达默尔看来解释并不是要重建作者心理,但是他也承认,只有当读者的现时视阈与文本的历史视阈实现“视阈融合”时才能产生真正的理解。人大释宪模式最大程度促成了这种融合,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并不是制宪机关。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常设机关的实质就是代理机关,由于全国人大会议结束后无法履行职权,因此将部分可以委托的职权交由常委会行使,代其履行最高权力机关的某些职责。因此,从常委会的性质来看,它与全国人大具有相当程度的同一性。从实践来看,常委会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参与甚至代替了全国人大的工作,包括宪法修改。因此,如果说制宪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话,那么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是对制宪意图最为熟悉的机构,由它探究制宪意图显然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
三、两起“疑似”宪法解释例中的原旨主义
论及宪法解释实践,恐怕令很多我国学者颇为尴尬,因为直到现在,我国是否存在宪法实践仍然争论不清。在这些争论中,既有完全否认的论调,认为我国从来没有进行过宪法解释*持此观点的如王磊:《试论我国的宪法解释机构》,《中外法学》1993年第6期。又如袁吉亮:《论立法解释制度之非》,《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也有肯定的观点,认为立足于中国宪法解释体制,宪法解释实践在我国客观存在并且已有若干次解释实例。肯定论的观点也存在分歧,主要表现在对宪法解释实例范围大小的判断上,有的学者对于宪法解释实践的理解无比宽泛,不仅把对宪法而且对其他宪法性法律的解释都视作宪法解释*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是周伟教授,参见其所著《宪法解释方法与案例研究——法律询问答复的视角》第五章、第六章内容。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有的学者对宪法解释实践的认识比前者要窄狭一些并列举了有限的几例宪法解释实例。*胡锦光、徐振东“我国宪法解释实践研究”,胡锦光、王丛虎“论我国宪法解释的实践”,均载于韩大元等著:《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346页、第359页。
在有无宪法解释实践以及哪些属于宪法解释实践的问题上,共识主要集中在两起解释个案上。几乎所有承认我国存在宪法解释实践的观点,都毫无例外地将这两起或者其中一起解释个案作为例证,可以说这两起解释个案是目前宪法解释实践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因此,有必要细致分析这两起“疑似”解释例,它们是否属于宪法解释,以及原旨主义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当然两起解释个案涉及的实质内容并不属于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的焦点仍然集中在解释方法上。
(一)关于国家安全机关性质的解释
1983年9月2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安全机关行使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的决定》。这一决定普遍被视为宪法解释,有人甚至认为这是我国唯一的一次宪法解释*参见胡锦光、徐振东“我国宪法解释实践研究”,载韩大元等著:《现代宪法解释基本理论》,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年,第346页。。这一决定内容全文如下: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决定设立的国家安全机关,承担原由公安机关主管的间谍、特务案件的侦查工作,是国家公安机关的性质,因而国家安全机关可以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安机关的侦查、拘留、预审和执行逮捕的职权。
该决定还附录若干相关宪法与法律条文——宪法第37条、第40条,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38条、第39条、第41条、第58条、第73条、第86条以及第91条。
一般来说,在某一决定中附录有关宪法或法律条文旨在为决定的内容提供宪法或法律依据。但是,在这一决定中,附录的宪法条文与刑事诉讼法有关条文恰恰需要明确其含义,而不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提供依据。所以,附录宪法条文的行文方法本身就说明,全国人大常委会旨在以正文的内容来解释附录的条文的含义。至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自己来看,这一决定是解释性质而不是单纯的关于某一事项的决定。
国家安全机关是在现行宪法颁行之后设立的,因此面临着在宪法框架内的定位问题。宪法第37条明确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从这一条款的字面意思来看,并不抽象也不存在模糊之处,“非经”二字明确排除了法院、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对公民的逮捕权。而在1982年宪法修改之时国家安全机关尚未设立,因此也不可能在宪法中给予其明确的定位。这类似于美国宪法第2条第2款的规定“总统是合众国陆军、海军和征调为合众国服役的各州民兵的总司令”所面临的问题,即后来出现的空军是否受总统统率?对于这一问题解决的方式就是原旨主义解释的进路,即从制宪者意图来看应为统率武装力量,只是囿于彼时情形无法预料到空军的出现,而不可能明确列举空军。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这一决定来看,寥寥数语难以揣摩其解释进路,由于缺乏推理与说明过程,看上去更像是一个纯粹的决定或命令行为。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或者在学理上将这一决定合理化的话,原旨主义便会浮出水面。宪法第37条是关于公民人身权的条款,该条第1款宣示了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第2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第3款明确禁止非法拘禁、非法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或者非法搜查公民身体。1954年宪法的规定与现行宪法略有不同,在其第89条中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公安机关执行”并未规定在宪法之中。1975年宪法大致沿用这一规定。1978年宪法则增加了“由公安机关执行”的条件。1982年宪法沿用了1978年宪法的做法,将公安机关执行作为执行逮捕的必备条件规定下来。相较于1954年宪法关于逮捕条件的规定,现行宪法增加公安机关执行的条件使得逮捕条件更为具体。之所以如此,彭真在1982年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作了说明:“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草案中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彭真:《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王培英编:《中国宪法文献通编》,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59页。可见,从制宪意图来看,赋予公安机关执行逮捕权在于更加严格地保障公民人身自由,这一条款主要目的是否定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非法逮捕随意限制人身自由的行为,而不是界定公安机关的职权范围,制宪原意是排除公安机关之外的其他机关行使逮捕执行权,而国家安全机关履行的职权本属公安机关既有权力,并不是新创设的权力,所以并没有越过宪法所明确规定的范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第37条规定的由公安机关执行逮捕作的解释,不仅没有超越宪法原意,而且恰恰是从遵从宪法原意的角度进行的解释。尽管这一解释缺乏必要的推理与说明,但仍可视作是一次原旨主义解释方法的实际操演。
(二)关于香港基本法的解释
香港基本法实施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其共进行过四次解释,分别是1999年6月26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第4款和第24条第2款第3项的解释》;2004年4月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一第7条和附件二第3条的解释》;2005年4月27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53条第2款的解释》;2011年8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13条第1款和第19条的解释》。这几次解释都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第一次解释还引发了巨大争议,两种不同的法律解释制度、解释方法之间的差异在同一个案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甚至有人称其为“宪政危机”。
这几次解释全景式地展示了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方法,其中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立法原意”的方法。在第一次解释即关于居留权的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明确宣布香港终审法院对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不符合立法原意”,而“本解释所阐明的立法原意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其他各项的立法原意,已体现在1996年8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4条第2款的意见》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这几次解释文件中,立法原意是唯一明确表述出来的解释方法或解释标准。当然,表明这几次解释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解释方法与特点的还有其他一些材料,例如有关官员的谈话、对于解释草案的说明报告等。
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解释中颇令人回味的一个问题是,在相关解释草案的说明中可以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解释基本法时考虑多重因素,而在正式解释文件中则仅仅提及立法原意,似乎是将其作为解释的唯一权威标准。例如,在解释草案的说明中特别衡量了实际的社会利益与判决结果的关系,详细说明了有关判决的可能的结果:“据香港特区政府的调查统计表明,根据这项判决内地新增加的符合具有香港居留权资格人士,至少一百六十七万(其中第一代约六十九万人;当第一代在香港通常居住连续七年以上后,其第二代符合居留权资格的人士约九十八万)。香港特区政府的评估显示,吸纳这些内地人士将为香港带来巨大压力,香港的土地和社会资源根本无法应付大量新进入的内地人士在教育、房屋、医疗卫生、社会福利及其他方面的需要,这将严重影响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详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1999年第4期,第328页。类似的理由在该解释草案中多处可见,解释者多次表明进行如此解释“完全是为了保证内地居民有序赴港,是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的”。而在公布的正式的解释文件中,这样的说明却不见踪影,所见的只是对立法原意的强调。这一差异似乎表明,解释者在解释过程中实际考虑了诸多因素,至少立法原意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但立法原意却是唯一能够“摆得上桌面”的解释理由。
而香港终审法院在居留权案件的裁决书中阐明了解释基本法的方法:
宪法是一份具有灵活性的文件,旨在配合时代转变和适应环境的需要。解释《基本法》这样的宪法时,法院均会采用考虑立法目的这种取向,而这方法亦已被广泛接纳。……在解决这些疑难时,法院必须根据宪法本身及宪法以外的其它有关资料确定宪法所宣示的原则及目的,……同时也须按文件的背景来考虑文本的字句,而文件的背景对解释宪法性文件尤为重要。*吴嘉玲等人诉入境事务处处长,FACV000014Y/1998。判决书全文见香港司法机关官方网站:http://www.judiciary.gov.hk/tc/legal_ref/judgments.htm。
判决书显示,香港终审法院在解释基本法时更为灵活,更加强调宪法与时代、环境的适应性,并且终审法院明确提出在解释公民权利和自由时“应该采取宽松的解释”标准。这种解释方法与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文书中表明的“立法原意”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在这种分歧的背后,是采取原则导向(保护公民权利)与采取政策导向(香港繁荣稳定)之间的分歧。”*强世功:《文本、结构与立法原意——“人大释法”的法律技艺》,《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从解释体制来看,一方是司法独立价值支配下的司法解释模式,另一方则是代议机关至上体制下的立法解释模式;前者更加注重法官对法律的权威解释,而后者则强调立法原意背后的人大权威不可挑战。
正是因为基本法解释释放出重大而丰富的意义,不少学者纷纷将其视为宪法解释。不可否认,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蕴含着重要的宪政价值,并且增强了人大解释法律的技能。但需要指出的是,对基本法的解释不同于对宪法的解释。有一种颇为典型的观点是,基本法在特别行政区居于最高法律地位,属于“小宪法”,而且对其解释又涉及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宪制关系,因此基本法解释属于宪法解释。*参见郑贤君:《我国宪法解释技术的发展——评全国人大常委会99<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释法例》,《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这种观点实际上混淆了宪法解释与法律解释的界限,误将法律解释等同于宪法解释。在成文宪法国家,宪法解释的对象只能是宪法典而不是其他,将对宪法性法律的解释等同于对宪法解释的逻辑就相当于将宪法性法律等同于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于香港而言确实是“宪法”,但对于全国而言,它当然不是宪法也不是什么“小宪法”。既然如此,何来宪法解释一说?*有人将基本法视作宪法特别法,因此对基本法的解释就属于宪法解释。这种观点颇有说服力,但是宪法特别法又是一个极其模糊而又难以界定的概念。见李琦:《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性质:宪法的特别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基本法对于全国与对于香港的意义不同,香港法院解释基本法当属宪法解释,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便不是宪法解释。尽管基本法涉及中央与地方的宪制关系,但这并不能成为宪法解释的理由,几乎所有基本法律都会涉及宪法规定的重大关系,例如刑法规定的人身自由的限制和剥夺,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说刑法解释便是宪法解释。实际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的解释文件中可以看出权力机关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对基本法的四次解释中,人大常委会在解释文件中均明确宣称,根据宪法第67条第4项和基本法第158条第1款而解释基本法。宪法第67条第4项的内容恰恰是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法律”的职权,由此可见,在解释者自身来看它是在解释法律而非解释宪法。
总之,将基本法的解释视作是宪法解释实际上是一个误读。尽管它展示了丰富的法理与宪政意蕴——包括我们关注的原旨主义与非原旨主义的对立,但是从本质上而言依然是个法律解释,在这方面它并不比上一个解释例更接近宪法解释。
The Value of Method of Originalism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n China
Zhang Yufei
(Research Office, Government of Shandong Province, Jinan, Shandong 250011)
As far as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is concerned, the theory of originalism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which insists that original intention or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onstitution should be a primary standard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designed to safeguard the popular sovereignty, the majoritarian democracy, authority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raditional values such as judicial restraint. The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endemic to China is that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interprets the Constitution. Under this special system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there is an intrinsic link between this system and originalism, and the system of interpretation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shortens the “social distance” of the interpreter and the author of the text, which leads to the certain natural superiority in the search for original intent of the constitution. Furthermor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ur constitutionalism the western-style problem of distrust of democracy does not exist. The practice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and constitutional laws shows that the basic theory of originalism more fits the system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originalism;the system of Standing Committee of NPC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judicial review; method of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2013-07-10
张宇飞(1979—),男,山东济南人,山东省政府研究室研究人员,博士。
①本文系作者主持研究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原旨主义宪法解释方法研究”(10YJC820163)的阶段性成果。
DF2
A
1001-5973(2013)05-0144-09
责任编辑:寇金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