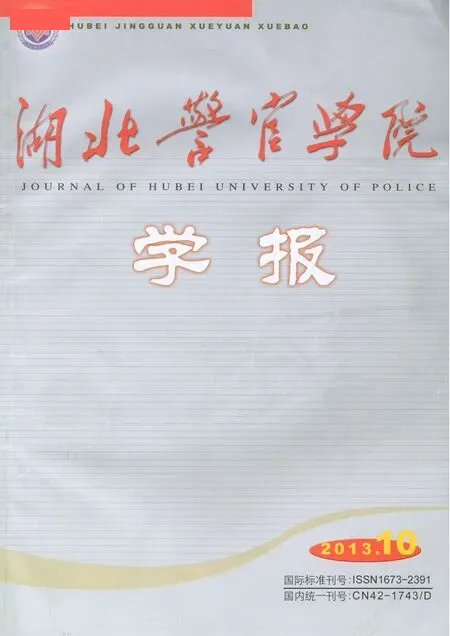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移植性探究
詹翔宇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 西安710068)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可移植性探究
詹翔宇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陕西 西安710068)
以具体的案例为切入点,从美国的政治、社会背景以及三权分立的权力结构出发,阐释美国违宪审查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在现行制度下某些问题的不可解决性,从而引发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的进一步思考,并进行解释,为何诸多国家在对美国违宪审查制度进行全面移植或部分移植后,却无法收到预期的效果。最终得出美国违宪审查制度难以移植的结论。
美国;违宪审查;移植
一、案情简介
首先简单介绍罗伊案。罗伊是德克萨斯州一个未婚先孕的母亲,她想去堕胎。但根据德克萨斯州的刑法典,除了母亲生命处于危险之中的情况,堕胎都是违法的,如果医生擅自给怀孕的妇女实施堕胎手术,也会被起诉。在一些律师的帮助下,罗伊对该法典的合宪性产生了质疑,便向德克萨斯州的联邦地区法院提起了上诉。法院认为,基于联邦宪法第九和第十四修正案,该法典确实侵犯了罗伊的隐私权,同时还存在自身的表述不清晰和管辖范围过大问题。但是,法院否决了罗伊的诉讼请求。随后,案件中所有的当事人都上诉到美国联邦第十五巡回法院,第十五巡回法院让他们直接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最后,联邦最高法院审理了本案,以7:2的票数达成了多数意见,支持了罗伊的全部请求,宣布德克萨斯州刑法典有关堕胎部分的违宪,布莱克门大法官发表了法庭意见。
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妇女有权堕胎,且妻子堕胎时可以不征得丈夫的同意,这一判决立即引起了美国整个司法体系以及社会的巨大关注,观点多种多样,褒贬不一。罗伊案判决之后,虽然妇女的堕胎权利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认可,但医院对实施堕胎仍然非常保守。判决3年之后,绝大多数公共和私立医院还没有做过一起堕胎手术;很多妇女不得不长途跋涉到外县、甚至外州,履行最高法院承诺给她们的宪法权利。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在马赫案和哈里斯案中的判决,则给了罗伊案判决执行一记响亮的耳光: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得向堕胎妇女提供医疗补助金。在1992年计划生育联盟Pennsylvania东南分部诉凯西案中,最高法院又部分地支持了Pennsylvania一项管制堕胎的法律。在这两个案件中,法院分别判决各州和公立医院没有责任为堕胎提供任何资助,也没有责任允许他们的设备被用来堕胎。最高法院的一纸判决,非但不能消除长期形成的意见分歧,而且还催生了美国社会中完全对立的两派:反对堕胎合法化的生命派和支持堕胎的选择派。争论的双方并不满足口头上的辩论,他们还竭力鼓动州议会和联邦国会出台各种禁止或允许堕胎的法律,从而使堕胎政治化。
20世纪80和90年代,保守的共和党连续执政12年,特别是所谓的“里根革命”推动了美国社会趋向保守。在这一背景下,最高法院对堕胎问题的看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经过马赫案、哈里斯案以及凯西案之后,虽然最高法院并没有推翻罗伊案确立的司法先例,但已经从其当初所持的最大限度保护妇女堕胎权的立场上后退了不少。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似乎希望减弱生命派与选择派之间的尖锐对抗。但事实上,最高法院的做法并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效果。
二、美国违宪审查的合宪性探讨
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始于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通过判决确认了法院对宪法的解释权,从而确立了美国历史上的违宪审查制度。但违宪审查制度在建立之初就遭到了许多强有力的反对,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的法官吉布森就在伊金诉罗布案中对其作出了经典的司法上的辩驳。吉布森法官首先承认宪法有可能与国会立法相矛盾,如两法相抵触,宪法当然高于立法,但不应由司法机关宣布它违宪无效。他说,如果由司法机关宣布违宪立法无效,那么“司法机关则是特殊的部门,可以修改立法,可以纠正立法机关的错误,我们在宪法的哪个条文中可以找到这种特殊地位呢?宣布一部根据宪法规定的形式制定的法律无效,这不是篡夺立法权吗?司法机关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审查立法者的权力。”其实,马歇尔大法官在马伯里案中只是解释了宪法高于其他法律,居于最高地位,关于这一点,几乎无人表示反对。但是,承认宪法高于国会通过的其他法律,并非就表示美国联邦和州的法院就有权力来行使违宪审查权,而且,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虽已确立,但是理论和实践中的司法主权问题、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对合众国宪法的解释权占有问题,至今仍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说法。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为司法审查之起源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体现的不是对个人权利的尊崇而是轻视:尽管法院承认马伯里道义上应当获得治安法官委任状,但他的权利最终还是成了法院政治考虑的牺牲品。①有美国宪法学者认为,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实际上是当时联邦党和民主共和党斗争的产物。根据当时的政治、法律环境,即便马歇尔大法官在判决中命令麦迪逊发出治安法官委任状,麦迪逊也完全可以拒不履行判决,这样只会进一步削弱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马歇尔通过认定《1789年司法条例》第13款违宪的方式来否定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初审权,将案件撤销,这样既避免了与行政权发生直接冲突,同时还确立了最高法院对宪法的最终解释权。可以说,该案判决在政治上的考量已经远超出法律救济的范畴,对当事人马伯里的权利诉求也有所忽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也并没有将保护个人权利作为其违宪审查的目的。一般来看,个人的宪法权利是稳定的,它本不因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它却没有受到法院的稳定保护。1919年的申克案和阿布拉姆斯案,1927年的惠特尼案,都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人权进行践踏的典型案例。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对于美国政治形势的屈从,不言而喻。
一般认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界限是政治问题不审查。但在1857年的斯科特案中,坦尼大法官宣布法院以7:2达成多数判决,认为曾经是奴隶而后又在自由州生活过的司考特不是美国公民,没有权利向最高法院提起诉讼,这成为了臭名昭著的错误判决。最高法院在内战前夕作出这样的判决,受到林肯总统的大肆攻击。他在1861年的就职演讲中指出,对于奴隶制这样一个关系到全体美国人民命运的重大决策不能受到最高法院的决定的永久束缚,因为如果那样的话,“人民将停止成为自己的主人,而因此将自己的权力拱手交给那个具有影响力的不可一世的法坛。”②Abraham Lincoln,First InauguralAddress(4March 1861),in Messagesand Papers,vol.7,3206-3213.而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政治问题不审查原则,也未能被之后的法官们遵守。罗斯福总统在刚开始推行新政时,新政措施屡屡遭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否决,他一怒之下转而进行“法院填塞”计划,要把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人数从9名增加到15名,这个计划虽然未在参议院通过,但最高法院却不敢再反对新政立法了。
在马伯里案中,马歇尔大法官认为,如果法院不能对国会的立法进行审查,那么议会将变成全能的上帝。但是,他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阻止议会变成全能上帝的权力就只能掌握在法院手中,而联邦宪法的制定者们,也同意将这一权力授予法院。所以,支持美国法院拥有违宪审查权的观点都建立在一个前提上,就是违宪审查权自然而且只能归于法院手中,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
三、美国违宪审查的不可移植性
从前文得知,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在运行当中,已经存在诸多问题。一项调查结果显示,1995年,当盖洛普开始调查这个问题时,投票结果是56%对33%的人支持堕胎;而现在,这条线已然被越过,51%的人宣称反对堕胎,而只有42%的人倾向于支持堕胎。从过去的个人信仰发展到法律约束,这是一个飞跃。35年来,大部分的美国人一直期望堕胎在必要的限制下合法,但是旨在产生更多限制的趋势变得显而易见。虽然美国的违宪审查制度至今仍然没有被废止,甚至运行良好,但是这些情况与美国的总统制、美国国民对宪法的尊崇,美国的历史等特殊情况息息相关。所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代替人民作出的判决,究竟具有多大的意义,而美国式违宪审查是否真的像人们宣扬的那样好,亦值得思考。那么,除了美国式违宪审查制度内在的缺陷和问题外,它不能移植到别的国家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首先,从欧洲来看,美国违宪审查的理论和实践对欧洲产生了重大影响,人民主权和三权分立为欧洲所称道。然而,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却未能在欧洲建立起来,欧洲各国大都根据其特殊国情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违宪审查制度。其中,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立法机关行使宪法监督权的模式;另一种是由专门机构行使违宪审查权的模式。英国模式的特点是,法院无权审查议会的立法。但在欧盟一体化进程加剧的今天,情况有所改变,英国也在2009年将最高法院从上议院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于议会和政府的司法机构。而第二种模式又分为以德国为代表的宪法法院制度和以法国为代表的宪法委员会制度两种。德国1949年的基本法规定了联邦宪法法院具有相当广泛的司法管辖权,有权审理的案件涵盖了抽象的法规审查制度、具体的法规审查等6个领域。法国1946年设立宪法委员会,其基本出发点是为了维护议会的优越地位,而1958年戴高乐总统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时根据宪法设立宪法委员会的基本出发点则是为了维护总统和行政机关的权力。在后来的实践中,法国宪法委员会又逐步演变为平衡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权力、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机关。
那么,为什么欧洲各国的法院都难以掌握违宪审查的权力?第一,从现实情况来看,各国的违宪审查权不是掌握在议会手中,就是掌握在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手中。以英国为例,“光荣革命”后,英国迅速确立了议会的至高地位。在这样的前提下,英国法院要像美国的法院一样,对议会通过的立法进行审查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而法、德等国家的违宪审查制度则是建立在凯尔森法律规则的等级阶梯理论之上,其渊源是凯尔森的专门机构监督说。该说认为,随着政治实践的发展,国家权力分配必然产生一定的变化,此时,需要打破国家权力的传统分类,去寻找一种新的制衡力量,即第四种力量,去负责监督前三种权力,以确保它们在宪法范围内运行。这种理论根本没有为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留下任何空间。第二,欧洲普通法院的法官无力实施违宪审查。欧洲的法官几乎都是职业法官,他们年纪轻轻就进入司法机关,大半是熬成老资历才被提升到上级法院。他们无法像美国的法官一样,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而自由判决。
另外,欧洲的意大利、比利时等国曾经实行过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然而都失败了。意大利在战后建立起宪法法院之前,曾在一段时间内采用过美国模式。违宪审查,特别是普通法院对立法的司法审查,曾在意大利讨论过很长时间,大规模的讨论和法国、德国的讨论差不多发生在同一期间。意大利是唯一一个美国模式的试验者,从最高法院1947年7月28日的判决开始,并随着1956年宪法法院的建立而终结。这试验不能说是成功的,就像卡佩莱蒂和科恩强调的那样:“普通的职业法官,特别是最高上诉法院和其它上诉法院的老年法官,在贯彻执行高度纲领化的进步主义的宪法时干得极为糟糕,因此强烈反对对反社会的或独裁主义的立法进行分类。”①Cappellettiand Cohn,Compartive Constitutional Law,p.14.总之,在制宪会议中,支持凯尔森模式的人占了上风,实施中的迟延只不过更加说明了要让美国模式适应意大利的情况是多么艰难。
其次,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也不具备完全移植美国式违宪审查的条件和土壤。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多数国家尚无法治可言,更别说建立违宪审查制度了。中国的情况与美国差异太大,国民的法治观念薄弱,法院的权威与公正性也没有树立起来。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缺乏必要的社会和法治条件。
那与美国政治经济情况类似的加拿大如何呢?加拿大于1982年加入了《权利自由宪章》,同时也引进了违宪审查制度。但是宪章只适用于公权力部门,并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加上以宪章为理由进行诉讼的成本较高,使得加拿大在对抗就业、居住、商业等领域的歧视问题上,联邦和各省的人权法案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拿大的违宪审查非常活跃,学者们认为这是因为有“不理会条款”的设计,反而使得加拿大的最高法院敢于宣告法律违宪。因为其民主正当性不足的问题,已经有“不理会条款”作为弥补,就算其解释得不好,立法机关也可以将之推翻,反而使得大法官在作违宪审查时心中没什么顾忌。由此可知,加拿大的违宪审查,与美国有着较大的差别,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加拿大联邦的最高法院不拥有随意否决国会立法的权力,最多只会作警告性裁判,对立法的效力并无影响;或者给予立法者翻案的机会,最终决定权仍在国会手中。
四、结论
由上可知,美国违宪审查制度具有不可移植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该制度本身在运行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宪法依据在哪里?在司法主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权力的界限又在哪里?当法院的判决与民意冲突,而后又不得不通过修改先例以顺应民意时,法院的形象和法律的至高无上性受到损害时,究竟是权力行使的方式不对,还是法院根本就不应该拥有这种权力呢?在美国政治斗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最高法院日益成为政治斗争的舞台,在布什诉戈尔案后,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最高法院的政治性,它的意识形态主导与个人偏好。但是,正如戈尔在2000年大选失败后说的那样,“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最高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②任东来等著:《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中存在的很多问题都消解于各种形式。然而,各种形式的消解并不能说明该制度本身不存在问题。
其次,各国社会和政治状况不同,不具备完全移植美国式违宪审查的前提和条件。正如凯尔森说的那样,违宪审查的自然本性是政治,无论法院如何将自己独立于政治之外,它都逃脱不了政治的影响,而生活在政治的阴影之下。因为其他国家很难拥有与美国相同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因此,美国式违宪审查的移植通常都会遭到强烈抵制,或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1][美]考克斯.法院与宪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2]任东来.美国宪政历程:影响美国的25个司法大案[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3][美]戴维·M.奥布莱恩.风暴眼: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M].胡晓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美]PaulBrest.宪法决策的过程:案例与材料(下册)[M].陆符嘉等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D93/97
A
1673―2391(2013)10―0019―03
2013-05-24 责任编校:江 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