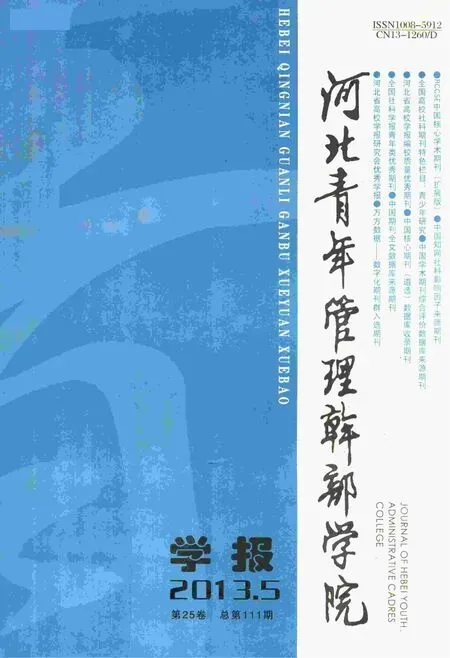“虐童”事件的刑法处遇思考
王晓芳
(中国政法大学 刑事司法学院,北京100088)
前段时间,各地频发的校园“虐童”事件引发了社会各界强大的关注,浙江温岭幼师为“取乐”将男童拎至悬空离地20厘米;山西太原一幼儿园5岁女孩因不会做题被老师狂扇70耳光;江苏南京多名儿童在幼儿园被打、戳、被迫吃厕纸;北京海淀区3岁男童被教师针扎生殖器形成刺伤;上海杨浦一幼师将芸豆塞进女童下体;浙江幼师用打火机烤烫幼儿脸部;广东广州一老师将4岁自闭症女孩吊起、摔下,折磨致其当场昏迷,等等[1]。这一系列的虐童事件令人发指,但却在现实中真实地发生着。这些事件引起了社会大众对儿童保护、学校教育、师德,尤其是法律完备问题的大讨论。法律作为规范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屏障,如何从法律角度对此类实践进行正确处理,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即是从刑法角度对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虐童”行为入刑的必要性探讨
“虐童”行为不仅对儿童的身体健康造成伤害,还严重侵犯了儿童的自尊心和人生权益,童年期受虐待经历会对其个体发展造成长期的消极影响,如自我概念和社会技能的差异、焦虑和抑郁、情感冷漠、混乱和内疚、网络成瘾、易产生攻击行为和危险行为等,更有甚者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有调查显示,中国约四成的孩子曾受到过不同形式的虐待,有4.4%受到过多种严重的虐待。挨过打的孩子男女比例分别超过一半和近三分之一,约三分之一被当众羞辱过[3]。在山东商报官博关于“是否应该设立虐童罪”调查中,新浪官博支持设立“虐童罪”的网友占96.3%,腾讯官博支持立法的网友占97.06%。网友们多用“强烈支持”、“坚决赞成”、“越快越好”等语气表达自己支持设立“虐童罪”的坚定态度[4]。基于严重的情势和强烈的民意,许多公众和学者呼吁将“虐童”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主张适用现行法律法规进行规制。对于严重的“虐童”行为,可以适用刑法中的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寻衅滋事罪处罚;对于相对轻微,没有达到触犯刑法程度的“虐童”行为,可以按照《侵权责任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行政责任[5]。(2)主张增设专门的“虐待儿童罪”。要通过完善刑事立法提高“虐童”行为的惩罚力度,针对性地对包括幼师在内的所有社会主体虐待儿童的行为进行刑法规制[6]。(3)主张扩大现有虐待罪的适用主体范围。在维持现有法律体系的前提下,通过将虐待罪主体范围扩大以解决虐待罪对“虐童”行为的规范障碍[7]。
笔者认为,鉴于“虐童”行为对社会产生的严重危害,将其在法律层面进行规制是确实必要的,但是要正确处理好“前提法”和“刑事法”之间的关系。刑法是法益保护的最后一道屏障,不宜介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能处罚其中部分严重侵犯法益的行为。刑法的补充性要求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足以抑制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禁止;只有当一般部门法不足以充分保护法益时,才需要刑法保护[8]24。首先,对于“虐童”行为的法律规制,应遵循一个“层层筛选”的过程:就相对轻微、未达到触犯刑法程度的“虐童”行为而言,完全可以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行政责任。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1条规定:“学校、幼儿园、托儿所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2、43条规定,公然侮辱他人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的人,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同时我国的《教师法》、《侵权责任法》等均对此类行为进行了规制,并规定了相应的处罚措施。现实中发生的多数“虐童”行为即可纳入民事、行政法律法规范围进行规制。其次,只有当上述民事、行政救济手段均无法完全评价“虐童”之罪责时,才可上升至刑法范畴进行探讨。
从我国现行《刑法》规范出发,严重的“虐童”行为可能涉嫌的罪名主要有:故意伤害罪、虐待罪、侮辱罪和寻衅滋事罪。下面对这些罪名是否能够适用于“虐童”行为依次进行分析:
1.故意伤害罪。教师虐童行为一般表现为罚站、拎耳朵等,往往不会造成轻伤以上的后果,更多的是给儿童造成了精神的刺激和心灵的创伤;如果造成儿童重伤、死亡的后果,即可直接按照《刑法》第234、232条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进行处罚,此处不存在什么争议。
2.虐待罪。虐待罪要求行为主体必须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即虐待人与被虐待人之间存在一定的亲属关系或者收养关系,虐童事件中的教师显然不符合此主体资格。
3.侮辱罪。侮辱罪是指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贬低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以温岭虐童事件为例,颜某的行为在性质上与侮辱极为相似,因此,有学者主张在“虐童”行为未达到被害人轻伤以上后果时应适用侮辱罪进行规制[5]。对此,笔者提出两点疑义:一是侮辱行为强调的是在公共场所“公然”地贬低他人人格,所谓公然是指采用使用让不特定或多数人可能知悉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而现实中的校园虐童案件发生在相对封闭的教室里,现场只有“虐童”教师、被虐儿童和其他旁观的儿童。“虐童”教师并没有当着外人的面实施虐待、侮辱行为,只是将相关的“虐童”照片“炫耀”式的向公众予以展示;二是侮辱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需有贬低他人人格、毁坏他人名誉的故意。但是现实中的“虐童”案件的行为人仅是出于“好玩、取乐”的目的,亦不符合侮辱罪的主观构成。
4.寻衅滋事罪。教师出于寻求精神刺激的动机,随意殴打、伤害儿童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第393条第1款“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情形,因此,司法实践中出现以寻衅滋事罪对行为人进行刑事拘留的情形。笔者认为,以寻衅滋事罪来规制“虐童”行为是司法机关的无奈之举,与公众的一般认知严重不符。除此之外,其不合理性还体现在:(1)“虐童”行为与寻衅滋事罪的客体十分不同。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而“虐童”行为针对的是个人,侵犯的是个人法益。随意殴打他人类型寻衅滋事保护的是一般交往中的个人的身体安全,因此,行为人随意殴打家庭成员或者基于特殊原因在私人场所殴打特定个人的,不成立寻衅滋事罪[9]。(2)寻衅滋事罪无法涵盖形式多样的“虐童”行为。例如,随意殴打、体罚儿童可以认为符合寻衅滋事的行为特征,但是让小孩亲嘴、侮辱咒骂等对儿童实施的精神上的折磨便不能由寻衅滋事罪来评价。因此,用寻衅滋事罪将“虐童”行为进行定罪时极易出现适用真空,无法惩治社会危害严重的“虐童”行为。
不难看出,对于“虐童”行为,我国虽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法律规制体系,但是在刑事处罚方面略显不足,由于刑事立法的疏漏,我国刑法尚未构建涵盖“虐童”行为的全面的、层次分明的罪名体系。
二、刑法须恪守谦抑本性:不必要增设“虐童”新罪
一系列“虐童”事件被报道出来之后,引起社会一片哗然,包括法学界在内的许多公众提出主张增设“虐童”新罪。但是笔者抛开民意和舆论的影响,理性地予以分析,认为持此种看法的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笃信“刑法万能”的倾向,更缺乏理论基础的正当性。先不说增设“虐童”新罪能否达到有效预防虐待儿童的效果,其对公众道德观念和刑法体系造成的冲击已是不可估量。因此,对于增设“虐童”新罪的建议,笔者不敢苟同,并提出以下论据支撑自己的观点:
(一)应当承认教师具有合理的惩戒权
我国一向奉行“尊师重教”的理念,“棍棒底下出孝子”、“玉不琢不成器”的传统思想在现代人看来也习以为常。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应试教育的盛行,作为儿童发展“重要他人”①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是指教师、家长、同伴等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个人或群体,他们构成儿童成长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参见张雅桦:“中国教师群体在儿童保护中的角色与作用”,载《教育学术周刊》2012年第9期。之一的教师,也面临巨大的工作压力。此处主张增设“虐童”新罪,即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将“教师依法享有的教育、惩戒权”在最严厉的刑法中予以否定,一方面不利于对儿童在强力下的价值指引,对公众的传统教育理念形成冲击;另一方面会导致惩戒与虐待之间的界限无法明确认知,拿捏不准合理惩戒的度。
应当指出的是,当今世界多数国家是允许教师对学生进行合理惩戒的。例如,美国法律即规定“教师可以用合理的适度的武力处罚儿童”;韩国在其判决中也体现了对合理惩戒的认可,但是同时对合理惩戒与体罚的界限予以明确。事实上,惩戒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当一个学生选择犯错的时候,便有义务接受正确的教育和引导,适度的惩戒便是对学生进行教育和社会化的过程。综上,笔者认为应当承认教师出于最佳教育目的的合理惩戒权是合法且必要的,相反地,对于过度惩戒行为则须纳入法律规制的视野,必要时由刑法予以评价,而不是盲目地试图通过增设“虐童”新罪来规制所有惩戒学生的行为。
(二)无节制增设新罪有违刑法的谦抑性
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凡是能用其他手段足以控制一定行为的时候,尽量不用刑法,以减少刑法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凡是能用较轻的刑罚足以抑制一定犯罪、足以保护法益的时候,尽量不用较重的刑罚,以尽可能地节约司法资源[10]。刑罚的目的是惩前毖后,而不是无节制地增加罪名。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在修改法律规则的时候,必须要严格控制入罪的关口,对于社会危害较为严重的、新出现的现象,则要慎重对待,一方面要考虑其是否穷尽其他救济措施后仍无法得到救济,从而不得不动用刑罚,以及适用刑罚制裁是否能够达到抑制此类行为的效果等;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刑事法律体系的简约性,避免增设新罪之后与原有罪名体系形成新的冲突,减少司法实践罪名适用的繁琐和累赘。动辄增设罪名或者修改刑法的做法,将严重影响法律的稳定和权威。刑法在整个部门法体系中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而罪责刑均衡和体系均衡是刑法严肃性的应有之义。对于“虐童”行为而言,如若增设“虐童”新罪,将产生“虐童”的范围无从确定的问题,使司法机关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划分“虐童”的民事和刑事界限。因此,专门的“虐童”刑法条文违背了刑法的谦抑精神,同时缺乏可操作性。
(三)增设“虐童”新罪不是预防“虐童”现象发生的必要保证
虐待儿童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005年,美国联邦卫生部儿童局在其《2003年全美儿童虐待报告》中称,全美各级儿童保护机构共收到多达290万起儿童虐待报案,其中近三分之二被立案调查;估计有90余万儿童受到不同形式的虐待[11]115。然而各个国家(地区)防治“虐童”现象发生的措施却大有不同。一种是设立专门的“虐童”罪名或相似罪名。例如,《新西兰刑事法典》在其侵害个人利益的犯罪的章节中规定的虐待未成年人罪,《德国刑法典》225条规定的“虐待被保护人罪”,我国台湾地区“刑法”286条规定的“妨害幼童自然发育罪”等。另一种是虽未直接规定“虐童”罪名,但在刑法中将严重的“虐童”行为纳入他罪的规制范围。例如,我国香港就将严重的虐待儿童的行为纳入侵害人身罪的范围进行规制。最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国家普遍建立起了一整套完整的儿童保护法律和政策体系。美国早在1974年就通过了《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对虐待儿童罪名的认定、调查处理和救济措施都作了详尽的规定,现已建立起了强制报告、受理调查、必要时带离监护人、永久安置听证等完善的应对体系和处理机制[12]97;在日本,政府从社区组织、社会服务、儿童个人发展、父母就业、特殊儿童救济等多方面为儿童提供规范系统、适应性强的儿童福利政策,同时强调以家庭为中心,政府、企业、社区、学校共同分担责任,使得儿童福利及保护得到全社会的高度认同[13]。由上述对比即可发现,增设“虐童”新罪并不是预防“虐童”现象发生的必要保证,以“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为指导,建立健全我国儿童保护的法律规范,完善我国儿童福利多元化保障体系,才是预防“虐童”行为的最有效路径。
(四)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体系倾向将“虐童”归入虐待罪
刑法规定虐待罪只能适用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之间,行为人与被害人通常具有一定的血亲、姻亲或收养关系。然而社会的发展导致社会格局和家庭模式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一些不为大众接受但事实存在的新型家庭,如非法同居家庭、“二奶”家庭。同时,对于共同生活的雇主与保姆、师傅与学徒间发生虐待行为在认定上也存有较大争议,但根据《刑法》的解释原则无法对上述人员的行为进行评价和规制,进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扩大虐待罪主体范围的建议。其实我国修订刑法和出台解释的时候已经体现出了扩大虐待罪规制范围的倾向性。1997年《刑法》在虐待罪由“妨害婚姻家庭罪”移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一章即是淡化虐待罪作为亲情犯罪属性的表现。此外,2010年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儿童犯罪的意见》第20条规定,明知是被拐卖的妇女、儿童而收买,同时对被收买的妇女、儿童有强奸、伤害、侮辱、虐待等行为的,按照数罪并罚的规定进行处罚,也即按照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和虐待罪(或其他罪)进行并罚。而收买者与被收买者并不属于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因此,对于同样不属于家庭关系但存在密切权利义务关系的教师与儿童之间发生虐待行为的,通过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即可予以评价。
三、“虐童”事件刑法处遇的应然路径:立法完善虐待罪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完全提倡“虐童”行为不入罪和设立专门的“虐童”新罪都是不合理和非经济性的,适用虐待罪才是“虐童”事件刑法处遇的应然路径。然而要对“虐童”行为考虑适用虐待罪,则要解决该罪规范障碍的问题。
(一)扩大虐待罪的主体范围
虐待罪将其主体限定为“家庭成员”,不仅无法规范新型的虐待行为,更不利于调整非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儿童、老人、妇女等情节恶劣的现象。因此,对于虐待行为不能再做适用对象上的限定,而应予以扩张,不仅包括家庭成员,还应包括负有照管、保护、寄养、教育、救助等义务的人。凡是具有长期施虐行为、情节恶劣而尚未达到构成伤害罪程度的情形,均可以适用虐待罪进行否定评价。将虐待罪的主体范围扩大,避免了单设“虐童罪”与原有刑法罪名竞合进而造成立法混乱的局面,促进了刑法与儿童保护相关立法的衔接,也是深入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外在体现。
(二)将“虐童”犯罪作为虐待罪“亲告”的例外
根据我国《刑法》第260条的规定,虐待罪在未发生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下属于亲告罪,亦即“告诉才处理”的犯罪。刑法设立亲告罪是因为其一发生在关系密切特定人之间的一些案件中,涉及被害人的隐私、名誉等特殊权益,将此类案件作为公诉案件进行处理可能违背被害人的初衷,因为他们的目的大都仅在于消除不法侵害,而非看到犯罪人受到处罚。而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在家长或者教师对其进行虐待的时候,根本没有告诉的能力,从而大大影响了虐待罪“亲告”原则的设计效果。因此,应将“虐童”犯罪作为虐待罪“亲告”的例外,允许公诉机关直接加以介入,以体现法律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适当加重虐待罪的法定刑
我国现行虐待罪的处罚分为基本刑和加重刑,前者为虐待家庭成员情节严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后者为犯虐待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现行虐待罪的法定刑偏低,不利于遏制频频发生的虐待案件。虐待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受害人的人身权利和家庭成员的平等权利,家庭成员应当拥有完整的人权,不能因身份而有所缺失[14]。同时,虐待罪与其他罪无法实现罪刑均衡,且不说持续虐待被害人致其轻伤的虐待罪,其基本犯的法定最低刑低于一次行为即致使被害人轻伤的故意伤害罪,两者在结果加重处罚上的差异则更为悬殊。笔者认为,不妨将虐待罪的基本刑调整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同时在现有法律条款中增加一项转化条款,犯虐待罪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直接按照《刑法》第234条(故意伤害罪)进行定罪处罚。
四、结语
保护儿童免受虐待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完整的体系,刑法建设仅是该体系中的一个细小环节。透过频发的“虐童”现象,反思更多的应该是我们的道德建设、学校监管和社会责任。预防“虐童”关键在于构建完整的儿童福利体系,只有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儿童社会保障制度,形成体系化的、成熟的儿童保护专门体系,建立专门的儿童福利保护机构,有针对性地直接帮助父母或者其他监护者履行职责,才是我们应当关注的焦点和着手解决儿童权益维护问题的出发点。只有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建设符合我国国情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儿童福利制度体系,才能切实有效地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真正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
[1]常晶.“虐童”难入罪,法律该如何作为[N].中国教育报,2012-11-25(2).
[2]张良,常淑敏.儿童期虐待经历对男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预测[J].山东省团校学报,2012,(4).
[3]周继中,胡永生.保护儿童应当设立虐童罪[N].人民法院报,2012-11-10(5).
[4]媒体调查显示九成网友支持设立虐童罪[EB/OL].http://news.sina.com.cn/c/2012-10-29/025925458456.shtml.[2013-03-25].
[5]刘宪权,吴舟.刑事法治视域下处理虐童行为的应然路径[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1).
[6]皮艺军.“虐童”浅析[J].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1).
[7]徐文文,赵秉志.关于虐待罪立法完善问题的探讨——兼论虐童行为的犯罪化[J].法治研究,2013,(3).
[8]张明楷.刑法学: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张明楷.寻衅滋事罪探析[J].政治与法律,2008,(1).
[10]赖修桂,赵学军.从许霆案看刑法的谦抑性[J].法律适用,2009,(2).
[11]张鸿巍.儿童福利法论[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12]韩晶晶.儿童福利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13]邓元媛.日本儿童福利法律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青年探索,2012,(3).
[14]王琳.身份情节下的“虐待罪”反思[J].人民检察,200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