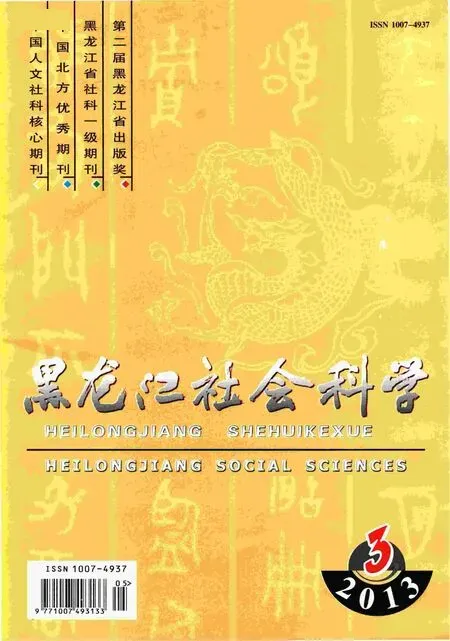试论韩非形名论、参验论与诸子学说的关系——以“名辩思潮”为视角
曲 文
(吉林大学 古籍研究所,长春 130023)
梁启超对“思潮”有如下定义:“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步,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1]郭沫若于《名辩思潮的批判》一文提出了“名辩思潮”的概念,其言曰:“名家”本来是汉人所给予的称谓,在先秦时代,所谓“名家”者流每被称为“辩者”或“察士”。察辩并不限于一家,儒、墨、道、法都在从事名实的调整与辩察的争斗……这一现象的本身是有它的发展的,起初导源于简单的实际要求,即儒者的“正名”;其后发展而为各派学说的争辩……在其后各家的倾向又差不多一致地企图着把这种偏向挽回过来,重新又恢复到“正名”的实际。待秦代统一六国以后,封建社会的新秩序告成,名实又相为水乳,于是乎名辩的潮流也就完全停止了。这样便是先秦名辩思潮的整个发展过程……[2]
不难看出,郭沫若所言“名辩思潮”产生、流变、结束的整体过程,大致符合梁启超提出的标准。本文即以“名辩思潮”为视角,尝试探讨在此宏观学术背景之下,韩非形名论、参验论的形成及其与诸子思想的取舍。
一、韩非形名论广泛的政治指向
形名之学,是名辩思潮的学术话题之一,诸子百家皆有论及,伍非百侧重从学术地缘角度对春秋战国时期的“形名”之学做了一番梳理:
形名之为学,“以形察名,以名察形”,其术实通于百家。自郑人邓析倡其学,流风被于三晋(韩、赵、魏),其后商鞅、申不害皆好之,遂成“法”、“术”二家。其流入东方者,与正名之儒、谈说之墨相摩荡,遂为“儒墨之辩”。其流入于南方者,与道家之有名、无名及墨家之辩者相结合,遂为“杨墨之辩”。至是交光互映,前波后荡,在齐则有邹衍、慎到,在宋则有儿说,在赵则有毛公、公孙龙、荀卿,在魏则有惠施、季真,在楚则有庄周、桓团,在韩则有韩非,皆有所取资于“形名家”[3]9。
在名与形的关系中,名是对形的命名,既是命名,自然需要通过文辞言谈来实现,所以名辩思潮自孔子言“正名”伊始就与“言”联系起来,《论语·子路》记载:“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庄子·天道》将“形”与“名”对举,认为“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既然“名”之“可听可闻”,自然是需要通过语言来表达。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化,名辩思潮发展至墨家后学以及荀子时,对“名”与“言”的认识趋于理论化。《墨子·小取》云“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墨子·经说上》则分别对“名”、“实”、“举”、“言”加以定义,从而为“以名举实”构筑了一个完整的逻辑序列,其言称“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举,拟实也”,“言,出举也”,“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者也”。在这个序列中,颇为明确地指明“言”的作用是“出名”,“名”通过“言”来表达,所以,有学者认为与前期墨家相比,“后期墨家则是从更理论化的高度提出和论述了名与言的问题”[4]192。荀子秉承儒家“正名”的思想传统而对“名”的概念极为重视,《荀子·正名》论及如何定名时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罗焌注:“约,谓言语之约束也”[5],可见荀子之“正名”、“制名”也均需附着于言辞的表达。而且,正是由于荀子所言的“名”是“约定俗成”,需要以言辞来表达,所以才会有《荀子·正名》篇所论“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以及“托为奇辞以乱正名”的情况出现。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伍非百认为“‘刑名’即‘形名’,亦即‘名实’……通言谓之‘形名法术’,析言之,则或称‘形名’或称‘法术’”[3]765,陈启天也认为“形字古与刑通用”,故“形名”亦作“刑名”[6]。从概念上来说,“名”是指事物的名称、定义,“形”是指事物的实际形态和状态,与“名”相对,“形”又可称作“实”。《韩非子》一书中多次论述到“形名”或“名实”,如《主道》言“形名参同”、“同合刑名”,《二柄》言“审合刑名”,《扬权》言“形名参同”、“周合刑名”,《奸劫弑臣》言“循名实而定非”,《安危》言“名实不称”,《功名》言“名实相持而成”,《难二》言“以刑名参之”,《定法》言“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诡使》言“名刑相当”,《八说》言“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八经》言“名实当则经之”等等,足见史迁所言之中肯。
韩非所论“形名”与前述诸子相同,也将“名”与“言”关联,但此种关联较前述诸子更为现实化和政治化,韩非所论之“名”直指臣下进言之“言”,所论之“形”或“实”亦直指臣下行事之功,并在此基础上将“形”与“名”广泛置于现实各种政治现象中加以对照。
以臣下之言为名,以臣下行事之功为实,《韩非子·二柄》云:“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以此为总则,《八说》从“前言”、“后功”的角度提出“明主之法……挈前言而责后功”,《南面》更为全面辩证地叙述审核形名的“前”、“后”关系,认为“前言不复于后,后言不复于前,事虽有功,必伏其罪”。《二柄》从“大”、“小”角度提出“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此外,《南面》更提出了“言默皆有责”的观点,其言曰:“人主使人臣言者必知其端以责其实,不言者必问其取舍以为之责,则人臣莫敢妄言矣,又不敢默然矣,言默则皆有责也。”可见,韩非以言为名、以功为实的思想已经脱离了之前诸子对名、形、言、实在一般抽象意义上的讨论,而直接指向现实政治概念,从而使其形名论的政治指导作用更为具体和实用。
同时,韩非“形名论”的政治指向并没有停留在政治中的“言”与“功”上,而是更为广泛地指向政治现象中的各个方面,并专注总结名实不副的现象。如对君主而言,以君位为名,以君权为实,《备内》以权势不如臣下的周天子为“有主名而无实”;对官僚制度而言,以臣下官职为名,以其行事为实,《二柄》举韩昭侯罪典衣、典官之事为例,以“侵官之害”为名实不副的后果;对学术思想而言,以言谈为名,以其言谈之效果为实,《奸劫弑臣》称“世之学术者说人主,不曰‘乘威严之势以困奸邪之臣’,而皆曰‘仁义惠爱而已矣’,世主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对舆论而言,以毁誉为名,以法规为实,毁誉与法规不合为名不副实,《诡使》云“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官非无法也而治不当名……而世一治一乱者何也?夫上之所贵与其所以为治相反也”;对等级地位而言,当尊不尊,当卑不卑亦属名实不副,《亡征》云“后妻贱而婢妾贵,太子卑而庶子尊,相室轻而典谒重,如此则内外乖,内外乖者,可亡也”……
由上述可知,韩非“形名论”特点不仅在于“没有在纯粹的哲学概念上大做文章”[7],更在于其将名辩思潮中的核心问题——名与形(实)的关系直接置于政治现象中来比照,并对各种名实不副的政治现象加以广泛总结,使形名论在韩非的学说中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意义,成为维护君主集权的强大理论工具。这一特点在名辩思潮之下的诸子学说中,是绝无仅有的。
二、韩非参验论对儒、墨的扬弃与发展
从名辩思潮的角度来看,追求形名相符是诸子形名论共同的理论目的,由于“名”与“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追求形名相符反映在现实中的任务之一,便是对言论的规范。诸家学说中,道家庄子主张“因是因非,因非因是”(《庄子·齐物论》),名家如惠施、公孙龙者醉心于“苛察缴绕”的概念游戏,都没有提出明确的言论规范;相比较而言,墨子、荀子及韩非对言论规范有着较为明确和丰富的论述。
《墨子·非命上》云:“言而毋仪,譬犹运钧之上而立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故言必有三表”。“三表”即《非命》中、下之“三法”,分别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有学者认为这三者分别指向历史的事实、人生的经验、现实的实践,是“墨子考察知识的客观标准”[8]。此外,《小取》提出以“效”定辩说之是非,“效者,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翟锦程认为:“所谓‘效’就是后期墨家的是非标准,其内容仍然是继承和延续了墨子所提倡的‘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兼爱’原则”[4]202。可见墨家一贯以带有实用功利性的标准来判定言谈的是非。
荀子从名实的角度将诸子百家的“邪说辟言”分为“用名以乱名者”、“用实以乱名者”以及“用名以乱实者”三类(《荀子·正名》),并称之为“三惑”。在荀子看来,所有“离正道而擅作”的“邪说辟言”根本的理论基础都可归到“三惑”。对于“用名以乱名者”,荀子提出“验之所为有名,而观其孰行,则能禁之矣”(《荀子·正名》),即以其名验与其行事之实;对于“用实以乱名者”,荀子提出“验之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则能禁之矣”(《荀子·公名》),对“所缘以同异,而观其孰调”,学者解释为“从人的直接观察和经验入手,而观其所调适”[9]185,即以实验名;对于“用名以乱实者”,荀子提出“验之名约,以其所受,悖其所辞,则能禁之矣”(《荀子·公名》),即以名验名。由此可见,对于“三惑”之类的奸言,荀子分别通过名与实、实与名、名与名的两两相互验证来攻破之。虽然荀子攻破奸言邪说用力如此之深,但他始终将“王者”作为“制名”不二人选,从而主张“明君知其分而不与其辩也”。“不与其辩”乃不必与其辩之意,因为荀子认为君主只要掌握了一民之道“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民之化道也如神,辨说恶用矣哉”。此处“势”、“道”、“命”、“论”、“刑”中“命”、“论”二者注家多有不同释义,但此五者要言之不出荀子“隆礼至法”(《荀子·君道》)之君道。
韩非以“参验”为判断言谈辞说的方法,《韩非子·奸劫弑臣》云“人主诚明于圣人之术,而不苟于世俗之言,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显学》云“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何为“参验”?《亡征》云“听以爵不待参验,用一人为门户者,可亡也”。陈奇猷先生注云:“参验,谓参验形名也”[10],即循名责实。但“参验形名”是具体方法,判定言谈的是非还需要具备价值标准。《外储说左上》云:“无度而应之则辩士繁说,设度而持之虽知者犹畏失也不敢妄言”。韩非以“功用”作为衡量言说的“度”,《问辩》云:“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所以,张纯、王晓波认为“参验”就是《显学》所言“夫视锻锡而察青黄,区冶不能以必剑;水击鹄雁,陆断驹马,则臧获不疑钝利。发齿吻形容,伯乐不能以必马;授车就驾而观其末涂,则臧获不疑驽良。观容服,听辞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试之官职,课其功伐,则庸人不疑于愚智”[11]。由此,韩非的“参验论”应包括统一的两个方面,其一是要求名与实彼此相符合,即《扬权》所言“形名参同”;其二是以“形名参同”后的实际功用效果为评判标准。
我们认为,韩非“参验论”思想内容是综合墨、荀思想而有所扬弃、发展而成。
首先,韩非“参验论”所秉持的实用功利主义是对墨学的扬弃。韩非以功用为言行之“的彀”是对墨家功利主义的继承,但是墨家“三表”说的具体内容却为韩非所驳斥。《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便是为直斥儒、墨“必定尧舜”而发,也即是对“三表”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的批判。“三表”之二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对此,《显学》云“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民智即百姓通过耳目之实总结的智慧,在韩非看来,民智都不可依据,耳目之实又怎能成为言说之标准?墨学“三表”之三为“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韩非则认为国之利便是君主之利,而百姓人民之利正与君主之利相异,《五蠹》云“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由上述可知,韩非虽然秉承了墨家的实用功利主义,成为其“参验论”的基本观点,但是在韩非学说中均能找到对墨家“三表”说的逐条驳斥,可见韩非仅仅是肯定了墨家的功利精神,而对墨家的具体标准则完全否定。
其次,韩非“参验论”另一基本要素是“形名参同”,这与之前分析荀子析破“三惑”时“以名验实”、“以实验名”的理路一致,只是荀子因十分重视“正名”,继而有“新名”、“旧名”之分,所以才会有“以名验名”的主张。但“名实相验”始终是荀子名学的基本原则,即张立文、陆青林所言“荀子从名实关系着眼批判的是‘惑于用实以乱名’和‘惑于用名以乱实’两种类型”[9]184。
也正因有此学术思想的承袭,荀子与韩非才会在对“先验”、“前识”的批判上有较为一致的观点。林翠芬博士认为:“对认识论问题,荀子反对所谓的‘先验论’,认为知识不是凭空而得的,‘生而知之’根本不存在,而所谓‘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正名》)即指出,接触外物是认识必不可缺者,足见知识不可与经验切断关系。”[12]林博士所言荀子对“先验”的反对,在韩非那里成为对道家“前识”的批驳,《韩非子·解老》云:
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何以论之?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题。”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在其角。”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以詹子之术,婴众人之心,华焉殆矣,故曰“道之华也”。尝试释詹子之察,而使五尺之愚童子视之,亦知其黑牛而以布裹其角也。故以詹子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是以曰“愚之首也”。
韩非认为即便是事后被证为“真”的观点,如果不是通过对客观事物的考察的方法而获得,也仍然需要被批判,是“愚之首”,这与上述荀子所言“知有所合谓之智”,一“愚”一“智”,用语相反而其意实相合。
需要说明的是,荀、韩均以参稽名实的手段来考量言谈的是非,两者思想的分歧在于这种手段最终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上。荀子针对的是社会上“析辞擅作名,以乱正名,使民疑惑,人多辨讼”的各种奇辞邪说,防止民众被“三惑”之类言说迷惑而不依循政令,因此荀子认为明君应当对民众“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以实现在礼主法辅、教主刑辅的政治模式下。参验名实的方法对荀子来说,是在当下“圣王没,天下乱,奸言起”的背景下,作为君子因为“无势以临之,无刑以禁之,故辨说也”所采取的手段。
韩非“参验论”虽然在方法上继承了荀子名实相参的观点,但与荀子相比,韩非“参验论”的执行主体是君主,即由君主以“参验”为方法、以实用主义为标准来考察各种言说。因此,韩非言“参验”所针对的言说包括两类:一是流行于社会可能会对君主有影响的学术思想,如前引《显学》所批驳的儒、墨“明据先王,必定尧舜”之说,又如《外储说左上》云“范且、虞庆之言皆文辩辞胜而反事之情,人主说而不禁,此所以败也”;二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如《八经》云“有道之主,听言,督其用,课其功”,又云“臣言必有报,说必责用也”,《主道》云“群臣陈其言,君以其言授其事,以其事责其功”等等,皆属此类。而韩非主张君主以“参验”考核言说的目的自然也可以划分为两类:一是避免君主被流行的言说所迷惑而乱政,《亡征》云“喜淫而不周于法,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二是避免君主被臣下之言所欺瞒,《八经》云“明主之道,臣不得两谏,必任其一语;不得擅行,必合其参;故奸无道进矣”。后者更与其赏罚思想结合,更成为其君主“术”治思想的重要内容,如《孤愤》云“人主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故主上愈卑,私门益尊”,《八说》云“明主之国,有贵臣无重臣……言不度行,而有伪必诛,故无重臣也”。
由上述可知,韩非“参验论”吸收了墨家的实用主义并以之为“参验”的标准,袭取了荀子析破“三惑”时采用的名实相验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发明,主张君主以“参验”来考量社会言论及臣下进言。至此,韩非“参验”论成为保证君主集权政治的既实用又具体的方法论内容。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1.
[2]郭沫若.十批判书[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7:183.
[3]伍非百.中国古名家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4]翟锦程.先秦名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
[5]王天海.荀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902.
[6]陈启天.法家述要[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8,40(下):859.
[7]施觉怀.韩非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90.
[8]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449.
[9]陆玉林.中国学术通史·先秦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85.
[10]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06.
[11]张纯,王晓波.韩非思想的历史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1986:62.
[12]林翠芬.先秦儒家名实思想之研究[M].嘉义:中正大学中国文学所,2004: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