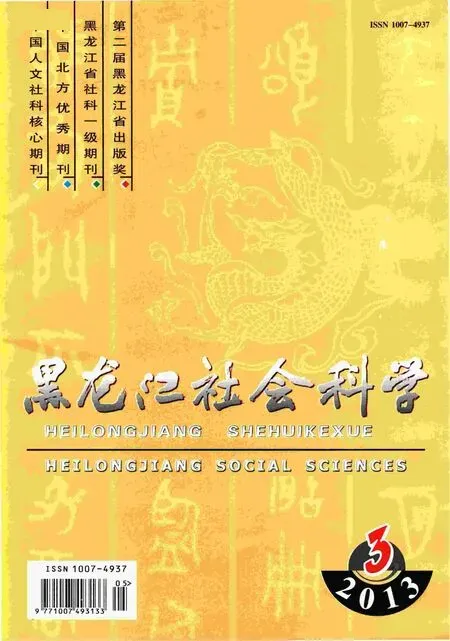流行文化的深层意义:从“江南Style”到“世界Style”
张 晓 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应用英语学院,北京 100024)
《江南Style》的演唱者是韩国嘻哈歌手PSY,因其成名曲是《鸟》,所以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鸟叔”。“鸟叔”原名朴载相,出生于1977年12月31日,毕业于美国伯克利大学音乐学院。虽然在《江南Style》之前,PSY 以夸张独特的台风、机智而充满讽刺的歌词、销魂大胆的舞蹈实力在韩国已家喻户晓,但是直到神曲《江南Style》在全球爆红,PSY 才从“韩国Style”走向“世界Style”。
一、“江南Style”表象下的流行文化
1.“江南Style”的媒体化
《江南Style》MV 中,身形偏胖的PSY 不断重复着扬鞭套马、策马狂奔的动作,不断重复着“oppa 江南Style”的歌曲宣言,但是这看似癫狂的舞步和简单的歌词却引发了从名人到草根的狂热崇拜和疯狂模仿。通过大众面对《江南Style》的态度不难发现,从“江南Style”到“世界Style”,电视、广播、网络对流行文化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例如,《江南Style》MV 刚发布阶段点击率并不理想,直到当红偶像贾斯汀-比伯的经纪人斯古特-布劳恩在社交网络推特(Twitter)上大赞《江南Style》,并附上MV 的YouTube 链接,才令低迷的点击率逐步攀升。紧随其后,布兰妮、安妮-海瑟薇、凯蒂-佩里在新一轮推特中力捧,再次为《江南Style》的火爆注入强心剂。可见,《江南Style》之所以成为全球神曲,除了韩国本土粉丝保驾护航的点击率外,布兰妮等欧美大牌明星的连番转载力推和口碑营销也功不可没,一度在点击率陷入低迷的初始阶段挽救了它的命运。而众多名人、网友的争相模仿以及多样化的演绎,本身就已经成为传播力的一部分。
这首神曲的走红,YouTube 在其中起的作用最大。正是通过视频分享网站,让全世界的网友看到这首歌的MV,才使这首歌如此迅速地在网络上传播。除了YouTube 以外,Facebook、Twitter等社交网络的分享功能,美国主流电视媒体和报刊媒体的强势跟进,以及拥有广大受众的《今日秀》、《Ellen Show》、《SNL》等节目的狂热宣传,也加速了神曲的爆红。正如美国著名学者本·阿格所言,在今天的社会中,人们几乎没有一天可以回避媒体——电视、网络。就当今现实的“电视化”而言,电视也许更为重要,只是不易察觉而已[1]。显然,在“天涯若比邻”的当代社会,当鸟叔和他的《江南Style》出现的时候,所有疯癫变得不足为奇,所有疯癫都变成了流行。
2.“江南Style”的模仿程式化。《江南Style》里的“江南”指的是韩国首尔的江南区,这是一个新兴富人的聚集区,许多有钱人和社会名流在此居住,象征着“时尚”和“富裕”。《江南Style》MV中大部分的外景都取自江南区的桑拿房、马厩、游艇、海滩、旅游巴士等。歌曲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该地区的有钱人向性感的姑娘发出邀约的过程。MV 一开始就是耀眼的阳光和性感的美女,PSY戴着墨镜在太阳伞下悠闲地享受着日光浴。此时镜头拉远,原来他不过是在一个儿童的沙滩运动场上,阳光、沙滩、比基尼都是他的想象罢了。《江南Style》歌词中所表达出的调侃、抱怨、吐槽、对比、反讽贯穿了整部MV,虽然歌曲中PSY 一直在重复对“高富帅”身份的炫耀,但歌曲的主人公对富人生活拙劣的模仿却显得十分可笑。PSY 在MV 中跳着模仿骑马动作的滑稽舞步,用令人捧腹的方式,隐晦微妙地讽刺了韩国社会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现状。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指出,大众文化能够使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人们和他们老板获得同样的精神安慰和娱乐。由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主导,他们有了相似的消费愿望和共同的物质世界观,这种普通文化似乎平衡了阶级差异[2]。《江南Style》的爆红为这种差异提供了“弥合”的平台。因为,“盛装狂欢”正是温饱之后的大众需要,他们在各自的高清摄影机前通过怪里怪气、载歌载舞的自我卖弄、模仿和创造,让个体成为狂欢盛宴中的“主角”。
对《江南Style》进行程式化模仿或抄袭,从而衍生成《某某Style》,无疑会跟随《江南Style》一起火爆,大大缩短成名时间。但是山寨版《某某Style》的背后,实则是法兰克福学派所认为的文化工业,即采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不仅让文化失却多样性,也让文化变得高度一致;文化工业造成了艺术的市场化,损害了艺术的独立性,让艺术变成一种商品,同时也扭曲了艺术家的独立人格。文化工业的标准化和伪个性化使受众的审美能力严重退化,个性被泯灭,失去了反思和批判的能力,人变得非人化。《江南Style》单曲的火爆,使带有“Style”符号的各类衍生品——鸟叔的T 恤、墨镜等物品都能在网络中热卖。对这一现象,菲斯克则认为,商品的同质化是为了满足各个方面的需求而被制造出来的。制造某种商品,要想获得利润,必须达到一定的规模,而消费者的需求又是如此的复杂,要想让自己的商品满足各个阶层人的需求,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人们之间共同享有的文化,一般说来也就是主流的意识形态倡导的文化来满足人们需要。
3.“江南style”的潮语化。所有文化形式都是通过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游戏来传播、接受和制定的。“Oppa Gangnam Style”(哥就是江南范儿),PSY 哼唱着这个在歌曲中重复了100 次以上的宣言,跳着搞笑的马步,一首神曲就横空出世了。从字面上分析“Oppa Gangnam Style”这句流行语夹杂了比较浅显易懂的英文,听上去比较时尚,具有新意,言简义丰,很容易使读者和听者受到感染。美国著名学者本·阿格认为,语言的好坏不在于对模糊性的阐释,而在于以一种持续不变的、富有启发意义的方式来反映本身的不确定性的能力。在此语境中我们“利用”他(如果不是的话,就是被他利用),就有可能阅读出或书写出许多的德里达来。对于各式山寨版的《江南style》来说,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动作、同一句歌词,无论你是哪国人,只要抓住神韵便能“跳”出搞笑味道,而且还能再创造出不同风格。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语境人们可以阅读和书写出许多不同版本的“style”。
“Gangnam Style”来自韩国俚语,指首尔江南区的豪华生活方式。全世界的人跟着PSY 高喊“oppa gangnam style”,他们的生活就真的能变成“江南范儿”了吗?草根觉得“oppa gangnam style”调侃了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则带着“装模作样的态度”来演绎这首歌,以此调侃富人。后结构主义表明当人们想要用合适的词来表达某种事物或情感时,他们不是未经思索随口说出,也不是在词典中搜索选词。相反,语言的意义很大程度上隐含在语言的使用中,因此,人们的说话、阅读和书写最终决定了他们要表达的内容。德里达认为语言绝不可能完好地传达语言使用者要表达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意义永远是不确定和不完整的。语言的不确定性注定任何文本都隐藏着内在的裂缝和断层。语言的困难本质能促进也能挫败批评思维和书写,如果合理利用,它能够帮助批评找到文本薄弱环节,发觉意义的宝藏,哪怕只是颠覆了表象意义的意义[1]。由此可见,各种戏谑、颠覆、搞笑、接地气儿版本的《江南Style》,一方面是大众自觉性地成就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幻象,另一方面也是大众对这种幻象所作出的歇斯底里的回应。
二、“江南Style”式流行文化的再思索
1.媒体化流行文化的价值重估。对于新时代的流行文化,网络是最有效的推广方式。从初期传播到明星相继转载再到全民热捧,《江南Style》走红全过程就是网络平台推波助澜的过程。“江南”不是PSY 一个人在跳舞,人们不管喜欢或者不喜欢都会去点击,他背后有千万人在转发,还有千万人在模仿。新一轮的互动、转发、模仿、恶搞将《江南Style》继续推向高潮。而且对《江南Style》走红原因的解读层出不穷,这些解读又构成了《江南Style》现象。那么,到底是什么在引领我们无意识的崇拜、模仿?本·阿格称电视网络等媒体为集体化景观,正如法国“情境论者”居伊·德波阐述的景观社会一样。德波认为景观社会是继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社会之后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控制形式,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幻象和使人昏乱的娱乐形式来麻木大众,面对消费的大众日益沦为景观社会幻象囚徒的困境[3]。新兴媒体——网络自由、开放、宽容,打破地域限制,因此在现实社会中受到限制的观念、行为被人们移植到虚拟空间中。虚拟空间与情境为青年个性的张扬提供了广阔的场域。是网络让“鸟叔”一炮而红。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的体验是由媒体构筑的。在此,我们不仅忘记了是谁书写的文本,而且还忽略了文本或模仿与他们所表述的真实世界之间的区别,我们对于眼前出现的流行很难做出评价[1]。在更深层次上,我们就是流行文化,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形式,对这些事件的生产和接收来明确身份。当今社会,每个人都暴露在媒体和文化当中,因此,我们应该拒绝媒体为我们设定的被动和非反思的角色,而且应该努力关注由于我们接触新时代媒体所带来的微妙变化。
2.虚假需求问题。韩国江南地区的居民习惯整容,习惯雇佣私人教练,习惯买奢侈品,习惯骑马贵族运动,这使他们看起来很漂亮、很有格调、很有生活品位。在《江南Style》MV 中,PSY 极力模仿富人的打扮——西装革履、大框墨镜、锃亮的皮鞋,但是看起来却“很土”;想要骑马,却只是在大街上装模作样地跳马步舞,或者是在游乐园里玩旋转木马……在这一切自欺欺人的行为之后,PSY 气势汹汹地说出一句“Oppa 江南style”(哥就是江南范儿)。很明显,PSY 的模样恰好与“江南Style”完全相反,他和他说的“江南范儿”也有天壤之别,但是这种“Style”却在全世界极受欢迎。美联社认为《江南Style》是用欢乐和搞笑诠释出江南所混杂的“爱恨交织”——欲望、嫉妒、苦涩等各种情绪。可见,《江南style》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它用一种国际通用的方式,表现了全球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它激活了这个时代的情绪,迎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而这种国际通用的方式则恰恰体现了本·阿格的观点,即文化是一种有利可图的娱乐,将虚假意识看做是一种态度,人们以这种态度来指导日常生活,对本质的社会变革可能性视而不见。可见跳着“骑马舞”的大众也和MV 中的PSY 一样,用虚假的面具掩盖真实的身份和用“骑马舞”的喜乐方式,看似是大众在驾驭他者,实则却是被他者所“绑架”。
当今的社交网络正在强化一种群体效应,当所有人都在听时,如果你不愿意听,就等于脱离了这个群体。更妙的是,人们一旦开始热捧一首歌曲,就会形成“滚雪球”的效应。人们的从众心理会让任何一个还没有接受这一歌曲的人变得格格不入。当各种版本的《江南style》在网络流行,你就得承认,不了解它是一种落伍。于是,你也带着疑惑开始学习“骑马舞”。可见,人们讨厌庸俗却又害怕落伍,追求认同又希望与众不同。经由媒介,他们掌握流行讯息,找到自己的位置;透过消费,他们借由流行商品实践时尚生活,他们创造、传播、接受,再制造流行文化,以展现自我与他人的同步。公众一面说PSY“疯癫”,一面却又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并不断地崇拜和模仿。虚假需求不是来自自发和理性思索的需求,而是被强加和自愿接受的需求。
3.解构性文化批评。《江南Style》MV 中呈现出怪异、荒诞的效果,这正与解构主义相契合,即颠覆传统、冲破禁忌、消解崇高和伟大。它引发的全球范围内的翻唱、翻拍和改编潮,内容充满了搞怪、诙谐、夸张的元素,甚至有欲与原版一争高下的势头。从各式山寨版《江南Style》的流行可以看出,自媒体时代出现以来全球网民对流行文化的解构。网民的解构某种程度上让所谓的主流变得难以立足,“主流”走向了更加分裂化、碎片化和无厘头化,原来的边缘渐成主流。本·阿格认为解构研究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还不如说是一种践行了的与语境的对抗。解构性文化批评将潜文本变成文本,从边缘来发掘文化的意义,在不重要之处发掘意义,根据文本的酝酿、调整和自我校正过程来重建文化文本。解构想要使读者成为作者,从而为他们自己写作。通过强有力的解构性阅读实践,文本就变成了社会文本和社会实践。《江南Style》本身及其众多的衍生作品就像Lady Gaga 走的路线一样,怪异又迷乱,只不过PSY 走的是老少皆宜的傻玩痴乐式无害的奢华,因此受到广泛喜爱。当下这个“庸常时代”,乏味平常的生活不符合流行文化的标准,需要类似“神曲”一般带有模仿、戏谑、颠覆、搞笑的游戏让人们为之狂欢,其草根化的表现方式更符合现代网络主体人群的心理需求。现代人要求“解放”,一些弱势群体也开始发声。
在这个模仿的时代,无论歌曲“疯癫”到什么程度,我们首先要做的,不是轻率地当裁判,而是要倾听、感受、理解,在相互欣赏中形成互动,使意见成为创作的一部分。至于流行文化究竟是以正常面目出现,还是以“疯癫”的脸孔示人,其实并不重要。问题的关键是要唤醒世人的艺术欣赏力、创造力和鉴别力。
[1]本·阿格.作为批评理论的文化研究[M].张喜华,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41.
[2]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张峰,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2.
[3]居伊·德波.景观社会[M].王昭凤,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