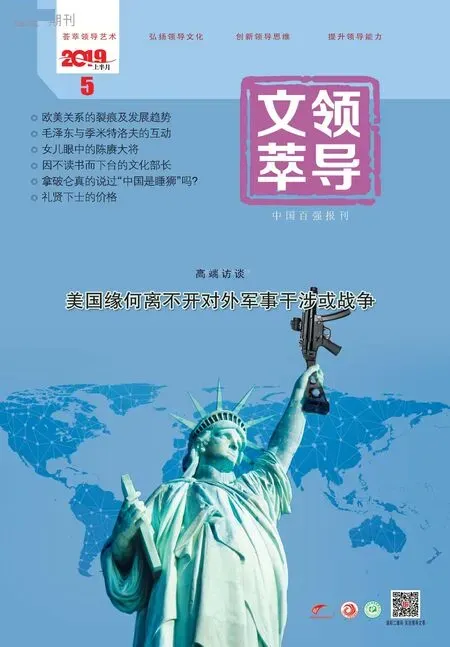寻访戴高乐
□唐霁

“我的家十分安静。在落日余晖中,我眺望远方,附近十五公里,没有任何建筑。跳过平原和树林,我的目光注视着长长的峡谷,一直延伸到奥布山谷和对面的山坡……”这是夏尔·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描写的住所周围的风景。这个位于巴黎东南方260公里、名叫科隆贝双教堂的小村庄看来非常普通,大片的农田在寒风中静默着,初冬的阳光显得苍白和寂寥。如果不特别说明,你很难把它和一个伟人的故居联系起来。然而,1970年,也是在这样的一个冬日里,戴高乐在这里辞世。
为了女儿
戴高乐纪念馆离戴高乐将军的故居不远,位于科隆贝双教堂的山坡顶上,淡黄色的纪念馆恢弘肃穆,与周围的田野和土地浑然一体。纪念馆背后的洛林十字碑高耸入云。这块十字碑是戴高乐二战时期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标志,高达44米,底座上只有一行大字:“致戴高乐将军”。
第一个展厅名为“科隆贝双教堂村,戴高乐式风景”,教堂村的风景映射在巨大的屏幕上,松涛阵阵、树影婆娑。墙上打出一行字:“这片土地影响了他,也被他所影响。”
戴高乐夫妇在科隆贝双教堂村购房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安娜,这个孩子天生有智力缺陷,戴高乐希望自己能够一直陪在安娜的身边,让她远离尘世的烦扰。不幸的是,安娜在20岁时就早逝了,戴高乐在她的墓前握着妻子的手说:“唉,她现在和别人一样了……”这里此后也成为戴高乐下野后撰写著名的《战争回忆录》和《希望回忆录》的居所。
第二展厅里展示的是戴高乐的成长经历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法关系。这里有大量的黑白照片和影片,甚至搭建了一个一战时的战壕,里面贴着战争时期戴高乐在前线的照片。在黑白影片的播放中,一个处在战争边缘,充满浮躁、野心和交易的欧洲在人们的面前徐徐展开,而此时,一个在法国北方城市里尔长大的高个子男孩,在爱国主义家庭的熏陶和战场的锻炼下已经成长为一名坚毅的军人、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抵抗运动领袖
走进第三展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会不自觉变得热血沸腾起来。大屏幕上显示的历史画面是1940年德军挺近巴黎,法国投降了,傀儡政府成立了。而戴高乐著名的“6·18告法国人民书”高高悬挂着。
人们仿佛回到那个历史时刻,戴高乐在英国广播公司的播音室对法国发表广播演说:“我是戴高乐,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一切军工厂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取得联系。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法兰西抵抗的火焰决不应该熄灭,也决不会熄灭。”
这是令人激情澎湃的宣言,但也是孤独的呐喊。因为此时巴黎沦陷了,法国举国上下却还在幻想用投降换来和平。当天法国本土没有多少人听到这个宣言,而收到这个电波的法国傀儡政府随即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
在这个展厅的结尾部分,是一段珍贵的历史镜头。1944年8月26日,巴黎解放,戴高乐在人们的欢呼中从凯旋门沿香榭丽舍大道徐徐向前,他举起手臂向200万欢呼的人群致意。法国人终于深切地明白,“戴高乐将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走了!”
从第四展厅到第六展厅,是战后戴高乐执政的经历,直至他逝世。展厅里摆放的各种海报、漫画、复原街景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简直就是法国战后社会快速发展的缩影。
1946年1月,戴高乐突然辞职下野,回到科隆贝双教堂村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在长达12年的沉寂后,1958年戴高乐当选总统,开创第五共和国,连续当了两届总统后,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中,在法国人一致反对中,戴高乐宣布下野。
在这个展厅里,我们还可以了解到:79岁的戴高乐下野以后,拒绝享受离任总统的薪俸和住房,他静静地回到了科隆贝双教堂村家中撰写回忆录。1970年11月9日,他在撰写《希望回忆录》时因心脏病猝然辞世。
戴高乐的遗嘱也摆在展厅里,里面写道:“我希望在科隆贝双教堂村举行我的葬礼。如果我死于别处,我的遗体务必运回家乡,不必举行任何公祭。我的坟墓必须是我女儿安娜安葬的地方,日后我的夫人也要安息在那里,墓碑上只写:夏尔·戴高乐……”
墓碑上,只有他的名字
戴高乐在遗嘱中,拒绝总统、政府官员和一切公共团体代表参加自己的葬礼,但是他允许军人参加。他始终把自己视为一个普通的军人,而不是一个万人之上的总统。
站在戴高乐简朴的墓碑前,不禁让人想起在纪念馆的最后一个展厅里,陈列着戴高乐辞世后法国当天所有的报纸和杂志——所有媒体都在头版头条用最沉痛的方式报道了戴高乐的去世。
当这样一个伟人溘然长逝时,那些曾经激烈反对过他的法国人,才开始深切地怀念他。他们才恍然醒悟,这个叫做戴高乐的人的性格中那些令他们无法接受的东西,恰恰是对这个国家最为珍贵的。
戴高乐纪念馆正门前,是一座老年戴高乐的雕像,消瘦的戴高乐拄着拐杖,向前大步行走着。他凝望着落日的余晖中远方起伏的田野,目光跳过平原和树林,一直向远方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