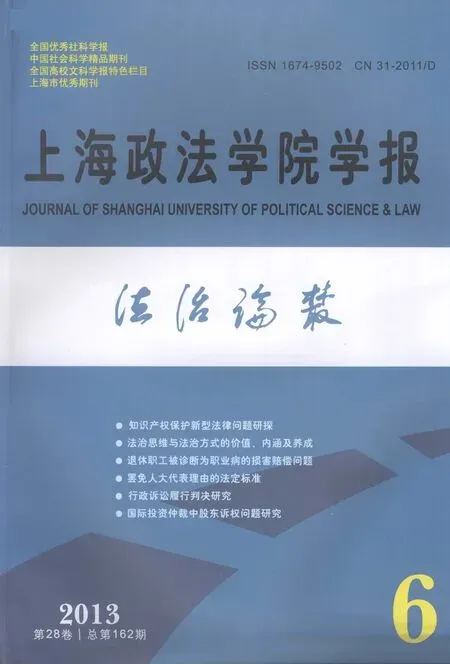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价值、内涵及养成
王 聪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 410007)
●法治时评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价值、内涵及养成
王 聪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 410007)
中国法治建设30余年的历程主要是围绕“立法中心主义”而展开,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虽已初步建成,但法治中国的道路仍然“道阻且长”。法治“器物”易成,但法治“观念”却难立。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概念,释放了法治向纵深处发展的一个信号。公民及政府是否依“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行事,是衡量法治社会是否成熟的标志之一。本文从反面透视当前背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种种表现,又从正面界定了“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应然特征。只有坚持法律规则至上、程序公正优先、确保法律实施的确定性、约束公权、保障私权,才能让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入人心,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法治;法治思维;法治方式;规则治理;程序公正
一、时代选择法治
文革时期的惨痛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经验,反复验证一个常识性的法理命题:法治优于一人之治。“要法治不要人治”的道路选择也是中国近30多年来取得快速、稳步发展的制度保障。因为法治是“使人类服从规则治理的事业”,其具有富勒所言的8项“程序的内在道德”,即普遍性、公开性、稳定性、明确性、不矛盾、不溯及既往、官方行为与法律一致。①[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第2007年版,第55-96页。因此,法治比人治更可靠,更稳定,不会因领导人的变更而改变,不会因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现实条件的偶然变化而改变。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对法治的呼唤,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并且在之后执政党的十五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方针,将“法制”改为“法治”,极其鲜明地突出了法治。然而,由于新中国的法治起步慢、底子薄,法治进程的前一阶段主要是“立法中心主义”,直至2011年,官方才正式宣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法治中国的道路仍然是“道阻且长”,如何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当下法治建设最为重要的目标。换言之,法律大厦已经初步建成,接下来最为关键的便是如何适用和遵守已经制定的法律。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法治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已经制定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二是大家服从的法律是良法。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99页。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央高层在“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养成的两个维度:公民与政府
上世纪90年代,一部名叫《秋菊打官司》的电影引发法学界广泛讨论。电影中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北的小山村,秋菊的丈夫因盖房子与村长发生争吵,被村长踢伤了“要命的地方”,怀有身孕的秋菊找村长讲理,村长拒不认错,向乡里公安局上访,公安局决定以村长赔偿200元的方式调解结案,村长虽然答应赔钱但心里并不服气,在秋菊面前将钱甩在空中,秋菊觉得受辱而不接受赔偿,又向上级公安局上访。经过市县两级公安局复议后维持原决定,“执著”秋菊仍不服气,在律师的帮助下最终走向法院“讨个说法”。在这一维权过程中,秋菊因难产在村长的帮助下才顺利产子,秋菊一家对村长感激不尽。然而,就在孩子满月之时,法院判决拘留村长15天,原本秋菊要“讨的说法”只是一个道歉,却没料想到法律给她的结果却是“抓人”,这让秋菊“困惑不已”。②“秋菊的困惑”隐喻了专业的法治观念与朴实的传统思维遭遇初始时,社会公众的不适应,这也从侧面暗示了长期在中国传统文化浸泡下的公民法治思维养成的不易与艰难。
秋菊“为权利而斗争”的故事给当时的“法盲”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治教育课。普法历来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一环,是培养公民法治意识与法治思维的重要方式。事实上,就在秋菊这个故事发生的相近年代,国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普法运动,试图让“法盲”都能知法、守法、学法、用法,而且这一运动从1986年的“一五”普法至今天的“六五”仍在继续。
普法在两个维度上持续展开:一个维度是培养公民法治思维,鼓励公民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治30多年的发展无疑是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上扬、权利话语高涨、权利本位意识逐渐养成的过程。以1999年的一个“一元钱官司”为例。有一位消费者在书店里购买一本《走向法庭》的书,离开书店后,发现这本书存在中间缺页的瑕疵,于是重返书店要求换书,同时要求该书店支付一元钱的往返乘车费用。书店店员只同意换书,双方对这一元钱的乘车费用彼此互不相让,发生争执。这位消费者果真“走向法庭”,诉讼请求书店支付一元费用。最终原告赢得了“一元钱官司”,却为此付出了3000元左右的诉讼成本。③关于“一元钱官司”的深度讨论可参见刘星:《一元钱官司该不该打》,《律师文摘》2004年第1辑。之后,德国磨坊主以“风能进,雨能进,国王的军队不能进”为由拒绝国王拆迁茅草屋的故事更是在我国广为流传,而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中上演的“最牛钉子户”维权抗拆则成为社会各界广为支持的对象,也被法学家视为是公民物权意识的觉醒与勃兴。
另一个维度是培养政府的法治思维,提高政府的依法行政能力。“六五”普法的重点导向就是 “不断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的能力”。“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更是明确指向“领导干部”。由此可见,法治首先是限制政府权力滥用,将政府行为纳入规范化轨道,观察中国法治建设30多年来的一个重要视角,就是中国官民关系的演化,即所谓“民告官”的行政诉讼逐渐成为化解官民矛盾的一种重要方式。④1996年,被称为“电梯业巨子”的陈锦洪因被佛山市原经济委员会的两则通知免除了其在公司集团中的一切职务,向佛山市中级法院提起行政侵权赔偿之诉,加之这起民告官案索赔标的额达1.6亿元之巨,列国内之首,故名“中国民告官第一案”。在民众眼中,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不再是天然的,它首先来自于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过程也正是将公权力逐步置于法治的制约与羁束之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的相继施行,对于规范政府行为、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对于政府公共治理的要求而言,“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和尊重保护人权,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①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版,第221页。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反向界定:不是什么
十八大提出“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其内涵究竟何为。从法解释学意义上来讲,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两个不同层面的概念,“法治思维主要是指思考的过程,而法治方式主要是以行为的方式表现法治思维的决策。法治思维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没有法治思维不可能有解决问题的法治方式。”②陈金钊:《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诠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但由于两者在行为决策意义上具有同一性,因此,本文习惯于将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割裂开来,从本质上讲,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就是要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让法治成为一种行为习惯,如和风细雨般潜移默化地内化于公民日常的社会交往行为与政府的公共治理行为中。然而,罗马城非一日建成。尽管我国法治建设在“器物”层面逐渐完备,但在“观念”层面却仍然任重道远。换言之,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我国仍未真正确立起来,相反我们常常看到的是其对立面。因此,首先需要从公民与政府两个维度清楚界定: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什么。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闹访”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矛盾凸显期。当各种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激化时,公民的维权选择却不是按法治思维出牌,而是选择非法治方式“闹访”。当事人“信访不信法”、“信网不信法”、“信权不信法”“、信上不信下”成为维权的首要策略选择。一些当事人甚至以自杀相威胁等极端方式“ 闹访”,向政府部门施压,而这种压力最终又转移给法院,结果涉诉涉法信访高位运行,成为司法不能承受之重。这种“闹访”深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平民百姓“拦轿告状”和“赴京喊冤”的信访情结,以及平民百姓心中所形成的“官大于法”,“官愈大、权愈隆、法愈刚”的固化观念,折射出十分浓厚的“人治色彩”,而“法治意识”则十分淡薄。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上访,它所体现的不是法律的程序,还是寄托在人,寄托在领导人的批示,应该说在某种意义上还带有人治的封建色彩。”③《温家宝总理同大学生谈法治》,《法制资讯》2009年第12期。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缠讼”
与当事人频频上访密不可分的便是“缠讼”。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判决生效后,胜诉方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称法院不执行生效的判决,判决书成了一纸空文;败诉方更是积极地到处找关系,申诉、上访,声称法院判决不公正,或法官徇私舞弊,埋怨法官素质太低等。他们都打着维护司法公正与法律尊严 的旗号,去党委、政府、人大要求领导批示干预;去法院要求领导“发现错误”以启动 再审程序;去检察院要求抗诉支持;去新闻单位要求曝光等。我们把这种在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千方百计通过各种渠道和手段,要求否定生效判决和裁定,启动再审程序的一系列行为称为缠讼。④陈柏峰:《缠讼、信访与新中国法律传统——转型时期的缠讼问题》,《中外法学》2004年第2期。司法判决往往是一种“非黑即白”、“一刀两断”式的纷争裁决与利益调整方式,因此它注定不可能令争讼双方皆大欢喜,而常常让“一方欢喜一方忧”甚至“两败俱伤”。在这种情况下,败诉一方当事人除了用尽常规的上诉程序救济,更是在判决生效之后,通过信访等各种方式千方百计启动再审等非常规程序反复“缠讼”,试图颠覆生效判决。有时,一个案件经过反复再审,仍然无法终结,司法的终局性荡然无存。结果,法治所要求的程序安定性与稳定性也就无从维系了。例如,2009年,湖南郴州彭某因为对郴州中级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决和执行不服,在网上发布《决斗书》试图与该案办案法官决斗,结果其达到了“引起领导关注并批示”的预期效果,这足以见得当下当事人对司法判决的“不服输精神”是多么强烈。这种“不服输”显然是背离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对当事人而言,维护自身权益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依靠自己可用的正当法律程序谋求对生效判决的颠覆,如果不可逆转的法律程序已经穷尽,程序就安定下来,当事人不应该无休止纠缠,①关于程序安定性,可参见陈桂明、李仕春:《程序安定论——以民事诉讼为对象的分析》,《政法论坛》1999年第5期。这才是尊重司法、维护法治确定性的必然要求。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捂盖子”
与当事人“闹访”相对应的便是政府部门的“息访”。当事人之所以选择通过信访实现其利益诉求,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戳中政府部门的“软肋”——“稳定压倒一切”。一些政府部门习惯于用行政管控思维化解社会矛盾,认为信访严重威胁社会稳定,于是采取“捂盖子”的方式掩盖、回避矛盾,认为“眼前无事便是平安”。面对当事人通过“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技术不断缠访、闹访,一些地方政府迫于压力,简单地“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正如广东省委副书记朱国明指出:“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是压倒一切的’,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 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 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这种“花钱买稳定”的方式息访看似很“省事儿”,却会误导民众对维护合法权益做出错误的理解和预期。这种解决矛盾问题的方式,是“锯箭杆”式疗伤,病灶并未根除。②黄星:《维稳的‘治标’与‘治本’》,《人民日报》2012年7月19日。结果便是告诉后来的闹访者:“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在这种心态下所诱发的“羊群效应”,使得之前“摆平理顺”成为了“按下葫芦浮起瓢”,顾此失彼,诱发更多的当事人信访,这既使得财政不堪重负,又使得法院负担加重。一边是公民非法治方式的“信访”波涛汹涌,一边是政府部门非法治方式的“维稳”,在两种非法治方式的相互强化之下,社会矛盾化解陷入“救助——息访——再访”、“越维越不稳”的恶性循环怪圈中。显然,这是一种政治思维而不是法治思维。
(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走关系、找熟人”
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杀熟”过程。然而,长期浸润在中国传统“关系—面子”文化下的民众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一视同仁、“不近人情”的法治规则。于是,在发生纠纷或遇到麻烦时,遇事“找熟人”、“走关系”而不是“请律师”则成为很多人的第一选择。人们通过关系进行社会资源之间的互换,架空法律框架的约束。诸如发生事故后诉诸“我爸是某某”其背后正是暗示“靠关系”就可以摆平理顺,在与法律打交道的过程中,只要“关系硬”,什么规则、程序都可能网开一面;因此,会出现“案子一进门,双方忙找人”的现象,“信关系不信法律”的结果便是法律权威与法治公信力受损。
(五)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机会主义违法”
犯罪学上著名的“破窗理论”揭示了一个常见的社会现象:一个房子如果窗户破了没有人去修补,隔不久其它的窗户也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打破;一面墙,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很快墙上就布满了乱七八糟的东西;一个很干净的地方,人们不好意思丢垃圾,但是一旦地上有垃圾出现之后,人们就会毫不犹疑地抛丢,丝毫不觉羞愧;一个人违反交通规则,闯红灯过马路,一群人就会跟着闯红灯,形成“中国式过马路”的不文明现象。事实上,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并非不知晓其行为可能带来的法律后果,但由于法律实施机制的失效,使得一旦有人逃脱了法律的及时制裁,其他人就会形成“法不责众”的责任扩散心理。牛栏终究关不住猫,只要法律的实施机制还存有漏洞,机会主义者总会抱着侥幸心理,铤而走险。结果,漏网之鱼越多,法律的执行力就越弱,其权威性和威慑力也随之弱化。这种法律实施的确定性、及时性的缺失会刺激机会主义违法,在无形中会逐渐削弱乃至架空法律的生命力。正如清华大学张建伟教授所言,“在一个不尊重法律的社会,法律犹如稻草人只能吓鸟。在这样的社会,司法神像也只是个稻草人。”①张建伟:《法律稻草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不是“选择性执法”与“运动性执法”
社会上之所以如此众多的机会主义违法行为,就是因为法律实施机制的失效。而法律失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执法者的“选择性执法”,即“法律实施主体针对不同的对象进行区别对待的一种法律实施方式。也就是说,一部法律是否适用,对谁适用、在何时适用以及适用程度,皆取决于执法者自身的判断甚至好恶。”其后果便是“无论是选择对象执法,还是选择时间执法,归根结底,都源于法治意识的缺席。与之伴随的,则是权大于法、钱重于法、情过于法的种种不良风气:动辄以权压法,批条子、‘打招呼’;‘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案件一进门,就有说情人’。这种唯权、唯钱、唯情所招致的‘选择性执法’,严重动摇威胁法律的平等性、权威性、正义性,也在很大程度消解着人们的公平观念和法治意识。”正如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用蜘蛛网所作的比喻:“法律是蜘蛛网,大苍蝇触犯没事;小苍蝇却给逮着。”古希腊法学名人阿纳卡西斯也说过同样的话:“法律很像蜘蛛网,小而无力的东西落在上面立刻被粘住;但是大的东西落上了,便挣扎网孔而逃之夭夭。”“选择性执法”刺激了机会主义违法行为,导致法律就如同建在流沙上的塔,置于风中的稻草人,沦为任人摆布的玩偶,形同虚设,无法获得社会的尊重与信任,最终戕害法治。
除了“选择性执法”,法治确定性的另一敌人是“运动式执法”。“运动式执法”是“运动治国”常用手段,其可能会在一定时间内带来秩序的安定,但终究不能带来长治久安。“运动式执法”与“法治治国”相背离之处在于,“运动式执法”往往将法律视为一种简单的工具,在需要实现某种目标时就使用;“运动式执法”往往依赖于当时的社会政策而动,一阵风式的执法运动往往容易带来矫枉过正的危险,甚至会出现牺牲人权的过度执法。对此,我们可以从各种追求从重、从快、从严的“严打”、“打黑”运动中汲取经验教训。②迄今为止,除去各种名义、各种规模的“专项斗争”、季度“严打“、地方“严打”之外,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展开了4次大规模严打活动,即1983年首次严打、1996年第二次严打、2001年第三次严打、2010年第四次严打。参见王宏玉、李明:《对‘严打’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运动式执法”、“运动治国”的多变性最终带给社会的是不稳定预期。多变的法治会让人感觉到是人治,③苏力:《法治与发展的特殊性创造性》,《人民日报》2011年7月6日。因为运动式执法从来就不是法治方式,只有法治的确定性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正如方流芳教授所言:“在运动治国之下,一个国家总是难以形成稳定的规则,民众总是难以对法治本身建立信心。在运动和矫枉的每个轮回中,国家治理朝不同的方向摆动,力量在摆动中对冲,法律的演进不时中断,然后重新开始。”④方流芳:《运动治国与依法治国》,http://www.21ccom.net/articles/zgyj/fzyj/article_2012121572982.html,共识网,2013年10月5日访问。
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正向界定:是什么
有学者从四个方面来诠释法治思维的特征:第一,法治思维是受规范和程序约束、指引的思维,第二,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是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行使的思维;第三,法治思维在价值追求上是一种趋于实现公平、正义,保护权利、自由的思维;第四,法治思维是理性思维,是讲究逻辑推理、修辞论辩和解释技术的思维方式。而法治方式则是以权利为本位、保护自由、实现公平正义为目标所建构的行为模式。①陈金钊:《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诠释》,《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应该说,这一界定是较为全面的,但在逻辑层次上缺乏渐进性与简明性。笔者认为,法治社会意味着“法律之治”,其核心是一种规则治理。因此,判断一国法治社会成熟与否,应以该国公民和政府在处理问题时是否遵循“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逻辑。具体而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至少包含以下几个必备特征:
(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坚持法律规则至上
法治意味着一种法律的统治,在一国之内,法律拥有最高的权威,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法律的统治。因此,法治思维意味着法律规则至上而不是关系、人情伦理等“潜规则”至上。具体而言,涉及到社会交往、社会管理的一切规则、程序都应该公开、透明,一视同仁。无论是普通公民还是政府管理者都应该“根据法律规则去思考”,所有人都是法律的臣民,受到法律规范的约束与指引:对于普通公民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对于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禁止,法治政府必须是限权政府;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司法具有终局性和最后确定性,无论是公民还是政府都应该尊重司法裁决,尊重司法权威。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坚持程序公正优先
传统中国秩序原理的特色是只问结果、不计手段,人们更强调的是实质性价值判断,而并非程序公正。②季卫东:《论法制的权威》,《中国法学》2013年第1期。然而,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作的。因为在各种利益冲突协调过程中,立场不同,双方的价值取向也会不同,因而在人们很难在价值问题上取得一致,而把价值问题转换为程序问题来处理也是打破僵局的一个明智选择,也许人们在实体公正上无法达成共识,但在程序公正的框架内,人们却能最大限度地达成共识。法律程序的意义在于:一方面,程序可以限制恣意,约束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维持法律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程序容许选择的自由,使法律系统具有更大的可塑性和适应能力,保障理性选择的作出;此外,程序还具有“作茧自缚”的效应,其所具有的“不可逆性”使其一旦终结便安定下来,从而维护法治的安定性。因此,正如季卫东教授所言:“如果我们要实现有节度的自由、有组织的民主、有保障的人权、有制约的权威、有进取的保守这样一种社会状态的话,那么,程序可以作为其制度化的最重要的基石。”③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坚持程序公正优先,能有助于更好地处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让实体公正不至于因为缺乏制约而走得太远。
(三)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要求确保法律实施的确定性
明朝著名改革家张居正在论及改革得失时曾言:“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律的生命不仅在于实施,更在于及时、确定的实施。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尤为强调法律实施的及时性和确定性,他在《犯罪与刑罚》中言道,“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因为犯罪和刑罚之间间隔的时间越短,在人们心中,二者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人们就越容易感受到刑罚的必然性”,④[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65页“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因为即便是最小的恶果,一旦成了确定的,就总让人心有余悸”。他还特别提请执法者注意:“仁慈是立法者的美德,而不是执法者的美德:他应该闪耀在法典中,而不是表现在单个的审判中。”⑤同注④,第69页。只有让法律做到“言必行,行必果”,法律才不会沦为写在纸上的“具文”和立在田间的“稻草人”,法治的权威性和确定性才会得以确立。这就需要杜绝“选择性执法”,只有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恒心去执行法律,让所有违法者都得到及时惩罚,才能让潜在违法者真正感受到:“莫伸手,伸手必被抓”,“若要法不知,除非己莫为”。在这样的制度逻辑之下,一切人,不论职位身份,不分贫富贵贱,都要服从法律约束,都要对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负责。法律实施面前,人人平等。
(四)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是约束公权力、保障私权利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极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定律”。如果政府权力不受制约,则存在两个方面的危险:一是权力寻租,正所谓“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二是权力滥用,公民权利遭受政府权力的不法侵害。因此,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核心便在于:其一,通过分权与制衡确立司法的权威性与终局性,所有政治问题的僵局最终都可以通过司法得以解决;其二,通过将公权力在各领域、各阶段的全方位、全过程的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保障监督权力的有效性;其三,将各类行政权力、侦查权力、决策权力的行使确立科学、民主、透明的程序,确保任何人的合法权益非经法律的正当程序不受侵害。
(五)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是一种内心认同与普遍信任
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对于法治,我们也不能简单的停留在工具主义的层面。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在更高层次上显现出我们对法治的态度——不单单是“有法可依”、“有法可用”,不单单是从形式上对法律的遵从与使用,更要形成内心里形成对法律的认同,把看起来枯燥的法条背后所应有的观念与态度作为我们的思维方式之一。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更为强调公民、政府对法律的心理认同以及对法治的精神信仰,从而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治国理念,以“法治思维”影响公民及政府按照“法治方式”采取行动。这无疑是一个从形式到实质、从被动到主动、从工具到目的的过程。这种法治精神的养成是法治的灵魂,“人们没有法治精神、社会没有法治风尚,法治只能是无本之木、无根之花、无源之水。”①人民日报评论部:《让法治成为一种全民信仰》,《人民日报》2013年03月01日第2版。
五、让法治成为一种社会生活方式
法治的生命不在于立法,而在于努力把法治精神、法治思维、法治观念熔铸到人们的头脑之中,体现于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正如卢梭所言“规章只不过是穹隆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隆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当我们每个人都察觉到法治如同我们每天所呼吸的新鲜空气一样不可或缺时,法治便已内化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这样的社会,公民都是虔诚的法律信徒,政府都是守法的管理者。古希腊先哲苏格拉底用生命的代价捍卫自己所坚持信奉的雅典城邦法律,在他看来,守法即是正义,即使判决不公正,公民也应该无条件的遵循,不服从便是一种罪恶。因此,他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拒绝执行司法判决,抹杀和破坏法律的权威。他说:“我仿佛是听到了法律的话,就好像我听见神的声音一样,他们的声音在我的头脑中回荡,我不能不听他们的,我坚信我所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②参见[古希腊]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严群译,商务印书馆2000 年版,第52页。这种“信法为真”的虔诚守法精神便是法治成熟的标志之一,因为它表明:法治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成为我们不可获取的习惯性生活方式,一如德萨米在《公有法典》中曾言:“这些神圣的法律,已被铭记在我们的心中,镌刻在我们的神经里,灌注在我们的血液中,并同我们共同呼吸;它们是我们的生存,特别是我们的幸福所必须的。”③转引自刘宏、李语嫣:《法律意识的三个层次》,《人民法院报》2012年8月3日第7版。
(责任编辑:马 斌)
DF07
A
1674-9502(2013)06-037-07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3-0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