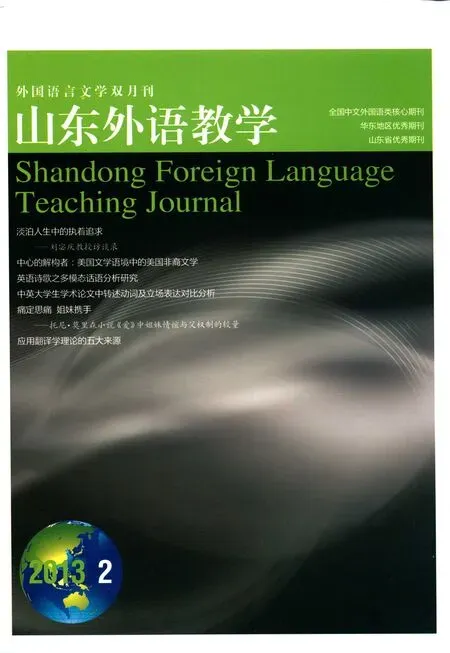淡泊人生中的执着追求——刘宓庆教授访谈录
章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 200081)
刘宓庆教授是我国翻译界贡献突出的学者和翻译理论家。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系统研究我国传统译论和西方译论的基础上,他创建了中国翻译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对翻译研究中几乎所有的基本理论课题都进行了阐述。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于2006-2007年间出版了《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十一种,这些著作在翻译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
由于刘宓庆教授在过去的20余年间主要生活工作在港台欧美等地,国内翻译界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只读其书,不见其人。2006年秋,他来到上海同济大学任翻译学方向博士生导师,因为同事和师生之谊,我有了很多直接与刘老师交流讨论的机会,在他身上强烈地感受到前辈学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他对翻译教学和翻译理论研究的执着以及为人的真诚刚正都让我深深感佩。
鉴于《全集》的影响力以及读者的需求,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决定再版《全集》。得知这个决定之后,刘宓庆教授对第一版进行了非常郑重的修订,很多书还加上了全新的章节和再版序言,这些工作非常耗时费力,对于他来说这样做已经和名利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曾问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修订增补,他说“为了对得起以后的读者”。但是无论是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来说,还是从其他读者的实际情况来看,并不是每个读《全集》的人都能体会到作者的心志,所以我建议刘老师通过访谈把自己的一些主要观点集中在一起以便于广大读者了解。起初,刘老师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他说他拒绝过好几个官方媒体的采访要求,因为作为一个学者,他想说的话已经都写进了他的著作里。对于他这种踏实做学问、低调做人的态度,我当然是表示尊重的。但是我认为,了解他的新观点和新思路对于读者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可以激励更多有志于从事翻译研究的学子和学者。在我表达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刘老师决定接受我的访谈。2012年暑假我利用访港的机会,与刘宓庆教授进行了交谈,话题从《全集》(第二版)开始。
章艳(以下简称章):您的《全集》正在出第二版,从已经出版的几本可以看出,这不是简单的重印再版,而是借此机会做了很多修订,甚至加入了不少全新的章节。在修订的过程中,您主要关注哪些问题?有没有什么对基本观点的调整?或提出新的主张?
刘宓庆(以下简称刘):除了有你参与研究的《翻译美学高级教程》是全新的著作外,很多对第一版著作的修订都是基于我这些年的研究心得和新思路,主要是四大问题:第一,语言之间的互补性和互释性,这个认知应该与21世纪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全球化与时俱进,否则翻译学又会落伍吃亏;第二,价值观问题,这几年,我身居中国,感到中国与世界的最大距离是很多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差异,就是佛学所谓“心距”、道家所谓“隔”。但我的研究重点是文化价值观和审美价值观;第三,翻译与美学的联姻关系,翻译美学的整体化理论构建,必须出几本有深度的理论书或高级教程,这样才能使翻译美学站稳脚跟,便于学者跟进;第四,翻译理论的本土化即“中国化”问题,就是所谓“中国功能主义翻译流派”的基本理论原则和架构。这个问题涉及中国人的历史使命。我们不应当在历史感中迷失。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有历史感的融合性民族。
章:您刚才说“不应当在历史感中迷失”是什么意思?
刘:我的意思是中国人应该维护自己的历史责任感,不要管别人承认不承认,中国人自己要主动承担发展和整理世界文化的责任,翻译学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项。实际上,世界天文学、自然医学(以经络为人体认识论、以草本为医疗手段、以辨证施治为治疗理念)、地屿与水文地质学、通鉴资治学(即古代政治学)、古代国家档案学、古代建筑设计及结构学、古代合金冶炼学、古人文地志学(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文化人类学)、古代军事学(战略战术思想研究,即《孙子兵法》十三篇载于《汉书·艺文志》)、大约始于元明两代的远洋航海学(1219-1440)都是中国人的首创。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我们也要学会“沿波讨源”,这样才能真正了解各个时期翻译理论的形成和演变,才能把翻译理论研究做深、做踏实。
章:您的《全集》是很多翻译研究者的必备藏书,我阅读了您所有的书,有些读得粗略,有些读得仔细,但几乎每一本书的“自序”我都读得特别仔细,因为从这些文字中,能看到您作为一个翻译研究者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这些对于更深刻地了解您所做的翻译研究是大有裨益的。您希望通过序言传递什么?希望读者从中得到什么?
刘:“自序”是我的日常话语,它不同于理论话语:日常话语更贴近一个人的平常心——他内心的感悟、情思、困惑、思索、诉求、愿景、世情评议等等。日常话语常常可以做理论话语的得力的、不可或缺的感性诠释。你不可能单单靠一个人的理论来理解他的“本我”和“真我”。
章:在平时的生活和工作中,您是一个非常谦和的人,但是在您的一些与学术研究有关的文字中,我觉得您像一个“斗士”。例如,您在《翻译教学:实务与理论》的自序中写道:“我庆幸自己具有我国楚人那种‘一息尚存,永不言败’的情怀,认定一定要走的路,就不要怕荆棘、不要怕陷阱,也不要怕人暗中伏击。我认为人生最大的挑战莫过于外人对自己最珍爱的信念的挑衅与否定。”(刘宓庆,2006-2007:xxxii)您觉得在您一生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和挑战?
刘:我从初中时代起就是足球队员,我估计我这一生大约摔过不少于100次跤,足球场上充满了对抗,一上场就得时刻提防对方把你绊倒、撞倒、铲倒。足球对锻炼人的坚韧性所起的积极作用难以估量。在我记忆中,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外国,还没有一个人能成功地在意志上压服过我。楚人是在被秦国人欺压中、爱尔兰人是在被英国人的欺压中锻炼出了自己的民族性格。这一点对做理论工作很重要。当然,意志坚韧并不意味着固执己见,在理论研究中,一旦认识到自己有失误就应该马上改正。比如我提出的饱受争议的“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就是一个例子,它很难不引起人们的误解。2008年我把它改成了“翻译理论的中国价值”。
章:您在《文化翻译论纲》第二版(即将出版)的题记中写道:“研究文化纯粹是为了为自己铸造和维护一个我所珍视的文化自我,使我不管生活在什么困顿迷茫的学术生态环境中,都能领略徐志摩所说的那一杯‘人生甘露’和保持一腔通常被西方人称为‘中国士人’的‘忧患意识’和‘生之热忱’。”读您的书,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做学问对您来说是一种毕生的事业追求,带着理想主义者的理念、热忱和浪漫情怀,一个人能够倾其一生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这是很让人感佩的,和当下学术圈的功利性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不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这种判断?
刘:是的。在我的全部学术研究中,我没有拿过国家一分钱来做“研究费”,《全集》十一卷我没有向国家或港府要过一分钱的资助。在中国,做学术研究要能耐得住贫苦、清寒、孤独、隐忍、冷遇、讥谗、含沙射影、暗箭中伤、封杀围堵、无期冷藏,如此等等,这些我在中国内地和“香港地”(香港人对“香港”的昵称)都经历过。做学问特别要保持与官方和权贵的距离。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还有一点很特殊:禁区、禁律、禁忌、禁语特别多,中国没有经历过欧洲的启蒙运动时期,很多基本理念不能作为基本价值依据,因此你的理论论证要能“曲径通幽”。英语中有一句话讲得很对:“Sweet are the uses of adversity”,逆境不仅仅可以锻炼你的意志力,还可以使你的逻辑论证依据更加多维化,可以富集你的反证手段。我在高中的时候读到一篇文章说伽利略在一封遗书里说“I am happy that death can be used to testify that I have been right”(我很高兴可以用死亡来证明我一直没做错”)。我想这真的是大智中的大勇、也是大勇中的大智。我后来一直没忘记他这句话。
章:您的理论书籍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也有一些人对您的观点持批评意见,您认为这些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您认为学术界应该怎样展开良性循环的学术讨论?
刘:香港和北京都有人认为我是“传统派”,深陷“误区”。这种指责其实帮了我的大忙。2001年我从台湾回来以后大约整整一年都在潜心研究中国传统国学——除了“911”那几天我忙于看美国那块“伤心地”的电视动态以外。我发现中国古代智慧太不公平地被埋没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被儒家的大树浓荫遮住了:道家、墨家、法家(尤其是韩非子等人),还有两汉的扬雄、班固、王逸、王充,魏晋时代的曹丕、陆机、刘勰、钟嵘,一直到清末的梁启超、王国维等,起码有50-60位文论家的观点很有助于中国当代翻译学发展和构建意义理论、语言符号学理论、文本和词语诠释学理论、篇章结构和语用理论、词语及章句审美理论、翻译风格学理论的借鉴和构建,这是翻译学非常可贵的未经开发的“珍宝库”。我觉得世界上最滑稽的事是哆哆嗦嗦“捧着金饭碗讨饭吃”。
西方学术界的流派之争很热烈,有时甚至很精彩。有一次我跟David Pollard(时任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系主任)说“他们大概是为了诺贝尔那块金奖牌”,他说“不对。他们完全是为了‘求真’,西方人历来把学问的‘真理价值’(truth value)看得很重,追求‘功利价值’的人也有,但很少,而且很快就会被人看出来,自己也就站不住。”中国学术界及其主管的“功利心”、“政绩观”太重。我可能说得不客气,这是中国学术界的“硬伤”。恐怕要从体制上动大手术。
章:刚才您提到“误区”。我是否可以理解为,这些认为您深陷“误区”的同行其实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传统国学对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深刻意义?我们现在很多翻译研究者对中国传统文论还缺乏应有的了解,需要好好地补上这一课,我自己对此也深有体会。我觉得,越是了解中国传统文论的学者,就会越认同它对中国翻译理论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刘:这就是历史感。就好比登山赏景,远近高低各不同,由于视角不同,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如果你真想知道眼前的风光究竟有多美,就应该时时转换视角,这样才能看得全面、真切。中国传统文论充满了精妙的智慧,认真研读对于开展翻译理论研究一定会大有帮助,这就叫做“开窍”。
章:在这一点上,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达成了共识。近来一些翻译界的学者开始对中国翻译界过多译介西方翻译理论的做法进行了反思,在2011年上海华东师大进行的“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及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潘文国教授提出了“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问题(潘文国,2012),引起与会很多学者的共鸣和认可,这和前些年翻译界对“中国特色翻译理论”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您在很多地方都提到类似的观点: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翻译理论,应该有传承于我们两千年来译论前辈的翻译理论,应该有有利于我们灿烂的民族文化发展前景的翻译理论。(刘宓庆,2006-2007:xxxii)。您认为,在今后的翻译研究中,中国的翻译研究者应该怎样合理地处理好译介西方翻译理论和发扬中国传统译论之间的关系?
刘:任何理论都有一个本土化问题,所谓“世界性”都是相对的,要么就是骗人的。美国的太空学具有明显的全球控制和先发制人(pre-emptive)的外太空操控和霸占战略特征和技术特征。德国和法国的太空学特别重视对欧洲和外围的天候观测、地质深层结构透视和地面通讯全方位覆盖。中国的翻译理论必须全面体现中国价值,我在《文化翻译论纲》(第二版)和《翻译美学高级教程》(即将出版)中比较全面地重新论述过了,请大家参阅。
章:您认为我们应该怎样开展中国古代翻译遗产的开发工作呢?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历史感的问题?
刘:是的。我想有志者都可以做。但我认为一定要有一个国家规划,由规模化翻译研究所来统筹运作,承担规模化遗产开发和发扬工作。这是一个古代智慧当下化的很有意义的工作。古代智慧常常可以使今人感到自愧愚钝,无地自容。
章:在您的40年学术人生中,有一半是在欧美港台度过的,虽然您的著作被广为阅读,但在国内翻译界却常常处于“不在场”的状态,缺乏在场的话语权。这是您自主的选择还是不得已而为之?这种不在场有什么利弊?
刘:英语说“It’s a good riddance”(“还是不在场为好!”)。可以说,除了喝红酒、吃比萨饼以外,我都愿意不在场。当事人不在场,人们可以品头论足、褒贬自如,不必有所顾忌,甚至可以破口谩骂。金圣叹说过一句很俏皮的话:“梦里骂人最痛快,嘴巴一抹没人怪。”当然属于理论上的质疑或误解,有机会能及时当场或当面澄清谈透,是再好不过了。维特根斯坦在英国读书时罗素是他的老师,他对罗素的很多见解颇不以为然,但他一直以当面与老师交换意见为原则,从不在老师不在场时对别人说罗素的三长两短。我个人倒是从不介意Catherine Blyth所谓的“small talk,big deal”(三言两语是非多)(Blyth,2009:47),因为我认为理论上的问题假以时日总是会越辩越明,不在乎你在场解释不解释,你如果在理,必有人为你申辩,如果不在理,自己在场也无济于事,而且徒使大家尴尬。
章:您这大概就是道家的“无为”论,我发现道家对您的影响很深,是这样吗?中国传统哲学对您的影响最深的是儒家还是道家?
刘:儒家除了“孝道”,对我影响很小,大儒们好像都是大官家。儒家看不起女人,我母亲和大姐姐都很反感,从小对我影响很大。道家对历代“中国士人”(也就是知识分子)的影响很深,因为道家的理念具有历史的延展性。道家对人生态度的相对论和逍遥观、对不可抗拒的客观状况和暴力政制的“无待”态度等等,对“身无半文”、“手无寸铁”、“上无片瓦”的劳苦大众和清贫士人是很大的精神安慰和道德支撑。
章:您刚才说“历史的延展性”?能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吗?
刘:例如老子说的“道法自然”对于现在就比在春秋战国时期更有深意。“道法自然”应该是现代生态学的基本理念和法则,一位德国柏林大学汉学家估计,由于违反“道法自然”,人类从上个世纪70、80年代开始,大约冤枉死了一亿两千万人,使大约两千万人成了残疾人。可怕的是这个进程还在继续。北极冰雪融化后,那块陆地下的资源一定会使它成为血溅黄沙的残酷战场。人类现在还不具备充分的智慧把“道法自然”的理念融进国际法和现代政治学中。
章: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出过翻译理论著作全集的学者,您怎样评价自己对中国翻译理论体系建设的贡献?
刘:我比较重视翻译学的整体性整合研究,这是我唯一的特点。我的书都是为中国、为中国学生——我们民族的子弟写的。我希望为中国的翻译学搭建一个稳稳当当的架子,哪里缺什么,我就写一本书补上去,而且不能使中国丢脸,如此而已。
章:到目前为止,您的研究几乎涉及了翻译研究的所有重要领域,如翻译理论通论、口笔译教学、汉英对比与翻译、文体与翻译、文化与翻译、美学与翻译、中西翻译思想比较、翻译与语言哲学等等。可以说,您这一生主要的时间都在从事翻译、翻译研究和翻译教学,是什么能够让您如此执着地做这些工作?做学问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您有没有感到后悔过?
刘:有些事必须得有人做,不能都来当大厨,没人当采购、做切工,就是英语里说的Somebody has to do it(有些事总得有人做)。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必须有人要教翻译、写翻译教材,说得“伟大”一点就是“匹夫有责”,往小里讲,就是“本店有货”。我当过好几年翻译,素材很多,写个教案很方便。也算是“历史的巧合”吧。我当时报请当翻译也是北大老师的期望和叮嘱。我个人很喜欢设计,从机械到时装,我都觉得很有意思。你要说“后悔”我不想完全否认,如果我做了别的工作,也许也能做得不错呢。像“悍马”那样的“酷车”,我不一定设计不出来,说真的(笑)。
章:但如果那样,就是中国翻译界的遗憾了。我想起杜甫《题张氏隐居》中的两句诗:“春山无伴独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其实人的一生能够排除外界的干扰,潜心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并且取得了像您现在这样的成就,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了。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期待着读到您更多精彩的译论和散文。
[1]Blyth,C.The Art of Conversation[M].London:John Murray Publishers,2009.
[2]刘宓庆.刘宓庆翻译论著全集(十一种)[M].北京:中国翻译对外出版公司,2006-2007.
[3]刘宓庆.文化翻译论纲(第二版)[M].北京:中国翻译对外出版公司,即将出版.
[4]刘宓庆,章艳.翻译美学高级教程[M].北京:中国翻译对外出版公司,即将出版.
[5]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2,(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