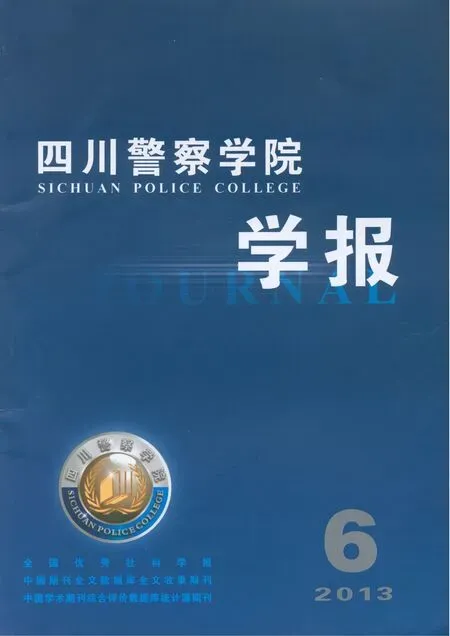现代性视域下乌托邦精神与科学发展观的文化阐释
何光英,马中全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现代性视域下乌托邦精神与科学发展观的文化阐释
何光英,马中全
(四川警察学院 四川泸州 646000)
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或精神资源,其价值在于对现实的超越性批判;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人的解放和社会发展,但同时也使人陷入工具理性的深渊,导致人的异化和现代性分裂的危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走出了现代性与乌托邦二元对立的误区,把马克思的人学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联系,不仅实现了对现代性和乌托邦精神的双重超越,更将中国特色社会社会主义理论提升到一个新境界。
现代性;乌托邦精神;科学社会主义;科学发展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一、乌托邦作为概念及意义
1516年,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在《关于最完善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简称《乌托邦》)首次提出“乌托邦”(utopia)的概念。此后,乌托邦作为一种概念,广泛出现于对社会现实批判和对未来理想社会设计的文献中,尤其是相关社会主义论述的文献中。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恩格斯在1882年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宣告社会主义运动中乌托邦思潮的终结。20世纪,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分化,乌托邦思想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其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理论对现代社会中乌托邦存在的合理性,乌托邦的涵义和作用,乌托邦与人的自由解放,实现乌托邦的途径等问题进行探索,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独树一帜的现代乌托邦理论。
乌托邦原意为乌有之乡,莫尔将希腊文ou(没有)和topos(地方)组合成新词utopia(乌托邦),用以表示一种未来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作为一种概念,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作为理想的同义词,乌托邦代表一种超越现实社会的未来理想社会,尤其是与现存的政治制度相对立的理想社会制度;其次,作为空想的同义词,乌托邦既然是一个超越的境界或理想,它包含了可望不可及的意义,是一个无法到达的彼岸。自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问世以来,人们往往把与社会现实不同的社会向往视为乌托邦,这种乌托邦被视为不能实现的理想。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乌托邦更是与空想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它的意义就与历史发展成反比。这实际上是一种“科学——空想”式的二元对立论。
事实上,乌托邦作为一种思想或精神存在,有其积极的意义和认识价值。恩格斯当年在从历史观上对空想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并没有对之全盘否定,而是说:“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思想的萌芽和天才的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1]莫里斯·迈斯纳认为:“历史的动力(而且的确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奋力追求。正像韦伯曾经指出的,‘人们必须一再为不可能的东西而奋斗,否则它就不可能达到可能的东西了’。也正如卡尔·曼海姆所言:‘如果抛弃了乌托邦,人类社会将会失去塑造历史的愿望,从而也会失去理解它的能力’”[2]。它“是一个使人沉思而不是使人行动的超历史的范型;它是一种现实道德判断的准则,而不是一种对未来的规定”[2]。
乌托邦的意义在于它对现实的批判性,而不在于将理想付诸实践。如果将对美好社会的设想制度化,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人间乐园,就必然为现实所不容或者形成对现有秩序的破坏,也许它能表达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但也往往造成一种“集体无意识”下的社会混乱。乌托邦批判现存的社会制度,追求美好的未来。但是,它不是把对美好社会的追求建立在现代经济发展的必然性上,而是依据道德判断,表达对不同于现实存在的美好社会的追求。因此,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对美好社会的制度设计,而在于突破现实的束缚,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体现出来的超越精神。虽然它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又承载着人们的精神追求。因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
乌托邦虽然有超越性,但它又是现实社会的反映。人们是根据现实追求理想的,因此尽管理想完美,但却是由现实所规定的。其实际意义就是为社会变革提供或许是一个尚不具现实性的目标。乔·奥·赫茨勒说:“每一项改革社会生活的伟大方案必须首先在人们的思想中形成一个大致的轮廓。思维形象总是先于物质器械在起作用。但是,思维起着更为奇特的作用,因为通过抓住公众的想象力,可以创造出供人效法的中心,并且以新的思想和理想沉入集体道德。它们还把人们的思想引向精神解放,有助于解开紧握着过去的僵死之手,鼓励人们大胆探索并追求更加美好和永远美好的事物的精神,使人们超越现实世界的限制”[3],从而在历史发展中是一种社会的诊断者,并且对不满于现实的人们开出一剂精神上的良药。
如果我们摆脱“空想——科学”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就会发现在资本主义寿命未尽、社会主义也并非完美的背景下,乌托邦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盟友,并在社会发展中体现着自己的意义。不论是从世界观上还是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上,我们都要与乌托邦主义划清界限,但在对现实社会的判断和超越上,它们却可以为人们提供借鉴,从而摆脱现实的束缚,在对现实的批判中保持一种追求未来的精神。
二、现代性分裂与乌托邦救赎
(一)现代性的悖论:人的解放与异化。
丰子义认为,“现代性作为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基本特征与表现,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概念。它既是指以启蒙为标志,以自由、民主、科学、理性为核心的时代意识和价值趋向,也是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科学管理等为基本构成元素的社会发展模式和内在要求;既是指祛魅化的、突出主体意识的生活态度,也是指按照现代化的规律行事的行为方式[4]。”
现代性以理性主义为武器,向传统的封建神权宣战,鼓吹个人的自由、博爱、平等与人权,把理性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作为现代社会的价值体系,‘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价值:独立、自由、民主、平等、正义、个人本位、主体意识、总体性、认同感、中心主义、崇尚理性、追求真理、征服自然等。与之相应的是,作为前现代社会,即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前现代性’体现为以下的主导价值性:身份、血缘、服从、依附、家族至上、等级观念、人情关系、特权意识、神权崇拜等”[5]。
现代性宣称,人可以拒绝任何外在权威,实现自身价值。对“前现代性”社会而言,现代性是一种先进而巨大的革命力量;对个体而言,它提出个人的自由,以现代理性取代盲目崇拜,打破了世袭的封建和神学枷锁。斯宾诺莎说:“依照理性的指导的人是自由的。”[6]启蒙思想家认为人的价值与意义与自由密切相关,他们将人视为社会的“单子”,“各种辩论从个体的议题出发,肯定人的原始、根本存在,并且借由各种方式衍生出法律及社会制度”[7],这种观点适应了反封建和批判宗教蒙昧的要求,同时又通过对科学、自由、人权的颂扬,使人从前现代性中解放了出来。
现代性伴随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起来,它带来社会物质和技术进步,但也给人类造成了很大的灾难。艾森斯塔特曾论道:“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着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8]在现代性推动下,西方各国实现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在商品经济的背景下,现代理性日益成为工具理性,人的自由成为商品交换的自由,它以竞争和交换的利益至上原则否定了包括情感、道德在内的非理性。正如马克思所说:“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类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9]。
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现代性取得了强势地位,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人却日益成为机械化和自动化时代的一个零件,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感和自由发展的可能性。人日益成为“单向度的人”,从而不能形成批判性的否定思维。在对现实的无法超脱中,形成了人的压抑感、孤独感和精神上的无家可归。齐格莱特·鲍曼说:“现代性是一种不可遏制的向前行进——这倒不是因为它希望索取更多,而是因为它获得的还不够;不是因为它变得日益雄心勃勃,更具冒险性,而是因为它的冒险过程已日益令人难堪,它的宏大的抱负也不断受挫。之所以这一行进仍需继续下去,是因为它到达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过是一个临时站点。没有一处令人特别垂青,也没有一处地方比另一处地方更理想。”[10]
现代性以解放和创造的面目出现,把人们从传统中解放出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它被编入了资本主义的运行中,服从市场理性和利益至上的逻辑,使人被工具理性所控制;但当它成长起来以后,又加速了人的客体化和异化。这就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所说:“正如在现代主义的未来主义和技术——牧歌的诸形式中,作为主体的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里能反应、判断和行动的生物已经消失。”[12]当现代性雄居于世时,人也就被推向了边缘。在现代社会发展中,一方面,人越来越被客体化;另一方面,又必须为人的自由提供新的空间。如何解决人在客体化中形成主体的自由,在现代性的视域下,这似乎又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二)乌托邦对现代性悖论的批判与救赎。
面对现代性的分裂及其造成的人的物化甚至异化,乌托邦思想家对其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并根据历史给定的条件,试图在揭露现实的有限性中追求无限,在终极意义上寻求人的自由。对乌托邦的研究,重点不在乌托邦对未来理想的设计,而在于它是如何以对未来的想象反过来批判现实世界的不完美,特别是现代性造成的社会矛盾和人的异化。正是通过对现代性悖论的深入批判,乌托邦在最终意义上追求人的再一次解放,即从现代性的压抑中实现人的自我解放。卡尔·曼海姆肯定了乌托邦思想家对现实的批判意义:“我们应该根据乌托邦因素的变化去理解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代的思想结构中最重要的变化。当乌托邦被摒弃时,人便可能丧失其塑造历史的意志,从而丧失理解历史的能力。”[11]
我们可以批判或否定乌托邦主义者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但只有当我们把乌托邦与现代性的分裂进行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不与现存同谋、以超越主义精神对现存不合理现象进行批判,以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的终极之追求。与现代性的无限扩张堵塞了通向未来之路相对应的,是乌托邦传达出面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拉塞尔·雅各比在评价曼弗德的思想时说:“他还发现,即便是‘头脑最简单的乌托邦’,也‘拥有显着的人类品性’”[12]。布洛赫提出了具体乌托邦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既来自现实又超越现实,进而把握未来的思想,并认为:“其一,乌托邦具有冲破现实的要求;其二,它表达了对更美好生活和世界的愿望和希望;其三,乌托邦的基本核心是人,它是人道主义的同义语。”[13]它直指现代性导致的人的困境,从而形成了一种“过程乌托邦”,它把未来视为人的本质得以实现的目标,进而探求人的解放的道路,表达着对人的自由的期待。
值得指出的是,当代西方的乌托邦思想,虽对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造成的人的异化提出深刻批判,但又提不出实现人的解放与自由发展的切实可行的方案,因此,有明显的局限性。因此,现代乌托邦思想,虽对防止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有抑制作用,但并不能为之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正如柯拉夫斯基所说:“乌托邦所要改变的,是不可能由‘现实的’即时行动来完成的,远远超出可预见的将来,而且无法预先策划。但乌托邦仍然是对现实有效的行动工具或策划社会活动的工具。”[6]
总之,虽然乌托邦大都对现代性充满直接或间接批判色彩,并在其中追求人的自由解放,但又不能成为一种实现人的解放力量。它的意义在于其超越现实、追求未来的批判精神和理想主义色彩。
三、科学发展观对现代性和乌托邦的双重超越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现代性的悖论中是一个无解的命题,在乌托邦思想中也没有实践的可能性。因此必须超越二者,以更高的理论视野探索人的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道路。对于中国来讲,片面强调现代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无异于违背历史和国情,走资本主义道路,并将加深现代性的弊端和对人的异化;而坚持理想主义,又往往导致教条主义和道德乌托邦的危险。因此,如何走出现代性与乌托邦的二元对立,并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与社会现实的变革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就成为当下亟待解决的命题。
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正是把握现代社会发展中的这一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仅为这一历史课题提供了理论指导,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升到了一个新境界。它超越现代性与乌托邦的局限性,突出人的主体性,把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命题与现代化实践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有重大意义。
首先,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是对现代理性和乌托邦的超越。
以工具理性为主要特征的理性主义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需要理性主义。现代性关注的是现实利益,而非道德的意义,“正如在现代主义的未来主义和技术——牧歌的诸形式中,作为主体的人——一个在这个世界上/里能反应,判断和行动的生物——已经消失”[14]。科学发展观则明确指出,“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15],中共十七大报告在阐释以人为本时指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利,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样,就使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带有公平追求的道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条准则,从而在工具理性和道德乌托邦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关系,在终极意义上把握现代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超越性的追求中不断反思现实,推进现代化的健康发展。
其次,它以构建和谐社会为选择,为人与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和谐共生创造了条件。
绝对理性主义必然导致现代性对人的控制,使人失去自主创造性和人自身的丰富性;乌托邦追寻人的意义并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但无力改变现实。乌托邦与现代理性二者的博弈并不能有效地解决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而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人类社会的不同侧面,是人自我发展的现实环境,只有有利于人的发展才能称之为文明。胡锦涛说:“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15]这就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再次,它强调发展的目的性,使社会主义实践体现出了理性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双重特性。
人类总是以理想为指南进行改造现实的活动,以此体现人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人的发展虽然受到客观必然性的主宰,但唯有在理想追求中才能保持动力,发现不足,矫正偏颇,为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创造条件。胡锦涛说:“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以现实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5]这就从现实与理想、目标与实践、无限与有限的统一上把握了人的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24-725.
[2](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张 宁,陈铭康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
[3](美)乔·奥·赫茨勒.乌托邦思想史[M].张兆麟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259.
[4]丰子义.发展的反思与探索—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5.
[5]俞吾金.现代性现象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36.
[6]斯宾诺莎.论理学[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206:1.
[7]雷索·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235.
[8][以]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M].旷新年,王爱松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67.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出版社,1995:275.
[10]周 宪.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104.
[11]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07:539.
[12]拉塞尔·雅各比.乌托邦之死:冷漠时代的政治与文化[M].姚建彬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7:260.
[13]陆 俊.理想的界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乌托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4](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精粹读本[M].周 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32.
[15]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08:30;35;29.
The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Utopian Spirit and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 the Domain of Modernity
HE Guang-ying,MA Zhong-quan
Utopia as an idea or mental resources,its value lies in the nature of reality beyond criticism; modern development,on the one hand to promote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nd social development,but also tools for rational people into the abyss,leading to the alienation of people and the modern division of risk. People-centered 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out of the binary opposition between modernity and utopia of the errors,to Marx'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is linked not only to achieve the utopian spirit of modernity and beyond the double,even a socialist societ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to a new level.
Modernity;Utopian spirit;Scientific Socialism;Scientific Concept of Development;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610.3
A
1674-5612(2013)06-0121-05
(责任编辑:赖方中)
2013-09-02
何光英,(1969-),女,四川泸州人,四川警察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中全,(1972-),男,四川泸县人,四川警察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