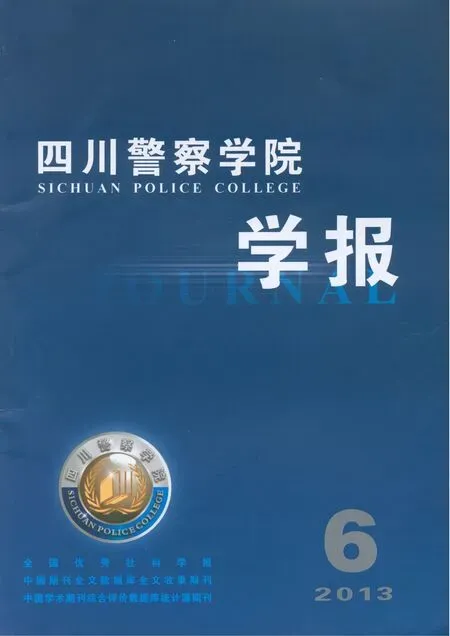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刘慰
(华侨大学 福建泉州 362021)
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启示
刘慰
(华侨大学 福建泉州 362021)
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深受儒家仁义道德主义思想的影响,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就是其中之一,古称“恤幼”。“恤幼”思想认为统治者和社会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主张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不同于成年人的特别宽容制度,在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上都主张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的关爱,并将其体现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
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刑事政策
一、古代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制度
(一)刑事责任年龄界定。
在中国古代立法中一般采用按照年龄大小和身体伤残程度的方法论定刑事责任。关于未成年人犯罪可以不负刑事责任或者减轻刑事责任的规定,在中国起源很早,历代相承不废,在唐律中形成了完备的制度。早在西周的时候,就有人按照行为人年龄来决定是否处以刑罚的制度:“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1]这里的“七年”可能只是一种概括的规定,并非具体的年龄确认。尽管如此,这则有关刑事责任年龄的最早记载已使我们看出在西周时期,人们已经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了一种有别于成年人的法律规定。另外,儒家经典中还有三赦的说法,“一赦曰幼弱,二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幼弱就是小孩子,老旄就是老年人,而所谓“蠢愚”,是指天生的痴呆与精神病人。在这里规定的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大概可以推断出是七岁以下,并且明确规定“幼弱”可以赦免,不再进行处罚。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逐渐提高,有关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开始变得更具体了。李悝《法经·律减》中规定:“罪人年十五,罪高三减,罪卑一减。”此时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确认,还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献记录得更加详细,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墓竹简中的“法律答问”。法律答问中规定以身高(六尺)作为标准来决定犯罪人是否承担刑事责任,虽然没有明确以年龄来划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但是古时一般认为男子15岁身高六尺,而成年男子的标准身高被认为是七尺,从这可以推断出春秋战国时期和秦代时期都是以十五岁这个标准来划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两汉时期,汉改秦律,又以年龄大小作为确定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依据,这就变得更科学合理了。但是两汉时期在规定刑事责任年龄上并不统一,《汉书》记载,惠帝时,“诏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犯诛死者,上清廷尉与闻,得减死。”[1]东汉时,“年未满八岁,八岁以上,非手杀人,皆不坐。”从史料看,两汉时期西汉以十岁、东汉以八岁这个标准来划分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不过,从《汉书》法令来看,当时未满十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后还要关押,而不是完全免除刑事责任。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与汉制基本相同。到了唐代,代表封建立法最高水平的《唐律》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相当完备的规定,它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赔),受赃者备之”。[1]从此可以看出唐代把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划分得更具体,分为四个阶段:十五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到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到七岁以上和七岁以下,根据不同的年龄阶段承担不同的刑事责任。这四个阶段的划分跟现代刑事责任年龄划分十分相似。唐代对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如此完善,以至于后代无法超越其地位,基本上都是沿用当时的立法和适用当时的原则,并不断地予以完善和大量应用于审判实践中。明朝实行唐明合制,对违法犯罪青少年及儿童的处理,基本上与唐朝相同但也有新的发展。《明会要·大训记》中记载“永乐二年二月已丑,刑科奏:‘强盗死罪,其中幼年十五以下者二人,蒙恩囿死,没入习匠输作终身虽年幼,既能行劫,亦当被刑。’上日:‘童稚无知觉,非成人诱之,岂能为盗?二儿去悼不远,朕特推此情矜之耳。’”该记载中的内容大概是说按当时的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十五岁以下,且流罪以下才能够适用收赎,其他罪并不免罪,很明显两个人应该被处死。但是皇帝考虑到“童稚无知觉,非成人诱之,岂能为盗?”故“特推此情矜之耳”,以“蒙恩囿死”。明朝是一个重典治国的朝代,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是表现如此体恤和宽宥,不得不说是历史的进步。[2]在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刑法,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也有类此规定。由此可以总结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立法延绵几千年,尽管历朝各代刑法都对未成年人罪犯刑事责任年龄作有基本一致的不同规定,其中的规定也并非严谨科学,年龄划分阶段多种多样,但大多以十岁、八岁、甚至七岁为起未成年人犯罪的起刑年龄,充分体现了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原则和恤幼的思想。
(二)刑罚适用原则。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我国基本上是一个成年人的社会,未成年人群体的特殊意义并没有得到应有重视,自然也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但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立法、著说、奏折,虽然不专门针对未成年人,但却隐含了当时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定罪量刑,从侧面来说历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都有其相关规定,并始终贯穿于“仁政”、“恤幼”、宗法伦理思想等各种政治法律思想中。纵观上下五千年文明,虽然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相关规定零散而缺乏体系,并且远没有形成在刑事责任年龄立法中所出现的世代传承局面,但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总结出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体现了以下几个原则:
1.适用减除或者免除刑罚和赎罪的原则。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犯罪情况,分别采用了减除、免除、收赎的方法进行处理。如《唐律疏议·名例》规定:“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十岁以下,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其内容规定可以用赎刑来代替流刑、徒刑和苔刑,而不需要受到肉体的折磨和自由的限制,十五岁以下犯流罪以下和盗窃伤害等轻罪可以只要求缴纳赎金,以金钱和特权来折抵刑罚。《唐律疏议·名例》中还规定:“对于十岁以下犯其他罪的,皆勿论。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里明确地说明十岁以下不论所犯为死罪、流罪以下或者七岁以下犯任何罪,皆可免除减除或者免除刑罚。这种不适用监禁刑、身体刑和减免刑罚的方法,一定程度上使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得到保护,保障了未成年人的利益,使其能够健康成长,在我们今天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方面依然还有借鉴意义。
2.适用避重就轻的处罚原则。中国古代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时适用避重就轻原则,让未成年人受到处罚时以较轻刑为主。如唐律中规定“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假有七岁死罪,八岁时案发,则死罪不论;十岁时杀人,十一岁案发,仍得上请:十五岁时偷盗,十六岁案发,仍以赎论”。此规定即是告诉我们未成年人犯罪不以被逮捕和审判时间为标准而是以犯罪时年龄为标准,按犯罪时幼小年龄轻条用刑。这种把犯罪时和案发时区别开来,在犯罪时仅以年龄幼小为标准来从轻处罚未成年人犯罪,体现了“恤幼”和人本主义思想。
3.适用感化教育原则。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以感化教育为主,辅以刑罚。如清末《大清新刑律》规定:“凡未满十六岁之行为不为罪,但因其情节,得命以感化教育。”可见在清末规定十六周岁为未成年人刑事责任能力年龄,对于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根据其情节以感化教育为主,一般不处罚。
(三)刑事特别程序。
跟古代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相类似,历史记载对于刑事处理方面的规定是比较零散,甚至可以用星星点点来说。尽管如此,在各种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在对未成年人进行逮捕、审讯、刑罚的执行等方面还是留下了丰富的资料和实践经验。
1.逮捕方面。作为重要的刑事强制措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逮捕规定较为直观地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有关对于未成年人逮捕规定的记载最早见之于西汉末年,由于当时各方面矛盾激化,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为了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平帝元始四年特别下诏,明敕百寮:“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他皆勿得系”。[3]这里“七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只有犯不道罪时才被加以逮捕拘禁。这很可能是由于统治者为了缓和当时政治、社会的恶劣环境而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怀柔措施,也有可能是对先前的形势政策的一种恢复。不管统治者是出于什么目的,只要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逮捕时给予了不同于其他人犯罪的规定,就可以体现出了统治者在立法上对未成年人的宽容和仁慈。
2.刑讯方面。中国古代一直有刑讯的传统,口供被视为“证据之王”,为了快速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法律赋予司法机关进行刑讯逼供的权力,但是在对待未成年人方面,由于传统“恤幼”和“仁政”等法律思想的影响,在立法上却是反对刑讯的,《唐律》中有“诸应议、请、减,若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者,并不合拷讯,皆据众证定罪。违者,以过失论”。这里告诉我们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审讯时可以“议、请、减”,并不准拷讯,若有违反当追究相应的责任。可以推测这肯定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生理特点,不适合进行拷讯,于是给予特别宽宥。在此影响下,其后宋明清都有相关的规定,在侦查过程中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时权益的保护。
3.刑罚的执行方面。古代在刑罚执行时一般以监狱机关为主,虽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监狱管理制度,但没有形成专门针对未成年人的监狱管理制度,仅仅在关押未成年人时在个别律令中显示出对其特别的关爱。其最早见于汉代,那时我国出现了“悯囚制”。《汉书·刑法志》中规定:“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及孕者未乳、乐师、侏儒、鞫系者,颂系之。”书中“颂系”是指散禁的意思,即不带刑具。对于八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关押时是不加械具的。唐代,虽然监狱制度十分严密,但《唐六典·刑部》亦有规定:“杖、苔与公坐徒,及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废疾、怀孕、侏儒之类,皆颂系以待弊。”唐代在汉代的基础上将未成年人关押时不加械具的年龄提高到十岁以下,扩大了不加械具的未成年人范围,从而更能体现出了对未成年人的关怀和体谅,当然两个朝代规定的范围不一样也只是统治者为了更好与刑事责任年龄相匹配。同样这也体现在后代的立法中,结合历代尤其是唐宋监狱管理的经验,如明代在《明会典》中规定:“令禁系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岁以下及废疾、散收、轻重不许混杂。”该条文明确告诉我们,明朝时期,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不许与其他罪犯混杂关押在一起,应该给予分别关押。立法者在对待未成年人刑罚执行时有很大的突破,既有防止交叉感染之作用,也有便于管理以更好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之意。而《大清律例》中也规定“凡老幼废疾犯罪,律该收赎者,若该例枷号,一体放免,硬的杖罪仍令收赎”。该条文不规定年龄的限制,只要是年幼的带枷号未成年人直接进行放免。
4.收赎方面。收赎是古代社会刑事强制措施的其中一种特有的制度,由于我国古法立法者一般将收赎作为官僚贵族及其亲属的一种特权,而平民百姓是无权享受此项权利的,所以涉及到法律公平和正义等敏感性问题。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想方设法地逃避或减少法律的处罚,所以规定了收赎制度——以钱抵刑。但是他们也许是为了彰显出实行“仁政”的一面,对弱势群体作出了一种例外,允许平民百姓中的老幼病残者收赎。如我国《唐律》中规定,七岁至十岁(含十岁)的人犯“盗及伤人者,亦收赎”。元朝刑法也规定:“诸十五岁以下小儿过失杀人者,免罪,征烧埋银。”记对十五岁以下过失杀人的犯罪,要用赎金的办法代替刑事责任。可见,统治者在收赎方面给予了未成年人较多的宽待。
二、古代未成年人犯罪立法的当代价值
我国古代对未成年人“体恤”的法律规定是一贯的、相互传承的,它反映了爱护未成年人的民族精神,蕴含着鲜明的人文关怀,体现了国家的仁政和刑法中的人道主义原则。这些传统、历史悠久的法律规定,在世界法制史上所少有,因此也可以说是中华法系的一个特点,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方面的新规定,在古代的立法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立法的科学性。
(一)体现在刑事责任年龄上。
古代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详细法律规定在此次《新刑事诉讼法》也有一定的体现。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274的规定,审判的时候被告人不 满十八周岁的案件,不公开审理。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不公开审理和对犯罪记录的封存能够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和隐私,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尊重和爱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挽救。
(二)体现在刑罚适用原则上。
古代对未成年人适用感化教育原则在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得到充分的体现。第266条的规定明确地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要求公安司法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中,应当加强说服教育,促使其悔罪服法,重新做人。对于有罪的未成年人,要坚持教育和矫治为主,尽可能采用非刑罚化的处理方式,以利于未成年人改过自新、复归社会。与此同时,古代对未成年人在减除或者免除刑罚的原则适用上也在此新《刑事诉讼法》中有所体现,确立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是对这一原则淋漓尽致的表现形式。新《刑事诉讼法》第271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涉嫌刑法分则第4章、第5章、第6章规定的犯罪,即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侵犯财产以及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可能判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符合起诉条件,但有悔罪表现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这一制度有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人格矫正,促使其尽快、顺利地回归社会,有助于对未成年人进行非犯罪化和非刑罚化处理,有助于维护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4]。
(三)体现在刑事特别程序上。
古代对未成年人在刑事司法逮捕和刑讯审判方面的宽容和保护政策同样也在此次新《刑事诉讼法》得到进一步的体现。第269条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这意味着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尽量适用非羁押性强制措施、降低羁押率。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可以尽量减少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适用逮捕,通过讯问、听取意见的程序及时发现并纠正诉讼程序中的违法行为。但是,“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之“严格”标准如何掌握,是实施中的一个难题,希望通过司法解释加以细化。第270条规定,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新《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可以通知”改成“应当通知”,并扩大了到场人的范围。需要注意的是,这里“也可以通知”含义是,讯问、审判未成年人案件,应当首先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在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的情况下,应当通知其他的合适成年人到场。“也可以通知”并不是授权性规范,而是强制性的。确立合适成年人在场制度,不仅可以帮助未成年人与讯问人沟通,还可以对讯问过程是否合法、合适进行监督,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三、目前我国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立法的局限性
整体而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的新规定,处处都闪现着古代立法智慧的亮光,但是,仍然不能避免立法的局限性问题。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的刑事立法是一个前进性与曲折性并存的过程,要重新重视当前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立法上的不足,再进一步挖掘古代立法的思想精髓。当前,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新《刑事诉讼法》有两个方面有待完善。
其一,没有跳出刑罚中心主义的思路。新《刑事诉讼法》离现代少年司法的理念还有较大的差距。现代少年司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主张“以教代刑”,以福利性干预措施(保护处分)替代刑罚,刑罚是一种不得已的最后手段[5]。尽管专章明确规定了“教育、感化、挽救”方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但是却没有规定非刑罚处罚措施(保护处分)的适用程序,这是立法的一大疏漏。
其二,虽然古代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对当今影响深远,新《刑事诉讼法》也专章对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给予特别的规定,但这远远不够,少年司法实践中所形成的较为成熟的经验并没有充分吸收,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建构还不完整,还未建立起真正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例如法庭教育程序、圆桌审判制度、心理测试制度、简案快审制度等,在专章中均没有规定。专章中已有的规定,例如社会调查制度、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等,也还过于谨慎,没有对少年司法实践较为成熟的经验予以充分尊重。当然,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专章只是我国少年司法法典化的开始,而实践先行积累经验,立法再选择性筛选固定的少年司法改革路径仍应成为今后我国少年司法改革的主要路径。
四、结语
尽管我国古代的未成年人犯罪在司法、立法、执法上远没有现代社会那么发达与科学,但在“恤幼”和“仁政”等法律思想的影响下,它充满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文主义关怀,这些刑事政策和法律规定不仅为当时的未成年人犯罪惩罚、预防工作指引了正确方向,为维护未成年人的特殊利益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当代科学完备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新《刑事诉讼法》的出台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又一历史性的进步,它更能进一步体现像古代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的宽容政策和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更能起到维护好未成年人利益的作用,但这些还不够完善,作为新时代法律从事者,全社会人们应该更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立法者在法律制定上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独立于普通司法制度之外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
[1]张晋藩.中国法制史[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39.
[2]刘 斌.浅议唐律中的刑事责任年龄[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3]张利兆.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
[4]王 娟.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调整[J].西北大学学报,2007,(3).
[5]陈光中.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与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保障[J].中国司法,2007,(1).
[6]唐 丹.简论中国古代“恤幼”思想及其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影响[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2009.(2).
[7]张利兆.“仁政”思想与我国古代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J].青少年犯罪问题,2005,(6).
On Revelation of Criminal Legislation for Juveniles in Ancient Chinese
LIU Wei
the ancient Chinese legal system was influenced by the thoughts of the Confucian morality and ideology,the juvenile crime is one of them,which is called"Sympathized-youth”.The thought of"Sympathized-youth”tended to the un-removable responsibility of the rulers and the society for the growth of juvenile,advocating that the juvenile crime was different from special tolerance system for adult,and the more cares and mercy to the juvenile in the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and embodied it in criminal legisla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These criminal policies and the laws not only guided the right direction for the ancient juvenile punishment and prevention,playing a positive role for the juvenile special interests,but also provided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the scientifically improvement of the crimin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for juvenile crime.
Juvenile;Criminal Responsibility;Criminal Policy
DF0
A
1674-5612(2013)06-0091-06
(责任编辑:赖方中)
福建省教科项目《城市“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预控研究--以泉州为中心的考察》,项目编号:FJCGZZ12-031。
2013-06-25
刘 慰,(1987-),男,湖北咸宁人,华侨大学法学院2011级法律硕士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