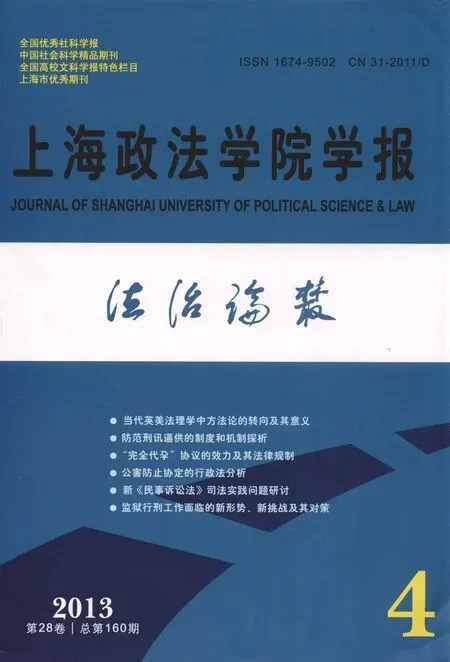我国开展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司法障碍
丁晓华
我国开展环境公益民事诉讼的司法障碍
丁晓华
关于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依赖行政手段的干预。近期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2011年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该事故造成渤海湾蓬莱840平方公里海域原本一类的海水,一夜之间变为劣四类海水,附近渔民及养殖户遭受巨额损失。按照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农业部全力推进渔业索赔行政调解工作。最终,农业部、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及有关省人民政府就解决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损失赔偿和补偿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由康菲公司出资10亿元人民币,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和补偿问题;康菲公司和中海油从其所承诺启动的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分别列支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渔业资源环境调查监测评估和科研等方面工作。①《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渔业索赔行政调解达成一致》,http://www.gov.cn/gzdt/2012-01/25/ content_2052167.htm,中国中央政府网,2012年12月25日访问。
对于公益损失的赔偿通过行政机关出面协调推动予以解决,是传统民事诉讼不支持公益诉讼制度下的惯有做法。那么,在2012年《民事诉讼法》新增第55条环境公益诉讼后,是否意味着环境污染中的公益损害问题也终于可以通过民事诉讼解决了?答案显然不是简单的肯定。当前《民事诉讼法》对于公益诉讼,仅宣示了起诉条件和原告资格问题,对于公益诉讼制度所需的诉的利益划分、损失评估、举证责任、裁判效力、监督执行等一系列立案、审理及执行中将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未作出专门规定,而这些问题构成了当前实施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的主要困难,需要我们仔细界定并加以研究,以期未雨绸缪,为公益诉讼的发展扫清障碍。
一、立法对公共利益缺乏统一定义,公益与私益的划分边界尚不清晰
传统民事诉讼坚持无利益即无诉讼的原则,诉的利益是法院受理审判的前提。原告起诉只能以与自己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权利或法律上利益为限,这一点体现在《民事诉讼法》第119条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中。而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公益诉讼超越了第119条的规定,明确对于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法院起诉,从而打破了传统的强调当事人必须与案件有直接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适格理论。但与私益诉讼不同的是,现阶段公益诉讼只能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提起。因而在开展公益诉讼时,首先应当作出界定的是,何谓公共利益,如何区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
从我国现行法律来看,当前共有128部法律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其作用主要有三类:一是表明立法的目的,如《行政强制法》第1条规定“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二是表明行为合法性的界限,如《合同法》第52条明确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三是表明公权力对私权利进行限制的依据,如《土地管理法》第2条第4款表明国家仅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虽然,公共利益这一名词在我国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迄今还没有一部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对公共利益的含义予以明确。目前仅有的对公共利益作出解释的规范性文件是国家版权局2006年11月2日《关于查处著作权侵权案件如何理解适用损害公共利益有关问题的复函》,该复函认为,就一般原则而言,向公众传播侵权作品,构成不正当竞争,损害市场经济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就是损害公共利益的具体表现。由于该复函仅针对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作出,且将公共利益仅等同于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环境,其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过于狭窄,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在我国,类似公共利益的概念还有“社会利益”、“社会公共秩序”、“国家利益”等,表达着基本相同的含义,但对这些概念,也没有任何立法作出明确的定义或解析。
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的明确界定,直接决定了公益诉讼的起诉条件和原告资格问题。一项行为只有在损害公共利益的情况下,才能被纳入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如果对公共利益的含义缺乏统一的解释,公益与私益界限不清,至少将产生如下危害:
1.公益诉讼的立案受理标准将无法统一。如果对于公益的理解各执一词、各行其是,同样的环境侵权行为,在某些地方可以被纳入公益诉讼,而在其他地方却不作为公益诉讼处理,全国各地法院做法不同,将直接影响司法的公正与公平。
2.私益诉讼的正常运行可能会受到损害。当前我国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只能是法律规定的机关或组织,如果公益与私益难以划分,私人提起的私益诉讼可能因涉及公共利益而被拒之门外,这不仅不能起到通过公益诉讼扩大民事诉讼保护范围的初衷,反而损害了私益诉讼的健康运行。尤其在环境污染事故中,在公益与私益难以区分的情况下,将直接影响受害者利益的及时维护。如在康菲溢油事故中,既有沿海渔民遭受养殖、捕捞损失,也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如果因该事故涉及生态环境等公共利益,渔民起诉索赔被法院拒之门外,显然将不利于广大渔民私益的维护。
二、损失概念未作扩大解释,损失评估机制难以有效运作
民事诉讼当事人对于损失金额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或者原告单方证据不足以证实损失具体金额的,法院会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委托独立第三方对损失作出评估,评估结论经庭审质证无异议后会成为判决的依据。由于环境公害涉及面广,当事人更难以对损害范围和金额达成一致,因此由独立第三方进行损失评估是无法避免的。但在现阶段,由第三方进行环境公害案件的损失评估至少会面临如下困难:
1.如何确定损害的范围。康菲渤海溢油事故发生后,经过油指纹鉴定,在辽宁绥中东戴河浴场沿岸、河北京唐港浅水湾浴场和来自河北昌黎海岸的数个油颗粒,被证实来自蓬莱19-3油田。因此10亿元康菲赔偿资金,基本上按照上述“三个范围”的油颗粒分配。①《康菲案乱局:十亿赔偿金或被三个油颗粒左右》,http://finance.qq.com/a/20120309/005119.htm,腾讯财经网,2012年12月25日访问。但事实上环渤海诸省的沿海地区,官方和民间均声称不同程度遭受了损失。由于油污在海洋中并非静止不动,通过油颗粒鉴定确定损害的范围受到了人们的质疑。在其他环境公害案件中,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同样也面临着如何科学确定损害范围的问题。如果损害的范围无法合理确定,则损失评估将无从开展。
2.如何确定损害的威胁。损害威胁是指虽然没有发生实际损害,但如果不采取一定的措施,损害的发生将不可避免。我国当前立法对损害威胁的规定除了体现在反倾销、反补贴及保障措施等国际贸易领域外,主要存在于海事诉讼中。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1条第(四)项规定,船舶对环境、海岸或者有关利益方造成损害或者损害威胁的,可以申请扣押船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也明确,船舶油污事故,是指船舶泄漏油类造成油污损害,或者虽未泄漏油类但形成严重和紧迫油污损害威胁的一个或者一系列事件。船舶发生油污事故,对我国海域造成油污损害或者形成油污损害威胁的,由油污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油污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可以说,在环境污染事故中,除了实际损害外,更多的是损害威胁。
如海洋污染中,广大渔民不仅遭受实际的养殖生物和渔业捕捞损失,将来一定年限内的捕捞损失的发生也将不可避免,因为油污清理及恢复海洋生态需假以时日。又如2013年1月中旬我国中东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大范围雾霾天气,空气质量都是六级严重污染,一条“污染带”由东北往中部斜向穿越我国大部地区,最密集的在京津冀地区。恶劣的天气致使各地呼吸道患者人数增多,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等疾病患者则雪上加霜。②《中东部大范围雾霾:多个城市空气污染濒临“爆表”》,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1/13/ content_724205.htm,东方早报网,2013年1月15日访问。虽然很多人没有出现明显不适,但空气质量的污染显然使得民众罹患上呼吸道系统疾病的风险大增,造成了对民众身体健康的损害威胁。然而我国当前关于损害威胁的规定,仅存在于船舶造成的油污损害领域,其他领域尚不涉及。至于对损害的威胁如何进行评估,更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则。
3.如何赔偿精神损害。损害可以分为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当环境遭受破坏时,不仅会造成财产损害也会造成公众精神损害。如噪声污染会导致不特定多数人产生睡眠障碍、心悸惊慌等症状,这些都可以构成精神损失。此外,环境污染事件可能导致优美的居住环境遭到破坏,原有的视觉享受被剥夺,或者海边居民因海水污染丧失了夏天海泳的乐趣,这些也不能不称之为精神利益损失。然而我国当前可以获得赔偿或补偿的精神利益损失范围十分狭窄。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2条规定,侵害他人人身权益,造成他人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也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必须达到严重后果才能获赔精神损害抚慰金,如果精神损害后果不严重,法院仅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但在环境公益损害领域,公民所承受的优美视觉享受、海泳机会被剥夺等损失一方面难以称之为严重的精神损害,无法通过伤残评定确定精神损害等级,另一方面我国司法解释对于不严重的精神损害所规定的救济方式,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并不适宜用于补偿环境生态受到破坏而造成的精神损失。
三、举证责任尚未合理分配,原有举证倒置规定难以全面覆盖举证需求
我国民事诉讼针对某些特殊类型的案件,设置了举证责任倒置规定,环境污染诉讼也在其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4条第(三)项明确规定,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侵权责任法》第66条也规定因污染环境发生纠纷,污染者应当就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者减轻责任的情形及其行为与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环境污染案件中由侵权人承担举证责任的规定减轻了环境污染受害方的举证责任,但对于环境公益诉讼而言,这些规定还不足以解决举证负担的全部问题,其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狭隘性在于:
首先,将损害仅定义为实际损害,未包括损害的威胁。如前所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包括肉眼可见的现实损害,也包括将来的潜在损害。如果举证责任的范围仅限于损害,则意味着损害的威胁不在赔偿之列。而在许多环境公害案件中,实际的损害尚未产生,但将来的损害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损害威胁的举证也应当纳入举证责任的规定之中,否则不利于对公众利益的全面保护。
其次,举证责任倒置规定无法适用于损害威胁。举证责任分配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平与正义。民事诉讼按照一定的原则将每一类诉讼的举证责任预先在当事人之间分配,如果采用了正确的原则,分配结果将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但民事案件的类型多样,案件事实错综复杂,按照一定原则进行的分配无法保证每一具体分配结果都是妥当的。①李浩:《举证责任倒置:学理分析与问题研究》,《法商研究》2003年第4期。在环境污染案件中,当发生实际损害时,要求加害方举证,固然可以通过举证责任的倒置来平衡弱势方的利益保护;但在损害尚未发生仅存在损害威胁时,被告其实难以举证证明损害的威胁与其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事实证明,许多环境污染事件,除了造成财产损失外,对人类健康的长期危害是巨大的,但在短期内无法显现出相应的症状,需要原告方积极搜集并保存证据,证明环境污染对一个地区公民带来的损害威胁。如在某地,由于饮用水的污染,食道癌患者数量在近几年来明显攀升,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没有身患癌症的患者,也可以搜集这些证据证明饮用水污染对自己健康构成的威胁,并据此要求侵权方停止侵害恢复清洁水源。所以,在存在损害威胁的情况下,如果坚持侵权方举证责任倒置规定,反而会造成待证事实真伪不明。
再次,举证责任倒置是否剥夺受害方的举证权利有待质疑。对于环境公益受害方而言,利益受损表现在多方面,既有物质损害又有精神利益损失,既有实际损害又有损害威胁。如果狭隘地理解举证责任倒置规定,仅允许被告对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举证,剥夺原告方对因果关系的举证权利,则意味着原告方的许多利益无法通过行使举证权利获得声张,这显然不利于受害方利益的维护。
四、既判力界限尚未突破,环境公害相关各方的利益无法获得司法保障
既判力是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学的基本理论范畴,它指民事判决实质上的确定力,即形成确定的终局判决所具有的基准性和不可争性效果。原则上,既判力作用的主体范围,仅包括提出请求及与请求相对立的当事人。①吴明童:《既判力的界限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6期。当前,我国法律对既判力主体界限的扩张,仅局限在少数类型的案件中。如离婚和收养关系的判决,因身份关系的特殊而发生,其约束力和执行力不仅及于当事人,还对社会上的一切人和单位产生约束力。此外,公司诉讼、代表人诉讼、破产案件也会发生既判力主体界限的扩张。
然而,对于公益诉讼判决既判力的效力指向,我国法律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公益诉讼的原告来看,原告仅为形式上的当事人,即原告并不是与民事实体权利义务有利害关系或者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真正的符合法律条件的当事人并未参加诉讼,但判决书又直接涉及其民事实体权益。因此,公益诉讼的裁判效力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事诉讼既判力的主体界限。
另外,从既判力的时间界限来看,普通民事诉讼主要是针对以往行为,而民事公益诉讼还可针对诉讼时尚未发生而今后可能会发生的侵害行为,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起诉时侵权行为已经发生,但损害后果可能还未显现,但不可避免会发生。如果说传统民事诉讼是为了解决纠纷,那么民事公益诉讼则兼有行为调整和公共政策形成的功能。
公益诉讼要求公益判决书的既判力至少在主体范围和时间界限上有所突破,但从我国当前关于判决的效力规定来看,民事判决的效力尚未随着公益诉讼的设置而作出相应的变更。民事诉讼的判决,其约束力和执行力仍然仅指向诉讼当事人,不能对案外人发生法律效力,除非是一些需要协助执行的单位。如在房屋确权案件中,判决确认被告名下的房屋应归属原告的,则房地产登记部门应受判决的拘束,根据判决将产权过户至原告名下。但公益诉讼的判决书,客观上要求其效力指向应包括所有未参加公益诉讼但由原告所维权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果对于公益诉讼判决书的效力指向不作扩张规定,那么公益受害者的利益将无法通过公益诉讼获得司法保障。
五、公益赔偿金的领取、分配、使用与监督亦存在立法空白
公益诉讼若胜诉,必然会涉及损害赔偿及补偿问题。如果判决的救济方式除了停止侵害、恢复原状、消除影响以外,还存在赔偿金的,则对于赔偿金的领取、分配、使用与监督,还存在如下司法障碍:
1.由谁领取赔偿金。对于谁能领取和支配公益赔偿金,法律并未明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原告应当是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法律授权的诉讼主体,公益诉讼原告虽然在诉讼中成为了公共利益的代表,但代表者并不等于享有者。对公益造成损害而给予的赔偿金,应当由受害方共同享有。然而法律仅仅规定了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并未对公益赔偿金的利益归属主体作出明确。因此,谁有资格领取公益赔偿金将是公益诉讼判决执行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于公益诉讼往往涉及不特定多数人,由受害方领取赔偿金显然并不现实。赔偿金的领取是否仍然由法定的部门统一领取尚待明确。
2.由谁监督公益赔偿金的分配及使用。如果法律法规或司法解释能够确定领取赔偿金的主体,那么接下去要面临的问题是,赔偿金如何分配与使用并且如何接受监督。在昆明一起非法采矿的刑事案件中,安宁市国土资源局代表国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经法院主持调解,6名被告赔偿因破坏国家矿产资源造成的经济损失44.3512万元,该笔赔款支付给“昆明市环境公益诉讼救济专项资金”。①《昆明市第二例环境公益诉讼案审结,被告赔偿40余万元用于支付环境公益专项资金》,http://yn.yunnan. cn/km/html/2011-08/07/content_1761854.htm,云南网,2012年12月25日访问。在这起案件中,由于昆明设立了环境公益诉讼救济资金,赔偿金的领取主体获得了确立,但纳入专项资金的赔偿金是否得到合理分配与使用,还需要监督主体的参与。由于公益诉讼涉及一定区域内的共同利益,是该区域的受害方全体来行使监督权,还是由公益诉讼原告、相关的协会、社团,抑或是相关行政机关或案件管辖法院来监督,也有待法律统一规定。
3.由谁起诉赔偿金使用或分配中的不当行为?如果公益赔偿金分配不公或使用不当的,公共利益将再次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公共利益受害方是否能够享有诉权?在法治国家,有损害必有救济。如果因赔偿金的不当使用或分配不公影响公共利益的,受害方应当享有救济途径,无论是行政救济还是司法救济。如果允许司法救济的,那么谁将再次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这也将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除了上述司法障碍,还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基于私法自治原则,普通民事诉讼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而民事公益诉讼中,为确保公共利益不受侵犯,原告方的处分权应当受到一定限制,其和解、调解、撤诉等诉讼权利应受到一定程序的制约。因此,在环境公益诉讼中如何制约原告方的诉讼处置权,也需要精良的制度设计。另外,《民事诉讼法》第55条将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仅赋予法律规定的机关和组织,在这些机关或组织怠于行使公益诉讼起诉权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允许私人作为替代性主体,在有证据证明相关机关或组织拒绝提起公益诉讼的情况下,直接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正如康菲溢油事故中,如果将清污费、恢复生态治理费用、资源损失等列为公共利益损失,而环保法规定的相关组织怠于出面维护上述公共利益的,势必将影响广大渔民的捕捞权的实现以及将来的养殖产业的开展。此时,如果不赋予私人的起诉权或共同诉讼权,显然不利于社会公正的实现。
综上,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设的公益诉讼规定,扩大了民事诉讼的利益保护范围,在民事诉讼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然而在如何具体实施公益诉讼的问题上,《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第55条关于公益诉讼的规定十分概括,尚缺乏可操作的规则,其宣示意义远远大于实践意义。民事公益诉讼尤其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还面临着诸多司法障碍,许多难题亟待破解,需要尽早在诉的利益划分、精神损失概念延伸、判决效力指向扩张等领域进一步进行拓展和制度改革,从而探索建立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具体规则,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尽早付诸实践,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早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2013-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