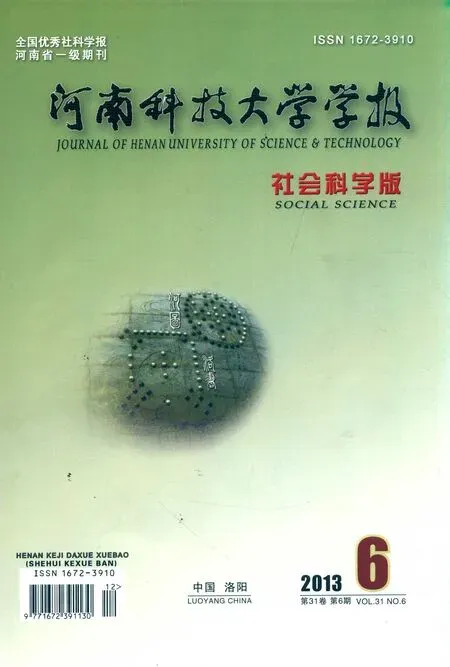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
——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杜鹏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14)
【艺文寻珠】
记忆、历史与“向死而生”
——论《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
杜鹏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南京 210014)
朱利安·巴恩斯的近作《终结的感觉》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对人生展开的回顾,借“死”来审视“生”。这部作品是一部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建构出的死亡叙事,凸显了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朱利安·巴恩斯;死亡叙事;“向死而生”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是当今英国文坛颇具才情的作家之一。早在1984年,他就以《福楼拜的鹦鹉》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普遍赞赏,其后作品获得众多文学奖项,并4次入围英国布克文学奖候选名单,最终在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摘取这一奖项,评委会主席斯泰拉·雷明顿盛赞《终结的感觉》为“真正的英国文学经典”,一本“写给21世纪人类的书”。这部作品一反巴恩斯惯常的后现代主义创作风格,情节简单,可读性强,这正是它获得布克奖的原因之一,作家用简约的笔风“将丰富的内容凝聚在短小的篇章之中”,[1]可谓字字珠玑,每次重读都会让读者的认识提高到新的高度。作品讲述了主人公托尼围绕好友艾德里安·芬恩的自杀对人生进行的回顾,全书分为两部分,上部是步入晚年的叙述者对前半生的回忆,好友之死占据记忆的重要位置;下部是叙述者对好友之死的探究,他不断纠正自己记忆的偏差,构建出截然不同于上部的人生故事。基于此,本文认为,《终结的感觉》是以死亡为参照展开的叙事,通过对个人记忆的还原和对私人历史的修正,探讨着死亡对个体生命的积极意义,透射出巴恩斯“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哲思。
一
《终结的感觉》是叙述者托尼通过诘问记忆而讲述的故事,“既是在回忆中写成,也是对回忆的心理特点的探究”,[2]2而死亡和他的记忆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死亡既是引发记忆叙述的原因,又是影响记忆叙述的元素。托尼进行回忆的动机源于死亡。他在退休后收到前女友维罗妮卡的母亲福特夫人的临终遗赠,包括五百英镑和好友艾德里安自杀前的日记,日记被维罗妮卡从信封中取走。日记的缺失使艾德里安的死亡成为不解之谜。理解这一谜团唯有借助对往事的回顾,因此,正是艾德里安和福特夫人的死亡开启了托尼的记忆之门。托尼的叙述开始于六幕彼此似乎全无关联的记忆片段,其中最后一个记忆片段“扇上了锁的门后,冰冷已久的浴水”是他的想象里好友艾德里安的自杀场景。[3]1死亡自开头就占据了托尼记忆的核心位置。艾德里安的自杀作为他生命的重要事件,引导着他对自己前半生最初的描述,将模糊、零落的记忆片段构建成完整、连贯的记忆之书,而随后对好友之死的探究将许多尘封的往事重新带入他的视野,为他所忽视或故意遗忘的细节不断浮现,冲击着这种原初的、完整的记忆幻象,最终改变了他对过去生活的印象。
托尼的记忆叙述不是对60年时光的平均分配,而是集中在自己的中学和大学时光,细述了与艾德里安在中学时代的相识、在大学时代的关系交恶,以及艾德里安的自杀。在谈到随后的婚姻、工作、离婚和退休时,作者仅用寥寥数页简单地概述。托尼的记忆描画出的生活呈现一种简单、完整、有“些许成就,些许遗憾”的略显乏味的状态。艾德里安的自杀虽然开始让他震惊,却因简单的阐释而“隐入了时间与历史的凹槽之中”,[3]72并不值得去深思和审视。然而,在结束追忆之后,托尼意识到:“记忆现在越来越像个机械装置,只是反复地重现那些貌似确凿的数据,鲜有变化差异。”[3]83他的记忆变成一种单调的重复,原因在于记忆叙述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是独白性话语,讲述着个人理解中的过去,所有无法为个人所诠释或异于个人理解的事件或言语会被间接地引述甚至全部省略,正如美国叙事学家詹姆斯·费伦所定义的,这种话语是“单个声音,因而是狭隘和只有单一价值的话语;不能接纳其他观点的话语”。[4]采用这种话语的叙述者有着强烈的主观性,会以自己的前见来建构对事件的讲述,托尼承认他的回忆并非对往事的真实再现,而是“我(托尼)现在对当时所发生的一切的解读的记忆”,[3]54就像他在做爱后与女友维罗妮卡分手,却将之解读为“我们分手之后,她和我上了床”,[3]47借以摆脱自己的道德责任。由此可见,他的记忆受制于个人偏见,满足着隐秘的、不可示人的个人利益,对它的叙述无疑会因为个人偏见而循环往复。
然而,死亡视野的引入修正着记忆叙述的偏差。托尼对艾德里安自杀的探究赋予他反思人生的认真态度,使他意识到必须纠正自己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而对记忆进行的调整、改动与删除,[3]54从而打破记忆的单调循环。自杀使艾德里安成为必然的不在场,与此同时,托尼也无法得到他临终前的日记,两者的缺失意味着托尼需要在记忆深处不断挖掘,“诱使自己的记忆走入另一个不同的轨道”,[3]83这样才能真正理解艾德里安自杀的行为,而不是自己以前作出的随意阐释。
在对艾德里安自杀的反思中,托尼直接引述着与自己的原初记忆相冲突的话语,其中既有维罗妮卡对他过去行为的责备,又有昔日写给艾德里安的“丑陋粗俗”的绝交信,[3]126所有这些都指出他对艾德里安的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在不同话语的对话中,托尼认识到“记忆是那些我们以为已经忘记的事情”,[3]82因而得以寻回“被遗忘的记忆”。[3]151在托尼原初的记忆中,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占据中心位置。前者操纵他的感情,使他不得不与之分手;后者与维罗妮卡的恋爱背叛了他的友情,他们卑鄙的行为赋予托尼一种“温和派”的受害者形象。[3]45然而,唤回的记忆纠正着往昔印象的偏差:40年前,他与维罗妮卡“是多么迷恋对方”,他们的性生活充满“爱抚、温柔、坦诚、信赖”,[3]151他们曾经“坐在湿淋淋的河边一块湿漉漉的毯子上,十指相扣”观赏赛文潮,而他的叙述却将她从这一场景中“抹去”,[3]153是他的不负责任和畏缩不前最终破坏了两人的感情;在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交往并告知他时,他发出一封满是恶毒诅咒的绝交信,断绝了与艾德里安的友情,也是这封信阴差阳错导致了艾德里安的自杀。
以死亡为参照的叙述,其最终意义在于纠正了时间带给记忆的扭曲变形。时间宰制记忆,在托尼看来,岁月的流逝一方面让他“听天由命,随波逐流,放弃审视人生”,[3]129另一方面又剪除着“人生的见证者”和证明记忆的“基本证据”。[3]127然而,在思考好友之死的过程中,托尼获得了超脱的死亡视野,消解了时间对记忆的干扰。艾德里安的自杀让他真切地体会到死亡的神秘,已过花甲的叙述者强烈地意识到人生必然走向的终结,对死亡的思考使他可以站在人生的终点,跳脱出时间带给个人的麻木状态,从而以一种严肃的姿态来审视过去。学者弗兰克·克莫德在《结局的意义:虚构理论研究》中认为:“对结局的预测反过来会影响到对初始和中间阶段的理解。”[2]14艾德里安的自杀将结局确凿无疑地摆在托尼面前,对死亡的意识成为他重新反思人生的出发点,让他认清了隐藏在时间之中的个人偏见,还原出对过去的真实印象。
二
巴恩斯一向质疑公认的宏大历史,他先前的作品“关注真实存在于史料外的个人和民族历史”,[5]如《福楼拜的鹦鹉》中关于福楼拜的三部相互矛盾的年表和《10·章世界史》里木蠹虫对“挪亚方舟”去崇高化的叙事。而《终结的感觉》则是“借个人记忆而探讨真实史料外没有文献记载的史实”,[5]历史不再是关于社会或民族的宏大叙事,仅指涉虚构的私人历史,用托尼的话来说,是“我们自己那微小、私密、基本无从记录的历史”。[3]78这里的私人历史尽管微不足道,少有人见证,却能反映个体对自我生命最本质的感悟。
《终结的感觉》存在着两种对立冲突的历史观,反映在托尼和艾德里安对历史老师亨特提出的“历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托尼脱口而出:“历史就是胜利者的谎言。”[3]20四十年后他又改变了这一观点,认为“历史……是幸存者的记忆”,[3]73前后两种观点表面看似不同,其实都将历史等同于人们对过去的主观阐释,一种单方面叙述,这与新历史主义者海登·怀特的主张相似,没有真实、客观或正确与否的历史,只有讲述者对历史的想象,历史与有意识的虚构相距不远。[6]与之相反,艾德里安则说,“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3]20就是说,外部史实将不断纠正人们的主观阐释,使历史叙述具有一定的客观性,而这符合巴恩斯的一贯看法,历史真实依然存在,正像他在《10·章世界史》中写到的:“我们还是必须相信,客观真实是可以得到的;……我们必须相信43%的客观真实总比41%的客观真实要好。”[7]相异的历史观分别建构出作品上下两部里不同的私人历史,显示出历史建构的复杂性。
作品第一部分是托尼对自己历史观点的实践,通过记忆建构出的私人历史与个人偏见和切身利益紧密相连,是一种主观历史。在这部私人历史中,他是一副温和、对人友善、没有多少过错的普通人形象。维罗妮卡则是满腹机巧的妖女模样,“魅惑迷人,神秘莫测,吹毛求疵”,[3]177玩弄他的感情,以性爱为手段操纵他,这就使两人的分手成为必然,而他作为受害者,不用承担任何道德责任,面对维罗妮卡的“强奸”指责,他一口否认。托尼的记忆赋予艾德里安一副高大的哲学家形象,他的自杀是其哲学思辨的选择:“他是我们这几个人里最较真的、最有哲学思想的:遗书里他写明的原因,就肯定是他自杀的真实原因。”[3]68自杀成为艾德里安的个人选择,与周围的人们没有任何关系,自然排除了托尼在这一事件可能负有的责任。同时,自杀的原因不再是一个谜,就没必要对之加以探究,托尼可以把它当作生活的插曲抛之脑后。平凡的私人历史像是托尼自我开脱的证词,隐藏在对维罗妮卡妖魔化、对艾德里安崇高化背后的,是他对自我责任的逃避和复杂人生的无视。
托尼的记忆叙述是间接引述别人的话语,外部史实经过他有意识地处理和改动已成为记忆的一部分,不可能与之“相遇”乃至碰撞;而在作品第二部分,当托尼探究好友自杀之谜时,外部史实原封未动地直接进入他的叙述,与他先前的记忆完全不相一致,在两者的冲突与对话中,客观的私人历史得以呈现。福特夫人的遗信暗示艾德里安自杀的神秘,使托尼开始重新审视这一事件。他从维罗妮卡手中得到艾德里安的日记片段,指明自己与艾德里安的自杀有着莫大的关联,促使他检视人生的错误。维罗妮卡保存着他早年写给艾德里安的绝交信,在40年后重新交到他的手中,信中他破坏两人恋爱关系的卑鄙企图颠覆了记忆叙述赋予他的无辜形象,被他有意遗忘的记忆片段不断出现在他的叙述中,修正着他精心建构的记忆。最终,艾德里安和福特夫人结合所生的智障儿彻底改变了托尼的主观历史,孩子的缺陷既是托尼在绝交信中恶毒诅咒的实现,又是他叵测建议的结果,正是他建议艾德里安向福特夫人“问清楚她(维罗妮卡)曾经所受的创伤”,[3]192促成了两人的结合,因此他对艾德里安的自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零零散散的外部史实消除了记忆叙述对过去的修改和扭曲,一点一滴地还原出客观真实。
历史既然由叙述而产生,那么叙述者的可靠性也决定着历史真相是否可以呈现,通过对好友之死的探究,托尼实现了从不可靠的叙述者到真诚的悔悟者之转变,讲述出真实可信的人生故事。《终结的感觉》上部采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年老的叙述者托尼放弃自己目前的视角,不露痕迹地采用当年作为人物的“托尼”的视角,然而当年的他既受偏见的干扰,又因视野的限制,显然无法展现过去真实的面貌,在“事实/事件轴”上作出了“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8]134因此是一位靠不住的叙述者,尽管他的不可靠性因为没有其他话语的“挑战”而不为读者所知。在作品下部,托尼不再追忆往事,而是直接讲述探究艾德里安自杀之谜的经过,把外部史实和维罗妮卡的见证完整地引入叙述之中,形成与先前的记忆相冲突的话语。写给艾德里安的绝交信凸显出托尼记忆叙述的不可靠,促使他成为一位真诚的悔悟者,“生平第一次……开始对人生——我(托尼)的全部人生——心怀悔恨”。[3]129态度的转变带来叙述话语的改变,托尼点点滴滴地寻回刻意遗忘的往事,一方面填补着人生故事的空白,另一方面修正了记忆叙述的偏差,最终再现出完整真实的私人历史。
三
死亡是巴恩斯笔下热衷探讨的话题,比如《福楼拜的鹦鹉》细致描述福楼拜的病终,《10 1/2章世界史》展示恐怖主义者的杀戮和核战争造成的人类灭绝,《没什么好怕的》谈论亲人们真实的亡故经历,死亡层出不穷地出现在他的作品里,难怪有评论家指出,巴恩斯具有浓厚的“死亡情结”。[9]82正如作家在一次采访中坦言:“如果我写死亡……它必须与我个人相关。”[10]他是以一种私人化的、存在主义的眼光看待死亡,将其视作个体的切身经历,一种“筹划人生“的途径。[11]在《终结的感觉》中,好友的亡故成为托尼阐释和界定自我生命的方式,正体现了一种“向死而生”的存在状态。
“向死而生”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提出的看法,他认为生命就是“向终结存在”,死亡作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悬临”于每个个体,[12]赋予存在以意义。换言之,“正是死亡和对死亡的意识,使生命获得了另一种性质……本己存在仅仅在于对确定无疑然而又是不确定的死亡的等待与忍耐之中。”[13]死亡既是存在的宿命,又是存在的共性,了解死亡必然带给个体更通彻的人生视野。托尼对好友之死的反思与这种“先于彼岸思辨阐释此岸”的死亡观点不谋而合,[14]14步入晚年的叙述者感到时光的流逝,而好友的自杀让他拥有对死亡的真切体会,因此,对终结的知觉成为他最本真的生存体验,探究好友之死正是在直面死亡的前提下,以清醒的终结感对个人记忆进行梳理。抽象的死亡带给年迈的托尼一种紧迫感,在他看来,“人生剩余的时间越少,你越不想浪费时间”,[3]88而对艾德里安自杀的探究又使他经历着真实的死亡,从而以一种严肃的态度审视过去,纠正个人偏见的干扰,重新建构对自我和人生的完整认识。
萨特认为死亡是“由他人代为保管的生命”,[15]也就是说,对别人死亡的态度决定了对自身生命的理解,叙述死亡就成为理解存在的最好方式。艾德里安的缺场使他的自杀成为一个别人永远无法解释的谜,因此,托尼的叙述并非是对好友死亡之真相作出推测,而是尝试去探寻好友死亡之意义,在他的叙述中,艾德里安从一个依从理智和逻辑的哲人变成一个挣扎于激情与道德之冲突的普通人,他的自杀也不再是践行信念、抗争命运的崇高举动,而变得不为可知,生活显示出其复杂多变、扑朔迷离的本质,理解“死”逐渐转变为反思“生”。这些观点的改变表明托尼最终意识到存在的玄奥,获得了认识上的飞跃。对托尼而言,尽管死亡意味着“生命中任何改变的可能性的终结”,[3]192生命却不再是日益走向终结的单向旅程,个人叙述通过赋予死亡以意义,指引着人生的进程,从而使生命成为一种充满变化的开放结构。
《终结的感觉》的死亡叙事是通过还原个人记忆和修正私人历史而展开的,它的意义在于促成叙述者的自我改变。自我源于记忆,并非稳固不变。原初的记忆造就了托尼狭隘的自我,使他缺少对人生严肃的反省和对他人真正的理解。在探究好友之死的过程中,托尼认识到人生故事经过他的“调整、修饰,甚至巧妙地删剔”,[3]123已经成为自欺欺人的谎言,导致他“中等就好”的心态,掩盖其“生命平庸,真理平常,道德平凡”的存在状态。[3]130由此产生的悔悟引发记忆的还原,带来真实私人历史的回归,托尼把握到人生的“累积、”“责任”和“动荡不安”,[3]193意识到自我生命与其他生命间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了生活里无限改变的可能。他变得具有同情心,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人生,最终完成了对过去自我的超越。死亡叙事开始于艾德里安的自杀,却结束于托尼的个人成长,死亡成为存在观望自身的参照,凸显出终结对人生具有的积极价值。
四
巴恩斯曾说,“对死亡的恐惧是我生命的一个根本组成部分”,[16]在他以往的作品里,死亡作为一种无可避免和不可逃避的结局总是带给人生无奈与绝望,而《终结的感觉》却是对这种死亡观点的超越,作家并不执迷于死亡的奥秘,反而借助死亡来反观生命,认识到终结对存在具有的积极的建构意义,这成为他摆脱死亡恐惧的一种尝试。在《终结的感觉》中,叙述者托尼探究好友之死的过程正是他重新审视人生的实践,对死亡的清醒意识赋予他一种超脱于时间和个人偏见之上的思辨的视野,从而纠正着个人记忆的偏差,还原出客观的私人历史。伴随死亡的叙述,托尼完成了自我的改变,开始了人生的又一次成长,终结不再是消融意义、消解存在的虚无,而是人们得以反思过去、认识到生命开放性的契机。由此可见,与海德格尔“挖掘出死亡的积极性”“却将存在抛入虚无中”不同,[14]14巴恩斯以独特的死亡叙事消解了死亡置于存在的荒谬境地,展现出“向死而生”具有的一种积极意蕴:死之玄奥固然不可穷尽,然而,叙述死亡却可成为审视生命、把握存在的最好方式。
[1]Brown Mark.Booker prize 2011:Julian Barnes triumphs at last[J].The Guardian.19 October,2011. http://www.guardian.co.uk/books/2011/oct/18/booker-prize-julian-barnes-wins?newsfeed=true.
[2]陆建德.回忆中的“新乐音”[M]//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导言.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3]朱利安·巴恩斯.终结的感觉[M].郭国良,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4]詹姆斯·费伦.作为修辞的叙事[M].陈永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72.
[5]毛卫强.小说范式与道德批判:评朱利安·巴恩斯的《结局的意义》[J].当代外国文学,2012,(6):119-126.
[6]海登·怀特.后现代主义历史叙事学[M].陈永国,张万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9-40.
[7]朱利安·巴恩斯.10%章世界史[M].林本椿,宋东升,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227.
[8]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4):133-143.
[9]张莉,郭英剑.直面死亡、消除虚无——解读《没有什么好怕的》中的死亡观[J].当代外国文学,2010,(3):81-88.
[10]Kate Summerscale.Barnes Julian,Julian Barnes:Life as He Knows It[N].The Telegraph,2008-03-01.
[11]段德智.西方死亡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36.
[12]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310.
[13]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88.
[14]陈民.西方文学中死亡叙事的审美风貌[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15]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7:693.
[16]Barnes Julian.Nothing to be Frightened of[J].The Oxonian Review.By Scarlett Baron.15 June,2008. http://www.oxonianreview.org/wp/nothing-to-befrightened-of-an-interview-with-julian-barnes/
Memory,History and“Being-towards-death”——On Death Narration of“The Sense of an Ending”
DU Pe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Nanjing University,Nanjing 210014,China)
Julian Barnes’latest work in 2011,“The Sense of an Ending”,relates the narrator’s recollection of past life during his investigation of his friend’s suicide.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death narration of the novel which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narrator’s examination of individual memory and personal hist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death for personal existence by application of death narration and interprets Barnes’existentialism of“being-towards-death”.
Julian Barnes;death narration;“Being-towards-death”
I106.4
:A
:1672-3910(2013)06-0063-05
2013-06-28
杜鹏(1984-),男,河南南阳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当代英美文学及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