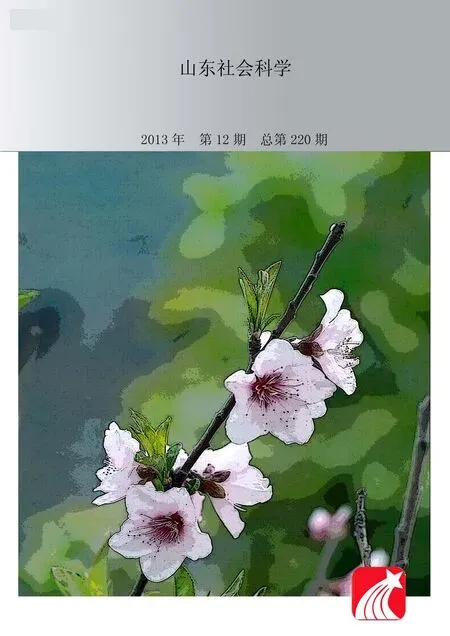博尔赫斯诗学中梦元素的精神分析阐释
陈 博
(中国矿业大学 文学与法政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在人类文学发展史上,梦与文学的关系可谓千古难题。作家因梦为文、写梦成章的例子有很多。梦既是作家表现的对象或主题,也是推动作家创作的动力。梦境、梦象、梦体验不仅拓展了文学表现的空间,而且丰富了文学创作的题材。梦是现实的移置、扭曲和变形,带给作家和读者强烈的审美体验。梦的虚幻性使得它的起源和产生具有了神秘化的色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之前的人们认为梦是真实而有意义的,它们是神谕,来源于神的恩赐,是神灵的启示,代表着超自然的力量,所以,人们相信梦,常用占梦的方式来预测吉凶或未来。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神赐或“神灵凭附”的观点,认为“梦是一种精神影像,它发生在睡眠中”①[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同人在睡眠活动中感官感知对象所产生的感觉印象的刺激有关。亚里士多德的梦学说强调梦属于人类的精神法则,他的观点将梦从神秘的哲学探讨引入心理学的研究,而最终将梦的研究引向科学化道路的是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荣格等。
作为享誉世界的文学巨擘,博尔赫斯的生活经历和文学创作与梦有着密切的关系。梦与阅读、写作一起构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而且,梦还是他体验事物、制造美的经验所在。可以说,他的生命因梦而精彩,他的生活因梦而改变,他的思想因梦而深刻,他的文学因梦而飘逸,他的写作因梦而厚重,这就是博尔赫斯,一个爱做梦的诗人,一个为梦所苦恼的凡人,一个喜欢写梦的作家,一个思考梦的哲人。博尔赫斯将他对梦的思考融入自己的诗学理论和诗学实践中,从而形成了自己玄幻奇美的创作风格。
一
梦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离不开人的生活、记忆和体验。弗洛伊德在《释梦》中指出,梦的本质是“欲望的满足”②[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9页。,是那些被压抑到无意识中的欲望趁着人在睡眠时稽查作用的放松进入人的意识层面所形成的。对博尔赫斯来说,“梦”既虚幻又真实。所谓“虚幻”是指梦的产生与形成机制让他感到十分神秘;所谓“真实”是指他的梦体验,他几乎每隔一天就做一次梦,而且梦象颇为清晰。但是,梦的生活和醒的生活不同,梦的生活和睡眠相关,睡眠是梦的第一特性,“梦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区别于醒的生活,梦似乎是介于睡眠和苏醒之间的一种情境。”[注][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61页。这种情境使梦显现出极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博尔赫斯认为,梦是一种创造,梦中的一切都源于梦者,梦是梦者创造的,这一点和醒不同,虽然醒也可以是一种创造,是另一种状态的经验,但是“醒时的经验与睡时或梦中的经验有本质的不同,其不同之处一定在于,梦中所经验到的东西由你产生,由你创造,由你推演而来”[注][美] 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虽然梦和醒截然不同,但是“白日梦”(又称“昼梦”)却将二者结合起来,指称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想象。白日梦和夜间的梦相对,是幻想的产物,和睡眠无关,常见于儿童期,比如儿童幻想长大成人、玩成人的游戏等,它在成人中也存在着。白日梦的内容往往和某种愿望和动机直接相关。弗洛伊德认为,作家的创作可以用普通人的经历来解释。作家的写作活动和儿童的游戏有着相似之处,即他们都以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想象的世界和真实世界的区别,用游戏将真实可感的事物和想象的事物联系起来,从而带来快乐和乐趣。随着儿童长大成人,他会停止游戏,但他不会放弃快乐的感觉,而是变换了一种形式,“以幻想代替游戏。他建造空中城堡,构造被称为白日梦的东西”[注][奥]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95页。。儿童游戏的愿望不用掩饰,成人的幻想羞于启齿,被压抑到无意识领域,以梦的形式表现出来。弗洛伊德还将富有想象力的作家和白日梦者、富有想象力的作品和白日梦相比较,指出“一篇创造性作品像一个白日梦一样,是童年期游戏的继续和替代”[注][奥]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1页。。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活动,将白日梦一样的作品呈现给读者,从而给他们带来类似于童年游戏一样的快乐体验。不同的是,作家运用艺术技巧将他的目的与企图隐藏起来,淡化了白日梦的利己主义性质,通过纯粹的美学形式将自己的幻想表达出来,最终将快乐传达给读者。这是作家所提供的一种美学快乐,能够帮助读者消除精神紧张,释放精神深处深层的快乐,获得审美愉悦。
博尔赫斯童年时,受家族祖先英雄事迹和父亲的影响,渴望成为作家,因此,“作家梦”是童年博尔赫斯最重要的“白日梦”。另外,还有很多关于游戏的白日梦。随着他长大成为一名作家,“白日梦”并没有消失,而是被他写入作品中。博尔赫斯的作品虽然充满神秘的色彩,但很多素材和内容都有他本人的影子,且不说他的自传性小说,单是其作品中大量运用的童年记忆的书写就表露无遗。弗洛伊德说:“一种强烈的现实体验唤起了作家对先前体验的记忆(通常属于童年期),从这个记忆中产生了一个在作品中获得满足的愿望。作品自身展示为最近的诱发场合和旧时的记忆两种因素。”[注][奥]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0页。镜子、老虎、匕首、牛头怪、迷宫、失明等之所以不断地进入博尔赫斯的梦和作品中,皆与博尔赫斯童年的记忆有关,它们曾给童年的博尔赫斯带来欢乐和愉悦。后来,它们遇到合适的诱因就会出现在博尔赫斯的梦中,赋予他真切的生命感受,促使他用诗化的语言汇成篇章,成为作品中的审美幻象。
二
在对作家的认识上,博尔赫斯提出作家是“不断做梦的人”[注][美] 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的诗学主张。这种观点的形成源于他对世界万物的认知和对写作活动的体悟。在他看来,世界是一个梦,是不可知的,万物是虚幻的,写作就是将一些素材加入这个梦中,赋予梦以形式,丰富这个梦。因此,作家就是写梦者,作家通过对梦的表现构筑“梦一般的虚构的世界,也就是通过写作行为营造出来的梦境”[注][日]古谷利裕:《梦中梦——作品的框架与二人配》,史姬淑译,《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7期。。
关于梦与文学艺术的共通性,弗洛伊德认为,从本质上说,二者都是人的欲望的实现;从形式上看,二者都是由显象与隐意组成的;从研究的目的来看,二者都是为了发掘潜在的意义。作为一个喜欢梦的作家,博尔赫斯一方面肯定了梦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幻想与梦的相似性。在他看来,当一个人陷入沉思构造作品时,那种凝神静思的状态和睡眠做梦的状态没有什么不同,有时梦就存在于作家的幻想或文学中,或者说,幻想、文学中都带有梦的影子。博尔赫斯将文学视为和梦紧密相连的存在形式,提出“文学是有引导的梦”[注][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页。的诗学观,进而将文学创作和梦的工作机制联系起来。
弗洛伊德指出梦的工作方式有四种,分别是压缩、移置、意象和润饰。它们对梦材料的加工和处理同文学创作中的想象活动差不多。博尔赫斯认为,想象是引导梦进入文学的重要途径,“想象是由记忆和遗忘构成,它是这二者的交融”[注][美] 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想象无处不在。博尔赫斯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在他的记忆库中,充满着大量神话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文学的、历史的信息,他所做的工作就是将这些信息创造性地分类并编撰成篇。
遗忘和记忆相对,表示不能正确地回忆和再认识曾经识记过的材料或知识。对个体而言,幼年的经验容易被遗忘;对种族来说,初期的经验容易被遗忘。遗忘有暂时性的和永久性的区分,但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被召回。博尔赫斯所说的遗忘是一种信息的潜在状态,指先前的经验信息积淀在个体或集体的记忆中,蕴含着个体和集体的原始记忆,有时候会出现在人的梦境、幻想及其他精神现象中。这种记忆在叶芝那里被称为“非凡的记忆”,在荣格那里指“原型的记忆”,在博尔赫斯这里则被视为文学创作源泉的潜意识,他说,潜意识“不仅是个人的记忆,而且是长辈们的记忆,可能也是原型的记忆,总之,一切都是那么神秘……但是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注][阿根廷]博尔赫斯等:《波佩的面纱》,朱景冬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博尔赫斯肯定遗忘对梦的引导作用,实际上是肯定那些作为人类集体无意识而存在的记忆信息对文学的作用。这种认识已经超越了弗洛伊德意义上的个体潜意识。
噩梦是博尔赫斯经常遇见的一种。噩梦带给他的是像真实的切肤之痛一样不可忍受的精神痛苦,让他通读了很多心理学著作,并形成了自己关于噩梦的看法。他认为,噩梦和其他的任何梦不同,它“或许是夜的寓言”,“或许是夜的幽灵”,许多著名的文学大师,如莎士比亚、德·昆西、卡夫卡、爱伦·坡等都描写过噩梦。虽然噩梦带给他苦恼,但他并不拘囿其中,而是将它们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加以审视。在他看来,噩梦是一种奇特的存在,当人们悲伤时,却没有噩梦,没有神秘与恐惧感,只有噩梦会使人们产生这类感觉。噩梦的这种奇特之处,使他禁不住发出这样的感慨:“噩梦,这梦之虎。它使我们产生的特殊的恐惧与我们醒时所获得的任何感觉都不同;而这恐惧或许正是对于地狱的一种预感。”[注][美]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由此可以看出,噩梦带给博尔赫斯的是地狱般的恐惧,这种恐惧就像他儿时对老虎的认知体验,所以,当谈论梦时,他主张将梦与噩梦联系起来,将梦与老虎联系起来。噩梦除了给博尔赫斯恐惧的存在体验外,更重要的是,博尔赫斯将其升华为个体审美视域中文学创造的启迪和灵感,他的很多优秀的小说、诗歌都来自噩梦,“并且以自己的独特方式对之进行了表达”[注]王宁:《世界主义及其于当代中国的意义》,《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6期。。他将噩梦视为作家创作的一种工具和原材料,“噩梦也是一种工具。我有好多小说的灵感都得自于噩梦”[注][美]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51页。。他认为作家的任务就是用文学形式把它们表现出来,将它们转化成小说或诗歌。博尔赫斯有三个基本的噩梦,即迷宫、写作和镜子,它们成为博尔赫斯创作的动机和来源。
总之,在博尔赫斯的生存镜像中,文学、梦、幻想赋予他独特的生命体验。他因宿命的安排选择了文学之路,混乱虚幻的现实和虚妄的人生使他沉潜于幻想的游戏之中,日常生活中的梦体验促使他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写梦、表现梦。于是,文学、梦、幻想在博尔赫斯的创作中成为相互融合的存在。
三
在文学实践中,博尔赫斯创作了许多类型的梦,常见的有循环梦、蝴蝶梦和原型梦。
“循环梦”是博尔赫斯经常使用的形式,即梦是循环的、重复的。博尔赫斯作品中,有许多这种循环的梦,如为祖国献身的梦,20世纪20年代博尔赫斯在诗歌《伊西多罗·阿塞韦多》中详细地描写了外祖父阿塞韦多临死前所做的为国献身的梦,20年后这又在小说《另一次死亡》中再次循环出现。这个为国献身的循环的梦里还有另一个循环的梦,即时间的梦,在这两个故事背后,都表现了博尔赫斯将现在与过去相交叉的时间概念,体现了循环的时间梦。这种循环的梦是博尔赫斯从英国诗人柯勒律治那里得来的。他专门写过分析柯勒律治梦的文章,即《柯勒律治的梦》。“柯勒律治的梦”的具体内容如下:1797年夏,诗人柯勒律治在一个农庄小住时,由于身体不适而吃了安眠药,睡前他读了英国教士珀切斯写的游记中有关忽必烈汗修建宫殿的事。在梦中,他得到了一首关于忽必烈汗宫殿的诗,醒后,他根据梦中诗的样子写了《忽必烈汗》。20年后,人们在巴黎发现的14世纪的著作《历史简编》(拉什德·艾德丁编写)中看到忽必烈汗依梦建造宫殿的记载。1691年耶稣会教士格比隆证实了忽必烈汗的宫殿只留下了遗址,而那首诗也只记下50多行。同样一座宫殿,在不同世纪、不同国别的人的梦中出现,从而造成了梦的循环。对此,博尔赫斯说:“一位13世纪的蒙古可汗梦见一座宫殿,根据梦中所见修建了宫殿;一位18世纪的英国诗人不可能知道那座宫殿的蓝图是一场梦,却梦到有关宫殿的诗。睡眠的人心灵感应,跨越空间和时间造成了对称,与之相比,宗教书里提到的白日飞升、死而复生和鬼魂显露依我看就算不上神奇了。”[注][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王永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49页。博尔赫斯指出,和柯勒律治梦中得诗一样,历史上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例子。如英国心理学家哈弗洛克·埃利斯(1859—1939)在《梦的世界》中提到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演奏家朱塞贝·塔尔蒂尼(1692—1770)梦到魔鬼演奏的小提琴奏鸣曲,醒后他根据不完整的回忆整理出了《魔鬼的颤音》;作家罗伯特·斯蒂文森在梦中得到《化身博士》的故事情节;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诗人凯德蒙在梦中得到创世的诗句,醒后,不识字的他向希尔德寺院的僧侣们复述,在僧侣的解释下,他唱出了整个《创世纪》的故事,并成为英国的第一位诗圣等。在这些例子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循环的梦,即关于艺术创作的循环的梦。那么,该如何理解这种循环的梦呢?博尔赫斯认为,在这两个梦的背后,有一个先验的图式在起作用,即在巨大的时间间隔中或许有一个超人执行者存在,但是任何企图寻找这个超人执行者的做法都将是荒谬的,也是不可能的。
“蝴蝶梦”的首创者是我国古代著名哲学家、思想家庄子。博尔赫斯非常服膺庄子,把他尊为“幻想文学的鼻祖”。博尔赫斯对蝴蝶梦的认识源于“庄周梦蝶”的故事。《庄子·齐物论》中详细记载了庄子所做的千古奇梦,“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注]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页。这个故事受到很多精神分析学家和研究者的厚爱,其中的庄周和蝴蝶与弗洛伊德的“自我”和“本我”、“意识”和“潜意识”是相通的。在梦中,庄周梦见自己化成一只翩翩飞舞、悠闲自在的蝴蝶,却忘了自己是庄周,体现出“本我”战胜“自我”、潜意识得到满足后“生命获得自由和超越”[注]任者春:《论教学大美的实现路向——老庄大美思想的教学启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2期。的快乐状态。但是,这种状态不会恒久,因为是梦总会醒来,所以,当“本我”退隐、“自我”意识重新恢复后,庄周陷入了现实的困惑之中。因为他搞不清到底是自己做梦化为蝴蝶,还是蝴蝶做梦化成自己。在这个故事中,庄子表现了一种物化的哲学思想,即主客体、人和外物和谐共存的状态,从而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审美感受。博尔赫斯非常喜欢这个故事,在他的梦体验中,经常出现类似“庄周晓梦迷蝴蝶”的情形,他说:“我总是按时醒来。但有时我梦见我醒来,发现我还在同样的街角上或同样的房间中或同样的沼泽地里,被同样的雾气包围或注视着同样的镜子——于是我就知道我并没有真正醒来。我接着做梦直到我醒来。”[注][美] 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这里所表现的那种突然醒来,或者有时梦见自己醒来,因思维依然沉浸在梦中而茫然失措的样子和庄周迷蝶的情形十分的相似。“庄周梦蝶”的故事在博尔赫斯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如在诗歌《漆手杖》中,他写到了庄子的梦:“我看着那根手杖,想起了那位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醒来之后却不知道自己是梦见变成蝴蝶的人还是梦见变成人的蝴蝶的庄周。”[注][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诗歌卷(下)》,王永年、林之木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296页。在散文《时间的新反驳》中,他引用了“庄周梦蝶”的故事来说明单纯的梦的时刻,反对将空间引入时间。在小说《1983年8月25日》中,84岁的“他”在和61岁的“我”的谈话中说:“究竟是谁梦见谁呀?我知道我梦见了你,但是我不知道你是否在梦见我。”[注][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小说卷》,王永年、陈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75页。其实,庄周、博尔赫斯的“蝴蝶梦”表现的梦者和梦中镜像构成的交互主体性象征关系网络也蕴含着他们关于幻象与真实的哲学之思。只有在语言构筑的象征性现实中,庄周与蝴蝶、84岁的博尔赫斯与61岁的博尔赫斯才能成为同一性的存在。而庄周由愉悦到疑惑的梦知觉与博尔赫斯迷惘的梦体验也体现出个人主体对生存现实幻象的思考,因为“梦里往往呈现了个人主体最真实的欲望对象,这种对象是建构全部现实生活的幻象支撑点”[注]张一兵:《意识形态幻象对伪现实的支撑》,《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1期。。正是由于有了梦的存在,才使得很多理论家、作家去探讨或表现梦境以及梦与现实的关系。
“原型梦”是博尔赫斯从荣格那里获得的启示。荣格将人格的整体称为“精神”,认为精神是由意识、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组成的。意识指被自我体验认可的东西,被压抑的则形成“个人无意识”,留存在人脑深处储藏原初意识的场所则是“集体无意识”,它既不是来源于个体经验,也不是后天习得的,而是先天存在于每个人身上。“集体无意识”概念使荣格的理论和弗洛伊德所主张的潜意识的私人性区分开来。弗洛伊德虽然承认在梦中会偶尔出现某些古老的遗迹,但他认为这对人的思维结构的发展不具有什么影响,人的思维结构是在成长中形成的。荣格则认为集体无意识是人类一切现有行为的基础,它的存在可以从世界各地不同种群之间有着相同的神话、仪式、艺术和象征中体现出来。集体无意识“使人的心灵本质有了整个人类历史积淀的深度,而不是局限于个人的历史性,并且这种先验遗传的历史积淀构成了原型”[注]贾澎:《荣格象征理论的语言学诠释》,《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2期。,因此,原型是所有与之相似的事物都模仿的最初模式,与柏拉图的理念同义,是对柏拉图理念的解释性释义。[注][瑞士]荣格:《原型与集体无意识》,徐德林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版,第6页。原型作为一切心理反映的普遍形式,广泛存在于宗教、神话、哲学、科学等人类文化的领域。博尔赫斯是荣格的忠实读者,在解释柯勒律治梦中得诗和忽必烈汗梦到宫殿这两件跨越不同时空的循环之梦时,曾引入了荣格的“原型”概念,只不过他将其置换成了“标准型”,他说:“也许有一个人所未知的标准型,一个永恒的事物(引用怀特海的说法)正在缓缓进入世界,它第一次表现于忽必烈汗的宫殿,第二次表现于柯勒律治的诗。凡是把两者作过比较的人都会看到两者本质相同。”[注][阿根廷] 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王永年等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50页。由此来看,博尔赫斯的“标准型”和柏拉图的“理念”、怀特海的“永恒客体”、荣格的“原型”概念是一致的,用以表示永恒不变的绝对实体和本源。博尔赫斯认为正是这种“标准型”进入他们的梦中,才使他们在不同的情境下梦到了相同的梦。博尔赫斯的创作中也有很多“原型”,比如他的武士小说或关于匕首的小说其实就是对那些潜藏在他的意识深处的“家族神话”乃至远古英雄神话原型的体现。此外,还有以迷宫、死亡、时间等为主题的作品,也是“原型”的体现。可以说,这些“原型梦”的存在,为博尔赫斯的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可以说,博尔赫斯写梦的创作实践极大地丰富了梦与文学的艺术宝库,带给读者极大的审美体验和美学快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有的精神分析学家——如弗洛伊德——未能深入探究作家表现梦的技巧或手段的缺憾。因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虽然肯定了作家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对于作家摆脱现实的羁绊、发挥想象和幻想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而且给人们找到了一条通往诗的效果的精神分析之路,但是他的理论缺陷也不言而喻,比如过多地关注幻想的研究而未能深入探究作家表达幻想的技巧或手段,甚至出于自己的职业特点一味地将表现幻想的人视为“神经症的受害者”而存在着以偏概全的错误。诚如他所言,“因我们的知识现状所导致”,他“所能做不过是给出一些鼓励和建议”。[注][奥]弗洛伊德:《论艺术与文学》,常宏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01页。博尔赫斯充分利用自己的想象和诗艺,以其高超的艺术技巧融梦入文,在这个坚不可摧、玄秘深奥和清晰可见的世界空出的狭窄而永恒的虚无缥缈的缝隙中游心驰骋,写作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在博尔赫斯诗学中,梦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践意义。梦模糊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构筑了博尔赫斯诗学的精神空间,凸显了博尔赫斯诗学奇幻空灵的张力美。博尔赫斯诗学中的梦元素既有对弗洛伊德、荣格等精神分析学家思想的继承和吸收,又有创新和拓展。他关于梦的诗学观和用“循环梦”、“蝴蝶梦”、“原型梦”等编织的诗性文本不仅启发了当代理论家的思索,而且为卡尔维诺、孙甘露、格非等当代作家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